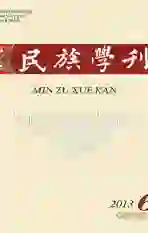人类学的灾害研究如何呈现
2013-04-29张原兰婕
张原 兰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藏彝走廊自然灾害及其应对经验的人类学研究”(项目编号:13XSH030),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xwd-s0304)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张原,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灾难人类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兰婕(1987-),贵阳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民族学专业硕士生。四川 成都610041
[摘要]以民族志的方式,对地方层面的灾害场景和灾害感知进行完整呈现和系统转述,是人类学灾害研究的关键。《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一书基于特定灾害场景的系统考察,来呈现人类社会与环境系统的复杂互动过程,并就不同人类群体如何借助社会文化资源来认识和应对灾害的经验图景加以辨析,这代表了灾害人类学研究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关键词]人类学;灾害研究;民族志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6-0056-07
近年来,频发的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愈加剧烈,这促使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开始关注灾害研究。[1]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常将研究焦点置于宏观层面的国家应灾行动的分析不同,人类学的灾害研究更强调以地方社会与世界体系的互动关系为背景,关注地方层面的灾害解释和应对实践,从而对灾害的社会文化属性加以辨析。自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之后,国内人类学的灾害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大批学者将目光聚焦于灾后的羌族地区,围绕着灾后重建中的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等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出现不少具有影响力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集,成果颇丰。①相较而言,针对具体的灾害类型所进行的全景性的系统考察在国内学界则未成气候,虽然针对具体灾害场景及其应对的经验个案研究也有所展开,但成果略显单薄,且多以论文形式呈现。②这暴露出中国的灾害人类学研究尚不成熟,特别是基于灾害发生机理与应对机制的田野民族志研究显得尤为欠缺。实际上,回到人类学立身之本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对发生在地方层面的灾害场景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以此呈现人类社会与环境系统的复杂互动过程,并对不同的人类群体如何借助社会文化资源来认识和应对灾害的经验图景加以辨析。这不仅是灾害人类学的关怀所在,也是国内学界急需加强的研究工作。[2]李永祥教授的《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以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8·14特大滑坡泥石流”为例》[3]一书的问世,正好弥补了国内灾害人类学研究的这一缺陷。该书是以扎实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灾害民族志,全面展示了云南哀牢山区新平县的泥石流灾害场景,并对灾害的规避应对和灾后社会文化变迁等问题进行了极有洞见的讨论。
一、灾害研究是何种人类学的问题
还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李永祥这位生长于云南哀牢山的彝族学者就对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灾害产生了兴趣。如其书中“后记”所述,他对自然灾害的研究兴趣可追溯到2002年,当时他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然而就在其田野调查阶段,他的田野点云南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发生了“8·14特大滑坡泥石流灾害”,这促使他开始思考自然灾害对于乡村可持续发展影响的问题。[3](P.316) 2005年获得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回到云南社会科学院的李永祥将他主要的研究精力放在了灾害人类学的研究中。作为国内最早开始研究灾害的人类学家之一,他对灾害人类学理论的细致梳理,以及对泥石流这一特定灾害类型的系统考察,③均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学术影响。此时,国内人类学的灾害研究,无论在理论视角上,还是在田野研究方面尚有太多的空白盲区。因此,李永祥当年所开始的灾害研究对他自己来说是个全新的学术挑战和研究尝试,对国内学界而言则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之拓展和田野经验之累积。
作为国内灾害人类学研究的先行者,李永祥必须要回答灾害研究到底涉及何种人类学的问题?或者说要回答,灾害研究对于人类学而言其学理意义和现实价值何在?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人类学如何看待自然灾害,更关系到人类学灾害研究的学术定位。而《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一书正是基于经验的田野研究和理论的学术思考,以田野民族志的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极为实际的回答。从学理而言,灾害之所以值得人类学加以关注和研究,是因为其本身的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所决定的。正如美国学者布莱基(Piers M. Blaikie)所强调的,灾害是由不可预知的物理因素的危险(hazards),可估算的自然与人为的风险(risk),以及植根于社会结构与历史过程中的人类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这三部分所组成。[4]因此,灾害的发生实为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文化体系复杂交汇的表现,它提供一个最具有戏剧性和展示性的场景,将生态环境、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历史过程之间的交互关系呈现出来。也如奥利弗-史密斯(Oliver-Smith)和霍夫曼(Susanna M. Hoffman)所指出的:灾难昭示了人们建构或“构架”(包括对其的否定)灾害的方式,即人们如何认知其环境和生业,以及他们怎样创造灾难成因的解释、构建道德观念和怎样将持续性和希望投射到未来。所以就人类学而言,很少有这样的场景能够就其形形色色的关怀及其理论综合提供如此多的机会。[1]今天,灾害研究对于人类学的视角拓展和理论发展的重要性,正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李永祥在《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一书中所完成的田野民族志研究,无疑正体现了将这些讨论和认识落实于实际可行的经验研究的一种努力,其对灾害的定义与灾害人类学的研究定位则是极具理论抱负和深刻现实关怀的。如书中强调:“自然灾害的发生和治理过程不是纯自然的过程,还是一个于社会、文化、人类行为、政治经济等密切联系的过程。灾害导致了严重的环境脆弱性和人类群体脆弱性,灾害后果、救灾过程和预防方法能够改变村民的生活方式、居住条件和文化类型;能够改变原来的族群关系和竞争模式;能够使人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反思乡村发展模式;能够使村民之间相互帮助,社会管理更加有效。救灾不仅仅是提供物质资料,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个系统的工作,其核心是社会平衡系统和文化功能的恢复。”[3](P.36)这个总结表明了李永祥的灾害人类学研究,是整体性地关照生态环境、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历史过程之间的交互关系;系统性地考察具体灾害的成因与预防、灾难的救援与应对、灾后的重建与恢复的关联过程;同时在研究视野上也将是对人类学的生态、政治-经济、文化视野的理论综合与实践。可以说,《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的田野民族志研究所要贯彻的正是整体观、过程论和综合性分析这三大人类学灾害研究的基本特征和学术要求。
如果说,灾害研究对于人类学理论发展和视野拓展的重要性在于,其缩小了人类学界的生态、政治、经济和文化视野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距离。那么反过来,坚持整体观、过程论和综合性分析的人类学则能够对灾害成因及其后果影响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系统的理论解释框架,人类学的灾害研究甚至能对当前人类生存境遇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分析。[1]今天,人类学的研究越来越强调,作为自然环境的一个基本元素,自然灾害所展现的风险场景实为人类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结构性特征和重要组成部分,而灾难则是历史地与结构地深植于人类的生活世界之中的。[5]因此,将灾难的考察融入对人们生活世界的整体把握之中,而不是将灾难从社会生活的经验图景之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抽象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这正成为人类学灾难研究的一个基本路径。[2]而李永祥的《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则无论在视野方法和理论关怀上,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成熟的人类学灾害研究的主旨趋势。如书中第一章不断强调,人类学灾害研究理论形成的标志,正在于将灾害与社会、文化、政治、权力、经济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使灾害成为社会和文化的组成部分。[3](P.16)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学的灾难研究是要全面地考察人们的生活经验图景,借助对灾难现象的分析,就人类的生存环境、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与历史实践进行深刻反思,从而审视人类社会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种种社会文化困境,并就地方世界如何应对现代化冲击,以及怎么维持其生活可持续性等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6]本书对于“面向生活世界的灾难研究”之学术旨趣的落实,正体现在这是一本真正的以人类学经典的田野工作方法为基础,从地方的实际生活状况入手来呈现具体类型的灾害场景之生成过程和应对实践的灾害民族志作品。
从李永祥产生灾害研究的兴趣,到他对人类学灾害研究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再到《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一书所落实的学理追求和现实关怀,可以明确人类学的灾害研究既符合地方社区的实际需要,也是人类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结果。这也正是一名中国学者用自己的研究实践对“灾害研究是何种人类学的问题”所做出的回答。
二、灾害民族志的研究何为
人类学的核心是田野工作,而田野工作的结果就是民族志。[7]人类学要实现一种“面向生活世界的灾难研究”,以田野民族志的方式来展开研究工作是不二法门。当前国内人类学的灾害研究,缺乏的正是长期的田野工作和扎实的民族志作品。恰如李永祥坦言,灾害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落后于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而能够在灾区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则是人类学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灾害研究的一个最为明显的优势。[3](P.290)因此,开展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多出扎实的民族志研究成果,这应该是当前中国人类学灾害研究取得学术进步的一个必然路径。
田野工作为什么是人类学灾害研究的一个核心?这是因为灾害本身构成了一个典型性的场景,使得人类学者被深深的嵌入进受灾群体的社会境遇之中,这种深度的参与性和特殊的在场感使得人类学的知识生产被赋予了一种主客杂糅的社会实践和文化理解之特性。也恰如李永祥所指出的,没有一种事件能像灾害一样将人类学家与当地社区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在灾害研究的田野调查中,人类学家不仅需要观察人们是怎样处理和回应灾害的,还可能成为救灾和政策应对中的一员,灾害研究的领域不仅需要责任心和同情心,还需要更长的田野调查周期和深刻的文化理解能力,这是人类学的灾害研究与其他学科在方法上的重要区别。[3](P.16-17)深入而长期的田野调查能让人类学者在地方鲜活的生活世界中把握到具体的灾害场景是如何历史与结构地生成的,从而能够对深嵌于生活世界中的脆弱性加以辨析。这样的田野观察也使得学者能够透过具体的灾害场景,来理解在人们种种应对灾害的行为背后所依托的文化逻辑与社会结构。并且通过深度地参与到地方层面的应灾实践与灾害管理等社会实践中,也可使人类学者更为系统全面地感知在特定的灾害场景中,地方社会的变迁境遇是如何与整个时代的社会文化转型相互交织的。由此可见,田野工作赋予了人类学灾害研究特殊的洞见力,使其能揭示许多被遮蔽的问题。作为国内人类学界的第一本灾害民族志,该书关注的是泥石流这一特定灾害类型。虽然泥石流灾害在中国西部有着频发的态势,且其发生带来的巨大冲击与损毁力并不亚于地震等自然灾害,但国内外的灾害研究对其却极少关注。实际上,泥石流灾害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其与中国西部山区的自然生态条件和居民的社会生活紧密相关,是一种不能被忽视的灾害类型。然而,由于以往的研究中常将这类灾害作为纯粹的自然过程加以考察,使得应灾实践中诸如社会文化的变迁、本土经验总结、社区成员的主动应对等具体问题被遮蔽和忽略。[3](P.33-34)因此,需要以扎实的田野工作来填补泥石流研究的空白,从而揭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是如何共同制造了特定地方的脆弱性,以及这种脆弱性在灾害中循环引发的特性,并对灾害的应对经验加以总结。
基于田野调查的灾害研究,是要通过灾害民族志的写作来展现灾害场景,并以深度的社会参与性和深刻的文化理解力对灾区的社会文化所受到的影响进行综合研究,最终完成相关的理论对话,并提出一些建议与对策。所以灾害民族志大致会涉及三个部分的内容:具体经验个案的呈现;灾害场景的综合讨论与问题分析;相关的理论思考和应用探索。《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一书也是从这三部分入手,展开其民族志的写作的。
该书的第二章作为田野背景介绍,系统地呈现了哀牢山的环境变迁与新平县“8·14特大滑坡泥石流”的灾害成因。哀牢山区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使得泥石流灾害的自然环境脆弱性较为突出,而这一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开发坡地改种经济作物、水电站修建、石料开采、林权制度改革等社会变迁,则导致了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成为泥石流灾害的诱发主因。“8·14特大滑坡泥石流灾害”的发生,深刻地暴露出这一地区的灾害脆弱性被循环引发的特性和问题。[3](P.62-65)本书的第三章至第六章,则通过新平县的5个村子的4个案例对“8·14特大滑坡泥石流”灾害及其影响展开了全面考察。这5个村子既有汉族村寨,也有傣族村庄和彝族村落,他们在面对共同的泥石流灾害时,因其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导致了应灾过程中表现出种种值得关注的差异和特点。傣族村庄曼糯村是受灾最严重的村庄之一,然而村民们在重建过程中则积极利用传统地方的社会文化资源,如借助原有的亲属关系和村庄间联系等社会机制获得不同层面的灾后救助资源,以及在新定居点举行传统的宗教仪式活动重新确定村寨管理者等等社会文化重建实践,使当地的社会系统和文化功能在灾后逐渐得到恢复。[3](P.120)大水井和大石板村民的避灾行为,则凸显了泥石流灾害的地方解释和传统知识对于躲避灾害与灾害应急的重要性。因为在泥石流发生的过程中,人们所有的应急反应都是建立在传统知识的基础上,所以对这些地方知识经验的总结,能为今后的灾害避险提供有益的经验;[3](P.150)彝族村落核桃坪村在灾后搬迁过程中由于缺乏大面积土地作为安置点,因而被迫拆分为五个部分迁至不同的村寨进行安置。这一变迁导致村庄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被打破,村民们在适应灾后新环境时陷入了文化冲突和人际关系隔阂等困局中,这对他们灾后生活的恢复带来诸多挑战和难题。[3](P.180-181)汉族村寨平掌田村则由于交通、种植环境等各方面基础条件较好,被选择成为灾后重建的搬迁“示范村”,在上海市政府对口援助下建设成为“上海新村”。作为一个典型的示范工程,它表明了国家权力对于乡村建设的干预是有力的。但当平掌田村的示范功能得到突出体现之时,其重建过程和居民生活也就被当成了一种具有政治与经济象征意义的展示,而搬迁重建背后存在的诸多问题则在“示范”功能中被遮蔽,因而这个村落在灾后重建方面获得的成功也未必具有典型性。[3](P.200-201)通过对5个村庄的田野民族志呈现,该书勾勒出了新平县滑坡泥石流灾害场景的一个整体面貌。作为新平县泥石流灾区的缩影,这些村庄在灾害应对中所暴露的问题与获得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该书的七、八两章则基于民族志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就灾害长期避险机制的建立、灾害的文化解释与地方性知识的应用,以及灾后的社会变迁这些灾害研究的核心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书中首先强调,泥石流灾害的长期避险与环境安全的建设息息相关。短期的灾害避险虽可通过建立完善的预警监测制度、村落搬迁与临时避让等方法手段得以实现,但更为长期治本的灾害避险则需要开展体系化的环境安全建设。如通过工程治理、退耕还林、梯田改造和沼气系统建设等手段,将这一地区的环境安全维持在稳定的范围内,而这也是乡村实现可持续发展之前提。[3](P.230-231)接着书中指出,在本土应灾实践中所包含的灾害文化解释和地方性知识应该得到重视。地方关于灾害的传统知识和本土经验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封建迷信”,通过细致的梳理总结,这些地方性的知识经验对灾害的预警和规避是能发挥积极作用的。最后在分析灾后重建中的种种问题时,李永祥指出,灾后重建作为历时最长、影响最大、所耗成本最大的灾害应对阶段,其导致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也最為突出,因此应从灾民的生活状况出发,来总结灾后恢复重建的各种经验与教训。[3](P.263-264)
该书的第九章“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理论思考和应用探索”,围绕着泥石流灾害人类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解释框架和应用实践这三个问题的总结来展开。其实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也就是在总结 “灾害民族志的研究何为”这一问题。本章首先强调了,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灾害研究的一种工作方法,其意义就在于田野工作使得人类学家能对灾区进行长时期的关注,从村民基本的生活状况出发全面系统的理解灾害对于当地社会的影响,并在倾听他们的声音以及和他们的交流中,获得一种更为深入的内部视角和理解洞察力。[3](P.269)正是田野调查中这种深度的参与性和特殊的在场感,使得人类学者和当地居民深度的交融(communitas)在一起,从而得以洞见地方的灾害场景及其引发的问题。犹如特纳(Victor Turner)所指出的,灾害与危机常带来一种“即时的交融”状态。[8]所以灾害的发生设置一种类似于阈限期(liminal phase)的社会场景,特别当人类学家进入灾区开展田野工作之时,就和当地居民交融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本质上的我们”。因此当人类学家在书写灾害民族志时,不仅会使用“他们”一词,来描述受灾群体的状况,还同时使用了“我们”一词表明人类学家作为受灾群体的一份子,来呈现人们对于灾害场景的感知。[9]那么这样一来,灾害民族志的作者是不是就能充当灾区居民的“发言人”呢?这是一个让李永祥颇为纠结的问题,他在书中给出了一个“是又不是”的痛苦回答。[3](P.268)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构成人类学者的一种纠结困惑,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曾说,人类学的研究无非是“就什么说些什么”(say something of something)。[10]如果我们坚持“理解他人对世界的理解,阐释他人对世界的阐释”这样一种人类学的研究旨趣的话,那么灾害民族志所要做的,无非是要转述一种地方层面的灾害场景与感知。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情景的转述和文化感知的翻译中,人类学能够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实现一种知识的整合。恰如书中最后的总结所提到的,“人类学家对田野点特殊的感情,能使研究者与受灾者之间的距离更近,人类学家不仅能扮演一个研究者的角色,还能扮演一个救灾者的角色,同时还能够将村民的意见和意愿反映给当地政府,对于灾区的建设方法提出自己的建议。” [3](P.268)
实际上,对于灾害这样一种特殊场景的研究而言,一方面,村民虽是人类学者最为重要的信息提供者,但他们并不能完全理解正在影响他们的灾害过程,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权力关系。[11]这就需要人类学家对地方层面的灾害感知有所超越,在一个更宽广的时空纵深和社会文化格局中对灾害加以考察;另一方面,灾难应对的决策者与执行者也不可能像长期从事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那样,能够以内部的视角来辨析地方应对灾难时出现的种种具体而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开展灾后重建工作时,由于决策者与实施者往往关注的是重建工程的任务进度以及经济恢复的进展效果,而对于灾区居民因灾后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所面临的复杂而艰难的社会适应与文化恢复过程多有忽略无法顾及,甚至是有意的遮蔽。这就促使人类学家有责任对地方层面的灾害场景和灾害感知进行完整的呈现和系统的转述。在这个意义上,灾害民族志的田野方法、解释框架与运用实践本身就是互为前提、相互关联的。也只有将三者融为一个整体的问题进行总结,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这样一本灾害民族志的学术理论意义和现实应用价值何在。
三、灾害人类学本土经验的形成
“汶川5.12大地震”发生之后,灾害人类学的研究在中国获得了一次发展的契机,但也有一哄而上的跃进之嫌。目前,国内人类学界呈现的诸多与灾害研究相关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灾后重建方面,缺乏对灾害场景的整体考察。灾害人类学在中国要成为一个体系化的学术研究领域,则无论在学理探讨上还是在具体实践方面都尚存不少盲点缺环和薄弱之处,需要努力去弥补。尽管国外的灾害人类学研究已有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厚实的经验积累,然而在引进并应用于国内研究时,仍面临着在地化的问题,并暴露出不少应用局限。实际上,中国目前所面对的灾害场景带有明显的复合特征和时代特点,其突显的脆弱性正是现代化变迁中的一种结构性与过程性的产物,特别是在中国西部的民族地区,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与当地社会变迁的剧烈性更加深了灾害场景的复杂化。所以针对这一区域特殊而复杂的灾害场景所形成的本土研究经验,可转化为新的理论阐释模式,丰富和拓展灾害人类学整体的研究关怀和考察视野。作为中国人类学界的第一本灾害民族志,《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的出版对于灾害人类学中国本土经验的形成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实际上,灾害的发生作为一个结构的和历史的过程,其并非为孤立的和突发的事件。且在时空关系上,灾害的应对实践则包括灾前的防灾减灾与灾后的赈灾重建这两个方面,以及社会整体应对和基层社区防范两个层次。中国的现实情况更进一步表明,当前许多灾害脆弱性的诱发不仅与特定的自然环境相关,更与现代化进程所导致的社会文化变迁紧密相连。而且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国家实施的各种工程项目所体现的权力意志与受灾地区的地方诉求和能动实践的纠结,则让中国的灾害场景集合了层次更为复杂的矛盾冲突。故而,中国的灾害研究更需要贯彻人类学整体观、过程论和综合性分析的原则。《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的研究正确认了这样一个方向,也向我们表明,要形成灾害人类学研究的中国本土经验,就必须拓展灾害研究的时空纵深来对灾害发生的社会脆弱性加以深度的辨析,并将灾害应对的实践过程放置在地方社会与世界体系的互动关系之大格局中来考察,同时注重用田野民族志的灾害研究方法,从具体的生活场景考察入手,阐释地方应灾实践的文化逻辑,理解地方对灾害之认识感知,以此来发挥人类学的研究优势,将其超社会的整体视角和跨文化的理解力,转化为一种能对具体的应灾实践工作提供实际的理论指导和经验参考的能力。今天,随着探讨的深入,学界越来越认识到,人类学的灾害研究不应抽象地去讨论灾害是什么,而应考察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有什么样的灾害感知。灾害民族志则不仅要揭示地方具体的灾害场景,更要从中对人们的生活世界在可持续性方面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挑战和机遇前景加以经验说明。[6]《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正为我们积累了这样一种研究经验,即人类学家需要形成一种感知灾害的地方性的视角,并通过展现不同地方群体的本土实践,来丰富和拓展人类应对的灾难,以及维持生活世界可持续性的经验图景。
灾害人类学本土经验的形成非一日之功,需要学者长期的坚持和巨大的投入。《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可视为中国学界开展这一工作的基石之作,该书虽在田野资料组织的技巧上,以及理论对话的创新性与政策建议的针对性等方面尚有一些需要改进之处。然而其在近十年间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和多次的回访考察的这样一种长期坚持,并以这样一本厚重的民族志作品来全景式地展现哀牢山区泥石流灾害场景,最终在扎实的田野材料上对灾害应对等问题进行了极具启发性的经验总结,已经将中国的灾害人类学本土经验的累积提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在“汶川5.12大地震”发生五年后,当灾害研究已成为一种学术潮流之时,对国内越来越多关注灾害研究的人类学者而言,《泥石流災害的人类学研究》一书将会激起更多的反思与回响。灾害人类学中国本土经验的形成,势必将为灾害研究与应灾实践,以及生活世界的可持续性开拓出一番新境界。对此,可以书中的最后一句话来做此文的总结,“我们期待着这一时期的到来”
注释:
①如张曦等编《持颠扶危:羌族文化灾后重建省思》,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黄承伟、赵旭东等著《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重建与本土文化保护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杨正文,蒋彬等著《阿尔村:援建主导下的灾后重建模式》,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
②如扎洛《雪灾防范的制度与技术——青藏高原东部牧区的人类学观察》,《民族研究》2008年第5期;梁景之《生物灾害的防治与社会变迁——青海省东部牧区的个案分析》,《民族研究》2008年第5期。曾少聪《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西南干旱——以云南旱灾为例》,《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等。
③如李永祥《灾害的人类学研究》,载《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李永祥《什么是灾害?——灾害的人类学研究核心概念辨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1期。李永祥《关于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载《民族研究》2008年第5期;李永祥《傣族社区和文化对泥石流灾害的回应》,载《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美]安东尼·奥立弗-斯密斯,苏珊娜. M. 霍夫曼.人类学家为何要研究灾难[J].彭文斌,译.民族学刊,2011(4).
[2]张原,汤芸.面向生活世界的灾难研究——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及其学术定位[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7).
[3]李永祥.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以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8·14特大滑坡泥石流”为例[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4]Piers Blaikie,et al., At Risk: Natural Hazards, Peoples Vulnerability and Disasters. London: Routledge,1994. p47.
[5] Anthony Oliver-Smith,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Hazards and Disaster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25, 1996.
[6]张原,汤芸.藏彝走廊的自然灾害与灾难应对本土实践的人类学考察[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3).
[7][美]保罗·皮科特著.人类学透镜[M].汪丽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5.
[8][英]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M].黄剑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49.
[9]Susanna M. Hoffman, “The Worst of Time, The Best of time: Toward a Model of Cultural Response to Disaster” ,in Anthony Oliver-Smith and Susanna M. Hoffman eds., The Angry Earth: Disaster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1999.
[10][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11.
[11]Alberto C.C. Costa, Conrad P. Kottak, Rosane M Prado, and John Stiles, “Ecological Awareness and Risk Perception in Brazil”,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actice of Anthropology Bulletin, vol.15:Issue 1.January 1995.
收稿日期:2013-07-12责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