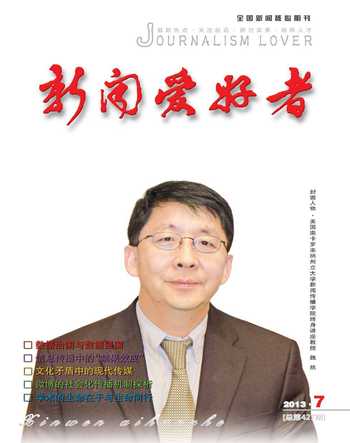邵飘萍媒介批评实践与思想论略
2013-04-29胡正强
胡正强
【摘要】邵飘萍对媒介批评及其社会功用有着明确的认识,他对源于封建专制心态、阻碍新闻传播正常发展的种种不当干涉行为,从现代新闻法制角度给予了猛烈抨击;对当时的新闻失实、新闻界腐败等种种不良现象,从专业的角度进行了严厉批评。邵飘萍的媒介批评活动在引介和普及现代新闻理论、促成中国新闻学术现代化方面,有推助之功。
【关键词】邵飘萍;媒介批评;新闻腐败
邵飘萍(1886-1926)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光芒璀璨、辉耀千载的一颗大星,在新闻采访、报业经营、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等方面,都做出过很多开拓性的贡献,被后人誉为报界巨子、新闻导师。邵飘萍还是一个杰出的媒介批评家,对媒介批评及其社会功用有着明确认识和殷切希冀:“庶几国民有选择新闻纸之知识,贻‘徒知为一人一派小己的利益而不顾社会全体者以极大之制裁,则彼故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惟以不正当手段欺蒙侥幸之辈,自无所施其技,终不能不屈服于‘舆论的舆论,从正当方面经营,以社会为本位之新闻事业焉。”[1]105做一个“新闻界战斗之壮士”的职业荣誉感,使他不时对新闻传播中的种种缺陷和不足加以批评,希望引起社会及同人的注意,群策群力,思谋改进。
一
邵飘萍先后经历了民国初年共和制带来的瞬间议论较为自由的开明时期、袁世凯专制擅权摧残舆论的时期、北洋军阀轮流执政禁锢言论的时期。从1912年到1926年,虽然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但与之相匹配的现代新闻自由观念并没有真正地内化为执政者的自觉追求和实际行动,不但法律条文苛刻,钳制意图明显,而且条文以外的人为迫害更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这直接导致当时的中国新闻事业步履维艰、前行迟缓。对源于封建专制心态、阻碍新闻传播正常发展的种种不当干涉行为,邵飘萍从现代新闻法制角度给予了猛烈抨击。
1922年10月,参议院议长改选。为争做议长,参议院内部互相倾轧,钩心斗角,丑声四播,满城风雨,一时间社会上传单飞扬,报纸也刊载了运动金钱以竞选议长一事。不料有几个议员不思自省,颜丑而归罪于镜,恼羞成怒,竟把矛头转向报界,主张控诉刊登此类消息的各家报纸。邵飘萍闻知此讯,迅即发表了《敬告因运动议长而埋怨报馆者》一文,紧紧抓住媒体报道来源这一线索,如剥茧一般,将议员们荒腔走板的论调批驳得体无完肤。他先坐实各报的材料大部分来源于参议院的结论,随之代读者提出“参院议员何以自献其丑于各报”的疑问,接着给出答案:“无非竞争议长者甲攻乙,乙攻甲,丙攻甲乙,互为反响之结果耳。”因为新闻记者不被邀请参加参议院会议,不可能了解会议内幕,他的结论就显得如铁板钉钉,无可置疑。“然则一般报纸收罗甲乙丙之所言者,以警告一般投票之议员,乃报纸应有之天职,欲控诉报馆,请甲乙丙先自行控诉可耳;欲保持参议院之神圣,先自令同为参院分子之甲乙丙不互攻,并根本上绝对部位可以被攻之事可耳。”[2]然后通过“材料所以达于报馆之径路”说明,消息首先是通过参议院内部的个人与派别散播出来的,无非是互相攻讦,制造舆论,达到打击对手,争夺议长的位置,争取个人与派别权利和利益的目的。邵飘萍至此笔锋一转,从法律角度批判了政执者们执法不知法的丑陋。他指出报纸与传单性质有不同,传单伪造事实,并在公共场合散布,侮辱了他人的名誉,须负法律责任,被害人可立即向法庭提出诉讼。报纸出现类似问题,由消息提供者文责自负,首先应在报纸上更正并道歉,拒不更正的,方诉之法庭。在这次事件中,并无一人要求报纸更正,这等于是对非法侵害他人名誉的默认。自己既已默认,却又吵嚷着要控诉报纸,岂非无赖且可笑?如此分析环环相扣,使被批驳者无法自圆其说,彻底暴露了他们企图委过于人的丑恶嘴脸。
1924年6月16日,《京报》转载了中美通讯社刊载的国务院寒电,题为《政府对德票用途之通电》。而中美通讯社又转录《世界晚报》的消息,同一天,《京报》还转发了国闻通讯社的消息“办理德债票案之文件——阁议通过之原议”。德票用途当时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国务总理孙宝琦与总统曹锟之间矛盾分歧很大。单方面发布孙宝琦对于德票用途说法的消息,不仅使曹锟大为恼火,也使孙宝琦十分难堪。新闻界16日披露的消息,国务院4天之后才在秘书厅致警厅的公函中,一面公开否认通电一事,一面函请京师警察厅对转录消息的《京报》《晨报》严加追究:“连日北京晨报、京报等报叠载院发寒电一节,殊堪诧异。查本厅寒日并未发出如各报所记通电。该项电文显系奸人捏造,意图挑拨。即希贵厅向各该报馆查明该电原系由何处发布,严切根究,依法办理。”显然,国务院秘书厅致警厅的公函有着弦外之音。在刊发寒电一事上,《京报》不过是转载,并注明了是转发中美通讯社的消息。且为慎重起见,18日的《京报》又转发一篇《国务院中之两大离奇案件,寒日通电果有耶无耶〓阁议节略何处得到耶》的消息,对寒电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转发的消息披露并且分析了府院内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尖锐矛盾。无论消息披露的事实真确与否,《京报》都是转载者,且转载了不同观点的消息,新闻处理态度十分慎重。最先发布这一消息的是《世界晚报》,社长成舍我与孙宝琦有着特殊的关系和交情,正是因为这层特殊关系才演发了这条消息,其他各报才相信并予转发。国务院佯装糊涂,对《世界晚报》不闻不问,也不追查中美通讯社,偏拿向不顺眼的《京报》《晨报》开刀,是想杀一儆百,既杀一杀《京报》的锐气,又给舆论界一个警告,同时还可掩盖政府内部矛盾,可谓一箭三雕。
邵飘萍对这种有偏有向的处理,非常反感和愤怒。从6月20日至24日,他先后公开发表《昏聩糊涂之国务院秘书长》《本社社长对孙宝琦严重质问》《本报并无过甚之要求——请同业公开批评》《从新闻学上批评院秘厅对新闻界之态度》4篇文章,从新闻法的角度理直气壮地质问秘书长不依世界新闻惯例先直接向报社要求更正,也未依法律手续向司法机关告诉,而遽令警厅严切根究依法办理者,所依果系何法?质问孙宝琦同罪异罚,对拥护者优容,对严正者威胁,是何居心?邵飘萍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类事件证明行政机关不承认言论机关、新闻记者具有独立平等的社会地位,任意压迫侮辱,是其脑筋落后腐败,缺少新闻常识和法制意识的表现,因为“夫苟新闻机关与新闻记者其地位皆不为政府所承认,是可谓新闻事业前途致命之伤,不宜视为一小问题而忽之”[3],是急需根除的可怪、可悲现象。他依世界各国通例,提出两项要求:(一)以后更正新闻,不得令警厅施行非法命令,而应直接致函报社;(二)非经司法上正当手续,不得动辄加报馆以严办根究等恫吓威胁。他希望以此来给新闻界争取到独立、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更加开放的新闻自由。
二
真实无误是新闻传播赢得人们信任、建立媒介权威的基础。邵飘萍将新闻真实性提高到媒体生命的角度予以强调,从各种角度对当时新闻失实现象进行批评。他认为当时我国新闻界对新闻真实性不够重视是新闻媒体不成熟、不健康的表现,“我国各种报纸之内容,最可认为幼稚腐败之点,一在新闻材料之缺乏,一在所载新闻之不确。非但报纸本身无重大价值可言,其影响于国家社会者,尤匪浅鲜”[4]15。他指出,新闻媒体既为活的教育之最良机关,新闻工作者就应该竭力矫正、设法弥补上述两种缺憾,以无负于社会教育者的责任。这需要新闻从业人员和一般社会中人共同努力,因为“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对于新闻纸上之记载,往往喜加以否定之态度,或挟怀疑之见解者”[1]108。邵飘萍公允持正地说,新闻失实固然有社会客观的原因,但这仍然是由于“新闻纸中所记之事,未必皆一一无误”而引起的社会观感不良所致,归根结底还是要通过提高新闻报道质量、确保新闻真实性来纠正。
造谣是一种主观故意的新闻失实,其背后往往隐藏着难以明言的卑劣动机,危害新闻界甚烈。“报馆纪事,不自采访,投稿者向壁虚造,报馆惟取以充篇幅,其真伪不问也,以故政界轻视报纸,尤鄙夷访员,几于报纸为‘谣言之代称,访员成‘无赖之别号。”[5]邵飘萍当时在新闻界名气很大,政治态度又一直激烈,因此,屡屡成为同业攻讦的对象。1921年3月,新闻界风风雨雨地谣传邵接受了三笔大的赠款:一是向某次长要求选举费若干;二是向某总长索要2万元,并说总长已向警厅报告;三是向某国代表索取巨款,也已被报告外交部并受到申斥。1925年孙中山北上期间,社会上曾有“邵与苏俄宣传部门暗有联系”“邵接受广东国民政府津贴”等传言,甚至借《京报》办多种副刊做文章,含沙射影地说“新闻界邵某向孙中山先生亲信索万元以包办报界”。新闻界互相揭露索贿丑闻,有时是各打五十大板以保护自己,有时却有着某种比较复杂的政治背景。如上述两例,第一次是在邵飘萍对苏俄代表表示热烈欢迎,积极倡导中苏通商之时,便谣传他接受了“某国代表”的贿赂。第二次恰逢中山先生北上,邵飘萍大力鼓吹南北政府和谈,之后,又赞扬广东政府,于是便有了他接受广东政府的钱,以此来贬低《京报》宣传的动机。邵飘萍对此“仅有24小时寿命的谣言”,一般不直接加以驳斥,进行正面反击,而是择机采取公布谣言的办法,一旦真相大白,谣言也就不攻自破。《附刊上言论之完全自由——欲造谣的请尽量造谣吧》《愚今始一言之》《原来如此令人捧腹》就是他这方面的媒介批评之作。这种方法既能达到媒介批评的目的,又可避免给外界一种“狗咬狗两嘴毛”的不良观感。
新闻失实在很大程度上与新闻观念有着直接关系,邵飘萍批评国人一向持有轻视记者的落后观念,“我国旧习,一般人对于报馆之访员,向不重视其地位。即以报馆自身论,亦每视社外之外交记者为系主笔或编辑之从属。例如今日号称规模弘大之报馆,其主笔先生之脑筋皆不免陈腐幼稚,不认社外记者为与彼处于同等重要之地位,此我国报纸内容腐败之重大原因”[4]15。因为记者社会地位不高,充任记者的人,大半皆缺乏新闻学的专业知识,也无专业训练和修养,很多人对新闻记者岗位并没有正确的观念,而是将之作为一种不得已的过渡职业,这种观念致使新闻记者队伍鱼龙混杂。邵飘萍尖锐地批评道:“更多不健全之分子,不能自重其人格,对于新闻材料不求实际之真相以忠实态度取舍之;或受目前小利之诱惑,或以个人意气泯没其良知,视他人名誉为无足轻重,逞其造谣之技。一旦被人指责,则以‘有闻必录一语自逃其责任。”[4]16他指斥这是负责精神匮乏的表现。
在社会上流行已久、常常被一些记者作为逃避新闻失实责任挡箭牌的“有闻必录”这个口头禅,邵飘萍与徐宝璜、林仲易等人予以强力批判。邵飘萍说:“愚意我国报纸中时见有所谓‘有闻必录之无责任心的表示,乃最易流于不道德之‘专制的恶习。以革新进步自任之外交记者,万万不可沿袭之,以招社会之厌恶与轻视。曩在北京大学及平民大学讲演新闻之学,曾对于‘有闻必录一语再三攻击,愿有志于新闻事业者,振起其责任心,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以‘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4]16他所说的“攻击”,其实就是媒介批评之意,“再三攻击”说明他对这个口号是多么深恶痛绝,他号召新闻从业人员,彻底抛弃“有闻必录”的口号,维护新闻真实性,以提升社会对媒体的信赖。
新闻失实也与当时媒体接受政府津贴有一定关联。由于经济原因,邵飘萍在接受政府津贴一事上虽未能免俗,但他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始终坚持钱照拿、话照说的一定之规,坚决反对那些纯靠津贴为生,或挂牌领干薪,不做实事,或因接受了贿赂就朝秦暮楚甚至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报纸。1922年8月4日,《京报》披露报界代表汪立元等人为“报纸津贴事谒见元首”事,报道了北京新闻界有28家报纸、9家通讯社靠津贴生存的事实。他鄙夷广告新闻以金钱为唯一目标的恶行:“津贴本位之新闻纸。我国在今日尚占多数,新闻之性质殆与广告相混同,既不依真理事实,亦并无宗旨主张,朝秦暮楚,惟以津贴为向背。此则传单印刷物耳。并不能认为新闻纸,与世界新闻事业不啻背道而驰。”[1]1361922年8月12日,他在《京报》的《读者论坛》上,借读者来信方式,批评北京一些报纸在接受了交通部的贿赂后,对其出卖京绥铁路权给帝国主义国家之事装聋作哑,失掉了媒体“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的监督功能。
三
邵飘萍除痛心疾首于当时的中国新闻界道德日坏,假造新闻、津贴新闻横行之外,还对一些导致新闻价值减少的“瑕疵”多有批评。他认为如下一些瑕疵的存在,会给新闻传播带来如“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而过之”的恶劣影响。
第一,含有广告意味者。所谓广告意味的新闻,也就是今天新闻媒体上人们所常见的软文一类材料。西方社会由于公共关系学极为发达,企业一般都设有公共关系部门,专门与媒体打交道,向媒体投递相关信息和宣传材料。在新闻媒体所接到的自由投稿中,含有广告意味的较多,邵飘萍指出这类材料的实质,就是“盖欲以新闻之面具而利用报纸为之宣传其目的”[4]68。他还介绍欧美国家凡老练记者,一见而知其用意,决不受其欺蒙。路透社即曾特下严厉训令给通信员,须注意勿采用这类具有广告性质的消息。他指出,所谓广告性质者,不仅仅存在于商品信息中,举凡医生律师之名誉、文学家艺术家之作品、军人之战功、官僚之政绩等,皆是广告也。“我国所惯称之‘作用两字,颇与广告之意味相合。”[4]68总之,凡报告新闻之外另含其他目的者,即系广告的性质。他提醒记者如果遇到半含新闻半含广告之类的材料,可削去其中广告(有作用)的部分,否则,会极大损害新闻的价值。
第二,揭发人之阴私者。邵飘萍指出,媒体的特质在于其“公共性”,若与国家社会无关之个人私事,竟为揭发于报纸,乃违背德义,是不人道的事情。“故凡个人私事,不问其善恶,皆不得用作新闻之材料;否则即大损害新闻之价值。”他称赞欧美一些国家的报纸对此最为注重,无论如何皆不肯揭发他人私事,有违反者,决为道德法律所不许,公私之界限判然。他举出一个掌故,日本明治四十二年的夏天,英国《泰晤士》之外报主任启罗尔与该报北京特派员莫利逊同访大隈,与早稻田三人私谈,其谈话的一部分内容,后被《朝日新闻》登载,启罗尔见之非常不悦,直致书该报诘责,谓所谈既属私事,不应未得其许可而遽行发表。日本记者颇因是而大窘。邵飘萍批评说:“我国有一部分新闻记者,对于此义,似未深考,且每以尽发他人私事为能,终日所探索者,皆为他人之私事,竟有将他人之家庭秘密,闺房私语,揭载于报纸者,是诚可恨已极。使外人见之,直轻视我国人为毫无新闻知识与道德也。”[4]68他希望新闻记者能高度注意这个问题,力矫弊风。他还认为若在这个方面实行禁载主义,可有效减少新闻记者借此敲诈的恶行。
第三,有害社会风俗者。邵飘萍认为报纸作为社会的教师,感化力之大,过于电影戏剧,故凡有害社会风俗之事,不可作为新闻而任意披露。“所谓有害社会风俗者,最当注意之点,为秽亵与残忍,淫书淫画淫戏之禁止。”[4]69他介绍英美诸国中等以上的报纸,对于惨死光景、尸体状态等,皆不加以细写。至如娼妓卖笑生涯,青年男女淫奔野合,更不肯略事叙述,“盖预防秽亵残忍之增长,方合于新闻之任务也”。他举例批评我国新闻媒体在这方面甚不注意:“某记者之本家,为仆役所杀,后其仆判决死刑而枪毙,某记者为一时快其私仇,竟大书特书枪毙时情形,愚读之心身皆悸,使一般无识人民日日灌输此种记事,畏法之效未可睹,未有不流于残忍者。又有陶某一案,关于翁媳间事,北京一部分报纸,皆视为珍闻而穷形尽相,苟日日以此灌输,羞恶之心未必生,亦未有不流于淫乱者。”[4]69他揣度报纸之所以如此悍然不顾社会大众观感,无非以此迎合一般劣等读者的心理,实不足为训,既有损新闻价值,又贻害社会风俗。他叮嘱记者在下笔时应存身处讲堂之心,谨慎而为,否则自失社会中教师之地位,蔑视新闻记者的人将更有借口。这不啻是新闻业者的自杀!
邵飘萍还对新闻媒体缺少独立的品性颇有烦言。他认为媒体不独立,固然是当时中国政治紊乱、经济凋敝的必然结果,但也是媒体没有定力的表现。记者与各方周旋,易受外力包围。“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此外交记者之训练修养所最不可缺者。”[4]69当时社会上不时有报纸受通讯社操纵的传言,邵飘萍分析说,通讯社在新闻界中的地位,原以供给新闻材料或提示报馆进行详细采访的路径,报纸编辑有取舍、剪裁改削的自由。“若谓通信社可以操纵言论,则自欺之谈,或一种对于外行者骗诈之手段而已。北京报馆以数十计,通信社亦相继而起,以十数计,通信社之能力似足以操纵北京之言论。然此乃由于报馆腐败之故。即因对于通信社稿不能剪裁取舍以求其适当之故。苟为稍有精神之报纸,吾未见其能听通信社之利用操纵者。”[6]有精神的报纸,自有记者采访新闻,对通讯社来稿必不糊涂登载。通讯社除却供给材料之外,有何作用可言?有何能力神通可显?显然,通讯社所可得而操纵者,必为那些腐败不堪、销量小、有名无实的报纸。既属此类报纸,操纵之有何益?故妄信通讯社为以操纵言论者,非外行即冤桶。北京新闻界的发达有一日千里之观,不可谓非一种进步,但是,“循名核实,所谓进步者,其外观乎,抑其真实之内容乎?”[7]邵飘萍明确指出:北京的媒体多则多矣,而有确实基础与言论之能勉成自由独立者,仍属少数。因而政治上每一大问题发生,必有如何收买舆论的传言出笼。风起于青萍之末,此类传言出现,每使人疑为收买多数亦属不难。此诚我新闻界的奇耻大辱。有志之士,不可不立起彻底一雪之!
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邵飘萍是一个豪气干云、有崇高使命感的领袖性人物,这种使命感使他密切关注新闻传播的现实发展,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介入和理论努力,帮助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逐步脱骨换胎,步入理想的境域。他的媒介批评活动几乎贯穿和存在于其所有的新闻活动形式之中,是他虽不长久但却异常光彩照人的新闻实践的一部分,在引介和普及现代新闻理论,促成中国新闻学术现代化发展并初步实现实践转化的过程中,有着不可磨灭的推助之功。他的媒介批评活动在本诸新闻实践的同时又能超出具体的事件之分析而达成某种理论约括,以批评的方式相对完整地表述其新闻理论见解,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学理层次,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值得宝贵的一笔。
[本文为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近现代媒介批评史(1815-1949)》(12YJA860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史(1921-2011)研究》(2012YBXM059)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邵飘萍.新闻学总论[M]//肖东发,邓绍根.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邵飘萍.敬告因运动议长而埋怨报馆者[M]//方汉奇.邵飘萍选集(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53.
[3]邵飘萍.从新闻学上批评院秘厅对新闻界之态度[M]//方汉奇.邵飘萍选集(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34.
[4]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M]//.肖东发,邓绍根.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张季鸾.追悼飘萍先生[M]//肖东发,邓绍根.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46.
[6]邵飘萍.通信社有可以操纵言论之能力否乎?[M]//方汉奇.邵飘萍选集(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346.
[7]邵飘萍:北京报界之宜自警惕[M]//方汉奇.邵飘萍选集(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476.
(作者为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新闻学博士,传播学硕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委)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