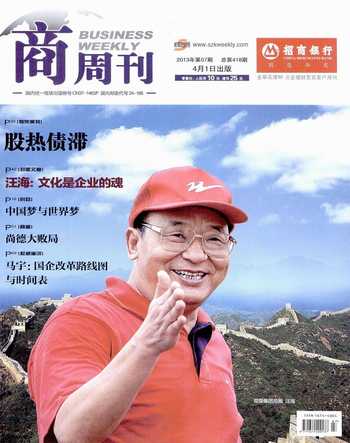非小说阅读的意义
2013-04-29薛涌
薛涌
非小说阅读,是基础教育中最被忽视、也最为重要的一个领域。我曾根据自己在中国教育体制中的经验,批评中小学的语文教学“语文和文学不分”,或者说语文课过分文学化。语文课本里小说散文过多,社会科学方面的材料太少。高考作文常常是文学性的写作,但大学毕业生对于法律、商务文书这样的实际写作技能则摸不着头脑。其实不仅中国如此,美国也不例外。女儿在美国快读完初中,查看她学校中的英语课程,从小学—直到高中毕业,基本是一色的文学作品,如《奥德赛》《简爱》甚至《罪与罚》,找不到非小说类的作品。
美国教育界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最近,由4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所采纳的“州际共同核心标准”要求美国中小学12个年级要逐渐用“信息性文本”代替“虚构性的文学”。支持这一新标准的力量相当有来头,其中包括“全美州长协会”和“州学总监委员会”等权威组织。他们认为,美国学生习惯于容易的阅读材料,丧失了接受复杂的非虚构性信息(包括研究、报告、原始文献)的能力。这使他们无法适应大学课程的要求和职场的挑战。为此,将在2014年开始实施的新标准,要求在小学的非小说阅读要占学生阅读总量的一半;到12年级(即高中毕业班)时,非小说阅读必须占据阅读的70%。
这一标准的提出,在中小学老师中引起不小的恐慌。老师们喜欢用故事书和小说教学,缺乏处理这些非小说阅读材料的经验,甚至连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也不知道怎么教。许多老师指出,喜欢读虚构性文学乃是孩子和青少年的天性,而且这种材料有重要的教育价值。让学生们突然改读非小说,一切就变得枯燥乏味,孩子们无法专心,丧失了对学习的兴趣,甚至会产生许多行为问题。可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的英语教学(相当于中国的语文教学),早已被文学所主宰。
我是在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读的本科,这是我当年的“第一志愿”。我从来不会小看文学。在我看来,解读文学不仅不“容易”,而且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对女儿的学校要求孩子们在高中最后一年读《罪与罚》暗暗感到吃惊。读过此书的高中生们也纷纷把话传给低年级的学生:“这书实在太压抑!”让生活得舒舒服服的美国学生在18岁前体会《罪与罚》中的灵魂煎熬,跨度实在很大,也非常具有挑战性。但是,绝大部分学生一生从事的职业所需要的阅读是什么呢?恐怕更多的是法律文献、商业报告、新闻、社会分析、政治评论等。他们一生所需要的写作技能,大概99%是非文学性的实用写作。但是,看看美国中小学的英语教程,在这方面几乎毫无准备。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美国中小学的英语课程,如同中国中小学的语文课一样,非改革不可。不错,美国的社会研究课,包括历史地理政治等题目,有许多阅读;科学课也比中国的物理化学更强调阅读。但是,这并不构成英语课不改革的理由。为什么?因为其他“文科”课程中的阅读其实并非阅读。比如历史课本,主要是一本流水账,告诉学生基本的历史事实,和中国的死记硬背相去不远。
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中小学必须改革阅读教学。这种改革应该是整体性的,即不仅要重新构造英语课或语文课的基本教程,而且要改革历史、地理等流水账式的教学,把阅读具体的作品(而非教科书)作为核心。
在这方面,美国中小学里的科学课倒是能提供些好的范例。以我的观察,中国的物理、化学等,太过注重解题,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最终演化为习题课。女儿上科学课,则会阅读许多有意思的文章,比如人脑容量的进化过程以及与其他高级哺乳类动物的对比等,其中没有定见,只是提供了几种假说、以及支持这些假说的证据,解读完全是开放性的。这样的阅读,在历史地理等“文科”课程中倒反而没有。
我们当父母和老师的都知道: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的阅读都是从童话开始,他们喜欢大灰狼、小白兔,再大点后会迷上《哈利波特》。但是,孩子终要长大,他们的世界也必然要从童话回归现实。阅读训练作为他们成长的关键,必须反映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