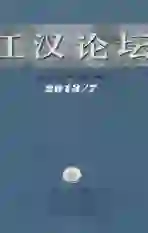京海合流与海派散文的生成
2013-04-29陈啸
摘要:京派与海派本就同源异流。1920年代末,文学中心在北京与上海的游走一定程度上成为海派散文生成的催生剂。京海合流,客观上提供了海派散文产生的平台,提升与雅化了海派散文的市井气与名士气,延续与发展了五四以来京派作家对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发现。京海融合的直接结果是产生或完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生活散文、文化散文,自然也是一种城市散文。当然,海派作家是现代都市的产儿与真正都市文化的代言人,海派散文更多的还是来自都市生活的刺激,但京海合流对其散文品格的规范与提升,使其更能以花样翻新及相较高雅的品格赢得文化市场的接纳。
关键词:京海合流;海派散文;论语派;市井气;名士气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7-0045-05
1920年代末,文学中心在北京与上海的游走一定程度上成为海派散文生成的催生剂,真正意味的海派散文开始成型并很快出现其鼎盛局面。一般认为,海派文学最多地“转运”了新的外来的文化,在文学上具有某种前卫的先锋性质;它迎合读书市场,是现代商业文化的产物:它是站在现代都市工业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的现实生活与文化的:它是新文学,而非充满遗老遗少气味的旧文学。这四个方面合在一起,就是海派文学的现代质。符合这样品格的海派,只能在1920年代末期以后发生。海派散文作为海派文学的一脉,其整体文学性亦当作如是观。以吴福辉、许道明、李今等为代表关于海派文学(主要指小说)的研究,已是硕果累累且日臻成熟,海派散文却涉及较少。而海派散文的作家构成、创作个性、发展流变等都有着不尽同于海派小说的个性色彩。在海派散文的生成史上,京海合流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首先,在创作构成上,海派散文的代表作家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京人海转型的作家,二是上海本地新起作家。前一部分作家就是随着“语丝”的分化及沪版《语丝》的出现而伴生的。“语丝”分化的直接原因是奉系张作霖政府因“有伤风化”之名查封北新书局,《语丝》受池鱼之灾。1927年12月,《语丝》移至上海出版,即周作人所谓的“沪版语丝”,1930年宣告终结。走马灯似的军阀执政及对文化人的迫害,使得鲁迅、林语堂、章衣萍等语丝同人避祸南下,语丝社友人风流云散。
北方的一些作家来到上海以后,似乎对海派文学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很快一改初衷,俨然海派。京派背景的散文作家在由京人海的过程中完全或基本蜕变成海派散文作家的,以“居士”章衣萍和林语堂为代表。章衣萍似乎早就有着“海派”的倾向。在北京时期的《语丝》上,章衣萍以“衣萍”笔名撰文28篇之多,数量居周氏兄弟后排第五位。此一时期即1924年11月至1927年7月间,章氏为文一概本着《语丝》刊物的固有宗旨,“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其文风主旨是对人生与社会的深切关注,语词激烈、率真和叛逆,以《樱花集》为代表。但也恰在此时,章衣萍已露出些许海派气息,如其在《情书一束三版序》中直言:“居古庙而想女人,虽理所不容,亦情所难禁。‘女人,女人,女人,想着,想着,写着,写着,这样所以有《情书一束》的印行。”或正因如此,章衣萍走在“京海合流”前头。早在1927年,章氏未等《语丝》终刊,便同妻子吴曙天联袂南下。在暨南大学当教授的同时,也把《情书一束》的传统发扬至极致,随后即有《枕上随笔》、《倚枕日记》的面世。章氏最终远离了“京派”,俨然成为一个地道的海派。
林语堂本为京派中人,但上海亦是其文学之源,他的大学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同是1927年奔赴上海,但他的声名和影响却远甚于章衣萍。林语堂的“海”化稍复杂于章衣萍,其庙堂意识和京派背景的根要深于章衣萍。但因身居上海而受到现实及时局的影响与冲击,其“海化”的散文小品也时或出现。如发表于1933年的《谈女人》如此说道:“近来觉得已钻入牛角尖之政治,不如谈社会与人生。学汉朝太学生的清议,不如学魏晋人的清谈,只不要有人来将亡国责任挂在清谈者身上。由是决心从此脱离清议派,走入清谈派,并书:‘只许我扫门前雪,不管他妈瓦上霜之句,放于案上玻璃片以下以自戒。书完奋身而起日‘好!我们要谈女人了!”“谈女人”似乎宣示了林语堂小品写作与海派的合流。林氏散文论及范围广大精微,政治病、西装,甚至牙刷等,信手拈来,真是无所不谈,追求自我心头的轻松,书写自己的世界,远离经世文章。然而,质言之,林语堂散文的“海化”体现着的至多是一种向上海市民社会的倾斜;它解放了读者的趣味,是一种“轻文学”的新文体。而实际上,林氏之救国救民之心一直潜藏于中,距离“海派”为文的“潇洒”尚远,其作为一个启蒙者的角色始终难以脱却。这从他的很多言行中,不难体会得到。如1932年他在《论语》发刊词中如此说:“无心隐居,迫成隐士”,在北伐革命及接踵而来的国民党的“清党”和“钳口”政策下,既不愿以头颅作政治的祭品,又不愿避世,生存技巧便成为在严酷的政治现实中实现个人价值取向的基本保证,有所坚持与有所逃避,结果便是走一条非普罗的路线:“一定要说什么主义,咱只会说是想做人罢。”1933年初林语堂在中央研究院任上曾参加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7年林语堂移居美国途经日本时写下的《临别赠言》说:“在国家最危急之际,不许人讲政治,使人民与政府共同自由讨论国事,自然益增加吾心中之害怕,认为这是取亡之兆”,“因为一个国决不是政府所单独救得起来的。救国责任应使政府与人民共负之”,“除去直接叛变政府之论调外,言论应该开放些,自由些,民权应该尊重些”。显然,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其“海”化是一种被迫与生存技巧,林语堂尚算不上地道的海派散文中坚作家。
诚然,林语堂不是海派散文的代表性作家,但以他为精神盟主的论语派却直接促进了真正海派散文的形成与发展。主要表现如下:
(一)刊物的市场导向
以林语堂为核心,论语派创办的期刊很多,主要有:1932年9月16日林语堂、陶亢德主编的《论语》;1934年4月5日林语堂、陶亢德、徐讦合编的《人间世》;1935年9月16日林语堂、林憾庐等主编的《宇宙风》等。论语派期刊已经不同于《语丝》时代的同人杂志性质。在上海特殊的工商背景下,出版商与文人将文字作为商品出卖的焦虑较前凸显。正因如此,林氏刊物及论语派刊物对上海以商业性赢利为动机的文化工业持认可的态度。将刊物定为“半月刊”,林语堂也有着商业性的考虑。他在《说小品文半月刊》一文中,就特别比较了季刊、月刊、半月刊、周刊等的区别,他说:“今人所办月刊,又犯繁重艰涩之弊,亦是染上带大眼睛穿厚棉鞋阔步高谈毛病”,“总不及半月刊之犀利自然,轻爽如意……稍近游击队,朝暮行止,出入轻捷许多”,“周刊太重眼前,季刊太重万世。周刊文字,多半过旬不堪入目,季刊文字经年可诵。月刊则亦庄亦闲,然总不如半月刊之犀利自然,轻爽如意……半月刊文约四万,正好得一夕顽闲闲阅两小时。阅后卷被而卧,明日起来,仍旧办公抄账,做校长出通告,自觉精神百倍,犹如赴酒楼小酌者,昨晚新笋炒扁豆滋味犹在齿颊间”。半月刊所隐含的灵活、轻巧、亲切等正显示着与都市大众文化的谐和及节奏的共鸣。同样源于商业文化的机制,论语派的诸多刊物相对开放,编辑是只认文章不看人,迎合着一般市民大众的欣赏口味,追求着大众流行。论语派的所谓“派”已然不是一个严密的社团组织,林氏刊物上的作者成员非常复杂:北京作家有周作人、俞平伯、刘半农、孙伏园、章川岛、李青崖、郁达夫、沈启无、姚雪垠、刘大杰、江寄萍、丰子恺等,左翼作家有鲁迅、陈子展、徐懋庸、风子(唐弢)等,另外像宋庆龄、蔡元培、胡适、郭沫若等也赫然在列,可谓八方汇聚。值得注意的是,在林氏刊物上,年轻一代海派文人纷纷加盟。主要有邵洵美、周劭、章克标、徐讦、陶亢德及黄嘉音、黄嘉德兄弟等:1940年代成名的苏青最早也于1935年以冯和仪之名为《论语》和《宇宙风》写作。另外,更大范围的新起作家还有林微音、钱歌川、叶灵凤、马国亮、梁得所、潘序祖、张若谷、周黎庵、周楞伽、毕树棠、钱仁康、燕曼人、林无双、林如斯、林疑今、林惠文、余新恩等,其作品经常出现在林氏主办的及林氏影响下的刊物上。如此,海派散文乘论语之风而起。新起海派文人表现出更为超拔、清新的散文风格,由此形成真正的海派散文并很快出现了海派散文的鼎盛期。林氏刊物实际为海派散文的兴起与兴盛提供了平台。显然,论语派刊物因市场导向及市场机制规约而显示出来的宽容,注定其不是一个严谨的散文派别。各组成成员的风格差异相较明显。一些北方成员如老舍及一些内地成员如老向与何容等本身就没有沾染多少上海气。然而,上海的卖艺为生与北平“吃皇粮”的贵族式学者的生存方式毕竟有着很大区别。南下文人的大部则显示出对上海现代物质文明所怀有的那份颇为暖昧不明的情绪以及与现代都市尚未完全融入但已切身感觉到的胶着。散文小品所表现出的游戏、趣味、幽默及闲适等已经显露出与1920年代散文路径的差异。在上海特殊的时空语境下,“语丝”时代的文化政治立场等已悄然发生了变化,“语丝”时代所看重的对于一切卑劣之反抗、排击及挑战的意愿似乎已经减退消沉,而以“谑而不虐”及“幽默”代之。这似乎也正意味着他们的“海”化,然而毕竟又未能使其变成地道的海派文人。传统文人的“问世”思维始终或隐或显地规约着他们。不过,由于论语派与林语堂的“宽容”,客观上却使一批“小海派”将之作为平台实现了带有“派”味的集结。
(二)北京作家的同情与“暗示”
林氏刊物实现了事实上的京海合流。京派散文作家在上海刊物的集体亮相及其作品的流行与流布,无论直接或间接,很难不对上海作家产生影响。这其中,周作人的影响尤为突出。周作人不仅影响了京派,同样对海派影响深远。海派散文代表作家很多都与周作人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周作人的散文在海派文学期刊中频频露面,数量颇多,而且往往排在头条,从1930年代的《人间世》至1940年代的《风雨谈》大多如此。上海文学期刊还常常刊登一些专门介绍周作人散文的文章,竭力加以推扬。如此,周作人散文便成为海派散文作家摹写的范本,其影响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本色为文。周作人为文追慕自然本色,从容镇静,安详沉着,他继承了中国散文的“和淡”传统,其小品有东晋六朝遗风。周作人文体的“本色”魅力主要源于两个方面:语言的简单味:平淡地处理与人生紧密相关的种种问题。喜怒哀乐不入藏腑,包住火气与芒角。其为文的情感、议论、行文叙述等,皆平淡自然家常,没有狂热与虚华。受其影响,海派散文完全是一种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原真本色。文风平淡,收放自然,是“放野马”式的散文。
其二,笑脸为文。周作人是闲适散文的始作俑者,是现代散文幽默风一派的宗师。他喜欢滑稽,喜欢那种“庄谐杂出”的“名士清谈”。他努力给读者一种严肃书写之外的文学选择——“轻松”与“随意”。当然,周作人的“轻松”是一种故作的“轻松”。“轻松”的背后隐含的是严正,潜藏着与政治话语的敌意。周作人立足于国民性剖析与改造的作品似乎一直占有多数。他无法脱离其隐逸背后潜隐的政治。显然,新起海派的轻松与幽默比周作人走得更远,渐趋一种完全的“轻松”与“幽默”。他们不追求空言与浮言的传道立场,不追求外在的价值联想,而是逼近与叙述现实,追求语言的狂欢,是一种放松的写实主义的“幽默”。比如章克标用嘻嘻哈哈的态度调试着自我与现实的冲突,彰显一种放恣的插科打诨式的小品风格。海派文人基本没有了周作人及大部分论语派作家于“幽默”中所显现的那份雍容,而是从低就俗,没有了深奥和神圣的感觉。
其三,生存之轻。对本色与自我个性及日常生活的关注,决定了散文小品所言话题远离了神圣性与崇高性,而偏重生存感觉之轻。在此层面上,上自周作人,下及论语派及新起海派散文,一脉相承。周作人的散文所表现出的“小”大致具有如下特征:知识丰富、情感节制、重视学理思考、意在文化批评;基本是随笔;重视个性与自我;重视凡庸人的真表现;言自己之小志,载自己之小道。林语堂等论语派,承周作人衣钵且大加发扬。他们更加重视小品文对世俗生活的偏爱与对日常叙事的热衷。正是在周作人的暗示及影响下,林语堂等在1930年代的上海文坛发动和形成了推崇晚明小品的热潮。但林语堂等论语派的散文依然有着潜隐的政治化的姿态,他们更多的是以文学的自主与独立作为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方式,并且他们所注重的往往也多是对“现代”与传统进行重新厘定与思考的相较宏大的内涵。质言之,他们市民化的痕迹尚不明显,与海派散文的超拔与“拉杂”并不在一个层面上。相较于周作人与论语派,海派散文更“小”更“轻”更“形而下”,甚至如章克标等人以极度“轻浮的态度”,写不三不四的题材,崇尚新奇,爱好怪诞,推崇丑陋、恶毒、腐朽、阴暗,贬低光明、荣华,反对世俗的富丽堂皇,申斥高官厚禄大人老爷等极端的态度表达自己“极端”的个性。有时不免带有媚俗及自娱的倾向。他们更有生活的现场感,更有与市民社会的胶着、认同与市井气。海派散文的风景线是真正属于市民的,它比周作人等的散文显得更轻松,更洒脱,更快乐,更市民化,更没有火气和艰涩,更觉轻逸与隽永。但海派散文的“轻”与“小”,似乎也同时显示出市民社会中个体生存状态的迷惘与无奈,如张爱玲、苏青等,在其散文的“闲”与“碎”中多有某种温柔的悲情。如果说周作人等的“生存之轻”尚保有深厚与神圣的话,海派散文的“生存之轻”则已完全转入了新锐、怪诞、惊诧、激扬、趋时、神奇之中,甚至亦有颓废。
质言之,海派散文所继承于周作人等的是个人的“言志”的文学传统,是个人的散文笔调。但周作人等似乎一直站得很高,尚不属于大众的一员。周作人的散文也始终有着“冷”与“怀疑”,他是彻底的怀疑主义者。而海派散文则是属于市民社会的,因为工业社会的刺激而发声,这声音是从下就俗的,有着市民社会的温热与吵闹以及工业社会刺激之下话语狂欢的轻松与放恣。
(三)消费文化与文体选择
京海合流形成了海派散文的作家队伍及创作之魂,但因生长的时空语境有别故而生成了异于京派的别样果实。晚清民国之际,西方列强以长枪巨炮迫使中国打开国门,中国跌人世界市场的旋涡,尤其是上海,自1843年开埠之后,成为华洋杂处的国际商业消费大都市,到了1930-1940年代,上海更是成为由发达的工商金融业和消费性文化构成的现代都市空间。上海流行的消费文化在悄然改变着一切。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审美态度等方方面面都体现着消费文化的影响。当消费文化深切地介入人们的生活,改变了创作、阅读与传播的每个环节以及参与其中的每个人时,文体也就只能随之变化。消费文化正是通过改变作家、读者、文本传播等因素进而影响到文学文体。作为海派文学重要一脉的海派散文正是以自己独有的话语方式完成了对都市消费文化背景下世俗百态的探索,实现了以文求生的现实目的,得到了在非常时期非常地点的读者的欢迎和认可。
在消费文化的规约下,海派散文作家的精神产品不再指向庙堂,效力于政治的主导者,也不指向书斋,而是指向市场。章衣萍曾直言不讳地宣称:“所谓文人的著作,在高雅人士看来,诚为不朽之大业,而在愚拙之我看来,在资本主义之下,一切的著作,无非皆是商品而已。”他公开宣称他的散文集《枕上随笔》“是一册粗劣而且浅薄的商品”。苏青说:“我很羡慕一般能够为民族、国家、革命、文化或艺术而写作的人,近年来我常常是为着生活而写作的。”作家为生存而鬻文,就必须建立在扩大销量与增加稿酬的基础上,因而其创作往往是迎合广大市民阶层的迫切需要,能够反映他们的观点、情趣并藉以交流、沟通、娱乐、消遣的文化产品。比如对“趣味”的追尚,海派散文承接周作人与林语堂等的衣钵,大胆、直率、自然地追求与张扬着文学的娱乐性。徐讦在《谈艺术与娱乐》里明确地说:“文学也不过是一种娱乐”,并且强调“把艺术说成是纯粹的娱乐并没有把艺术看低”,这是公开为文化消费正名。海派散文的“娱乐”、幽默与轻松,已经不同于前期周作人、林语堂等的轻松与幽默。周作人、林语堂等的轻松与幽默往往是主体对政治文化等被动反弹的静态观念及内涵,而海派散文的幽默与轻松却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它即时适应着一般都市大众的社会文化心理与读者的审美需求,成为生活的调节剂。
为了赢得市场,海派散文常常以常人地位说常人的话,或者说,海派文人视自己为市民中的一员。即如穆时英和叶灵凤说他们的杂志文章“不够教育大众,也不敢指导青年(或者应该说麻醉),更不想歪曲现实,只是每期供给一点并不怎么沉重的文字和图画,使对于文艺有兴趣的读者能醒一醒被严重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只是如此而已”。海派文人弱化文学的教育功能,将自己归入读者群,寻找自己文章的卖点。在此基点上,海派文人做出了避免高深难懂的严正,从轻就俗,偏爱一般,力主安稳,亲近大众等的题材选择。
语言与思想的新奇及破格也是海派散文吸引读者大众的重要卖点,这是市民社会的率直与泼辣。如苏青一直被人称为“大胆女作家”,她敢于抒怀,大胆直言,常常发出别的女性所不敢吐露的惊人奇论!《谈女人》如此说道:“许多男子都瞧不起女人,以为女人的智慧较差,因此只会玩玩而已:殊不知正当他自以为在玩她的时候,事实上却早已给她玩弄去了。”这话在今天看来,仍然让人叫绝!直言坦率,多用怪论,其实质亦是追求散文的世俗化,这似乎远离了纯文学,但更刺激与迎合了大众。
奢谈女人,似乎永远是消费社会的卖点。海派文人无论女性亦或男性,都喜欢大谈女性。这里有女性生活的感觉,如苏青的谈女性的系列散文几乎涵盖了都市女性婚姻、家庭等生活的各个领域。而男性作家所谈的女人,则往往变成了欲望的对象,他们似乎也正是借此来刺激与吸引读者的神经与眼球。如张若谷的《对于女性的饥渴》开篇就说:“我今年二十六岁了,我对于女性感着饥渴。”整体上看,海派散文作家笔下的女性是欲望,是生活,是饮食男女的一部分。当然,在消费文化规约下,海派散文也常常忽视技巧,随笔性与散文结构上的“本位”性凸显,时或有因追求短平快而带有的粗浅等缺憾与不足。
三
京派与海派本就同源异流,吴福辉先生曾如此说过:五四运动是海派势力延伸到北京去,并进而突破了京派的士大夫传统的结果。然而后来这个海派势力的一部分重新又南下,另一部分仍留于北京接受了士大夫传统。南下的京派文人本就有着海派文化的天然因子,而新起海派似乎天然有着与北京作家及论语派的亲切感,加之上海文化的开放性,似乎都在规约着其合流与产生影响的可能。京海合流虽也带来了北方作家的“海”化,使其开始有了市民文学的印记,但终究没有使京派作家变为地道的海派作家,论语派小品与超拔的海派散文并非在同一风景线上。但京派散文作家周作人、林语堂等在上海的精神加盟,却分化与改组了上海的散文作家队伍,导致与促进了海派散文的生成,甚至可以说,没有京海合流就没有现代海派散文的产生。以林语堂为首的论语派及论语派刊物,并没有形成“论语派”本身的整齐划一局面,“论语派”的出现似乎仅仅标志着“语丝”时代在上海的终结。但论语派刊物却在客观上造成新起海派相较整齐的“派”性集结,成为论语派刊物中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周作人、林语堂等北京作家的同情与“暗示”规约和提升了新起海派散文品位及现代性,加之上海工商化的特殊背景,使得海派散文迥异于同期的京派散文以及与之关联的论语派散文。京海合流,使得海派的浮浪气、市井气与名士气因着绅士气与书卷气多了几分典雅与庄重。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海派散文继承与发展了北京作家的对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发现。“五四”时期,京派散文小品常以身边琐事为表现对象,留心体察世俗人生,追求生活趣味,领略与观照人生情味及人生意义,到1920年代末,社会矛盾加剧,作家思想随之转向,改变了散文小品的题材倾向,“身边琐事”似乎变得无足轻重。然而,海派散文小品却继续发展了书写“身边琐事”的传统。当然,海派散文的书写琐事,毕竟有别于语丝散文的个人性,语丝散文整体仍有一定的寄情性,到了论语派散文时期,是想说而不便说或不敢说,但毕竟潜藏着一定的理想,当不属于纯粹个人笔调。而海派散文则完全由社会退向个人,是一个小写的“人”。它更加浓化了对于世俗人生况味的吟咏,加重了散文小品的消遣性,更加体现出处于商品经济旋涡中的市民心态。它的十字街头的审美趣味,痛快、新奇、趣味至上,失去了严肃,获得了通俗。当然,海派散文更多地还是来自都市生活的刺激,其对世俗人生及趣味性与消遣性等的表现是自然的而非做作的,是敏感和细腻地表现瞬间的感触,现实的刺激。海派散文同样表现与发挥哲学大义,透析世态炎凉,描摹人间世相,但它们往往有着较切实的现实生活场景,为文姿态平和,不摆架子。新起海派散文作家是现代都市的产儿与真正都市文化的代言人,由于京海合流,规范与提升了他们的散文品格,使得其市民性及日常性更能以花样翻新及相较高雅的品格赢得文化市场的接纳。
作者简介:陈啸,男,1975年生,安徽淮北人,文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4。
(责任编辑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