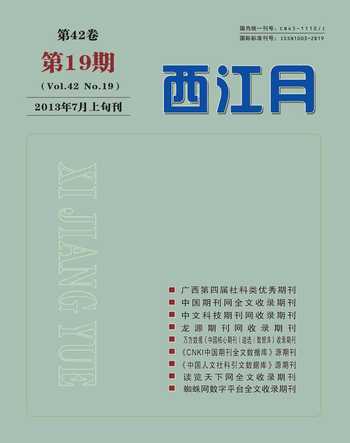由经书辅翼上升为权威经典
2013-04-29陈咏仪
【摘 要】儒家经典是儒学的基础,而被认为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论之汇编的《论语》更被视为经中之权威。然而《论语》这种崇高的地位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建立起来的。从春秋时期直到明清,《论语》的地位得到逐步的提高,实现了“从经书辅翼上升为权威经典”的这一转变。而这一转变的实现,一方面是由于它适应了当时转型社会所提出的种种要求,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复杂的政治和文化斗争来达到的。《论语》地位的提高,植根于传统社会,又深刻地影响了传统社会。本文通过对两千年来《论语》地位的逐步提升进行研究,以便为儒家思想和传统社会的互动研究提出一点抛砖之见。
【关键词】《论语》;儒家经典;孔子;儒学演变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汇编,“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箴言﹑经典语句,“论语”即是论纂(孔子的)语言。全书由孔子门生及再传弟子集录整理,是如今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料之一。《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
《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到汉代时,有《鲁论》(20篇)、《齐论》(22篇)、《古论》(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以《鲁论》为底本吸收《齐论》部分内容编订成俗称《张侯论》的新本子,是为《论语》的第一次改订。东汉末年,郑玄混合《张侯论》和《古论》又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这是《论语》的第二次改订。此后《齐论》和《古论》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唐代韩愈和李翱合作的《论语笔解》,宋代邢昺《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今本《论语》就是郑玄编成的那个本子,共20篇,约1万2千字。
总体而言,《论语》在后世地位是不断提升的。北宋宰相赵普便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而南宋朱熹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合为“四书”,使之成为儒家经典,后世更是推崇到极为重要的地位。然而《论语》在宋以前虽然被儒者看作一部重要的书,但儒生是没有把它当做经典的。当时儒家崇奉的是《易》、《诗》、《书》、《礼》、《乐》和《春秋》“五经”。官方设立“五经博士”,儒者传习也按五经分科,《论语》则更多的是作为儿童学习的初级课本。
儒家经典是儒学的基础,而《论语》地位的提升自然与儒学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学术地位的沉浮有关。儒家的核心内容是如何修齐治平,注重礼仪制度和心性理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最终,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儒学每一次或大或小的转变,都伴随着每个时代所尊儒经的转变,《论语》的地位也随时代而改变。
一、汉代儒学与《论语》
汉初所推行的是黄老之术,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汉景帝时,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此事使当权者认识到需要用儒家的主张建立一套尊卑分明的礼仪制度,因此在汉武帝继位后董仲舒的建议就得到了支持。这一时期西汉所推行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
但《论语》在汉代并不是经。班固释“儒”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 [1]这里仍然只提到六经,而《论语》仍然不在其中。另外,当时统治者所重视的学科都设立了博士,而《论语》博士的存在只是昙花一现,可见《论语》在官方学术体系中是地位不高的。
孔子虽然在汉代已被视为圣人,但是《论语》在汉代还不是经。汉代独尊儒术,却不能把儒家创始人孔子的言行集作为经,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汉代独尊儒术,尊的主要是“诗书礼乐易”中的术。这就是说,他们认为,孔子所传的先王之道﹑仁义礼智之说,就是在这些著作里面。《论语》仅仅是对这些著作中某些内容的解说,不能代替这些著作。所以,《论语》与《孝经》等同一道在汉代主要是儿童诵习识字的读本,作为经书辅翼,地位并不显赫。
二、魏晋至中唐儒学与《论语》
汉末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转型时期,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诸子学派在沉寂了数百年后重新活跃起来。从微观角度而言,西汉前期董仲舒的儒学是吸收了别家学说重新整合后的新儒学,而汉末魏晋时期这种新儒学则在新的形势下又进行了一次整合,尤其在政治思想领域,儒学或是进行自我修正,或是汲取别派思想以自我完善,从而更加成熟。
魏晋时期,对《论语》地位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就是何晏的《论语集解》。《论语集解》其实是当时众儒者的集体著作,它虽成于众人之手,但何晏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此书保存了大量的古注,增加了丰富的新解释,其序文不仅探讨了《论语》的撰集者、內容、版本和传授情况,而且历数了《论语》研究方法的演变,其注释中少有玄虚之语。《论语集解》也是我国训诂史上第一部集解体训释专著,它打破了两汉学界的师法门户之限,杂糅古今经学,吸收了汉魏以来八家学者的优秀成果,训释简洁精当不但在后世跻身于《十三经注疏》之列,亦破除了两汉注经的烦琐和阴阳五行之说,给经学注入一股清新简洁之风,致使魏晋经学出现“儒道兼综”思想格局的形成和经学的玄学化,可谓影响深远。同时,它也使《论语》成为名士谈资。
但在唐代,《论语》注释大体呈现出衰落的局面,无论从注释总量来讲还是注释专著的流传情况来讲,《论语》研究都较前代有所下降。究其原因,是唐代重视佛教和道教思想对儒学的地位有所影响。盛唐时期,儒家虽因官方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的垄断以及科举制的推行而表面兴盛,但实际上处于一种衰落的状态。儒家的衰落可以上溯到唐高宗时期,其时“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于是醇醲日去,华竞日彰,犹火销膏而莫之觉也。” [2]整个经学呈现衰落局面,《论语》学的衰落就不难理解了。而这期间官方又把三礼三传并皆入为经,连同《易》、《诗》、《书》号称“九经”,但《论语》仍未入经。
三、晚唐至宋儒学与《论语》
自唐玄宗天宝十四载持续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55—762年)的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动乱爆发不久,儒家学者就对儒家进行了沉痛的反思。如陆贽﹑梁肃﹑欧阳詹﹑李观等著名儒者,都提出了改革科举考试,重整儒家经典的举措。对于《论语》来讲,由韩愈和李翱师生合作的《论语笔解》将其带入“儒经新义”改革风潮之中。《论语笔解》没有去给以前的注释作疏,而是直接注解《论语》,并且批评了以往儒家学者的失误。
更具突破意义的是,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史称十二经,自晚唐始《论语》首次进入了官方肯定的经书之列。《论语》首入经之列,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儒学到来。
宋代儒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理学成了儒学的新形式。理学流派纷纭复杂,北宋中期有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司马光的朔学,南宋时有朱熹的闽学、陆九渊兄弟的江西之学。
在新的历史机遇下《论语》的地位开始推向了权威之中。宋初的科举承唐制,在诗、赋、论、策之外,增加了《论语》十通,后来试经义,出题也包括《论语》。南宋末年,朱熹把《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列为“四书”,并抬高至“五经”之前。他认为“四书”是儒学的根本,读通了“四书”就可以无所不晓,朱熹曾如是说:“人若能于《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穷究得通透,则经传中折莫甚大事。以其理推之,无有不晓者。”[3]他如此表彰和推崇“四书”,另一方面也就是对其他儒经的贬低。当时又出现了“十三经”之说,也把《论语》列入。这就是宋以后《论语》不但成了“经”,而且位列“五经”之前,乃至今天许多人谈起儒家不知有五经,但知有《论语》的原因。而《论语》占据学术主流地位之后,它仍然是用来指导儿童学习社会行为规范,而成年人和儿童同时学习这部典籍,不过学习的方向和深浅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四﹑明清儒学与《论语》
明代朱元璋继续把程朱理学定为正统儒学,《四书集注》受到空前未有的重视,八股文的题目皆出自《四书》,并以程朱理学的解释为准。《论语》而且是经过程朱学派注释的《论语》更是成为每个读书人判断是非的标准、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成为入仕须臾不可离的经典。
有清以来,“四书”在学校的教育和科举考试中仍然处于首推地位。直到清末,有深远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曾说到:“垂髫童子,目未知菽粟之分,其入学也,必先课之以《学》《庸》《语》《孟》,开宗明义,明德新民,讲之既不能通,诵之乃徒强记。如是数年之后,行将执简操觚,学为经义。” [4]可见其时一代又一代人由幼童开始就必须对“四书”烂熟于胸,否则仕途无望。而在这种极端压制的文化统治和科举制度下,被认为直接传承了孔子道统的《论语》 更视为经中之权威。
五﹑近代儒学、现代新儒学与《论语》
历经1840年的鸦片战争, 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面临着民族危机的中国人,进行了一次次抗争。而抗争的屡次失败,使得一部分人将之归结为中国文化的失败。早在清末,就已经出现了群言交攻孔子的现象。爱新觉罗王朝的覆灭,儒学失去了制度性的保障。之后,袁世凯在企图复辟帝制时,又以尊崇儒学作为先导,这更加强化了部分知识分子对儒学的恶感。“五四”期间,以讹传讹的“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的广泛流传,正反映了部分知识分子对待儒学的态度。在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认同陷入严重危机的形势下,现代新儒学作为一个文化哲学流派出现和形成了。1921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可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奠基之作:“今天的中国, 西学有人提倡, 佛学有人提倡, 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若非我出头提倡, 可有哪个出头?”此后,儒学虽然继续遭到全面批判,但势头有所削弱,同时要求发扬中国文化传统,建设中国新本位文化的呼声得到了加强,而南京国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儒学发展给予了扶持。
1949年解放后,中国大陆对儒学的态度是有一定政治取向的,其生存和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与此同时,港台的新儒学也重新遭到自由主义者的攻击。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思想解放政策的贯彻和文化交流的活跃,儒学又从海外回到大陆。在这100多年来儒学的曲折历程中,儒家学说的变化发展是比较复杂的,仅仅是现代新儒家,从梁漱溟,熊十力,直到余英时,成中英,林毓生等,就一共有五代。大陆新儒学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也开始重新发出自己的声音,如蒋庆,盛洪,陈来,康晓光等等。而《论语》则是其中的焦点之一。无论是支持或者反对儒学,双方都从《论语》中寻找支撑自己论点的根据,新儒家则更是通过重新注释《论语》来进行自己“体圣人之意”的“改制变法”。直到现在,今人仍然在通过学习《论语》来学习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和获得修身处世的正确方法。
后 论
几许沉浮,《论语》逐步被推崇为权威经典,可以从“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一说法的长期流行中清楚地看到。现今《论语》热再度升温,以至于许多人提到孔子及儒学就只是想到《论语》而已。然而《论语》这种崇高的地位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建立起来的。从汉代到清末,经过长期复杂的演变,《论语》的地位才得到逐步的提升。《论语》地位的提升,既与社会政治的具体需要紧密相关,同时也和儒学自身的变化及学理的发展直接关联。
当今,如何利用传统文化精华以促进中华文明的承传是今人面临的一个艰巨的任务。而我们研究儒学的角度亦已不同于从前,总的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儒学“和谐思想”研究成果较多,而且多数论著都从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和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的角度进行阐释,注意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国与外国的对应。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有的论者较多地关注现实,因而对于儒学的深层理论分析似仍有所欠缺,特别是哲学诠释不够,这会有待学术界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渐克服。
儒学“和谐思想”对世界文明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今,通过对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的发展流变的学习研究,将有利于国家和谐社会建设。而在这个过程中,了解我国经典之一的《论语》其地位是如何提升的,对于今人适当地运用传统文化应该是有所裨益的。
注释:
[1]《汉书·艺文志》,志第一,汉书卷三,文艺志,第17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2]《旧唐书·儒学传》,列传第一三九上,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卷上·序,第49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3]《朱子语类》,第七册,第一百一十八卷,朱子十五,训门人六,第28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严复《救亡决论》,载天津《直报》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七至十四日(1895年5月1—8日).
作者简介:陈咏仪(1984—),女,汉族,现在广州农讲所纪念馆工作,历史系本科毕业,助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