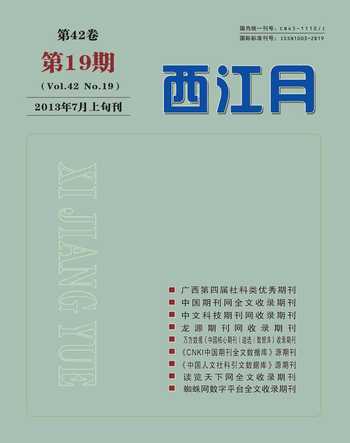成都“乌木案”的法律思考
2013-04-29余帮国
【摘 要】闹得沸沸扬扬的成都“乌木案”不仅在普通公民间争论颇多,而且法学界对此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都“乌木案”暴露了我国在民事法律制度特别是物权法律制度上还有很大的缺陷与不足。这要求我们完善相关立法,以实现物尽其用和最大限度地保护相关主体的利益。本文从成都“乌木案”入手,首先对乌木的性质进行了分析,指出乌木应属埋藏物。接着对乌木的归属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最后针对该类事件的法律规制,笔者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对该类事件的解决有所帮助。
【关键词】乌木;埋藏物;发现埋藏物
一、“乌木案”的由来和乌木的定性
2012年2月成都彭州市同济镇麻柳村村民吴高亮,在自家承包地中发现一批乌木(经鉴定为乌木中最珍贵的金丝楠木),就乌木的归属问题,当地政府与吴高亮发生了争议。7月9日,彭州市国资办召集林业、国土等部门,正式答复吴高亮:乌木规国家,奖励发现者7万元。吴高亮不服于7月26日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起诉状。这就是围绕乌木归属问题而发生的各方议论纷纷的成都“乌木案”。
关于乌木的性质,法学界观点很多,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自然孳息说”、“矿产说”、“文物说”、“无主物说”和“埋藏物说”。现将以上几种学说作如下分析:
1、“自然孳息说”。“自然孳息说”认为吴高亮发现的乌木属于土地的自然孳息。笔者认为此种说法值得商榷。关于自然孳息的概念,不同的国家或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史尚宽先生认为“天然孳息为物之有机的自然之出产物,及其他依物之用法而收获之出产物。”i德国和日本规定“孳息为依物的用法所收取的出产物”,法国似将孳息限定为植物的果实及动物的仔,瑞士将孳息限定为定期出产物或以通常使用方法使用该物所得的收益。
2、“矿产说”。“矿产说”认为乌木属于矿产。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也不恰当,理由有以下三点:第一,矿产和乌木虽然都有利用价值,但乌木的利用价值却与矿产大相径庭。乌木主要用于制作家具、辟邪等,而矿产资源则是发展采掘工业的基础,是社会生产的重要物质资源。第二,矿产还必须具有富集性的特点,而乌木在现实中大多都零星地分布,不满足矿产富集性的特点。第三,我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矿产资源的矿种和分类见本细则所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
3、“无主物说”。“无主物说”认为乌木属于无主物。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有不足之处。因为无主物一般指看得见的物(笔者咨询过梁慧星教授),而乌木多埋于地下,因此也不宜将乌木定性为无主物。并且将乌木定性为无主物还有以下弊端:如果乌木为无主物,那么其便适用先占制度,谁先占有乌木谁就拥有乌木的所有权。这可能会引起巨大的社会混乱和资源破坏,因为大家都会争相去挖掘乌木。
4、“埋藏物说”。“埋藏物说”认为乌木属于埋藏物。笔者对此种观点表示赞同。罗马法中,凡隐藏于他物中,因时隔多年而不能确定其所有人的动产皆为埋藏物。王泽鉴先生认为“埋藏物指埋藏于他物之中,而不知属于谁所有的动产。埋藏物具有三个特征,即埋藏物需为动产、包藏(隐藏或埋没)于他物之中不易由外部窥视或目睹、不知属于何人(有主物)”。ii法国民法典规定“一切埋藏或隐匿藏的物件,任何人不能证明其所有权且其发现又纯为偶然者,为埋藏物”。德瑞民法未规定埋藏物的概念,但其立法理由书表明埋藏物指因长期埋藏而不能查明其所有人的物。日本通说认为“埋藏物指埋藏于土地或他物中,其所有权归属不能判明的物”。iii由以上观点可以看出,法国民法典强调埋藏物必须是偶然发现的,德瑞民法强调埋藏物的长期埋藏性,日本民法和王泽鉴先生的观点较为一致,都强调埋藏物需包藏于他物中、不易由外部目睹、所有人不明。笔者认为王泽鉴先生的观点比较合理,这也符合我国目前多数学者的观点。
二、乌木的归属问题
既然乌木属于埋藏物,那么其归属问题的解决就应该适用我国《物权法》第114条的规定,参照适用拾得遗失物的有关规定。我国《物权法》第109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物权法》第113条规定:失物至发出招领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根据我国《物权法》第114条、第109条和第113条的规定,乌木应该属于国家所有。因为物权法虽然规定了公告和认领,但实际上没有人可能来认领乌木,乌木最后会归国家所有。
三、我国关于发现埋藏物制度的不足
由上文可以看出,如果乌木归国家所有,那么这对于诸如吴高亮这样的发现人来说显然不公平。依据民法通则,吴高亮这样的发现人还可能获得一定的的物质奖励,但如果依据物权法,发现人连一定的物质奖励都可能得不到,因为物权法并没有规定发现人可以获得一定的物质奖励。可见我国关于发现埋藏物制度还存在很大的缺陷与不足,笔者将这些缺陷总结如下:1、未明确规定何为埋藏物,导致理论和实践中对埋藏物的理解有较大分歧。2、《物权法》规定发现埋藏物参照适用拾得遗失物的有关规定,未明确规定发现人的报酬请求权,这对发现人很不公平。3、针对发现埋藏物未采取发现人有限取得所有权主义的立法模式,不符合世界的立法潮流。
四、我国发现埋藏物制度的完善
我国发现埋藏物制度一味强调无人认领的埋藏物属于国家所有,拔高和扩大了现代市民社会中人的思想意识觉悟之程度,忽略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对利益的追求,过高地估计了人的自觉性,并由此对人的行为提出了统一的不恰当的法律要求。iv针对我国发现埋藏物制度存在的缺陷,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修改《物权法》,对埋藏物的概念作出明确的规定。首先,我们应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将埋藏物定义为“埋藏于他物之中,不易由外部目睹,所有权归属不明的动产。”并应该明确规定“埋藏不以人为埋藏为限”。其次,为防止人们因肆意挖掘乌木而损害乌木、破坏社会秩序现象的发生,将发现埋藏物的“发现”限定为为“偶然”发现。
2、修改《物权法》时对发现埋藏物采取发现人有限取得所有权主义的立法模式。目前世界上对发现埋藏物的所有权归属主要有三种立法模式,即发现人有限取得所有权主义、公有主义和报酬主义。发现人有限取得所有权主义认为:埋藏物被土地所有人发现时,全部归发现人所有;若由他人发现,则半数归于发现人,半数属于土地所有人或隐藏物所有人。v德国、法国、日本等采取此种立法例。
五、结语
成都“乌木案”折射出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特别是物权法律制度还存在有大的不足,应该完善相关立法。从长远来看,修改《物权法》,对乌木的性质进行科学的界定并完善发现埋藏物制度是解决此类纠纷的根本办法。但鉴于我国目前不太可能立刻修改《物权法》,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让经常有乌木被发现的省份尽快制定地方性法规,对乌木的归属等问题作出具体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定分止争,保护相关主体的利益,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乌木这种珍贵的资源。
注释:
i史尚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72.
ii王泽鉴.民法物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96.
iii陈华彬.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62.
iv梁慧星主编.中国物权法研究(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526.
v江平主编.物权法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154.
作者简介:余帮国,四川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