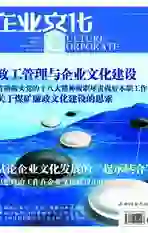女人的1.0与3.0时代
2013-04-29宋铖铖
摘 要:都市知识女性通过确立自我、认知自我的方式进行自我发现,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独特话语权。文清丽小说《女友的1.0时代》中,婚姻内外的“我”与卓乐分属女人的3.0与1.0时代,但在女性自我主体性问题上却有本质的相似。在传统文化标准与现代女性自我定位之间,女性的主体性建构应进行更深刻的升级换代。
关键词:女性主体性 自我发现 文清丽 知识女性
以都市环境中知识女性为主要人物形象的小说作品,在描写女性对待婚姻、家庭、事业,与爱情时所表现出的自我主体性意识,十分耐人寻味。从女性主义角度看,拥有较高文化素质和视野平台的知识女性,在对待自己的事业与感情生活时,应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和主动权,更有条件和资本遵循自己的内心体验。然而,事实境况中,独立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对女性肯定自我,建构起真正完善的主体性意识,所起的作用可能并不尽如人意。在文清丽的小说《女友的1.0时代》中,“我”与卓乐,作为大学时的密友,现在的至交,分别在婚姻围城内外扮演着看似相去甚远,实则异曲同工的角色。当卓乐慷慨激昂地宣泄着,“在高科技年代里,你的生活已经升级到3.0了,我还在落后的1.0时代”时,两个同样具有高学识素养的都市知识女性,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本质上惊人的一致性,即将女性自我的幸福与价值,确立在男性及婚姻对自己的肯定之上。看似独立自主、受人尊敬的新时代知识女性,也许在软件上仍然停留在传统的0.0时代。
一、自我发现的征途
在现代文明的关照下,女性身份得以认同,城市为女性意识的崛起提供了现实的舞台,大量知识女性、职业女性游弋穿梭于各种平台之上。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绪论中说道:“两千多年始终蜷伏于历史地心的缄默女性在这一瞬间被喷出、挤出地表,第一次踏上了我们历史那黄色而浑浊的地平线”。[1]从文学领域看,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女作家作为一个性别群体的文化代言人浮出历史地表,从此便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价值多元、文化失范的时代语境给予了女性自身创作及作品形象塑造以无限生机。
然而,女性文学中女性自我意识的建构,其发展形势却崎岖坎坷。在男权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男性这个性别群体一直在书写着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男性光辉身影的背后,女性却一直处于历史的阴影之中。叶舒宪在《性别诗学》中写道:“在社会活动中,女人的主体身份乃至她与自然的关系,都主要是通过男人实现的,一则表现为她分享并占有男人改造了的自然,二则是她对自然的认识和态度,总是以男人的意志为转移。”[2] 在传统文化思维中,女性个体只是作为种的延续中的一个环节而偶然存在,并没有她自身的目的和价值。在几千年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度下父权文化渐渐地被人们所认同,历史、社会、文化仿佛都已先在的决定着女性的角色,女性在现实中扮演的各种角色:无论是作为母亲、妻子还是作为女儿,全都是以男性为依托。而长久以来女性被动地接受这一切,更可悲地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枷锁使女性想要突破自我,真正建构起属于自己的一方世界,困难重重。澎湃的创作激情,急欲表达的女性意识,都无法掩饰女性文学作品中流露出的父权文化对自己的影响。一方面女性作家用写作这种形式突破着男权话语所建造的精神堡垒,另一方面她们又处在传统与现代、边缘与主流的夹缝之中,游弋徘徊。观察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女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大多保持着在场的沉默。他们的黯哑,主导话语的缺失,使得女性的声音得以凸显,这或许是女性作家张扬自我意识的战略选择。然而,这种这种叙事姿态,使女性作家们在文本创作中越走越远,以至于到达了绝望的边缘。向往自由,无拘无束的生命形式,使她们拒绝回归传统的女性,然而城市文明所潜在的对人的异化,又使她们前进的脚步看起来是那么摇摆不定;拒绝传统,又无法融入现代:女性文学陷入了两难与尴尬的境地。
立足于女性自我的生命意识是女作家们的创作基点,如何在这个基点上完成自己的使命,实现超越将是她们共同面对的目标。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著作《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说“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3],“一间自己的屋子”即代表女性写作的独立姿态以及文本所体现的女性独立的主体意识。然而,与男性确立主体性的途径不同,尊重自己的内心体验,进行深层次的“自我发现”,无疑是女性确立自我的有效途径。本雅明曾指出:“女性”一词不是仅仅代表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缺乏与否定,而且也代表着获取主体经验的不同途径,那就是“自我发现”。这一词蕴涵了一个与女性心灵空间相关的隐喻,即不再被动的等待,而是通过寻求一种与欲望之间建立的自由关系,并在与他者的差异中获取自由。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不仅实践了独特的话语言说,同时也在努力完成“自我”的主体性建构。
二、女人的1.0与3.0之别
作为有着军旅经历的现代女作家,文清丽的小说创作大多以部队生活为题材。而不同于大部分女兵的出身背景,来自农村的文清丽在笔触中有着一种女性独特的敏感细腻和一丝凝重。文清丽的创作喜欢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产生有一种“亲历者”的效果,仿佛决意要把读者带到她的生活现场,放弃作为旁观者的审视,而带上强烈的表达生活的渴望,进入生活的中心,以特别动人的温存态度表达出自己对生活的惊喜与热情。在其近多半的以都市女性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中,文清丽在保持了自己一贯的细腻之外,更多了对人物的多层面剖析,冷静而客观,挥洒自如。
在其中篇小说《女友的1.0时代》中,作者以“我”的视角,叙述了主人公卓乐的一段人生,一个女教授寻找爱,渴求被爱,最终失去爱的过程。虽然小说全篇都围绕着卓乐努力走进婚姻殿堂而展开,“我”的作用似乎只是作为小说叙述者以及帮助好友解决个人问题,但是作者在刻画“我”这个人物形象时,无疑是将其婚姻家庭的美满状态,作为凸显卓乐人生之不幸的重要工具。“我”与卓乐,是一种帮助互动关系,更加是一种对比参照关系,“我”与丈夫的相处画面、家庭温暖的场景,都成为反衬卓乐孤独寂寞的强音。“我”去卓乐家做客,丈夫两次打来电话催促;“我”下班后丈夫接“我”一起去赴卓乐的邀约;“我”与卓乐打电话联系时正巧赶上一家三口约好去逛公园;风雪中“我”被丈夫用车送去上班,而卓乐为了讨好男友,冒着大雪骑车送男友的儿子上学,等等。事实似乎就像卓乐所说的那样,“在高科技年代里,你的生活已经升级到3.0了,我还在落后的1.0时代。”到后来,卓乐终于找到了认为属于自己的理想伴侣方磊,并且在其他人眼中看起来,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以至于之前对卓乐大有意见的丈夫,都不禁说:“卓乐变了,真的没想到,她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真让人难以想象。”然而,在看似就要走进幸福的关键时候,命运无情地开了一个大玩笑,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夺走了方磊的儿子,也夺走了卓乐就要到手的“幸福”,而卓乐也随之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原因是她“怕自己再也回不到那些没有爱的日子了,……那样的日子我一天都没法过了”。
从表面看,导致卓乐人生悲剧的原因,有其性格的某些因素以及命运的偶然性。然而,如果没有最后的那场意外,卓乐顺利地披上梦寐以求的婚纱,是否就是一个童话故事般的结局?答案或许是否定的。卓乐是悲哀的,原因并不在于其缺少婚姻的一生,而在于她始终没有爱自己的能力,“我”也不一定是真正幸福的,因为“我”的幸福从某种意义上并不取决于“我”,而维系在丈夫、婚姻之上。“我”与卓乐从本质上看,都将女性全部的关注点集中在男性身上,对自身价值的评判也全部取决于男性对自己的肯定之上,而真正源自于内心体验的呼声却几不可闻。卓乐与“我”的区别只在于,卓乐更加缺乏自我的主体意识,而依赖男权话语。从上大学起就是文学系的高材生,被大家一直推称为才女的卓乐,最大的愿望却是想当一个小鸟依人、“绯闻缠身的女人”,甚至会怕旁人瞧不起自己而精心营造出自己有男朋友的假象。成年以后,已经是副教授的卓乐为了寻找一个“具有完美的男性气质的人”,迟迟拖到三十七岁还待字闺中,而自己“为什么考研,为什么要考博”的原因竟只是派遣寂寞,“让时光快点过去”。认识了方磊之后,卓乐又一反之前女教授种种的挑剔古板、不近人情的毛病,全心全意对方磊好,不但“像研究课题一样”地学习做菜,甚至为了方磊儿子的学业,“一向清高的她,竟然容许领导把那双长毛的手放在她的大腿上”。所以在最后方磊儿子出现意外的时候,卓乐才会万念俱灰,选择自尽。卓乐将自己的生命价值构建在男性权威之上,从男权文化的标准中审视自己,而从未将自己作为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进行考察,是女性主体意识匮乏的悲哀存在。
反观“我”这个形象,虽然在作品中是作为卓乐的参照物而出现,但却更加反映出了作家潜意识中的男权文化思想。同样是知识女性的“我”,在全国第一的大报社任职,有夫有子,是卓乐眼中的“女人的3.0时代”。然而“我”的喜怒荣辱又何尝不是时刻维系在丈夫身上。“我”会因为陪女友过夜而担心丈夫生气,特意趁早赶回家讨好;会因为同事羡慕自己下班有丈夫来接而“得意半天”;会在吃饭的时候小心翼翼地观察丈夫的情绪,在留意到丈夫看对面漂亮女孩子时“狠狠地踢他一脚”;会听到丈夫夸赞卓乐转变性格后,问丈夫是否嫉妒;也会因为下雪天坐在丈夫车里看着卓乐,内心在想“我比她幸运”。如果说卓乐是作者有意安排塑造的悲剧形象,那么“我”就是另一个表面幸福美满,实际上拥有婚姻家庭的“卓乐”。同样是将自我的主体性抛之脑后,以传统文化眼光要求自己、评判自己的知识女性形象。
三、结语
新时代的女性作家在尝试进行女性地位、女性意识的探讨的同时,在亟不可待地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渴望着自由却总是迷失其中,找不到正确的方向。在努力叛逃男权文化的束缚时,却总是兜兜转转,可以轻易尝试放飞自己的身体,却没有那么容易使潜藏于意识深处的父权阴影消失殆尽。女人的绝望与悲剧,并非单纯的知识与社会地位就可以改变。如何真正关注自我的内心体验,认识自己的精神需求,建构起属于自己的主体堡垒,才是女性解放自己心灵枷锁的良方。
注释:
[1]孟悦、黛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 5 页。
[2]叶舒宪:《性别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版,第 46 页。
[2]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王还译,三联书店,1989 年版,第 2 页。
参考文献:
[1]文清丽:《女友的1.0时代》,《百花洲》2007年第5期。
[2]叶舒宪:《性别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版。
[3]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
[4]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王还译,三联书店,1989 年版。
[5]孟悦、黛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作者简介:宋铖铖(1988.8.16-) ,女, 河北省保定市 河北大学文艺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