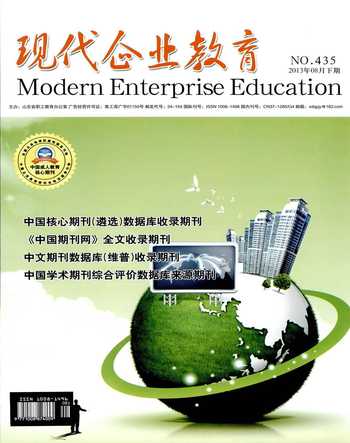米哈伊尔?普塞洛斯的教育经历和贡献浅析
2013-04-29赵法欣
赵法欣
摘 要:米哈伊尔·普塞洛斯是11世纪拜占廷帝国的著名学者和文化精英,他早年曾接受而系统的教育,对希腊罗马古代传统和基督教神学两方面知识兼收并蓄,这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和政治生涯带来诸多益处。与此同时,普塞洛斯成年之后还积极办学,与许多同时代的学者一起推动了拜占廷帝国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拜占廷帝国 米哈伊尔·普塞洛斯 中世纪教育
米哈伊尔·普塞洛斯(Michael Psellos)是拜占廷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学者,在文化学术诸多领域皆取得辉煌造诣;比他稍晚一些的同时代史家米哈伊尔·阿塔里亚迪斯称普塞洛斯“在学问方面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人”,①而安娜·科穆宁公主更是盛赞他“达到了知识的顶峰”②。这样广博的知识自然是因为普塞洛斯自幼接受过系统而良好教育的结果,同时普氏也身体力行为当时拜占廷帝国教育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一)普塞洛斯的个人教育经历
普塞洛斯天资聪慧,自幼在纳尔苏修道院接受启蒙教育。普塞洛斯5岁时母亲便把他带到老师那里开始上课,对小普塞洛斯而言,学校的课程“不仅简单而且比任何其它儿童游戏都更能够吸引他”③。普塞洛斯在学习中找到了乐趣,同时也激发了他日后研习文学的热情。到了8岁那年,就普塞洛斯日后学习方向的选择问题,众多亲属的意见与普塞洛斯自己的想法不同,因为他一心想要投身于文学研究。最后还是他的母亲力排众议,坚决站在自己儿子的一边,支持他的决定。根据普塞洛斯在其《悼母文》中的回忆,他的母亲塞奥多蒂因为在梦中得到一名修道士(另一个版本说是圣母玛利亚)的启发而最终决定让普塞洛斯专心学习文学。④
进入青少年阶段以后,普塞洛斯从16岁开始跟随当时的大学者约翰·马乌洛普斯(John Mauropous)⑤和尼基塔斯(Niketas)学习修辞学,⑥年纪稍长后又跟随法学权威约翰·克西菲林诺斯(John Xiphilinos)⑦研习法律。⑧至于某些自然科学的领域以及哲学,据普塞洛斯自己讲他基本上依靠自学。普塞洛斯在其《编年史》中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求学经历,显示出他当年所涉及的领域是多么广泛:
那时我年方25岁,正在专心研习基础性的学问。我的学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通过修辞法训练语言能力,将来要做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同时通过学习哲学升华我的思想。我很快便充分掌握了修辞学技巧,可以分辨出一个论断的中心思想,进而将它与我主要的和次要的观点有机联系起来。这样,我在这门学问面前变得不再畏惧,亦不再像孩子一样对每一项原则亦步亦趋,甚至我自己还做出了一点小小的贡献。随后我开始学习哲学,彻底掌握了推理的技巧之后,包括由原因推导结果的演绎法和由结果总结原因的归纳法两种,我开始转向自然科学,希望通过研习数学获得对哲学而言属于最基础性原则的知识。⑨
后来由于经济原因,普塞洛斯不得不离开家乡,远赴异乡求职。他姐姐去世后,普塞洛斯返回君士坦丁堡,重新专注于自己的学业。
在普塞洛斯的成长道路上,对他影响最大、相互关系最为亲密的一位老师,非约翰·马乌洛普斯莫属。普塞洛斯自十几岁时便开始在马乌洛普斯的私人课堂中学习,直至1037-1038年前后方才离开马乌洛普斯的学校,师徒二人从此被迫分开。11世纪30年代末,马乌洛普斯隐退至修道院中,而普塞洛斯则离开君士坦丁堡开始了自己的任职生涯。但是他们二人之间始终保持着相对频繁的书信往来。在这段时期内,普塞洛斯和马乌洛普斯师徒二人不仅来往密切,而且还在文学和政治领域通力合作。⑩普塞洛斯在一篇赞扬性的演说中流露出对昔日恩师马乌洛普斯的仰慕之情,“在我很年轻的时候便与这个非凡的人物走得很近,因为我对教育的渴求被他点燃,从他那渊博的知识海洋里获得各门学问养料的滋润。”B11
总之,普塞洛斯的教育经历符合一般拜占廷人受教育的基本特征,与此同时又具有自身的一些特色。
(二)普塞洛斯教育经历的特点
普塞洛斯早年的教育经历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普塞洛斯的兴趣遍及多个学科,涉猎广泛,这是他教育成果的最显著特色。据他自己讲,他10岁时便能够背诵《伊利亚特》并能对其娓娓道来。“我并不只是简单地学习文本,包括修辞格、词汇、比喻以及句法结构上的和谐都要涉及”。B12这一方面说明普塞洛斯智力非凡、记忆力超群,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普氏在接受初级教育是便注重各门知识的学习。
在此基础之上,成年之后的普塞洛斯学术领域极为广博,涉及神学、法学、历史学、地理学、哲学、伦理学、修辞学、考古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几何学、医学、气象学、自然史和农学等多个领域。B13更加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他在几乎每个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造诣。拥有这样的知识储备,普塞洛斯便可以在写作时涉及某个学问的时候达到信手拈来的程度,比如他在《编年史》中对于占星术的论述,对于历史学与修辞学关系的辨析,以及对于某些哲学问题的阐释、对某些哲学派别的评判,都显得极为专业。另外,普塞洛斯还十分强调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了解精神和物质世界。他在《编年史》中不惜笔墨记述了自己如何学习各门知识,并且在它们之间找到联系的纽带和相互促进的动力。B14
其次,古典传统和基督教思想在普塞洛斯身上有了很好的结合,这应该是他多方面地吸取知识的结果。对于一位中世纪的拜占廷学者而言,我们在普塞洛斯的作品中见到基督教神学的痕迹,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其《编年史》中随处可见普塞洛斯对于古典作家的引用,如《荷马史诗》和修昔底德的作品等。此外普塞洛斯在书中还多次提及占星术等古代多神教知识,这也是他醉心于古典文化的一个表现。
上述特点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普塞洛斯的老师马乌洛普斯的影响。马乌洛普斯是11世纪前半期最伟大的拜占廷学者,他为我们留下的作品包括诗歌、书信、布道词、宗教法规以及圣徒传记等,他的这些作品曾经提及《圣经》、教父作品、伊壁鸠鲁、品达、普鲁塔克和柏拉图等多方面内容。B15马乌洛普斯对普塞洛斯在学术方面的影响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哲学上将物质层面作为通往精神层面的途径,这是普塞洛斯哲学的一个典型特点,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马乌洛普斯身上找到原型。再有,普塞洛斯坚持修辞手段与哲学相结合的必要性,同时用美丽的语言来表达作者思想,这些主张应该都是受到了马乌洛普斯的影响。B16普塞洛斯正是在老师的影响之下广泛涉猎希腊、罗马古代文化和基督教神学的各种知识,成为教、俗学问兼通的大学者。
最后,“学而优则仕”,是普塞洛斯良好教育的最大收获。他正是依靠着由系统教育得来的知识技能最终得以涉足仕途,并且步步攀升,最后成为11世纪拜占廷政坛的风云人物。普塞洛斯甚至在其《编年史》中炫耀式地写道,他因为演说技能出众而进入宫廷,并且担任君士坦丁九世皇帝的秘书;后来又因为与同样喜爱修辞学的君士坦丁·杜卡斯比试技能,两人的关系由是变得亲密起来。B17由此可见,在演说术和修辞学方面的高深造诣,甚至将他与某些拜占廷统治者的关系拉近,令他可以和拜占廷统治者近距离频繁接触,从而为他写作《编年史》提供了别人难以获得的珍贵素材。除此之外,普塞洛斯许多昔日的同学师友日后都成为11世纪拜占廷政坛或宗教界的领军人物,他甚至在1043年后返回君士坦丁堡之后向君士坦丁九世皇帝举荐自己的恩师马乌洛普斯,从而将后者引进宫廷为官。这种关系网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普塞洛斯在仕途的顺利发展,同时影响了他许多政治观念的形成。(三)普塞洛斯对拜占廷教育的推动作用
普塞洛斯在11世纪拜占廷教育领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与那个好斗、自负、咄咄逼人的文人普塞洛斯相比,作为老师的他倒是显示出几分温情,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个对学生充满爱心的普塞洛斯此时变得更加具有魅力。B18普塞洛斯开设私人课堂,前来听课的学生数量十分可观。其中不仅有君士坦丁堡本地的学者,还有来自西方(意大利)以及东方(阿拉伯地区)的人士。这些人不仅可以从普塞洛斯那里学习法律知识,更是可以涉猎所有古代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并且可以聆听有关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演讲。普塞洛斯鼓励学生勇于提问,他自己则竭尽全力对学生们的问题予以答复。普塞洛斯教学的目的,如他自己所言,“是要学生们摆脱那些‘世俗的习惯,促使他们全心投入各门科学,鼓励他们向往哲学,提高语言水平,并且关注自己的文风。”B191045年,普塞洛斯被任命为“首席哲学家”,这是专门为他设置的一个头衔。普塞洛斯还曾作为教师辅导君士坦丁十世之子米哈伊尔,普氏在其《编年史》中难以掩饰这种自豪的情感。B20
正是在以普塞洛斯为代表一批知识分子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情况下,拜占廷的高等教育在11世纪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整体而言,拜占廷的初级和中级教育体系在11世纪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课程设置基本保持不变,语法和修辞学仍然是各门课程的基础。学校类型仍旧以私人教师在家中开设的课堂为主,学生和老师之间形成一种类似于行会间流行的关系。B21然而这一时期拜占廷的高等教育却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首先,教育事业不再像10世纪(至少是10世纪中后期以来)那样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并且被国家严格操控。具体而言,那时的教师由国家高级教、俗官员构成,而他们培养学生的目的则是训练他们日后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续编》的作者在关于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 Porphyrogennetos)B22兴办教育的一段记载中,强调了这种功利主义以及教育事业在培育国家精英方面的重要角色。B23然而自从瓦西里二世皇帝(Basil II Boulgaroktonos)以来,大批学者开始放弃这种功利性的教育,着手兴办更加自由的私人学堂,这其中便包括马乌洛普斯以及普塞洛斯本人。
其次,在组成教师队伍的学者们当中,有很多人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中等阶层(如普塞洛斯和君士坦丁·利户迪斯),另有一些来自帝国其它省区(如马乌洛普斯和克西菲林诺斯),这便打破了10世纪那种由都城官僚贵族阶层垄断教师职业的局面。这种转变实际上也有助于自由化教育的展开,使教育活动不再像以往那样受到国家严格控制,同时也有助于学者们自由地研究各门学问。B24
最后,与上述两点紧密联系的就是,教育的方式和内容也有所变化。课堂不再仅仅局限于传播那些固定化的知识,教师们开始引入古希腊作家的和教父的作品,并且对这些文本进行解释分析。普塞洛斯自己讲授的课程便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包括语法、古典文献解析、修辞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学、天文学、音乐、物理学、形而上学和神学。B25除此之外,新式教育更加强调对于真理的探究,更加重视学生的原创性,强调他们的对话、辩论和煽动技能。B26普塞洛斯对于昔日同学和挚友尼基塔斯教学方法的评论,十分具有代表性,“他关于荷马、阿基洛户斯和品达以及其他诗人的知识是非常广博的,他不仅仅局限于一字一句的解释,或者停留在对表面意思的分析,而是可以深入到文字的深层次含义,进而发掘出不同作品那种不可思议的美感。”B27
注释:
① Michael Attaleiates, The History, translated by A. Kaldellis and D. Kralli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37.
② The Alexiad of the Princess Anna Comnena, trans. by E. A. S. Dawes, Kegan Paul, 2003, 5.8, p.133.
③ Psellos, Encomium for his Mother, 5b, in Mothers and Sons, Fathers and Daughters: The Byzantine Family of Michael Psello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A. Kaldelli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2006, p.60.
④ Psellos, Encomium for his Mother, 5c-5d, pp.60-61.
⑤ 拜占廷作家,公元1000前后生于帕弗拉戈尼亚,1075-1081年之后死于君士坦丁堡。马乌洛普斯曾经在君士坦丁堡开设学堂,担任教师,君士坦丁九世统治期间担任宫廷修辞学家,1050-1075年间出任尤哈伊塔都主教,最终隐退至君士坦丁堡佩特拉的先驱修道院中。马乌洛普斯曾作有一部编年史,但是因为政治观点而被销毁。他的讲演辞往往选择一些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为题。1050年被迫离开君士坦丁堡远赴尤哈伊塔任职后,马乌洛普斯专心于教规和圣徒传记的创作。他的演说辞、书信和讽刺诗中充满了生动的形象,并且积极地为古代作家(如柏拉图、普鲁塔克)进行辩护,称他们并非无神论者。他的演说辞同时还是我们了解拜占廷与北方各邻邦关系的重要材料。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editor in chief A. P. Kazhd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319.
⑥ Psellos, Encomium for his Mother, 6b, p.62; 15a, p.75.
⑦ 即君士坦丁堡牧首约翰八世·克西菲林诺斯(1064年1月1日-1075年8月2日在任)。克西菲林诺斯1010年前后生于特拉比仲德,他早年既来到君士坦丁堡求学,与马乌洛普斯和普塞洛斯等人关系密切。克西菲林诺斯被君士坦丁九世皇帝任命为君士坦丁堡法律学校的校长,但是在1040年左右失去信任,并于1050年与一班好友(包括普塞洛斯在内)离开君士坦丁堡,克西菲林诺斯从此成为一名修道士。1063年君士坦丁·利户迪斯牧首去世后,君士坦丁十世皇帝任命克西菲林诺斯继任牧首一职。约翰·克西菲林诺斯于1075年死于君士坦丁堡。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p.1054.
⑧ Ε. Κριαρá[KG-2][XC8月-26TIF], “Ο Μιχα[KG-2][XC8月-27TIF]λ Ψελλó[KG-2][XC8月-26TIF]”, Βυζαντινα, 4 (1972), p.56.
⑨ Fourteen Byzantine Rulers: The Chronographia of Michael Psellu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 R. A. Sewt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53, 6.36, p.173.
⑩ .J. N. Ljubarskij, Η Προσωπικ[XC8月-28TIF]τητα και το ′Εργο του Μιχα[XC8月-27TIF]λ .Ψελλο[XC8月-29TIF]. Συνεισφορá στην Ιστορíα του βυζαντινο[XC8月-29TIF] ουμανισμο[XC8月-29TIF], μετáφραση: Α. Τζ[XC8月-30TIF]λεσι, Αθ[XC8月-27TIF]να: Εκδóσει[XC8月-26TIF] Κανáκη, 2004, pp.74-76.
B11 Psellos, Enc. Maur., 150.194-196, 200-207, in Michaelis Pselli Orationes panegyricae, ed. G. T. Dennis, Stutgardiae: Teubner, 1994, pp.147-148.转引自P. A. Agapitos, “Teachers, Pupils, and Imperial Power in Eleventh-Century Byzantium”, in Pedagogy and Power: Rhetorics of Classical Learning, Y. L. Too and N. Livingstone,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77.
B12 Κριαρá[XC8月-26TIF], “Ο Μιχα[XC8月-27TIF]λ Ψελλó[XC8月-26TIF]”, p.56.
B13 Κριαρá[XC8月-26TIF], “Ο Μιχα[XC8月-27TIF]λ Ψελλó[XC8月-26TIF]”, p.59.
B14The Chronographia of Michael Psellus, 6.36-45, pp.173-178.
B15关于马乌洛普斯的生平和学术贡献,参见Α. Καρπóζηλο[XC8月-26TIF], Συμβολ[KG-3][XC8月-27TIF] στη μελ[KG-3][XC8月-30TIF]τη του βíου και του [KG-3][XC8月-30TIF]ργου του Ιωáννη Μαυρóποδο[XC8月-26TIF], Ιωáννινα, 1982.
B16 J. M. Hussey, Church and Learning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867-1185, New York, 1963, p.41.
B17The Chronographia of Michael Psellus, 7.A7, p.334.
B18Κριαρá[XC8月-26TIF], “Ο Μιχα[XC8月-27TIF]λ Ψελλó[XC8月-26TIF]”, p.111.
B19Psellos, De oper. daem., 151.转引自Κριαρá[XC8月-26TIF], “Ο Μιχα[XC8月-27TIF]λ Ψελλó[XC8月-26TIF]”, p.111.
B2020 The Chronographia of Michael Psellus, 7.C4, p.369.
B21 A. P. Kazhdan and A. W. Epstein, Change in Byzantine Culture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 1985, p.121.
B22马其顿王朝皇帝(945-959年在位)。生于905年5月17/18日,为利奥六世与第四任妻子邹伊的儿子,959年去世于君士坦丁堡。尽管君士坦丁七世早在908年既已被加冕为共治皇帝,然而却长期被排斥于最高权力以外长达几十年之久,先后经历了亚历山大、牧首尼古拉一世和邹伊以及罗曼诺斯一世等人的摄政,直至945年君士坦丁七世才开始独立统治。相对而言,君士坦丁在文化学术方面的贡献远胜于他作为一名统治者的贡献。在他统治期间有大量的文字作品问世,包括百科全书《论出使》和《农业志》,以及两部历史学著作《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续编》和《列皇纪》。除此之外,像《论帝国的管理》、《论军区》和《礼仪书》也都是在他的主持下编纂完成的。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pp.502-503.
B23Agapitos, “Teachers, Pupils, and Imperial Power in Eleventh-Century Byzantium”, p.176.
B24 Agapitos, “Teachers, Pupils, and Imperial Power in Eleventh-Century Byzantium”, pp.179-180.
B25Κριαρá[XC8月-26TIF], “Ο Μιχα[XC8月-27TIF]λ Ψελλó[XC8月-26TIF]”,p.109.
B26Kazhdan and Epstein, Change in Byzantine Culture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pp.123-124.
B27转引自N. G. Wilson, Scholars of Byzantiu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