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关注疫苗后遗症患者的困境
2013-04-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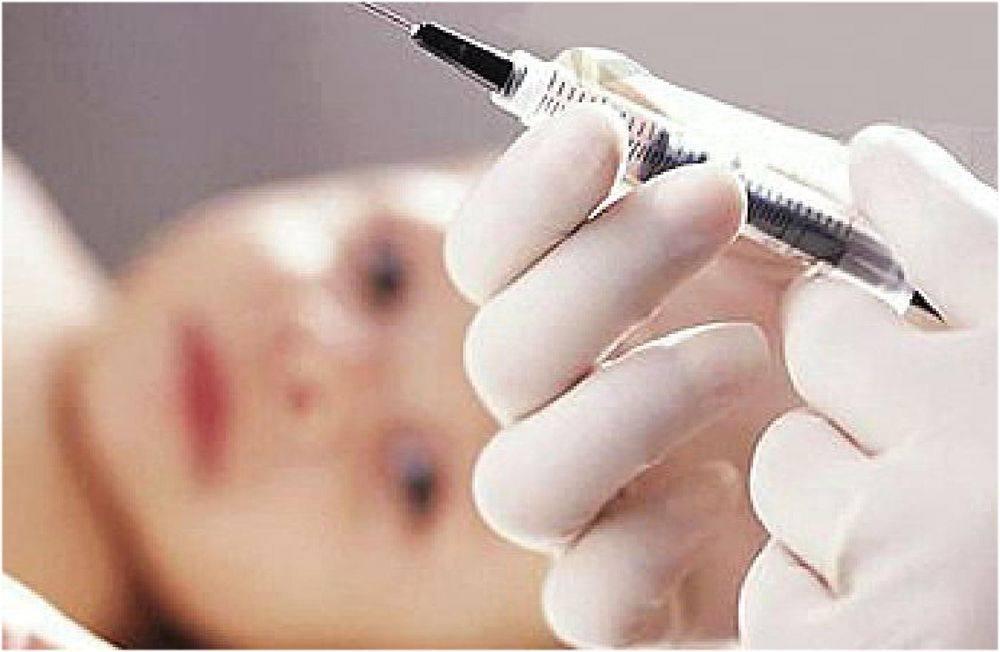

中国每年有超过1000个孩子患上各种疫苗后遗症。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也许这个数字微不足道,但对于个体乃至家庭而言,却是百分之百的苦难。而疫苗后遗症鉴定之难,再加上中国疫苗接种保障机制的缺失,更是让这些家庭陷入无尽的深渊……
7月的酷热阳光下,在广州市人流量密集的天河购书中心大门外,梁嘉怡静静地瘫在马路边一张破旧的躺椅上。与同龄人相比,这个已经12岁,但身高只有1.3米的女孩似乎已有多年没有发育。除了异于常人的瘦小身材外,她的双手双脚始终蜷缩着,看上去令人心悸。更让人悲哀的是,在过去10年时间里,她就像个木偶一样,对所有外界刺激全无反应。
梁嘉怡脚下摆放着个红色的募捐纸箱,每当路人往里面放进零钱时,她那神色悲戚的父母梁永立和刘雪云就会向对方点头致谢。而梁嘉怡总是偏着头,面无表情地斜视着天空,眼里只有虚无和漠然。梁永立一边轻轻拍着女儿胸口,一边悲哀地说,导致女儿悲惨身世的罪魁祸首是十年前的一针乙脑疫苗。
噩梦
在当年接种乙脑疫苗后袭来
2001年夏天,梁嘉怡诞生于广东江门市灵镇村的一个普通人家。依靠在当地农贸市场里贩卖水果,梁永立和刘雪云维持着不算糟糕的家庭生计。在出生后两年的健康生涯中,梁嘉怡曾经给终日劳苦的父母带去了诸多欣慰。“她从小爱笑,能走路之后,成天不停地蹦蹦跳跳”,梁永立痛苦地回忆着女儿往昔的快乐时光。他至今还记得,女儿在两岁的时候,就能自己剥开龙眼吃了。在梁嘉怡为数不多的照片中,其中一张留下了她活泼可爱的身影:身穿粉红色裙子的她赤脚站在一丛竹林前,手握一朵鲜花,脸上流露着俏皮的笑容。而多年后,这张照片成为了她瘫在街头募捐的可怜凭证。
2003年8月15日下午,刘雪云带两岁多的梁嘉怡到江门会城医院下设的爱民诊所第二次接种乙脑疫苗。按照规定,每个接受疫苗接种的孩子都会有一个疫苗接种卡,上面详细记录下每次接种疫苗的种类和接种时间。此前刘雪云总是准时带女儿到诊所接种疫苗,在她眼里,这是预防孩子染上疾病最便宜有效的方式。但这天成为了这个家庭噩梦的开端。
在接种后带女儿回家途中,刘雪云发现,平日爱闹的女儿显得烦躁不安,“老是摇头晃脑的,问她话也不搭理。”当天夜里,梁嘉怡出现额头发烫,烦躁不安的症状。次日一早,有些不安的刘雪云带着梁嘉怡到村卫生站诊治。一位医生简单看了下病情后,告诉刘雪云,梁嘉怡“有点发烧,咽喉有炎症”。这听起来不过是儿童夏季容易遭遇的常见病。像往常一样,在医生给孩子打了针退烧针后,刘雪云便带着梁嘉怡回家了。
然而梁嘉怡的发热症状却并未减轻。两天后,她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开始出现反复抽搐、呕吐症状,神志逐渐不清,并最终陷入昏迷状态。8月19日,梁嘉怡被送进了江门市中心医院抢救。救治期间,梁嘉怡一度昏迷长达11天之久,院方数次下了病危通知书。当她在9月10日被抬出中心医院时,“就像个木偶一样毫无知觉”,梁永立说,女儿从那时开始便只能一动不动地躺着。医院诊断结果显示,梁嘉怡染上的是“重症病毒性脑炎”。病毒不可逆转地侵袭了她的大脑和肢体,从那时开始,她和她的家庭便沉沦在病毒的阴影之下。
悲哀
艰辛挣扎只为延续女儿麻木的生命
此后数年中,梁、刘夫妇倾尽所有,四处借贷,带着梁嘉怡多次到江门、广州的医院里求治。所有这些努力,只不过延续了梁嘉怡麻木的生命。
自从女儿病倒后,梁永立一家从此在痛苦艰辛的泥沼里挣扎。除了在当地开摩托车搭客外,不定期到广州“摆摊”就是梁、刘夫妇仅剩的经济来源。梁永立把他们一家到广州街头募捐的举动称为“摆摊”,作为一家之主,他用这个称谓来保持家庭所剩无几的尊严。在妻子为小便失禁的梁嘉怡更换裤子时,他久久地注视着女儿,黯然说道,“其实我们跟乞丐有什么区别呢?”
多年前,在自家老旧的砖瓦房墙体开裂后,负债累累的梁永立家人便栖居在邻近的兄长家里。这是位于灵镇村内一栋有个狭小院子的两层砖房,院子里有几株高大的杨桃、琵琶树。风和日丽的时候,梁永立和刘雪云常常将女儿推到树荫下呼吸新鲜空气。这是一个喜忧交织,令人动容的时刻——父母温柔地注视着沉默的女儿,一边为她按摩身体,一边对她说着从未得到过回应的话。
直到现在,只有当毫无前兆的抽搐发作时,梁嘉怡才会表现出怪异而强烈的生命迹象——她僵硬的手脚像着了魔似地剧烈颤抖,两眼翻白,面部也因为痛苦而扭曲。她经常在睡梦中遭遇这样的时刻,梁永立说:“好像是在告诉我们,她还活着。”
残酷
被“偶合”的鉴定结论击垮
梁永立想不明白,自己的女儿为何会突然染上如此恶疾。他坚持认为,摧毁女儿的人生的罪魁祸首,就是当年接种的那一剂疫苗。
“要不,为什么原本活蹦乱跳的孩子,接种之后就一病不起了呢?”在江门医院住院期间,曾有医生隐晦地向梁永立提及,梁嘉怡染病或许与注射疫苗有关。此后,这位满心猜疑的父亲开始长期向接种疫苗的诊所、当地疾控中心,乃至各级政府和卫生部门讨要说法。
2004年,由江门会城医院垫资委托的江门市医学会、广东省医学会,对梁嘉怡的病症进行了医疗鉴定,并分别于6月和11月出具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书中,有关专家通过描述接种过程、疫苗来源、发病时间、致病原理、同类案例等多类情况,均认定接种疫苗与患者病情无因果关系。江门市医学会称梁嘉怡的病症为“偶合重型病毒性脑炎”,广东省医学会也称,“患儿出现的神经损伤,是在目前医疗情况下不可预测和不可防范的偶发事件”。两级鉴定机构均对梁嘉怡得出了“不属于医疗事故”的结论。
“偶合”是在类似鉴定报告中出现最多的字眼。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医师刘大卫曾专门对此进行解释:“偶合症是指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接种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或者是患有某种感染性疾病,正好要发病,处于潜伏期,打疫苗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所以偶合症和疫苗没有关系。”
一旦被鉴定成偶合,就只能自己承担责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说:“写不写偶合,很多时候是良心判定。从科学角度而言,没有绝对的事,如果专家内心不想认定,就有一万条理由说它与疫苗无关。”
在医院和各个政府部门间长期奔走之后,梁永立被残酷的鉴定结论击垮了。“我忙了两年,最终一无所成,感觉很心酸绝望”,他恐惧于女儿如何在早已赤贫的家境里生存。
2005年5月4日,梁永立骑着一辆黑色的永久牌自行车,沿着107国道,恍恍惚惚地孤身前往千里之外的北京上访。这位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民认为,遥远而陌生的北京是“能讨到说法的地方。”走时,他甚至没有跟妻子告别,以至于刘雪云曾一度到当地派出所报案。
在好心路人的接济下,一个月后,蓬头垢面精疲力竭的梁永立抵达了北京。这是一次盲目而又毫无意义的上访之行——他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北京游荡了几天,只在卫生部的信访处获得了一次短暂的接访,接访人员告诉他,会将事情交有关方面跟进。
当他又花了大半月骑自行车回到家乡时,在刘雪云眼里,已“跟叫花子没有区别。”除了“瘦了30多斤”,这位固执的父亲一无所获。
疑问
同一病房四名同样遭遇的“偶合”儿童
唯一令他欣慰的是,在他外出上访时,一位名叫余同安的人找到了他家。余同安是距离梁永立家30多公里外的江门古井镇人,他与梁永立一样,是另一位怀疑自己孩子遭到疫苗伤害的家长。
余同安小孩的经历跟梁永立几乎一致。2005年3月11日,他已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余荣辉放学回家后出现发热、头疼、呕吐症状,而当天,镇防疫站工作人员刚在学校内为学生接种了“A群流脑疫苗”。村卫生所医生告诉余同安,这是接种后的正常反应,“多喝开水,过一阵就好了”。但余荣辉的症状却始终未见好转,这个原本健康的小学生反复发热、呕吐,有时还会莫名其妙地用力眨眼。一次上体育课时,余荣辉再次呕吐,随之晕倒在地。
到6月初时,余荣辉被送进了新会人民医院。此时这名男孩高烧不退、肢体不停抽搐。当他在两天后被转入江门市中心医院抢救时,已经陷入昏迷状态。跟梁永立一样,余同安也多次接到了院方的病危通知书。一个多月后,顽强生存下来的余荣辉出院了。医院对他的诊断结论是“重症病毒性脑炎”。在悲痛的父亲眼里,此时手脚萎缩变形,肢体扭曲,双眼斜翻呆滞的儿子“只不过是没有死而已”,余同安说,那时的儿子就像“鬼”一样。
在余荣辉住院期间,余同安发现,同一病房有另外两位病童也因注射了A群流脑疫苗而正在抢救之中。而当其中一名孩子因无钱医治而被家人带离医院后,新住进来的第三名孩子也刚注射过相同疫苗。从医生口中,余同安得知,所有人接种疫苗都面临一定风险:“只不过受到疫苗伤害的几率极低,只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分之一的可能。”
余同安认为儿子不幸成为了疫苗的受害者。而江门市卫生部门召集的专家组,乃至卫生部组织的专家组均认定余荣辉的病症与疫苗无关,将之视为偶合现象。但余同安难以接受同一病房住进四名同样遭遇的儿童还是“偶合”的现实。像梁永立一样,他也陷入长期借钱为儿子医治和在政府部门间奔走求告的困境中。当意外得知梁永立的遭遇后,他在灵镇村里挨家挨户地问到了梁家的家门。
10亿剂次VS百万分之一的悲剧
过去三年中,记者走访了国内多个省市,采访了近50名患上各种疫苗后遗症的残疾儿童的家庭。在他拍下的一组触目惊心的照片里,一个个与梁嘉怡、余荣辉有着相似命运的病童或坐或卧,他们的脸上都有一样的特征——痛苦与麻木。而他们的父母脸上,则只有绝望和悲哀。
“我的家庭已经彻底毁了。”梁永立说。他终日忧虑于自己和妻子年老体衰后,谁来照顾无知无觉的女儿。这样的忧虑也深藏在余同安心里,尽管余荣辉近些年有所好转——他现在能站立行走、能与人对话交流,甚至还能玩电脑游戏,但除了手脚仍然不能灵活运动外,他不时会毫无理由地狂躁不安,“动不动就会打人,甚至连他妈妈也打”,余同安说,儿子无法在社会上独立生存。
据统计,中国每年的疫苗预防接种达10亿剂次。即使按照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公布的疫苗不良反应概率是百万分之一到二,也意味着每年要有超过1000个孩子患上各种疫苗后遗症,留下终身残疾。郭现中说,“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也许这个数字微不足道,但对于每个不幸的家庭而言,却是百分之百的苦难。”在没有尽头的治疗中,巨大的精神折磨和昂贵的医疗费足以压垮所有家庭。除了生存在痛苦中的儿女,梁永立、余同安都有沦落街头,靠乞讨为生的经历。他们负债累累,曾被路人当成骗子嘲讽,也曾在城管的驱赶下仓皇逃离。“为了让儿女活下去,我们失去了做人的自尊。”梁永立说。
就在梁永立带着家人在广州“摆摊”时,一位名叫黄泽春的年轻母亲也找到了他。黄泽春的孩子郭海章尚未满一周岁,去年10月曾在广州医院服用过脊灰糖丸,数日后便出现发热、肢体乏力症状。两个月后,靠抢救夺回一命的郭海章被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诊断为“急性脑脊髓炎”。现在,这名幼小的孩童与当年的梁嘉怡一样,手脚就像没有骨骼支撑一样绵软无力,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而22岁的黄泽春,则正在恐慌中等待着孩子的鉴定结论。
谁来关注疫苗后遗症患者的困境
直到现在,横亘在所有病童及他们家人面前的巨大障碍是,他们必须拿到病症与疫苗之间存在关联,才能获得相应的赔偿。但根据中国《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如遇疑似异常反应,应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专家进行调查诊断;有争议时,可向市级医学会申请进行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再有争议,可向省级医学会申请鉴定。
“你觉得这样的设计合理吗?”余同安愤懑地大声问道,“他们都是一家人,能给你公正的鉴定吗?”他至今不知道当年为儿子提供鉴定的专家组成员的名字。在他多年的维权经历中,相关部门的推诿已是家常便饭。
通过互联网,余同安在全国诸多省市搜集到上百位怀疑子女遭受疫苗伤害的父母的名字。在他整理出的一份长长的名单上,这些父母都留下了各自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他们中几乎所有人的鉴定结论都是病症与接种疫苗无关。”余同安说。
包括梁永立、余同安在内,许多怀疑子女遭受疫苗伤害的家长纷纷采取到各级政府上访的方式讨要说法。对这些已被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只能获得少许救济甚至毫无救济的患者家庭,这似乎是最后一条可走之路。
过去数年中,梁永立、余同安曾多次到北京、省、市级相关部门上访,期间曾数次被截访、被限制人身自由。尽管鉴定结论至今未变,但这样的举动似乎有助于他们改善治疗和生活费用的紧缺境况——余同安说,过去三年中,镇政府曾给他提供过6万元的医疗费用。梁永立也曾获得过一定数额的救济款,但据他说,数额要比余同安少得多。
通过接种疫苗预防疾病传染无疑是有益于社会的举动。据了解,对疫苗不良反应的损害救济,全球已有诸多国家立法。在美国,根据该国已实施多年的《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案》、《疫苗伤害赔偿程序》,无论是个人接种还是群体接种,只要怀疑伤害与接种的疫苗有关的受害者都可申请疫苗伤害救济。在日本,政府也从立法层面设立了专项基金,可向受疫苗损害的被接种人给以补偿。
与之相比,中国的疫苗接种保障机制却缺失——虽有《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并规定“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具体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但实际上,由于缺乏细致的法律条文支持,且地方往往没有具体补偿办法,使得陷入困境的家庭一筹莫展。谁来关注疫苗后遗症患者的困境,是应该纳入相关部门的议事日程了!(据《南都周刊》)
编辑/吴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