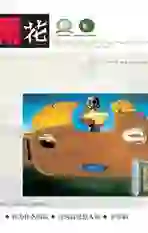永远的阳光
2013-04-22刘志成
刘志成
还有什么能宽过母亲泪水的河?
还有什么能高过母亲伫望的岸?
感到有人在耳边轻轻呼唤……睁开惺涩的睡眼,挣扎着坐起,看见母亲正站在床前,向前倾着腰,一手搭着床沿一手按在我的额头上,郁郁地看着我。由木格窗棂横浸到室内的阳光,正晶莹地倾泻在母亲肩上。我发现母亲本来就沟壑簇叠的额头又添了几道细细的皱纹,密密的一层汗点儿浸出,如水晶球在阳光中晶晶泛亮。一头稀发灰白灰白,垂下两腮,但怎么也遮不住一脸的爱怜与焦虑。气管炎缠身的母亲唿哧唿哧的粗喘,浸泡在斜浮的阳光中,波光粼粼地振荡。听着那干瘪得没有一点韵律的喘息,我的心扩展成了一片泪水的海……
母亲的目光像阳光流淌,开放的忧伤,岂止是苍茫,岂止是把怜爱种子样植在我灵魂的黄壤,冷寂地绽放。我是土地的背叛者,但在远离故土的另一座高原,始终走不出母亲比黄连还苦的泪光。被母亲的眼睫毛渐渐收紧的远方,人群柱子一样行走的远方起伏着一种怎样的温柔呀!那是我今生最崇拜的诗歌。我这个飞不起来的儿子纸上的文字比起她的诗,显得多么苍白。比如我在孩提时,常猝不及防地晕去。听姐姐说,脸色苍白的母亲总抽抽搭搭地一手将我紧紧搂在怀,一手掐着我的人中穴,悲呼着我的名字……真不知道,母亲那些随风而逝的泪滴,是如何在岁月的铜镜中留下真实的幻影?尔后又如何塞满我一个个梦幻或忧伤的夜晚?后来同一位医生朋友谈起童年里的昏晕,朋友说我那时是因营养不良而缺钙抽搐。不知儿时的晕去会令母亲怎样的心急如焚?怎样的痛楚如蜇?但每次醒来,泪珠润慰双颊的凉凉惬意,母亲绵白的脸上溶化郁结后绽放的一丝笑意,却像这悄悄漫进屋的阳光,以张扬的活力柔和着我的心。
穿过母亲滑落的清乳般的目光,我看见了窑洞东墙上贴的“巴黎教堂”图(那是我几年前从鄂尔多斯带回来的。画已被水气熏得陈旧,不知母亲为何没有撤换?)。在五月柔和的阳光中,画的缥缈而又真实的颜色,流淌着美学意义上的阳刚。我的眼眶又开始湿润。母亲。母亲。还记得你牵着我送我入学的第一天吗?疯惯了的我眷恋着鸟的歌蝶的舞,鼓动起两三个小伙伴逃离了校园,摇曳着一头的蓬草在明澄的野外整整享受了一个下午的心灵迷醉。当母亲知道这事后,高扬的手掌重重地落在了我裸在留裆裤外的屁股蛋子上。心里律动着那一巴掌的疼痛,恐慌地哽咽着还准备承受下一巴掌时,但那手却没落下来,母亲乌云密布的脸上早已是泪雨横溢了。之后,屁股蛋烙上的那一片耀眼的水晶红,悠悠地转成了青紫色。当时稚纯的我忖不出母亲为什么会火药味十足?为什么会一改往日浓浓的怜爱?直到现在,才在小儿绕膝爬肩的呀呀学诗里滋生的那一份恨铁不成钢的心境中,体悟出用扶正玉米的手扶我的母亲拳拳的苦心。
成儿,你好点了吗?喝点米汤吧。母亲柔柔的在阳光中游泳的音波,使我猛然间回过神来。母亲正转身从桌上拿起一小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阳光蓬蓬松松,漆在母亲额头的纹路上,弥散着忧郁的气息。尽管横了一扇窗,我还是心酸地看见母亲泪水结成的琥珀风样一闪穿过阳光,焚烧成襟子上几摊玉质的湿渍。
还有什么能让我们遍处鳞伤的内心生动起来?
还有什么能让我们懵然迷离的忧郁迈向春天的路途?
所有的声音此刻都变成了母亲唿哧唿哧的粗喘和迈向炕头的嚓嚓声。我作出一脸的轻松,接过小米粥喝了起来。我的委顿已潮湿了母亲满含语言的眼窝。除了塞满真实的谎言,还有什么能使母亲从沧桑和心疼中走出?我是一座陷落在远方的城。是母亲虔诚的目光遥遥的感召和呼唤,我和我的影子,从远方羞愧地回来了。一路的颠簸与风寒,使我浑身软得没一点劲,头晕乎乎的仿佛要爆炸,一吃点东西,肚子里的肠儿翻江倒海,直往嗓眼涌。
泪花中,屋顶矮了下来,阳光爆溅如受惊的鸟,在母亲的白发上跳上跳下,无声地荡漾着。我一鼓作气地吮溜出了碗底。母亲的脸开成了一朵灿烂的花。掖好被角后,母亲拿着碗默默地到屋外忙去了。母亲经过门口时,把木板箱上放的一个千手观音瓷像带入了我的眼帘。阳光静静地流泻在瓷像上,闪烁着神秘莫测的光芒。瓷像观音的一双双手像蒙娜丽莎的目光,柔和着一种温馨的气息。此时,母亲的头颅,在观音的千手之上独自高昂。当这个秘密伴着母亲唿哧吻哧的令人窒抑的喘声向我飘过来时,我的心也正羞愧到了极点。母亲。母亲。还记得蒲公英样漂泊的我前年过年时拍你的几桢照片吗?图片冲出,有朋友翻看。这老婆婆豁牙皱脸挺有艺术味,你是从哪里找到这么一个好题材的?朋友指着图片上微笑的母亲问。我不禁心里一阵羞愧,为刚刚四十几岁的母亲过早地凋谢了应有的光彩而脸红成了颗柿子。岁月的沧桑把面容磨成了苍老,这就是母亲吗?现在,除了将一朵朵水晶的泪花开在五月深处,又能怎样?在母亲柔柔的目光里,我该怎样扶正自己的未来?该怎样穿越人生所有的门和路途,抵达纯洁神圣的文学殿堂?
还有什么能宽过母亲泪水的河?
还有什么能高过母亲伫望的岸?
母亲。母亲。还记得我读初二那年吗?因弟妹多,那时家里拮据得连学费也凑不出来了。在贫苦的包围里,父亲所有的努力都近乎无望。成儿,不是爹不供你念书……父亲植在玉米地中央的目光,布满了苦焦。除了一脉深埋在心底的泪水,还有什么能穿透我血液的渴望?我春天的面孔尽管蕴藏着深沉的忧郁,但想到家里为凑那几十元的天文数字而孤汤寡水的生活,就想应该像村里好多同龄人样出去半年八月揣把票子回来,滋补滋补家里。不,让娃念,我想法子。母亲的坚持,救活了我痛苦的目光。从此,在每年春秋两季农忙时,母亲天不明就起床,拿把镰刀,去四壁沙丘中割了盈细光直的柳条回来,用两根拇指粗的干短柳棒,将一头用柳皮绑好,把柳条夹在中间,吱儿吱儿地剥皮,以便编成柳制品换取我的庞大学费。每次周末回家,我默默地放下书包要帮母亲干,可母亲说什么也不肯,让我好好温习功课,我只好回屋打开课本,可怎么也静不下心,屋外吱儿吱儿的音乐和唿哧唿哧的喘息总是挤进耳鼓,撕咬着我的心。就是农忙季节,我常常夜里一觉醒来,还见母亲在如豆的煤油灯下编织。昏暗的灯火无声地摇曳着,像母亲内心最后的守望。躺在被窝里,往往听着那沙沙的编织声,父亲和弟妹们甜美均匀的呼吸,禁不住暗暗流泪,将枕巾濡湿了一大片。母亲什么时候才能无虑无忧地进入恬静的梦乡,好好睡上一个通宵觉呢?漆黑的夜里,只有我一双清明的眼睛在不停地走动。
母亲。母亲。还记得八岁的我为捡来的兔撅着牵牛花样的小嘴吗?那是冬闲时去沙丘中拉柴禾发生的事。一路上,母亲的故事把我带进了春天的意境。我在牛车上晃荡着,挂在丘尖上的冷阳在我的背上晃荡着,牛绳弯弯像母亲讲的故事一样美妙地晃荡着……母亲温馨的气息,时至今日仍洗濯着我漂泊中的嘈杂与迷离。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母亲土地一样的朴素拒绝了来自远方的诱惑和庸俗……记得沉在母亲故事中的我,猛然间发现前边的柳林中有只网住的肥兔。我的眼立即亮成了两颗黑色的玛瑙。我跳下车,飞快地向肥兔跑去。慌乱乱地解了拴在柳枝上的兔网,准备迎接母亲的微笑。成儿,快把兔送回去。母亲看着我比梅花开得还鲜艳的笑脸一脸严肃地说。我感到了一阵委屈,泪花禁不住顺着脸颊滚了下来。自己网的兔,心安理得。别人网的兔,我们不能要。母亲抚摸着我的头说。我默默流着泪盼着母亲改变主意,但泪水失去了效果。母亲牵着我的手向解网处走去。母亲朴素的大幕下,掩藏着怎样的生命经卷呀……
去年六月的一天,老家来人说:一千块钱,两个疗程,河北的平喘药,对气管炎效果很好呵。你妈身子弱,快给治治吧。亲切的泥土弥漫在屋子里如新月初照,故乡就那样静立在心里了。我立即将积攒的一千多元稿酬汇给家里,让母亲医病。可不久,读初中的小妹忽然来信说,南方洪水发着鬼祟的声音,惊慌的村庄在水中无助地飘摇。当母亲看了实况播出的画面,好几夜辗转反侧,肆虐的黄水和冷得发颤的灾民已移在她的心头……泪水指引中,母亲将我寄去的那笔钱背着父亲捐给了灾区……谁能读懂母亲的忧戚和忧戚中的冲动呢?在当今这个人人都为一己私利而蚕食的社会上,母亲的这种行为是愚抑或还是什么?我在黑夜的最深处看见母亲清澈的泪水和那颗温情的心在一起舞蹈……
肚子又开始翻江倒海。屋外忙活的母亲忙跑进来,一手搀了我,一手在我的背上轻轻地拍……当擦眼角的眼泪时,才发现母亲的胸前溅了不少污迹。她却毫不介意,只擦了擦,就扫了地上的污迹出去了……
就在母亲穿过那细如丝柔如絮的阳光团的刹那,我突然发现母亲的背上罩了层多彩的光环,晃动的背影突出于整个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