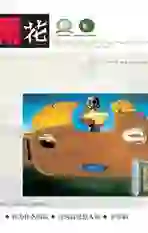官到高处惹人烦(外二篇)
2013-04-22游宇明
游宇明
曾国藩的所谓幸运是国家的不幸造就的。
任何俗话、成语几乎都可以被反证,俗话说,天上不会掉馅饼,但早年的曾国藩硬是接到过这种馅饼。想想看,一个湖南乡下的农家子弟,要钱没钱,要背景没背景,参加全国研究生考试只是侥幸过线,也没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按常理,这种人做国家公务员不会有太大的前途,然而,曾国藩却十年七迁,连升十级,42岁就做到礼部副部长,而且皇帝好像故意要让他过足官瘾似的,除了实授他礼部副部长,还要他兼任兵、户、刑、吏四部副职,使曾国藩成为当时兼职最多、年纪最轻的汉族高官。
只是有一点特别出人意料,副部长的椅子还没坐热,老曾就对官场生出了深深的厌倦之心。他在写给好友刘蓉的诗里说:“我虽置身霄汉上,器小仅济瓶与罍。立朝本非汲黯节,媚世又无张禹才。似驴非驴马非马,自憎形影良可咍。……”意思是说,我虽然如今在京师也算个人物,其实不过是朝廷一个无用的摆设,我既做不到像汉代汲黯一样直言进谏,又不甘心像张禹那样吹吹拍拍、谋取高位,只能像现在这样非驴非马地混日子,真是面目可憎。不久,他又寄诗给几个弟弟:“微官冷似支床石,去国情如失乳儿……径求名酒一干科,轰醉王城百不知。……”大意是说,我这样一个小官像支床的石头一样微不足道,天天想念家乡,犹如离娘的孩子。真想找几瓶好酒,喝个酩酊大醉,让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心情极坏时,曾国藩甚至想如陶渊明一般归隐田园。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他升任礼部副部长才十个月,即在家信中说:“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也就是说,他不喜欢官场那种繁琐庸俗又对国计民生毫无用处的生活,希望几个弟弟发奋努力,解决家里的经济困境,到时他打算辞官回家,一心一意侍奉家里老人。类似的话他说过多次,比如在给陈源兖的信中说自己“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给欧阳兆熊的信里说:“本欲移疾归去,不复尸素此间,重乖高堂之望……计期岁以内,终当蝉脱不顾,从子于万山中耳。”给江忠源的信中云:“计期岁内外,亦且移疾归去,闭关养疴,娱奉双亲。自审精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无为久虱其间,赧然人上也。”
自古以来,读书人最热衷的就是做官,孔夫子当年说过“学而优则仕”,他老人家还身体力行在鲁国做过三个月大司寇。曾国藩年纪轻轻位列正二品的副部级,其内心原本是非常得意的。他曾致信家人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后来他又给陈源兖写信:“不特仆不自意速化如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换句话说就是,不但我没有想到升迁得这样快,就是那些非常了解我的朋友,也不敢作这样超越常情的期望。为何居高未久就想辞职呢?
曾国藩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原则性强,晚清官场的腐败、敷衍使他身心极其疲惫。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书提到这样几件事。咸丰帝即位后,有人参奏陕甘总督琦善在任内“妄加诛戮”,“将雍沙番族刑求逼供,杀毙多名”。皇帝决定将琦善革职并交刑部审讯。刑部的人却有意开脱琦善,会审人员只寻“微琐细事”令其回答。刑部部长恒春甚至准备将举报人萨迎阿的四名下属当罪犯抓来,与琦善一起审讯。对此种公开违反律法的行为,满朝无人反对,只有身兼刑部副部长的曾国藩表示异议。他说:琦善虽然贵为将相,但既然是奉旨查办,自然应该以罪犯待之。举报他的几个司员职位虽低,但人家没有犯罪,岂有将他们抓来与罪犯对质之理?如果这几个司员因为举报琦善受到处罚,今后再有大员犯罪,谁敢过问?并且皇帝只命令会审琦善,没有命令兼审司员,如果一定要审讯司员,则需再请旨。因为曾国藩的坚持,恒春不得不取消动议。咸丰二年初,赛尚阿等因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过程中决策失误而被朝廷“交部议处”。朝中诸人都主张从宽处罚,曾国藩又“以军务关系重大,议处罪名宜从重者,不当比照成例”,提出不同意见。会议否决了曾国藩的建议,曾国藩不服,向皇帝告状,赛尚阿才被革职。做这一切,曾国藩完全出于公心,没有任何谋私之意,然而,他的公心触犯了其他官员的既得利益,大家像事先约好了的一致孤立、冷落他。“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加上后来向皇帝提意见,差点被皇上砍了头。在如此环境下为官,曾国藩的心情怎么会愉快?又如何会不生去职之念?
曾国藩最终没有退归田园,晚年封侯晋爵,极其风光,不是因为曾国藩面临的逆淘汰的官场环境有何改善,只是由于其时洪秀全占据江南大片河山,唯有曾国藩才能将其打败,使晚清苟延残喘。曾国藩的所谓幸运是国家的不幸造就的。
奕劻的反反腐败
生活中许多事物是相反相成的,有聪明就有愚蠢,有高尚就有卑鄙,有美丽就有丑陋,有阳光就有阴雨,有反腐败就有反反腐败。
晚清腐败的总头子当然是慈禧太后,整个天下的臣民和财物都是她的赃物,但若论起反反腐败来,庆亲王奕劻却是一等一的高手了。原因很简单:慈禧是没有人敢反她的腐败的(针对她的革命又当别论),而奕劻之上却有个慈禧。
说起来,慈禧还真反过一次奕劻的腐败。
奕劻的大儿子载振是个大色鬼。1906年,载振奉旨去吉林督办学务,途经天津时,当地官员陪他去看戏,一见到色艺双佳的京剧名伶杨翠喜,载振的双腿就情不自禁地发软。天津警察局总办段芝贵级别只相当于四品道台,却想做从二品的黑龙江巡抚,于是挖空心思拍载振的马屁,派人做杨翠喜的工作,承诺只要杨翠喜满足载振的性要求,就以十万银元相赠,杨翠喜应允了。载振自然也懂得投桃报李,通过父亲奕劻的运作,将段芝贵升为布政使并署理黑龙江巡抚。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载振准备将杨翠喜娶进家门时,监察御史赵启霖参了他一本。赵启霖不嗜烟酒,性格耿直,嫉恶如仇,参奏载振纯粹出于公心。赵启霖的奏折说:“朝廷锐意整顿,本来是好事,不料段芝贵乘机运动,攀附亲贵,逢迎载振,无微不至,以一万两千金于天津大观园戏馆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接着,他将笔锋一转,矛头对准奕劻父子:“以亲贵之位,蒙倚畀(倚靠信任的意思——游注)之专,唯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旬日以来,京师士大夫晤谈,未有不首先及段芝贵而交口鄙之者!若任用滥绾疆符,诚恐增大局之阽危,贻外人之讪笑。”奏折送到慈禧手里,慈禧批了两个字:“彻查”。
依当时的规矩,既然是“彻查”,得先交军机处议议。奕劻是领班军机大臣,因为牵涉到自己儿子,不得不回避一下,瞿鸿禨成了牵头主事的。经太后批准,瞿鸿禨拟了两道上谕,一道是“撤去段芝贵布政使衔,无庸置理黑龙江巡抚”;另一道是“着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确实查明,务期水落石出,据实复奏”。
事情到了这一步,奕劻丝毫不敢掉以轻心,立即与幕僚商量如何进行“危机处理”。有人提醒“先得将天津那边的事处理好”,奕劻立即叫门人通知徐世昌赴天津与好友袁世凯商议。袁世凯的意见是,段芝贵已臭如烂鱼,不能再出面,他觉得可以派自己的心腹、津榆铁路总稽查兼探访局总办杨以德去处理。这杨以德果然是个人物,摸一下后脑袋就有了主意,他将天津盐商王益孙叫来,叫王益孙揽下这一档子事。商人历来就喜欢攀附权力,面前摆着现成的好事,哪有放过的道理,王益孙将头点得像风中的柳枝似的。其后,杨以德又与载振方面联系,让其赶快将杨翠喜送进王益孙家。
手脚做完了,“彻查”的人才姗姗而来,对“皇家纪检委”的人奕劻也一一进行了打点,加上袁世凯的接待十分到位,没过几天,“彻查”的人就给朝廷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说:“卑职到天津以后,即访歌妓杨翠喜一事……天津人皆言杨翠喜为王益孙买去。当即面询王益孙,称名王锡瑛,系兵部候补郎中。于二月初十间,在天津荣街买杨氏养女名翠喜为使女,价三千五百元,并立有字证。再三究问,据王锡瑛称,现在家内服役。”故事讲到这里,结局我不说您也知道,上谕裁定:花花公子载振继续“为人民服务”,撤消赵启霖御史职务,罪名是“率行入奏,任意污蔑”。
皇家统治者都有两重性,一方面自己本身就是腐败的化身,无休无止地索取天下财富;另一方面为了一家、一族的长远利益,当下面的人手伸得太长,他们有时也反一反腐败,斩掉那么一两只激起公愤的贪手,慈禧自然也不例外,然而,她对载振接受性贿赂一案却处理得颠倒黑白。回顾案子的来龙去脉,我们会发现,相当一批官员充当了奕劻反反腐败的马前卒。徐世昌情愿为他跑腿,袁世凯、杨以德积极为其灭火。这也难怪,当时官员能否获得足够高的位置,靠的是上司的赏识,而非民众的推举。既然官场的上下级存在赏识与被赏识的关系,那么官场的拉帮结派也就在所难免。所谓“人脉”,其实就是互相帮衬的利益同盟的代名词。在人脉圈内,下级遇到麻烦时,上级固然会千方百计为之开脱;上级碰到麻烦时,下级也会挖空心思助其过关。
皇权下的反腐败寸步难行,反反腐败却轻而易举,腐败也就成了黄河的砂子,怎么淘也淘不尽。
端方的“逆向性贿赂”
对“性贿赂”这个概念,国人并不陌生,现在许多贪官就是享受“性贿赂”的老手。性贿赂包括性行贿和性受贿。所谓性行贿,就是有求于人者自己或委托他人给被请托者提供不正当的性服务。所谓性受贿,是指某些关键人物利用职权谋求不正当的性行为。性贿赂表面上只是床笫之欢,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权力、影响力的利益交换。一般说来,性行贿者处于弱势地位,性受贿者则相对强势。然而,晚清两江总督端方的“性贿赂”恰恰与此相反,他行贿的对象,无论是职位还是权力,都远远弱于自己,这种特殊的“性贿赂”,我将其名之为“逆向性贿赂”。
光绪32年(1906年),同盟会员孙毓筠受孙中山之命刺杀两江总督端方,不料事情还没开始操作,就被人告发了,孙毓筠被捕。按清律,谋反是大逆罪,不判凌迟处死和腰斩已是客气了,但端方不想杀孙毓筠。不想杀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孙毓筠的亲叔祖父孙家鼐是光绪帝的老师,时任正一品的武英殿大学士,每天可以在皇帝面前晃来晃去,能量大得很,得罪了他,绝对不是件好玩的事;二是清国发展到后期,官场腐败透顶,政治极其黑暗,民心思变,端方并不是个完全昧于大势的人,他早些年就主张维新变法,不知道以后是朝廷可靠还是革命党更可靠,不愿将事情做得太绝。抓住孙毓筠的第二天晚上,他特地派了江宁城的道员何平斋去向孙毓筠示好。何道员一进巡捕厅就对孙毓筠说:“好生生的,造什么反?幸亏遇到了爱惜人才的端午帅,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此时的孙毓筠还抱着为信念献身的念头,坐在那儿一动不动,连眼睛都没有抬一下。何平斋先是介绍了自己的身份,然后告诉孙毓筠,端午帅有意为他开脱,口供时千万不可提及“种族革命”等字眼,否则将有杀头之祸。孙毓筠没搭理他,还很不友好地“哼”了一声。何平斋没有计较这些,临走时扔下一句话:“端午帅纯粹出于怜才考虑,不可误会他同情革命。”
第三天,何平斋又来了。见孙毓筠还是坐在地上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微笑着说:“你倒是沉得住气,可有人快为你急死了。”孙毓筠抬头望了望何平斋,满眼写着不解。何平斋慢条斯理地从袖口掏出一张桃红信纸交给孙毓筠,孙毓筠一看“锦云”两个字,心脏就怦怦跳个不停。
锦云姓江,南方人,她与孙毓筠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当年长得楚楚动人的江锦云在北京的胭脂胡同做妓女,孙毓筠常去点她的单,通过一段时间的来往,两人已到难分难舍的地步。正在孙毓筠准备娶江锦云为妾时,端方横插一杆子,将江锦云接入了总督府,从此孙毓筠再也没有听到江锦云的消息。
江锦云的信写得非常缠绵,孙毓筠一看,雄性荷尔蒙立即涌满全身:“客冬一别,不图伯劳飞燕,遽尔分飞;似海侯门,相见何日?乃闻羁身囹圄,忧心如捣;铁窗风味,憔悴何如?当竭力营谋,藉酬旧谊,至盼乐天安命,勉抑愁怀;努力加餐,再图良会。”孙毓筠问何道台“能否见她一面?”何平斋点了点头,当天晚上,就将打扮得像仙女一般的江锦云送进了巡捕房。
接受了“性贿赂”,孙毓筠立即变了个人,一切听从何平斋的旨意。他在受审时居然说:“我早就想做和尚,端午帅如要保全我,我绝对要做和尚到底,妻儿财产一无留恋,任何党派概不闻问。”甚至将革命党的情报透露给端方:“革命有两个源流,一是政治革命,即不问政府是满人还是汉人,只求改良政治,富国强兵;一是种族革命,由黄兴、孙文领导。黄兴是个不怕死的角色,他们仇视午帅最力,一心要杀午帅。黄兴的党羽多数是湖南人,所以请午帅对湖南人要特别注意……”端方也果然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替孙毓筠抹掉了“大逆不道”的罪名,只判处其5年徒刑,而且这5年也没有让孙毓筠真的坐牢,而是将其安排在总督府后花园读书。
孙毓筠算得上是一条硬汉,否则,他当初也不会那样视死如归,只是孙毓筠有个缺点,他太好色。人一好色,别人就有机会实施“性贿赂”,“性贿赂”一来,硬骨头变成了软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