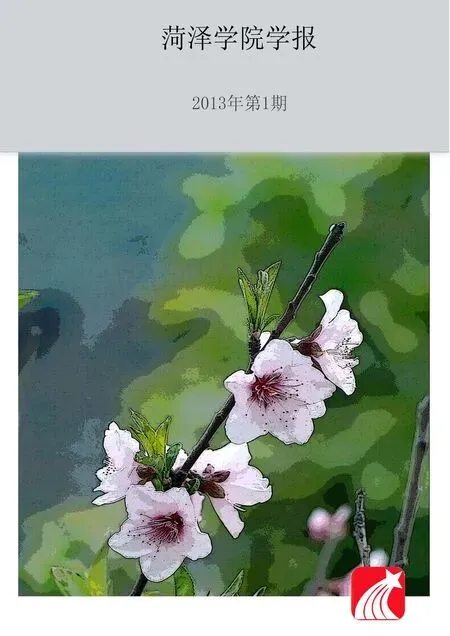解构与重塑
——从《玩偶之家》看易卜生戏剧的传播与接受*
2013-04-12黄婷婷
黄婷婷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文化经历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新文化运动者否定了中国的旧文化,但是要开启民智、反对封建旧思想、旧文化,就必须引进新的文化,一种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形式上都能承担起去除蒙昧、开启民智的历史责任的文化。于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将西方的思想文化介绍到中国,而在戏剧领域“西方各种戏剧流派,如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以及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现代主义流派,对中国新兴话剧产生了影响,但以现实主义流派影响最大。”[1]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以“伊孛生”之名将易卜生及其著作介绍到中国,之后胡适与郭沫若分别在《易卜生主义》与《〈娜拉〉的答案》中对易卜生做出了自己的理解。
在这场运动中,正式对易卜生进行介绍的是1918年《新青年》出版了《易卜生专号》,其中《娜拉》(下文统称为《玩偶之家》)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反响,一经演出引发了观众的共鸣,于是易卜生戏剧开始在中国扎稳脚跟,迅速传播。《玩偶之家》主要讲述的就是女主人因为忍受不了自己丈夫多年对自己的管制,于是愤然出走,随着门“砰”的一声关上,故事戛然而止,但是也正是这样的安排才能使读者进行多重解读,于是一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针对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对之进行了中国式的解读。
一、被解构的易卜生思想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者对易卜生主义进行了符合中国实际的解读,然而这每一次的解读都是对易卜生思想的一种解构,将易卜生思想进行了分裂与解体,然后将这些碎片重组,使之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殊不知我们所熟悉的易卜生早已不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挪威戏剧家了,而是被中国的文化逻辑和中国语境重新锻造出的易卜生。”[2]在新文化运动者看来易卜生已经不是原来的艺术大师,而是一个能够唤醒国民、开启民智的工具,就像陈独秀曾经说过的:“戏园者,实普天下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之大教师也。”[3]易卜生和他的思想已经被认定为是“天下之大教师”。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三种思想并存,但是最符合当时时代发展或者说最符合知识分子期望的是现实主义,新文化运动者将旧思想、旧文化一概否定,于是一些向内的东西被否定之后,他们就开始向外寻找能够适应运动发展的思想,于是胡适等人发现了易卜生主义并将他介绍到中国,并且根据他的几部作品对他的思想做出了自己的理解,那就是勇于批判现实的写实主义精神,虽然写实和现实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实质内容却是相隔甚远,前者是忠实于所见所感的写作手法,将其真实地表现出来,后者的写作手法是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以仅仅用写实主义对易卜生思想进行界定是片面的。而且在介绍的过程中,新文化主义者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思想大于形式,思想高于一切。虽然这是一个需要思想的时代,但是戏剧毕竟是剧本与舞台表演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所以在此过程中,思想与形式同等重要,但是“‘五四’是一个需要思想且必须产生思想的时代,因为‘思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表现”[4],于是观众在台下看到的更多的是演员们所讲的内容,而不是关注演员们的表演,而当时像胡适这样的介绍者还在洋洋得意,认为自己用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征服了、教育了大众,他们这样的做法在那个时代无可厚非,因为当时的中国民众被一种全新的思想唤醒,但是这种“唯思想论”就有待商榷了。
但是也有很多的新文化运动者注意到了这一点,洪深、闻一多、徐志摩、熊佛西等人都曾经指出过这个问题,洪深就曾尖锐地指出,胡适教人写西洋剧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将戏剧转变为思想传播以及改良人性的一种工具,甚至有的学者提出了“纯形”的审美理念,虽然这种观点有些矫枉过正,但是这也体现出一些新文化运动者对“唯思想论”的关注,虽然并没有起到很大的影响,重思想轻形式仍在继续延续下去。
另外,新文化运动者将易卜生作品中的思想也进行了重新的定义,或者说他们是“节选”了易卜生的思想,在易卜生晚年的作品中,如《野鸭》、《海上夫人》、《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象征主义、神秘主义的思想远大于现实主义,但是像胡适等新文化主义者对这些作品介绍很少或者是根本没有介绍,所以说五四时期对易卜生的介绍是不全面,是通过新文化主义者重新解构的。
二、重塑的易卜生思想
艾纳·豪根曾经对易卜生的文本做过如下的界定:“易卜生的每一部戏剧都是一个具有隐含意义的文本,这是作者或多或少有意识编制进密码的。读者只有对这些文本进行细致入微的阅读和研究才能打开密码。”[5]而中国的几位最先介绍易卜生作品的学者都犯了没有细读文本的错误,没有将易卜生文本中的隐秘思想挖掘出来,反而套上了中国思想的“外套”。
很多学者从自己理解的角度解读了易卜生和他的思想,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1923年鲁迅曾经做了一篇《娜拉走后怎么样》,对娜拉出走以后的生活进行了自己的解读,他认为娜拉出走以后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回去,一条是堕落,因为她没有赖以独立的资本,也就是钱,在这次演讲中,鲁迅首先对娜拉的出走表示了赞许,这说明她已经开始“启蒙”,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但是还有比启蒙更加重要的,那就是“立人”,娜拉的出走虽然没有后续,但是在鲁迅看来,她的结果只有两个,所以在此他更加关注的是妇女启蒙之后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妇女解放启蒙固然重要,但是一旦没有安身立命的资本,启蒙思想只能落为一句空口号。他曾经说过:“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的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为之可靠。”[6]所以鲁迅是从个人出发给妇女解放提出了一条从“启蒙”到“立人”的道路。但是应该看到,鲁迅对娜拉的理解放在了中国这一语境之下,他将娜拉想象成一个中国女性,从而设想这一“中国女性”出走之后将面临的种种困难,“这就好比把娜拉从“崇高自由的塔尖”拉进了“柴米油盐的天井弄堂”之中。”[2]这样的做法在中国的语境之下无可厚非,因为娜拉在中国已经成为了女性独立的代表、标杆,新文化运动者为易卜生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现实主义道路,用中国式的方式来解读娜拉。
胡适曾经专门就易卜生的介绍写了一篇名为《易卜生主义》的文章,他在文中大力赞扬娜拉思想的觉醒,摆脱了海尔茂的束缚勇敢地从玩偶之家走出,寻找了一条自我解放之路,而文中胡适对于娜拉那种抛夫弃子的行为,并没有持批判态度,反而赞扬这是个人主义的胜利,娜拉的出走是她向内寻求自我的解放,为社会的变革准备了一个新社会的分子。[7]在国外文艺思潮的发展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再到现实主义,最后是现代主义的一个线性的发展方向,而在五四时期,中国的文学思潮随着旧思想的否定,打开国门迎接西方思想,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思潮涌入中国,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承担着开启民智,启蒙思想的责任,要培养民众的社会责任感,首先必须让民众了解自己的价值,于是五四时期个人本位思想以及社会本位思想并存,而胡适对于娜拉的解释就是受了个人主义的影响,于是他鼓舞人们用个人主义思想冲破来自于社会的束缚,而这也是他为什么大力介绍易卜生的原因,胡适曾经在《易卜生主义》中提到:“发展个人的个性,须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7]娜拉的出走是个人意志的体现,而出走后就必须担干系,成为新社会的储备力量。
20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思潮已经广泛影响到了中国的文坛,而就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之下,郭沫若对于易卜生进行了一场现实主义的解读。1942年7月,郭沫若将自己对于娜拉的理解写成了《〈娜拉〉的答案》一文,在文中他不仅仅只限于对《玩偶之家》进行文本的解读,而是联想到了一个跟娜拉很相似的中国女性——秋瑾,秋瑾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著名的女英雄、女战士,而她的成长也是经过了娜拉般的抗争,起初她嫁给了一个纨绔子弟,过着没有思想没有地位的玩偶式的生活,但是她受到了《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文章的影响,开始觉醒,追求自我的解放之路,于是毅然出走,参加革命。由于4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抗战的胶着状态,所以现实主义思想在中国是最适合的,同时五四时期的个人本位思想由现在的社会本位思想所取代,于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学者就开始向现实主义靠拢,更加注重文学的启蒙作用,如果说娜拉给妇女争取了自由的地位,那郭沫若想通过这篇文章给广大的中国女性指出一条“出走后的道路”。
三、易卜生思想在中国的接受
易卜生一生一共创作过25部剧作,但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主要就是以《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社会支柱》为代表的社会问题剧,于是社会问题剧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并且在五四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些戏剧家受社会问题剧的影响开始将创作的视角转向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胡适就曾经创作过《终身大事》,而剧中的女主人公也以“出走”的方式来反抗家庭对自己的不公正的待遇,而且在剧中胡适喊出了“孩儿的终身大事,应该由孩儿自己做主”的时代最强音,他将关注的视角投向了青年男女的婚姻问题。同样题材的作品还有田汉的《获虎之夜》,剧中对家长的包办婚姻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家长的专横导致了有情人终难成眷属,上演了一场爱情的悲剧。另外还有像欧阳予倩的《泼妇》、郭沫若的《卓文君》,在这些作品中都表现出了青年男女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这种蛮横的干涉进行了反抗。同时还有一些剧作更具有革命性,比如说张闻天的《青春的梦》,就将青年人的爱情解放同革命相结合。同时还有剧作关注下层人民的生活,将他们在军阀、官僚和买办的压迫下的窘境表现出来,比如说陈绵的《人力车夫》、欧阳予倩的《车夫之家》等。在易卜生的影响之下,他们开始注意到了戏剧这种文学形式的斗争作用,在五四这个急需思想解放的时期,以胡适、郭沫若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利用戏剧创作启蒙民众思想,激起人们的反抗精神。
同时还应该注意到的就是,《玩偶之家》在中国的传播掀起了一场“娜拉式出走”的创作热潮,很多作家都模仿《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安排自己剧作中的主人公出走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反抗。欧阳予倩创作的《泼妇》中,女主人公于愫心与丈夫自由恋爱而结婚,当时两人都十分崇尚民主思想,主张一夫一妻,但是结婚后丈夫就从民主斗士转变为封建卫道士,开始想要纳妾,遭到了于愫心的坚决反对,而她的婆婆、小姑等人都十分赞成丈夫的观点,于愫心感到自己在家里孤立无援,于是决定离开这个让人窒息的家庭,并且还带走了孩子和丈夫要娶的小妾。另外一些作家还将青年男女的出走蒙上了革命的色彩,算是对这种思想的升华。
虽然这些剧作家在创作手法和技巧方面对《玩偶之家》进行了模仿,塑造了很多中国式的娜拉,而且将创作的视角转向了小人物的普通生活,希望能够从小事中反映出大问题,但遗憾的是他们的思想远远没有达到易卜生的高度,他们仅仅是反映问题,而不对这种社会问题进行细致的剖析,最终导致了人物形象过于单薄。
丹纳曾经在《艺术哲学》中提到,任何一个文学现象的发生与它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于是他提出了文学发展的三要素,那就是种族、时代、环境,其中在这三个要素中,时代可以说是影响易卜生思想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因素。将易卜生戏剧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是1918年在《新青年》中开辟的易卜生专号,而其中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妇女解放的话题。我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自晚清就开始盛行,一直延续到五四时期还长盛不衰,女性开始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她们积极地参与社会的变革,开始在社会占有一席之地,而一些学者、文人适时地将国外的一些优秀女性的事迹引入中国,更加促使了女性运动的高涨,以秋瑾为代表的一些新女性,更是成为当时中国广大女性的榜样,她们勇于走向社会,承担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大任。而就在女性运动高涨的时候,《娜拉》被引入了中国,娜拉一出现就成为文化偶像,成为广大女性竞相模仿的对象,因为在娜拉的身上她们很容易看到自己的影子,在那时虽然广大女性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到了一定的地位,但是还没有能够改变自己的婚姻状况,男尊女卑、父母之命还是存在,于是她们急需一个榜样帮助自己冲破婚姻的樊笼,于是一个被重塑的娜拉就此走进了中国民众的视野。
[1]孙庆生.中国现代戏剧思潮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2]万同新.论“五四”对易卜生戏剧的误读[J].剧作家,2011.
[3]三爱:论戏曲[J].党史资料丛刊,1980.
[4]季玢.20世纪中国先锋性戏剧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
[5]豪根.易卜生的戏剧:作者与观众[M].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79.
[6]鲁迅.娜拉走后怎样[M]//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胡适.易卜生主义[J].新青年,191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