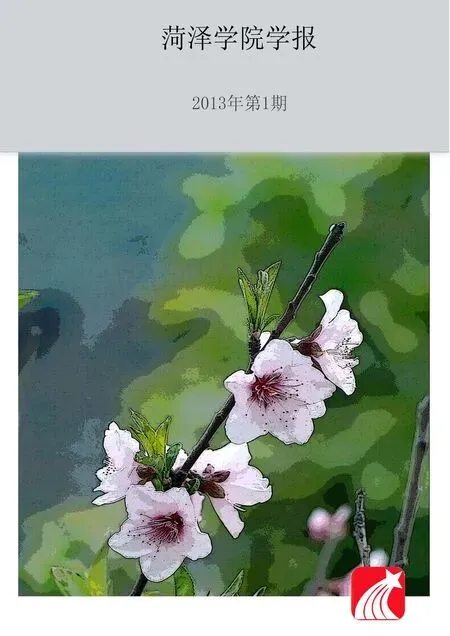接受美学视野下新版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阐释*
2013-04-12高日晖
高日晖,李 欣
(大连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接受美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范式,把文学研究转到接受者、读者这一级,认为接受不是被动的反映,而是作品意义的积极建构。文学本文只有被阅读、被接受才实现了意义的最后一环,才能称之为作品。接受美学视野下任何文学本文都具有未定性特征,存在着许多“空白”和“未定点”,这种“未言部分”就对不同时期的接受者提供了一个“召唤结构”,需要接受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进行创造性“填空”。当然不同时代接受者的阐释、接受又受到特定时代意识形态、文化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才形成了文学作品意义阐释的多元化局面。《水浒传》写成于明代中叶,从它产生之日起便拥有了大量读者,上至皇帝公卿,下至贩夫走卒都不乏“水浒谜”。明代批评家把它列入“四大奇书”中的一种。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水浒传》真可谓是空谷足音,它的出现给读者打开了一个崭新的阅读世界。历来的研究者在解读这一文学巨著的过程中,由于所处时代文化环境的不同,形成了《水浒传》主题接受的多元化局面。
一、《水浒传》主题接受的历史回顾
历史上的明代中后期是一个思想解放、个性觉醒的时期,这个时期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起来的《水浒传》受到了以李贽、袁宏道等当时名士为代表的读者的高度评价,说它表现了梁山好汉“诵义负气,百人一心。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1],把梁山英雄视为实现正义公平的社会良心,既肯定《水浒传》的忠义思想,又高度评价了它的艺术成就。托名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叙》也明确地指出《水浒传》是宋代遗民施耐庵、罗贯中的“发愤之作”,其表现了“水浒忠义”的主题,认为他们借写草莽英雄忠义参天的故事来发泄心中对于元代异族入侵统治的不满。
一部《水浒传》,有人称赞它是“忠义”的教本,有人却痛斥它是“诲盗”的渊薮。明清时关于《水浒传》主题已然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忠义”说和“诲盗”说。清代是满人入关建立的封建政权,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统治者实行严密的文化控制。面对《水浒传》以及水浒戏的广泛传播和秘密结社、盗匪、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此时主流社会舆论对《水浒传》多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是“诲淫诲盗”之作,为不逞之徒立传,视《水浒传》为最败坏人心的作品。例如,清代乾隆、嘉庆、咸丰三朝都曾明令禁止销售、刊刻《水浒传》以及水浒戏,俞万春更是特作《荡寇志》来消弭《水浒传》的不良影响。
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许多研究者借《水浒传》来比附当时的社会斗争,故有“倡民主、民权”的“政治小说”提法。梁启超在《小说丛话》中认为《水浒传》梁山旗上书“替天行道”,堂上书“忠义堂”,是“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施耐庵“因外族闯入中原,痛切陆沉之祸,借宋江之事,而演为一百零八人,以雄大笔作壮伟文,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以为排外之起点”[2]。黄人在《小说小话》中指出《水浒》一书,纯是“社会主义”。对于有人借《水浒传》喻“实行宪政”或“当代革命”,鲁迅加以嘲讽道:“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因风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径的假李逵。”[3]
新中国建立之后,研究者侧重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文学研究工作,故“农民起义说”应运而生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宋史》中记载:“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4]“农民起义说”从反映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水浒传》反映了农民革命起义的历史,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文革”时期,《水浒传》又被认为是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工具。关于《水浒传》主题与思想内容的接受、阐释往往与接受者所处时代的思想政治倾向、文化政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中国人对《水浒传》的态度,一直以来被看作是社会思潮的风向标。
新时期以来,伴随思想解放风潮,学术界的面貌焕然一新,学术氛围空前活跃。随着西方新的文学理论的引进与接受,不少学者不再固执于一种说法,而是在肯定“主题多义”的前提下,全方位、多角度地对《水浒传》进行阐释,产生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例如:“为市民写心说”、“忠奸斗争说”、“伦理反省说”、“讽谏说”、“复仇说”、“明、暗主题说”、“游民说”、“多元融合说”、“泛农民趣味颂歌说”……,真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二、新版电视剧《水浒传》对小说主题的阐释
小说《水浒传》的内容结构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逼上梁山和离别梁山,贯穿整部作品的价值取向是除暴安良、替天行道,宣扬的是如霆如电、如雷如火、血性阳刚的艺术精神。2011年版新《水浒传》在接受历来《水浒传》主题研究中的“忠义说”、“忠奸斗争说”的基础上,结合当下的社会文化突出了“除暴安良”、“兄弟情义”、“护国安民”的主题。其中尤以“兄弟情义”、“护国安民”在景冈山演唱的新《水浒传》片头曲《兄弟无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兄弟投缘四海情兄弟交心五车话兄弟护国三军壮兄弟安民万世夸兄弟生离两行泪兄弟死别一枝花。兄弟情夜空中万千星点 兄弟情红尘里无限光华。”
(一)电视剧“除暴安良”主题对小说侠义思想的接受
几百年来,《水浒传》一直为世人所喜爱,并奉为经典,究其原因之一,即小说通过描写英雄的事迹、活动,酣畅淋漓地展现了水浒英雄除暴安良、嫉恶如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文化精神,感人至深。电视剧新《水浒传》在接受小说侠义文化精神的前提下,运用现代影视技术,通过大量剧集、桥段来浓墨重彩地表现水浒英雄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侠义之举。
鲁智深无疑是除暴安良的典型,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人须救彻”(见百回本第九回)的精神令人敬仰,所以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将他推崇为“人中绝顶”、“上上人物”。新版《水浒传》用大量剧集展现鲁智深除暴安良的侠义行为。第四集即为“鲁智深义助金翠莲”,他在听完金翠莲、金老儿的悲惨经历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将镇关西的恶行告知小种经略相公,这不得不说是新版的一个全新演绎。新版《水浒传》通过鲁智深摔碎经略府中题为“松荫堂”的牌匾展现其对官府的失望与彻底决裂。鲁达送素不相识的金翠莲父女五十两银子让他们逃离渭州,并三拳两脚打死了欺软怕硬的恶霸镇关西,是典型的仗义疏财、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侠义行为。新版《水浒传》中鲁智深在刘太公庄上痛打桃花山前来强抢民女的小霸王周通;瓦罐寺中与史进联手杀死霸占民女,欺压众僧的恶人飞天道人丘小乙、黑和尚崔道成;大闹野猪林解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豹子头林冲。鲁智深这种路见不平仗义出手,救人于为难之中的行为,正是所谓的“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见百回本第三回)。令人读之观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鲁智深无意为侠客,但是他的古道热肠却使他从一个草莽英雄向侠客华丽转型。
小说《水浒传》第二十九回,武松醉打蒋门神之后说:“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见百回本第三十回)历来研究者认为,虽然武松自诩为“侠客”,但是他身上表现的更多是“义”的因素,他的所作所为无非是报答施恩对他的信任与赏识。电视剧新版《水浒传》为了给广大电视观众展现武松的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特意在血溅鸳鸯楼之后加上几个百姓对于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的痛斥,“该杀、该杀”。由此可以作为一个缩影来窥探蒋门神、张团练等恶霸平日里对于普通百姓的欺压鱼肉,武松血溅鸳鸯楼相当于为民除害,这也就更贴近了新版《水浒传》英雄除暴安良的主题定位。
新版《水浒传》中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雄,七星聚义劫取不义之财生辰纲不是为了一生富贵,而是取不义之财,散之于民。新版更是通过刘唐之口交代了生辰纲的用处,原来晁盖变卖生辰纲为东溪、西溪、石碣村三个乡缴纳租子,这不得不说是除暴安良主题另外一种形式的解读。
(二)电视剧“兄弟情义”主题对小说“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接受
小说《水浒传》中英雄之间的结义行为俯拾即是,通过结义的形式,异姓陌路人变为兄弟甚至比亲兄弟更加亲密。例如,武松与宋江、张青结为兄弟,林冲与鲁智深结义为兄弟,七十一回排座次之后,众好汉“各人拈香已罢,一齐跪在堂上”(见百二十回本第七十一回)对天盟誓是总的结义。来自八方异姓的英雄豪杰啸聚梁山,靠的就是“义”这个纽带的联络,“义”是梁山英雄聚义的精神旗帜。正是在“义”字大旗的感召下,各路英雄好汉如百川归海,齐聚梁山,成为与朝廷相对立的理想化的江湖世界。电视剧新《水浒传》在将文学语言转换为影视语言的阐释过程中主要接受了原著“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提法(见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第七十回英雄排座次情节),重点突出了兄弟“情义”这一主题,更多地演绎为“手足之情”。
新版电视剧《水浒传》武松与宋江重逢在孔太公庄上,晚上在一处歇卧,回想初次相逢柴进庄上似乎是昨日之事,一见如故,情深似海,义结金兰,宋江还劝告武松,凭着他的拳脚,日后到边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可如今,二人都是脸刺金印的囚徒,所有的豪侠壮志都化为南柯一梦,可悲可叹。只怕自从你走后,铁狮子一哭会生锈。牵挂月月又年年,无眠半宿又一宿。新版《水浒传》为表现鲁智深与林冲之间的兄弟情义情深似海,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崭新的情节设计。新版《水浒传》中,鲁智深与林冲本为同门师兄弟,初次相逢即以武会友,义气相投,结为兄弟。林教头刺配沧州道,嘱咐智深代为照顾林娘子,可就是因为鲁智深的一次酒后误事,导致林娘子葬身火海,一向嗜酒如命的鲁智深发誓从此之后再不饮酒,并且自缚其身向林冲负荆请罪。鲁智深六和寺坐化,林冲拎一坛清酒来坟前拜祭,此时画面中运用视觉蒙太奇法闪回鲁智深曾经的音容笑貌,江山非画美如画,豪杰壮士影叠叠,斯人已逝,徒留林冲无限感伤与思念。
新版《水浒传》中梁山排座次及五台山盟愿所言都是“只愿众兄弟生生相会、世世相逢、永无断阻”;宋江军攻克杭州城时,摆设灵堂御酒洒地来祭奠阵亡将士;李逵为兄弟情义自己喝下毒酒,“生时服侍哥哥,去那边也为哥哥做个先锋”。
(三)电视剧“护国安民”主题对招安的新阐释
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宋江起义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并没有赠予宋江忠义的桂冠。后来宋江故事在“说话”中不胫而走,“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5],并且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被赋予“忠义”思想。《水浒传》的雏形《大宋宣和遗事》中,广行忠义、殄灭奸邪构成了这部话本的主旨。在民族矛盾激烈的元代,水浒英雄又成为见义勇为、为民除害的草泽义士,高举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大旗。从“不假称王”、“广行忠义”到“替天行道”,“忠义”思想始终是制约水浒故事发展的轨迹,所以《水浒传》作为一部文人在集体创作的基础上完成的作品,不可能超越这个故事流传过程中形成的“忠义”思想格局。《水浒传》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后,描写了受招安的内容,谱写了一曲乱世忠义的悲歌。新版电视剧《水浒传》在接受这种“忠义”水浒思想的基础上,将其演绎为“护国安民”主题。新版《水浒传》中的招安情节,不再是小说中众英雄因“封妻荫子”的目的而为,而是为了建功立业,还百姓清明大宋。
电视剧中,宋江率梁山军马攻打青州,一路对村民秋毫无犯,反观青州太守屠村,下毒栽赃的行为真可谓是坦荡磊落了,并且劝解呼延灼“忠义”并不是愚忠,杀慕容知府,待罪之身也要行替天行道、护国安民之事。新版《水浒传》中杨志对吴用、晁盖等劫取由他负责押运的生辰纲之事始终耿耿于怀,并借机非难吴用什么是忠,什么是义,吴用对曰:“对上无二心,对友无二心,梁山泊好汉都是忠义之士。”林冲满以为被派去大名府做制使,可以征战沙场,为国尽忠,没想到是押解不义之财生辰纲,所以毅然请辞。燕青辞别李师师,出征方腊也正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宋江请求早日出征,徽宗以毒酒试其忠义,宋江道:“其本为卑微小吏,误犯典刑,流配江州,酒后狂言犯下大逆不道之罪,今蒙圣上宽恤收典赦免本罪,微臣披肝沥胆尚不能报圣上之恩,我主陛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纵是毒酒,宋江感恩于心。”忠义之心可昭日月。吴用在蓼儿洼宋江坟前告诉花荣,他与公孙胜早就预测招安后难免兔死狗烹的下场,但是即便是这样也要助宋江招安成功,其九死亦尤未悔。
三、当代价值观与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接受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日益提高,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大量涌入,其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重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轻个人利益的精神产生了剧烈碰撞。加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文化乃至人们的生活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革,激发了人们新旧价值观念、信仰的急剧冲突,人们更加注重个性、自由的发展,形成了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格局。正是在这种土壤之下,注重人性、人情、全民参与、平等性、娱乐性的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为普通大众所喜爱,并且迅速崛起。影视艺术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以其视听结合的直观特色,信息传播的快速便捷,拥有了广泛的受众。在这个注重品牌和知名度的消费时代,一部古典名著无疑是一个著名的文化品牌,更能为广大电视观众所接受,所以《水浒传》也搭上了名著改编的末班车,新版以当下文化视野对小说进行了全新审视,展现了名著新的时代内涵。
新版《水浒传》电视剧在接受小说侠义思想的基础上,着力表现水浒英雄除暴安良的主题,对于原著中英雄的过度杀戮行为进行了纠正。编剧温豪杰表示,梁山好汉必须是正直的,小说中的过度杀戮行为是少儿不宜的。新版《水浒传》中还通过店小二之口大加赞扬鲁智深的侠义精神:“我家提辖是遇酒便吃,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歹便打,这渭州大至六街三市,小到路边小小茶坊,人人敬佩我家提辖,我家提辖可是好汉。”在当下人的意识中,人人生而平等,不容许欺压弱小这等封建糟粕行为存在,水浒英雄当然被塑造成正义的化身,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并且水浒英雄形象必然是正面的、积极的。所以新版中,观众看不到李逵排头砍看客,水浒英雄拿坏人的心肝做醒酒汤这种镜头,就连母夜叉孙二娘卖的人肉包子也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在消费文化盛行的今天,人们日益被物质所包围,激烈的社会竞争环境,渐渐导致人们情感交流的荒漠化,在代偿心理的作用下,人们更希望在影视剧中获得情感、人情的审美需要。新版《水浒传》接受小说“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提法,将兄弟情义演绎得感人至深。兄弟非亲心更亲,情义兰舟通彼岸,四海兄弟赴盟约。这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新《水浒传》中为什么具有美化女性的倾向。新版的这种定位,赚足了广大电视观众的眼泪,在名著翻版浪潮中赢得了不俗的收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新版《水浒传》中的梁山英雄俱是忠义之士,身虽百死而无怨,俱怀忠义笑问天。“护国安民”主题体现了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中对于善的追求,对于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价值取向的肯定,同时也契合了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
[1]天都外臣.《水浒》评论资料[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94.
[2]马蹄疾.《水浒》资料汇编[G].北京:中华书局,1980:425.
[3]鲁迅.鲁迅全集:集外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201-202.
[4]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11114.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0:85.
[6]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31.
[7]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6:38-42.
[8]王鸿卿.《水浒》主题新论[J].明清小说研究,2005,(2).
[9]宋克夫.乱世忠义的悲歌——论《水浒传》的主题及思维方式[J].湖北大学学报,19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