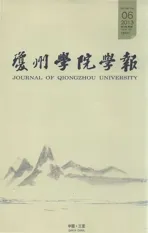东晋南朝文化场域下的陶渊明接受研究
2013-04-12郭世轩
郭世轩
(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 阜阳230037)
在宋代之后被公认为伟大诗人的陶渊明(365-427)在生前与死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尤其是南朝)主要是以隐士的身份被历史记载。即使被萧统予以褒扬,也多出于道德人格的认同,《昭明文选》的选文与其高度评价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悖论。[1]钟嵘的肯定也是小心翼翼的和有所保留的,在《诗品》中给予“中品”的评价与辩护,并被定位为“隐逸诗人之宗”。[2]66-67至于以经纶群言、体大思精而著称的刘勰对他则采取无视的态度,引起后世学者的质疑。[3]陶渊明在东晋南朝文名不显的事实,一方面直接说明了陶渊明在生前与身后的人微言轻,另一方面也间接说明了陶渊明始终处于被误读和被遮蔽的状态。本文试图从东晋南朝的文化场域方面进行切入与探讨,以就正于方家学者。
一
布迪厄认为,一个分化了的社会并不是由统一的权威统摄而成的浑然无间的整一体,而是由各个相对自主的“游戏”领域组合而成的聚合体。这种“游戏”领域就是场域。每个场域都相对规定和拥有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和调控原则。这些原则界定了一个社会建构的空间。在这种场域内,行动者根据自己在空间里所占据的位置进行着争夺,力求改变或企图维持在空间中的范围或形式。场域既是一种空间——充满着竞争与斗争的场所,又是一种关系——具有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结构。场域包括政治场域、文化场域、经济场域和学术场域等大的、主级场域,其中又可分为小的、次级场域。场域具有两个关键特征,那就是体系性与竞争性。前者认为“场域是诸种客观力量被调整定型的一个体系(其方式很像磁场),是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这种引力被强加在所有进入该场域的客体和行动者身上。场域就好比一个棱镜,根据内在的结构反映出外在的各种力量。”后者认为,“场域同时也是一个冲突和竞争的空间,这里可以将其比作一个战场。在这里,参与者彼此竞争,以确立对在场域内部能发挥有效作用的种种资本的垄断——在艺术场域里是文化权威,在科学场域里是科学权威,在宗教场域里是司铎权威,如此等等——和对规定权力场域中各种权威形式间的等级序列及‘换算比率’(conversion rates)的权力的垄断。”[4]17-18所谓文化场域,主要是指在文化空间之内各种利益集团与个人对文化资源的占有、分配与争夺的状况与情形。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东晋南朝时期在政治场域逐渐走向分化的同时其文化场域分布的具体状况。
大一统的汉王朝结束之后,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场域发生了剧变。门阀世族的政治势力逐渐凸显,新旧贵族之间的勾心斗角日趋激烈,核心价值观念的缺失导致政治离心力逐渐增强。政治场域的分化直接影响与制约着文化场域等方面的变化。东晋南朝的文化场域以刘裕篡宋为节点,大致可分为东晋和南朝两个阶段。东晋的文化场域主要为门阀世族所掌控。以郡望、出身与血统为炫耀资本,以谈玄论道、不务实事为高尚品格,成为此时文化场域至关重要的标志。刘裕篡晋标志着文化场域的新转折,孕育着历史发展的新方向——寒门士族的崛起和门阀贵族的衰微。当然,寒门士族的崛起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寒门子弟都能够搭上这趟“顺风车”,其中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刘裕是寒门士族的代表,在低贱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一旦掌握实权并称帝之后,高度看重文化权威的价值。虽然他文化修养不够,却十分重视子孙的文化教育。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后代为文化场域建立新规范。一方面,尽力扩大自己家族的文化实力,强化自己家族在文化上的发言权和领导权;另一方面,极力压制门阀士族在文化上的话语权力与发展空间。前者设立“文学”馆,与儒学、玄学和史学相提并论。这种标新立异之举,确实为寒门士族建立新功、后来居上奠定了坚实的晋升台阶和广阔前景,使有文学才能的寒门士子看到出人头地的希望。后者则是借助政治上的高压手段,在软硬兼施中实现对贵族势力的遏制与打击,在无形的政治场域中以无可匹敌的政治权威逐渐消解了王、谢、顾、陆等百年名门望族的文化实力与政治权威。前者最明显的成就在于,在刘裕的后人中以文学知名者逐渐增多,如刘义隆、刘义庆等人为刘姓皇族增光添彩,至少可以挽回刘裕当年在世家贵族面前所丢失的面子。到萧齐、萧梁时代,皇室家族多以文学之士称盛,甚至出现了文学家族和主盟文学集团的领军人物,如萧子良、萧衍、萧统、萧纲、萧绎等,陈叔宝更是酷爱文学而不务正业的失败帝王之一。后者则是打压贵族势力,把他们放逐到清闲无权的职位,使之在享乐中逐渐丧失政治实权。统治者对于其中的异端和稍有不满者痛下杀手,轻则流放,重则杀头。谢灵运等人的被杀就是最好的说明。
东晋南朝的政治局势和文化场域不利于陶渊明理想抱负的实现和文学作品的传播。在这样的政治空间和文化空间之内,陶渊明的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都不足以抵抗政治场域的压抑或参与文化场域的竞争。作为立身之本,陶渊明的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都是相当贫乏的。唯一能够抵抗世俗压抑和权力异化的,则是他独立不羁的个性和闲适率性而又认真执着的品格。所谓文化资本,是指一个人由于自己的努力而在文化资源上所能调动的权利与优势。政治资本是指一个人借助门第血统所带来的政治优势与权力资源。东晋是门阀世族掌权执政时期。重视门阀血统、强调出身地位,几乎是政治资源的代名词。在政治上,世族与寒门势如水火,形同陌路,可谓“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诗十九首》)。政坛上优越的职位、丰厚的待遇和清闲的工作,非贵胄王公子孙莫属。而吃苦耐劳的工作和俸禄菲薄的职位,只能由寒门子弟充任。前者以王谢家族为代表,后者以陶侃家族为证。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为东晋的开国元勋,为东晋政权的建立与稳固立下汗马功劳。由于出生低微贫贱,虽然以武功建立爵位,但仍然被门阀世族呼之为“溪狗”而不耻于士林。(《世说新语·容止》)可以说,相对于刘裕后来的发迹与显赫,陶侃可谓生不逢时。即使在死后,他仍遭受世族的诋毁,其子孙受到压制。凡贵族子弟皆可过上衣食无忧、不问俗务的优越生活,而寒门子弟无论你多么优秀也难以望其项背。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南朝结束。其间虽然在刘宋王朝建立新政权之际有所改观,但整体看来却是换汤不换药,以一种更加严厉与残暴的手段打压贵族豪门,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武功特权阶层。新贵逐渐取代了旧贵,原先的王、谢、顾、陆等大家族逐步走向衰落,而掌握政治大权之后的新贵权臣开始向文化进军,最后形成如此的新局面:日薄西山的旧贵族大权旁落,在政治与文化上逐渐失去发言权;如日中天的新贵们摩拳擦掌,取得了政治与文化的双重领导权。
事实上,政治优势与文化优势是相辅相成的,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均掌握在新旧贵族手中,寒门子弟只能望“门”兴叹!与之相适应,经济资本是指一个人所拥有的财产和金钱等经济能力。如果你在政治上默默无闻、英俊沉下潦,即使拥有文化资本也难以彰显其应有的作用。倘若你没有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也不会有多大改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能力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政治地位与现实处境。相比较而言,陶渊明既没有可以骄人的政治资本,也没有丰厚的经济资本,更没有显赫的文化资本,聊以自慰的是自己的个人资本——那就是追求自由的个性和独立不羁的天赋。在这种文化场域内,作为败落家族的子弟,由于家族内讧败落,亲族之间来往稀少,[5]这就使九岁丧父的陶渊明在政治上处于“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曹操《短歌行》)的困境。政治资源极度贫乏的他只能担任小吏,俸禄微薄,聊以养家糊口,肩负起人子、人夫与人父的伦理责任和道义使命。进入这一政治场域之内,必须遵守官场游戏规则:迎来送往,以礼相待,对于上司与长官需要毕恭毕敬。“卷入游戏的游戏者彼此敌对,有时甚至残酷无情,但只有在他们都对游戏及其胜负关键深信不疑、达成共识时,这一切才有可能发生;他们公认这些问题是毋庸质疑的。游戏者都同意游戏是值得参加的,是划得来的;这种同意的基础并非一份‘契约’,而就是他们参加游戏的基本事实本身。游戏者之间的这种‘勾结关系’正是他们竞争的基础。”[4]135“性刚才拙,与物多忤”[6]而又性情执拗的他确实忍受不了这种游戏规则,但又迫于生活的压力和奉亲养家的责任,十余年间在官场三进三出,前后总计不过三四年。最后,经过利害权衡和心灵煎熬之后终于做出自己的人生抉择——躬耕田园,亲力自养。
仕途无望,只能转向田途。他回归田园,不能算是归隐。对他来说,回归田园只是为了谋生活命。归隐山林,那是渴望功名利禄者的待价而沽。陶渊明从来就没有说过自己是归隐。“归去来兮”,只是回归自己的家园,而非沽名钓誉之徒的闲情逸致和浪得虚名。回归之后的他物资上虽然清贫,精神上却非常自在、自由与自得。常言道,甘蔗没有两头甜。任何事物皆是利弊相生,人生也是福祸相依。在乱世中,做一个正道直行的谦谦“君子”只能“固贫”(《论语·卫灵公》)。这事连孔夫子都概莫能外,何况陶渊明乎?!到了南朝时期,“贵贱贤愚,唯务吟咏”,崇尚奢华浮靡、丽词淡情,人人竞奇争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7]相比之下,陶渊明的为人与为文根本难入时尚主流。要么被视为隐士,要么被视为道德圣贤,虽勉强忝列于隐逸诗人行列,仅处于中品位置。[2]66-67
二
在东晋百年的历史视野内,审美趣味逐渐由西晋的缛彩繁文、巧构形似[8]120-124转向以质校文、抱朴说理[8]144-147。历史上常常具有惊人相似的一幕。每当改朝换代之际,无论在治国方略还是审美趣味上,后来者往往要改弦更张、反向运转。东晋王朝汲取西晋灭亡的教训,一方面分化瓦解皇室子弟的实力,以防止宗族势力坐大一方,再次出现“八王之乱”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在宗族混战中士人丧生的现实使得大难不死的显赫文人与门阀士族逐渐看淡政治功名与社会时局,虽然有清谈误国之教训,但历史的惯性仍然裹挟着他们沉迷在失国之痛的自怨自艾之中,“对泣新亭”(《世说新语·言语》)之后,不问政事、挥麈超然的气派很有市场。谈玄论道之际,借助于诗歌的形式将意犹未尽的雅兴展现为他们的审美趣味。如此以来,“平典似《道德》论”[2]17的玄言诗歌大行其道,重申名教的呼声与说理论道[8]138-147的实践并行不悖。平淡质朴的文风恰与西晋华丽浮靡的文风形成对比。而在充满竞争与斗争的政治场域中失败的陶渊明最终选择了自食其力的农耕生活是他别无选择的选择:如果能够忍受官场游戏规则的束缚和宰制,小吏般的仕途生涯也可以让全家过着衣食无大忧的生活,当然损失的是人身和个性自由。可他偏偏忍受不了世俗功利与繁文缛节的双重枷锁。因此,他在适当的时候毅然决然地摆脱双重枷锁,重新恢复自由、保全自己的真性情与真习性。“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应该是“十三年”,引者注)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9]6-7这就是他的性情与习性。“习性作为一个历史的产物,是性情的一个开放性系统,这个系统不断服从体验,并因此以一种加强或改变结构的方式不但受到体验的影响。”[10]可以说,习性在陶渊明的人生抉择中发挥重要作用。倘若陶渊明依然做着人微言轻的小官吏,在政治场域中还是进入不了中心地位;而回归田园之后的他则是处于真正的社会边缘。当然,在村夫野老中间他得到必要的尊重与敬佩,心中还是快乐的、自由的[9]7,39。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许多田园诗歌与散文中得到佐证。即使在他不善于营生与稼穑致使生活陷于困顿之际,仍然有来自左邻右舍有限的帮助与接济。微薄的接济不亚于雪中送炭,给他以非常及时的温暖与安慰。艰难的生活困境也许使他有难以言说的苦楚与后悔,但通盘考虑之后还是欣慰大于失落,心安理得与乐天知命成为他“归园”之后心灵的主旋律。
如果说在政治场域采取边缘立场是他的性格使然,那么在审美趣味上选择另类的品位,仍然执着于“高情淡采”[1]的一路,则与他的性情气质、审美取向和生存语境密切相关。面对玄风炙热的文学场域和说理玄远的审美场域,陶渊明本来无意于成为作家和诗人,只是出于内在性情的本真面目和率性而为的生活节奏,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下自己的生命感喟和生活轨迹,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日记与总结。也许诗人本来无意于创作,所以才在无意中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以原生态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也许就是苏东坡所谓“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11]的境界。写出自己的心得与足迹,进行自我欣赏与备忘,遇上二三知己也可以边喝酒边交流,“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9]5-9性格的自适、趣味的恬淡和环境的质朴,使他坚持本色的生活与写作。正因为乡村环境的优雅和淳朴才契合他热爱自由、崇尚恬淡的天性,使他在快乐中坚守本色,而远离他厌恶的华丽辞藻和做作姿态。正因为如此,他才不加修饰,基本上以一种本色的语言记录自己本色的心迹与体验。虽被玄风包围却避免了玄言的空疏与空洞,在流行的审美场域中独树一帜,坚守另类的审美趣味——“高情淡采”。“高情”体现在不虚美、不炫耀、不做作,将自己的人生思考与审美体验深入细致地表达出来,既别于玄言诗的枯寂寡味[2]17,也迥异于西晋的绮靡述情。[8]122“淡采”表现为以本色的语言和本色的生活作为言说的形式与内容,呈现为一种本色之美和平淡冲和的境界。[12]他的“淡采”迥异于东晋的虚空和西晋的华丽。这样另类的审美趣味不仅难以进入东晋人的视野,而且同样也为南朝人所忽视。刘裕篡晋称帝之后,开始以武人军功阶层的世俗趣味取代贵族的高雅玄远趣味,从此奠定了南朝的审美取向。
东晋之后,偏安江南的局势使得士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沉浸在江南秀丽的山水滋养和丰腴的物欲享受之中,流连忘返,沉醉迷离。宋文帝设立“文学”馆,揭开了文学与玄学、经学并驾齐驱的新篇章,同时改写了汉代以来经学与玄学交替控制学界的沉闷局面,并将预示着文学凌驾于经学与玄学之上的趋势。相比于西晋的“八王之乱”和东晋的篡乱动荡,南朝在长达一百七十年的时间内除了侯景之乱外基本上没有大的动乱与战争。相对承平日久的现实环境很容易激发文人士子的情愫与文采。南朝帝王对文学的喜爱大大激发了文学形式美的热情。局促的江南地理环境使他们的审美视野变得较为狭窄幽僻,秀丽的江南山水美景又使他们的审美趣味变得较为柔美浮靡,文案台阁和宫廷应酬使他们逼仄的生活和趣味更加孤寂与暧昧。前有大小谢清远的山水歌咏,中有浮华的永明文学,后有萧纲萧绎艳丽的宫体细描。其间如被压抑的鲍照的《将进酒》等诗歌成为南朝的空谷足音和浮世异响。被贬谪的江淹的《恨赋》、《别赋》令人怅恨良久,出使北朝被扣留的庾信的《哀江南赋》使宫体诗歌的巨子突变成感时伤世的歌手。可以说,正是以上几位杰出者的突出表现改写了南朝文学名声不佳的历史,使得南朝文学不仅是“风花雪月”的世界。在如此的文学场域之内,绮靡艳情的审美趣味长驱直入,陶渊明的“高情淡采”肯定不会得到更大范围的关注和很高价位的评判。友其人不亲其文者有之,以隐士看待者有之,高评低选者有之,视而不见者有之,强为之辩解者有之,不一而足。
总之,在南朝的文学场域之内,陶渊明的“高情淡采”是曲高和寡的,真正的知音只有在另外一个时代出现。陶渊明是寂寞的,同时也是幸运的。在历久弥新的历史淘洗与读者阅读的自觉选择中,陶渊明的影响会呈现出层累似的积聚状态,仿佛地壳运行过程中能量的积聚一样,一直在等待喷薄而出的绚丽时刻。那一刻将在四百多年之后的北宋才出现。
三
如果说历史上的气候变冷期恰巧发生在两晋南朝,那么陶渊明可谓生不逢时,等于遭遇了双重的“冰河期”。生前的寂寞与冷遇足以使旷世诗人饱受生命的凄怆与悲凉,而死后所遭遇的误解、误读与冷遇使人倍感世俗的强大惯性与知音的旷世难遇。纵观陶渊明的文学接受史,我们为陶渊明所遭受到的冷遇感慨良多。我们分别从颜延之、沈约、刘勰、萧统和钟嵘对陶渊明的评价入手,更好地了解陶渊明所遭遇到的“误读”。
首先看看陶渊明生前好友颜延之(384-456)对他的评价。在江州任后军功曹时,他与陶渊明过从甚密;其后出任始安太守,路经浔阳,他又与陶渊明在一起饮酒,临行并以两万钱相赠。他们之间的“忘年交”情较为密切。颜延之也许是史书上所能记载的、陶渊明家族之外关系较为密切的好友之一。就是这样一位官场失意、当时颇有隐逸之志的著名诗人,按理说他应该是与陶渊明心心相知相印的故交,然而在纪念追悼这位旷世诗人的文章《陶徵士诔并序》中,仅仅提到“文取指达”[14]268四个字,其余的主要叙述陶渊明的性格气质、理想抱负等。“文取指达”四字颇值得玩味。从颜延之“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的文风来看,他所代表的是时代的审美趣味。相比之下,谢灵运“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15]的诗文显得自然清丽。陶渊明质朴的诗文在颜延之看来就只有“指达”的价值,难免被无视的命运。连生前好友就有如此的看法,陶渊明生前所遭受的待遇与境况由此可见一斑!我们可以设想一下,陶渊明生前主要以“徵士”、“隐士”的身份被人们认同着、误读着。“浔阳三隐”的称呼可能就是最好的说明!从客观原因来看,政治资源的边缘处境使他无法进入东晋政治场域的中心;从主观因素考量,另类的审美趣味使他无法进入东晋文学场域的中心。这大致就是陶渊明在东晋时的接受情形。
我们再看他在南朝文化场域的具体状况。作为南朝文化场域中四个重量级的人物,沈约、刘勰、萧统和钟嵘的接受与评价又会是怎样的呢?
沈约,身处宋、齐、梁三个历史时期,是齐梁时期的文坛领袖,永明文学的盟主和齐梁政坛尤其是梁朝政治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无论在政治场域、文化场域还是在文学场域、学术场域,他都是不可忽视的重量级人物。他的话语资源对于一个进军文坛的小人物可谓一言九鼎,刘勰的《文心雕龙》写成之后乔装打扮而恭候他的出行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就是这样一位文化大碗,在他纂述的历史著作《宋书》中,作为“文苑传”的《谢灵运传论》中竟然没有陶渊明的位置[14]296-297,而却把陶渊明“流放”在《隐逸传》中。[13]沈约的阅历和学问可谓丰富至极,为何偏偏对陶渊明视而不见呢?原因无他,主要在于陶渊明的文化资源和文学资源在他看来非常单薄、非常贫乏而已。如果他的历史评说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量,那就尽可能做到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从文化场域的视角来看,不管是文化资源还是文学资源,在当时及其之前,陶渊明都是势单力薄、易被忽视的人物。可以说,《宋书》所代表的不仅仅只是沈约的观点,而是那个时代的审美趣味与文化评价。当然,作为《宋书》主笔的沈约之所以对陶渊明有如此的记录与评价也与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观念相关。纵观沈约的审美趣味与文学观念,不难发现沈约重视华丽柔美的审美趣味和声律词采兼顾的文学形式美。他的“四声八病”说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6]在沈约看来,陶渊明的诗文不被认可,他只是一位“隐士”而已。因此在文学场域之内,作为文化资本的优势掌控者,沈约拥有绝对的权威。对陶渊明的拒绝无异于对文学入场券这种稀缺资源的垄断与把握。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把文学资源进行随意扩张,以确保文学场域的“纯净”与“雅致”。
如果说沈约作为文坛领袖对陶渊明的拒绝代表了文学场域的现实维度和审美时尚的话,那么作为他的粉丝之一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无视陶渊明则是历史维度和范式规约的表现。前者是作家的、同行的眼光,后者则是专家的、权威的视角。但二者一脉相承之处恰恰体现在:时代的偏见与审美的规训。对于刘勰而言,“情采”既是他论文的篇目,更是他建立审美标准和文学规则的一个知识范式。“情采”的内涵就是要为文学建立内容上的情感维度和形式上的辞采维度,最终使文学成为深厚丰富的情感和华丽柔美的辞采和谐统一的样态。这仅仅只是一种理想的知识范式。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任何人皆难以超越时代局限和个人好恶。事实上,刘勰虽然也一直主张要做到“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9]586但在具体作家的分析上却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别的不说,仅就他在《文心雕龙》中提及的几百名作家中,难道都比陶渊明优秀吗?[17]显然是不可能的!文中涉及到的许多作家而今仅仅只有一个“名字”而已,其文不足观、其人不足名者不在少数。由此看来,被后世视为“博大精深”的大家同样具有“洞见”与“盲视”。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也是很辨证的:每个人都是有限的理性,凡人皆有局限,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作为昭明太子,萧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之一。他充分利用皇家藏书,广收博览,占据了天时、地利与人和优势。他的智囊团中,不乏文学家和文学爱好者。尤为重要的是,他为人低调,性至孝、“孝谨至天”、“仁德素著”,温文尔雅。[18]在做太子期间,他被梁武帝寄予厚望,潜心于经史子集等文化典籍,饱读诗书,心仪儒学。在年长位久、深文周纳的父皇督导下,他只能做些文化整理之类的工作,实难有大的作为。这种性情与处境促使他的心境与陶渊明发生了共鸣与契合。对于仅活了31岁的萧统来说,整理《陶渊明集》,主持编撰《昭明文选》是他短暂一生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在《陶渊明传》和《陶渊明集序》中,他高度评价了陶渊明的人格与文格,并指出文学与道德、文学与饮酒之关系,[14]332-335为后人理解陶渊明指明了方向。这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较为系统论述陶渊明的文章。深究其文,其重心聚焦于论人——陶渊明的道德品格与性情淡泊上,论文则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而《昭明文选》中的选文数量则与对陶渊明的高度评价极不相称,出现了“高评低选”的悖论现象。[1]这也许体现了萧统内心世界的矛盾与冲突——潜意识层面的“本我”喜欢而意识层面的“超我”却有所顾忌,或者相反。
南朝另一位著名的诗歌评论家钟嵘,在《诗品》中将陶渊明定位于“中品”,在后世引起热议。平心而论,《诗品》的核心主旨在于风力与丹采,要求诗歌在内容与形式上倾向于和谐与阳刚,在创作方法上主张有感而发、直抒胸臆的“直寻”,以纠正“掉书袋”、喜“用事”等不良习气,从而达到既有回环往复的“滋味”和纯净爽朗的“真美”之接受效果。以此标准相较于“上品”的十一位诗人,而真正符合者大概只有陶渊明。之所以没有把陶渊明选定在“上品”,原因已在钟嵘的辩驳之中。“岂直为田家语耶!”[2]66如果把他所引用的那几句诗算作“丹采”的话,实属勉强。如前所述,陶渊明的诗歌是以“高情”与“淡采”而著称,这一点在与曹植、陆机和谢灵运的比较中凸现出来。从曹植以来,魏晋六朝文学呈现出越来越浓重的宫廷审美趣味:丽—艳—丰赡,写神—重骨—崇肉,声律—骈体—隶事。[19]如果说曹植等人的诗歌是“丹采”的话,陶渊明的诗歌只能算作“淡采”。在钟嵘所罗列的几个必备要件中,陶渊明所欠缺的恰恰就是华丽柔美的“丹采”。再加上当时文学新贵们在文学场域中继续秉承不务尘事、不言尘世、不用尘语的“习性”,这就在无形中把陶渊明拒之于门外。所谓的尘世、尘事,就是指需要亲力亲为的体力劳动和农耕生活。这恰恰是贵族阶级所一贯主张的,其根源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隐士痛斥孔子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论语·微子》)。所谓尘语,大概就是指“田家语”,也就是指农夫的口头语言、村夫野老之语。从这个角度来看,钟嵘将陶渊明定位在“中品”确属不易,是在据理力争的语境中完成的,是对当时文学场域的突破,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然而,细细寻绎,我们不难发现,居于“中品”者也有僧人和隐士。这里似乎又隐藏着不便于明说的因素:钟嵘不拘一格选诗和诗人的前提下,是否有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之顾虑。但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文学场域之内能将陶渊明“提升”到“中品”宝座实属远见,但仅仅局限于形式的层面尚未进入陶诗的内容与境界层面,尚未吸取萧统的研究成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倘若要说萧统和钟嵘是陶渊明的“知音”的话,那也只能是加引号的。而真正堪称陶渊明“知音”的只有在四百年之后出现的苏东坡。
如上所述,陶渊明的接受过程与东晋南朝的文学场域息息相关。文学场域的形成制约着作家准入、等级确立和权力分配。“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4]134事实上,曹操、曹丕贵为帝王,也只能被定位在中下品,因为这里通行的是文学场域的游戏规则——艺术形式的语言至上法则。而陶渊明的经典化历程之所以那么漫长,恰恰与他自己的性格气质和审美趣味密切相关。另类的选择使他最终远离政治场域,处于政治上的边缘地带;边缘立场使他的文学趣味游离于审美时尚,在文学场域长期处于被遗忘的角落。与当时文化场域的疏离制约着陶渊明在文坛上的生死沉浮。当然,文学的场域并非一成不变的,不同时期的文学场域充满着偶然性与变动性。在历史的淘洗中,伪文学家或非文学家终会露出马脚,由生前的喧嚣回到被遗忘的角落;而真正的文学家终有一天会被后世读者所认可,在拂去历史的尘埃之后露出“庐山真面目”,绽放出绚丽迷人的光辉,以弥补生前的孤寂与逝后的沉没。这大概就是文学艺术的辩证法,也许是对今天仍然坚守艺术阵地的献身者最大的艺术启示与心灵安慰。
[1]郭世轩.萧统为何对陶渊明高评低选[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3):5-9.
[2]周振甫.诗品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
[3]杨合林.陶渊明不为刘勰重视的原因[J].湖南大学学报,2002(3):57-60.
[4][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5]杨合林.陶侃及陶氏家族兴衰与门阀政治之关系[J].史学月刊,2004(7):22-26.
[6][晋]陶渊明.陶渊明集[M].袁行霈,杨贺松,编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43.
[7]周祖诜.隋唐五代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2.
[8]龚鹏程.中国文学史:上册[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9]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
[10][法]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80.
[11]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314.
[12]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62-170.
[13][南朝]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1522.
[14]郁源,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15][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586.
[16]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2版.北京:中华书局,2006:298,
[17]周振甫.文心雕龙辞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6:271-286.
[18][唐]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111-115.
[19]张法.中国美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45-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