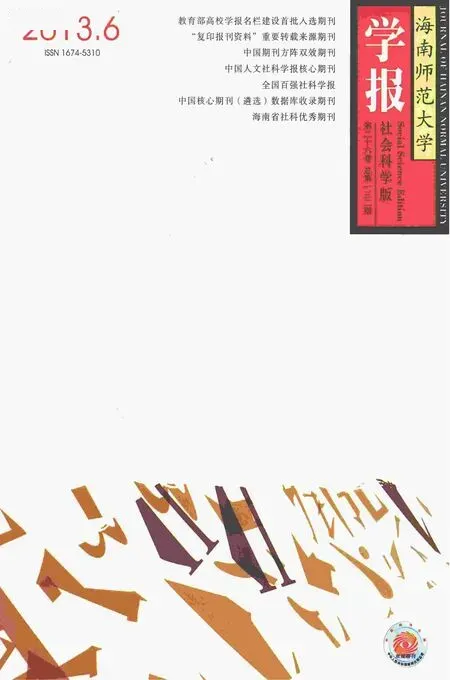专注于描写底层的心灵病相——论吴君小说中的“深圳叙事”
2013-04-12孙春旻
孙春旻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65)
吴君是一个有特色的作家,“深圳叙事”就是她的突出特色之一。她说:“除了一部长篇,我所有的小说都以深圳为背景。通过深圳叙事,我有了成长,学会了宽容。”[1]评论家洪治纲说:“很少有人像吴君那样不遗余力地书写深圳,也很少有小说中的人物像吴君笔下的人物那样对深圳爱恨交加、悲欣交集。深圳,这个带着某种抽象意味的特区符号,已成为吴君审视中国乡村平民寻找现代梦想的核心载体,也成为她揭示现代都市内在沉疴与拷问潜在人性的重要符号。”[2]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作为改革开放标志城市的深圳,无论形象还是意义都有相当清晰的一面。但是,在当代文学中,深圳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城市意象”,或者用时髦的词语来说,没有自己清晰的文学“镜像”。虽然吴君“不遗余力地书写深圳”,可是,深圳作为一个新兴国际大都市的“城市意象”,在她的笔下并不完整鲜明。吴君自己也说:“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好像为了拖住时间,我总想写点什么。于是写了一批反映特区生活的作品。有的人看了认为这不是深圳的生活。而我知道这不是深圳的全部生活,但却是我眼里的生活。”[3]她书写的深圳,不是一个现代的、国际的、新兴的大都市,而是一个欲望的对象,一个梦想的载体,一个精神的病源。吴君笔下那些以深圳为背景的人物,几乎全部身处底层,且都有着残缺的、病态的心灵。可以说,在有意无意之中,吴君就是在描写他们的心灵病相。
一 身份迷失精神焦虑
吴君所刻画的大多是底层人物,且都有着“移民”的身份,被人歧视地称为“乡下人”。他们因此而自卑,渴求深圳的一纸户籍从而在法律的意义上成为深圳人,可是这一愿望总是难以实现,导致他们的精神总是处于焦虑和痛苦之中。封建时期,统治者为了政权的长期稳定,曾制定严厉的法律限制百姓的流动及身份的改变,朱元璋及其子孙们将这一政策做到了极致。然而,空间的流动性应是人类生存的常态,人为的限制是不可能长久的。近现代,中国的人群就有若干次较大的迁徙行为。例如,旧社会以“闯关东”为代表的求生迁徙,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仍然热度不减的“出国潮”,以及当下还在持续进展的乡下人“进城打工”潮等。城与乡,是当代中国区别人群的最基本的分界线。“移民”,表面上只是生活空间的转移,从深处看则是身份的置换。吴君在她并非“深圳叙事”的长篇小说《我们不是一个人类》中,对此也曾有过相当深刻到位的描述:那些生活在东北某城市“灰泥街”的人们,是从河北、山东逃荒来的移民,被当地人视为“关里人或农村人”,是被人看不起的“异类”,生活范围被限制在“灰泥街”这样类似于贫民窟的狭小空间里,大多无业,从事着低贱的营生,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与当地人通婚,或者搬出灰泥街居住。说到底,无非就是取得与人平等的地位。在强烈的自卑之中,他们无法认同自己的身份,这是他们精神痛苦的根源。
中国是一个封建时期特别漫长的国度,封建社会的特征就是“等级制度”,人们被分为贵贱不同的若干等级,上等人可以作威作福,下等人只能逆来顺受。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强烈的“身份”意识。在当代,“身份”一词成为学界用来表达人类的精神困境的关键词,无法说出究竟有多少人因“身份认同”问题在心灵的漩涡中挣扎。所谓“身份认同”,无非是对“我是谁?我是什么人?我拥有什么样的权力和社会地位?”等等人生基本问题的追问和确认。孔夫子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种身份伦理,“安分守己”被视为基本的道德规范。一个人如果认可自己当下的身份,他的精神就处于相对平衡、健康的状态,否则就是身份的迷失、精神的失衡。然而,当代人并不认可“安分守己”的道德准则,他们渴望身份的提升,心灵为此骚动不安,天长日久,渐成疾患。吴君的小说,包括她的“深圳叙事”系列,都是从这一角度切入当代社会生活,揭示当下人生病相的。
“深圳叙事”系列的所有作品都在演绎一个母题:追寻。所有的人物,离乡背井来到深圳,无一例外都是为了追寻一种新的生活。其追求的具体目标,又可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寻爱”,此类人物集中于中篇小说集《不要爱我》之中。有评论家说,女人写小说,绕来绕去,总是绕不过“爱情”二字,这话有些绝对了,但爱情确是女性作家最关注的话题。《爱情的方程》、《爱比冰更冷》、《不要爱我》、《与爱无关》,单看这些标题,就可以感受到“爱情”在其中的份量。《不要爱我》中的作品,基本都是以年轻女性为主角,女主角的来路多少有些含混,但她们的追求都很明确:爱情和婚姻。但是,越是渴望的东西越是难以得到,爱对于她们,称得上可想而不可得的奢侈品。在《阿米小姐》中,因为停电,阿米与“我”的“爱情鸟”突然飞临。但是,这“爱情”却没有结出任何正果,因为对于“我”来说,爱情远没有深圳户口更有价值,为了户口,“我”留神的都是当地的丑女人。阿米曾经是优秀的女大学生,最终堕落到向老外出卖色相的地步。“如果有人爱我,我就爱她”,这是《爱情方程式》中李媚的爱情标准。可是即使按照这个完全没有高度的标准,也仍然得不到爱情。李媚的丈夫钟培元暗中与人偷情,李媚也在偶然的机遇中邂逅了同自己一样有婚姻没爱情的梁显。“钟培元不把我放在眼里,但总有人把我放在心上了。”就在李媚的爱情生活即将重现光明的时候,梁显却脱身而去,为了保住自己的身份回到老婆身边去大秀恩爱。《爱比冰更冷》中的孙南,真诚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她所爱的人却只把她视为一个晋升的阶梯。这本书中的女子们,要么堕落,要么轻生,结局都很灰暗。她们所追求的,说到底也不是真正的爱情,还是一种身份的认同。她们就在这样的漂泊之中失去了灵魂,其命运结局,也只能随风而去,归入堕落或虚无。
第二种类型是“寻梦”。吴君的主角们所寻之“梦”各有不同。有一些很实在,譬如追寻职位,如《亲爱的深圳》中的张曼丽;追求户口,如《福尔马林汤》中的程小桃,《复方穿心莲》中的方立秋,《樟木头》中的陈娟娟。也有一些不太具体,比较抽象,譬如追寻尊严,如《陈俊生大道》中的陈俊生;寻找一方能够放置理想的彼岸世界,如《出租屋》中的孙采莲和《十二条》中的曹丹丹。追寻本身并没有错,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也就是一个寻梦的过程。问题在于,这些人物的追寻,大多处于一种偏执、病态的状况之中。例如《亲爱的深圳》中的张曼丽,基本算得上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为了地位和虚荣,她不承认自己农民的出身,不惜与亲人割断联系,时时向人虚构自己的“高贵”出身,她不是在生活,而是在表演,虽然演得并不高明。《福尔马林汤》中的程小桃为了摆脱自己“打工者”的身份,直言自己的理想“就是想找一个当地人结婚过日子”,有爱无爱是无所谓的,对方是离婚的还是分居的也无所谓的,她甚至认为“暂时做个二奶也不算委屈”。程小桃的理想没能实现,她遇到的都是一些骗子。即使实现了,又能怎么样?《复方穿心莲》中的方立秋和《樟木头》中的陈娟娟,都是嫁了当地人的,依然没有任何幸福可言。公婆歧视,丈夫偷腥,梦寐以求的户口还是得不到,她们在家中的地位还不如奴仆。《出租屋》中的孙采莲,只是在深圳关外城中村的歌舞厅里做过清洁工,染上脏病后被迫回到老家,却整日在做深圳梦,把深圳作为圣地一样膜拜,灵魂已极度扭曲、畸形。相比而言,《十二条》中的曹丹丹和她的梦想,还没有那么变态,只是有些浪漫情调。她厌倦了在深圳的没有爱情没有活力的生活,记忆中总是浮现北京一个平平凡凡的胡同“十二条”,那是她在读大学时曾经短暂去过的地方,在潜意识的作用下,那里居然升华为一个能够放置理想和趣味的心灵栖息地。好在她最后明白了,那只是自己心造的一片家园而已,人还是只能在当下的“此在”中生存。如果说在追梦的旅程中,还有人的精神基本处于健康状态的话,那就只有陈俊生了。这是个孤傲的人,卓而不群,虽然只是个打工仔,并不悲观厌世,甚至有些精神胜利式的乐观情怀,表现在他在心中把自己常走的一条小路命名为“陈俊生大道”。他其实也是一个白日梦者,只不过多些达观而已,也就没有上述那些薄命女子身上令人绝望的悲剧气息。
是的,“令人绝望”,吴君笔下的人物,就是处于这种身份迷失精神焦虑的绝境之中,她们在命运的漩涡中挣扎,无法自救,也没有救世主拯救她们,只能在挣扎中不断沉沦。读吴君的作品,很难有一个明净的好心情。弗莱认为,文学在经历了以神为主角的神话、以英雄为主角的传奇、以领袖为主角的高模仿、以凡人为主角的低模仿之后,会以智力和能力都低于凡人的人物为主角,我们会以俯视的姿态审视他们。吴君的不少人物,当可归属此类。只是,他们的病态,乃是全人类之病,只不过他们的症状比普通人更严重而已。身份对他们的扭曲,是他们不可抗拒的命运悲剧。吴君对他们的态度,决不能简单地归之为批判和讽刺。吴君同时也以慈悲的情怀,表达着对他们的同情和关怀。
二 理想下移原欲膨胀
然而,批判是不可缺失的,否则,文学就失去了现代性。吴君笔下的人物,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只有欲望,没有理想。理想与欲望,都是需求,都是向往和憧憬,但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理想属于精神层面,是超我性的精神升华;欲望则更多隶属于肉体,是本我式的动物本能。伴随着理想的,总会有光明的前景、英雄的行为、崇高的责任、奉献的乐趣、诗意的氛围、健康的情趣。穿上这些外衣,理想才是健康的美丽的,脱下这些外衣,理想就蜕变为赤裸裸的欲望。某些当代人的精神空间日益萎缩,物欲则日益暴涨。或者说,理想不断下移,不断祛除崇高的色彩,也不断强化本能的成份,终于,理想彻底被欲望所取代。
吴君笔下人物虽然有时也畏惧伦理,渴望尊严,但强大的欲望还是占据了主位,他们追求的对象无非是户口、股票、房子、财富。为了获得这些对象,他们不惜利用婚姻、性、谎言、引诱、欺骗、告密等种种手段。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被原欲驱使的“本我”是被压抑在无意识深处的,原欲必须通过伪装才能在意识中浮现,否则会受到超我严厉的道德谴责。可是在当代,一些人的人格中已没有了“超我”的位置,只剩下赤裸裸的“本我”,欲望已无需升华,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狂奔,道德标准已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约束力。
《海上世界》不能算是吴君的代表性作品,评论界和吴君本人都较少提及。在这里,却有必要把这篇作品作为一个案例分析一番。这个故事发生在师生之间。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大概应是世界上最纯情的、最具有记忆珍藏价值的关系之一。尊师,也是文学常见的主题。吴君创造的这个老师的形象,却是颠覆性的,它揭示了一个老师的人格中如果丧失了理想的成份,将会怎样失去尊严、失去人性、失去起码的道德意识。主角依然是一个从北方来深圳的年轻女性,这个名叫胡英利的女孩子,曾在一家公司做广告员,日日为工作发愁,生活很不得意。现在,她正在赶往“海洋世界”,去见自己10年前读大专时的老师,那个曾经年轻潇洒、风度翩翩,曾经写过朦胧诗和自由诗的老师张爱国。张老师也到深圳来了,并且因为写了一首歌颂“海洋世界”的“特别美”的歌曲,成了这个地区的名人。张老师是胡英利的暗恋对象,他写给胡英利的励志信,影响着胡英利的成长岁月。在胡英利的心目中,张老师仍然是优雅的、高尚的、乐于助人的。胡英利甚至想着,见到才华横溢又有社会地位的张老师,必能获得他的帮助,自己就不用再为工作发愁了。可是,凭借着早年留下的电话联系到张老师并且约定相见的时候,胡英利就感到张老师已经变了。“想不到,他们在异地见面,最后也要上床。”“这个问题差不多在电话里就已经谈好了。”尽管张爱国用的不是“上床”,而是“休息”这个较为文雅的字眼,但是,他在电话里已经“把话说得很直接了”。胡英利“不怕与人上床。不去跟人暧昧,哪有饭吃?”但是师生这种关系,让胡英利觉得“这件事要比强奸来得更痛苦”。见面之后,张爱国在迫不及待的行为中露出庸俗、猥琐甚至卑鄙的一面。他完全没有了当年的洒脱,一面行着苟且之事,一面像失去金钱的守财奴一样向胡英利哭诉:欣赏他的老板因贪污已经倒台了,他失去了靠山。他失去的岂止是靠山,连男人的阳刚之性也荡然无存了。虽然他还能做出当年朗诵自由诗时的潇洒手势,但胡英利再也不会被这个动作迷倒了。这是一个为师不尊的故事,同时也是一则理想在人格中消失、原欲赤裸裸地现身的故事。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张爱国由一个风度翩翩的少女偶像,堕落为一个肮脏猥琐的丑恶男人。
在程小桃、方立秋、陈娟娟等人的头脑里,只有“深圳户口”,其他一无所有,精神世界已彻底成为一片荒漠。记得一位作家曾说过一句精辟的话:“什么是城市?城市就是让乡下人自卑的地方。”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城市都是进城的乡下人可望不可及的高地。城市因程小桃们的身份背景对她们采取拒斥与漠视的态度,程小桃们则为自己的身份背景而自卑。她们在怀疑、悲观、焦灼、痛苦的精神状态中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家园,“我要做城里人,我要做深圳人!”这种欲望在压抑中越来越强烈,在黑暗中疯长,一直到决堤泛滥淹没一切的程度。在《亲爱的深圳》中李水库和程小桂这对还算恩爱的夫妻之间,也在半真半假地讨论相互分手各找性伴以图留在这座城里的可能性。除户口外,还有股票,这种东西曾经让许多到深圳淘金的人一夜暴富。《红尘中》的离异女人泊其,之所以被许多男人想着,一个重要原因是股票。从澳洲回来的前夫阿林想着泊其的股票。邂逅相识的大学生李鸿问泊其“你有多少股票”时,“很响地咽了一口唾液”,还“低头看泊其半透明的衣袋里的纸张,极力想辨认它的份量”。前夫的朋友阿轩,似乎很关心泊其的生活,总是以借书为借口来看望她,还称赞她的美丽。这个家伙最后终于露出了底牌,他问泊其,“你不是有很多股票吗?”然后搓着粗糙的手掌狡黠地笑了:“我知道你有的。不要以为自己老了就自卑。”《岗厦14号》中石春雨的父亲,一门心思是想找回岗厦人的身份,无非是看到了岗厦村拆迁的巨额赔偿金。而石春雨,则又因此成为中年弃妇胡玉则的性欲发泄工具。所有这些人生乱像,用“人欲横流”四字来形容绝不为过。
在理想原则的支配下,我们生存的世界曾被想象得十分美丽。到如今,仍有人相信人们可以在天地之间“诗意地生存”。现代艺术执着地终结着这种“诗意”,用一个时尚的词语来说就是“去魅”。有学者说,“去魅”是指“那些充满迷幻力的思想和实践从世上的消失”。在“去魅”的过程中,与非诗意相伴的,还有非英雄、非崇高、非爱情、非理性的态度,表达着对终极意义、人类理性的质疑。再也没有英雄来拯救,而且,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为真理作判断的公众集体已不复存在”,“个人已从群众中回了家,变成了单独的个人”。周思明认为,对孤独的克制,对世界的憎恨和使个性丧失都是消极的逃避方式,结果就成为弗洛姆所说的“失去自我”。人一旦处于极端孤独的状态,无法获得崇高的光照,自身也只能隐藏在猥琐的阴影里,甚至连自救也变得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君的小说表达着一种具有现代感的文化态度因而显出了特有的深刻。
三 伦理缺失情感破碎
当代人的心灵病相除身份的迷失、原欲的亢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伦理的缺失和人性的泯灭。当“一切美好的友情、亲情和爱情,被无情的肢解”[2]的时候,人类的情感世界已支离破碎,在人与人之间维系和谐关系的纲常伦理日渐疏松。对此,吴君也有着相当悲观的描述。
在吴君的小说中,亲情是极度匮乏的,在“深圳叙事”之外,也是这样。如果你随着她走进东北某城市的那条“灰泥街”,你会明显感觉到,最令你窒息的不是物质的贫乏、身份的低贱,而是亲情的缺失。无论走进灰泥街的哪一家,你都找不到亲人之间的温馨和关怀,而只能看到相互厌恶相互仇视的目光。也许你忘不掉那段描写:小英被一个变态的露阴癖调戏,她哥哥二宝正巧撞上,赶走了变态佬之后,二宝竟骂妹妹是“骚货”。小英也用最恶毒的话语回骂:“他妈的,你为什么不死了,谁让你来坏老娘的好事”,“你他妈的才是骚货呢,你的祖宗八代都是骚货!”二宝居然接着骂出“你这种人,天生就是给人强奸的”这样的话来,兄妹俩的对骂实在令人瞠目结舌。还有小利骂爹娘的那一段,也同样令人崩溃:“他考上考不上关你个屁事,你有什么权力对我的事说长道短?”“你先管好你自家的门,不要一天到晚往家里招野汉子还装着看不见,不就是想让人家帮你养老婆孩子吗!”亲人之间,恶语相伤,居然到了这般礼仪廉耻全然不顾的地步,仇恨完全压倒了亲情,这灰泥街哪里还是人待的地方?真如小利自己所言,这是个“狗屎街,婊子街,窑子洞”。
在深圳叙事之中,亲情缺失这一点仍然被吴君一再强调。《亲爱的深圳》中的张曼丽,对乡间父亲的重病入院、无钱交医药费,完全无动于衷,却向人表白自己的“爹地”住在别墅里,“是位高级领导,每天工作忙得很,除了周末家里举办的宴会,我并不是总能见到我爹地”。在《深圳的西北角》中,四舅的两个女儿之间,姐妹相妒;母亲与四舅之间,姐弟互骗;老家亲人传言王海鸥是“干那事儿的”,恶意诋毁。最终,表妹夫刘先锋强奸王海鸥,还要强占她的美容店,将王海鸥逼上绝路。《念奴娇》的主角皮艳娟,靠在风月场卖笑来养活一家人,包括父母和哥嫂,却又不断地承受着母亲和哥哥的指责和辱骂。最终,为了报复,皮艳娟把自恃清高有所谓“知识分子”身份的嫂子杨亚梅也拉入风月场中,让她也失身堕落,直到离家出走。值得注意的是,皮艳娟的母亲,堪称一个“恶母”,这种母亲形象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但在吴君笔下,却不罕见,如灰泥街上的那些母亲,还有《出租屋》中那个没有给过女儿燕燕哪怕一丝母爱的孙采莲。《樟木头》中的陈娟娟,倒是对女儿百般关爱,可是女儿却对她十分冷淡,亲情依然缺席。这个名叫江南的还在读初中的小女孩,为自己没有当地户口、险些被遣送回老家的母亲感到耻辱,她当面对母亲恶语相向:“你们北方人除了脏、老土,还有什么,如果还有那就是穷。”陈娟娟偷着攒钱买了间单身公寓,为的是能够通过购房获得“蓝印户口”,她女儿竟然说:“如果你真爱我,就应该换上我的名字。”最终,单身公寓被兑换成美金,成为女儿到异国读完初中的学费,“她已经和六约街上那些小流氓混在一起,如果不出去,可以预见接下来的事情,吸毒、打架……”家庭,数千年来都是人们遮风避雨的港湾,一旦失去亲情,家庭就只剩一个躯壳,没有关爱,只剩孤独。
爱情曾是文学的基本母题,可是吴君显然不再相信爱情,或者说,不再相信以往文学中那种纯洁的、浪漫的、忠贞的爱情。她所塑造的男男女女,并不缺少性,但基本没有爱。阿米14岁就勾引语文老师,“从容地向一个女人的道路上提前迈进了”,她“是一个无情的女子”,却又“太喜欢制造一些邂逅的事”。她勾引一个有妇之夫,仅仅是因为那男子对女人从不正视,有神秘感。可是,“只用了两招就抓到手了,你说我还认为他神秘吗?”在小说的结尾处,阿米“和一个冒充美国人的阿拉拍人在酒店里被抓住”,她已经跟暗娼没什么区别了(《阿米小姐》)。曼云可以在网上与男人做爱,可以向公司老板投怀送抱,可是恐怕连她自己也说不清,这里面有没有爱情的成份(《不要爱我》)。离异女人泊其的性生活相当淫乱,她可以和保安、搭客的摩托仔、卖水果的丑男人苟且,只有和阿轩的那一次可以依稀看到爱的影子:“阿轩伏在床上眼里流着爱慕说:‘阿其,我要娶你,我发誓。’”可是泊其的反应却是:“她一面穿睡衣一面拉窗帘:‘好吧,那你讲一讲你有什么本事养活我。’”爱就这么轻易地灰飞烟灭了(《红尘中》、《有为年代》)。阿媚的情史乱到了难以理清的地步,但她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她没有向别人付出真情,别人同样没有向她付出真情(《伤心之城》)。情人之间没有爱,夫妻之间同样也没有。杨亚梅靠色相在酒楼当上了经理,有了靠山,立刻离开丈夫,连一句告别的话都不肯留下(《念奴娇》)。方立秋的丈夫歧视外地来深圳的妻子,在外面偷鸡摸狗,还恬不知耻地向方立秋说:“其实,男人堆里,我算是好的了。”(《复方穿心莲》)陈娟娟的丈夫江正良,没文化,腿脚还有残疾,陈娟娟嫁给他,纯粹是为了一张深圳户口。而江正良却迟迟不肯办理妻子的户口随迁,逼得陈娟娟只好走购房入户的路子(《樟木头》)。孙采莲指着身上的疤痕告诉女儿:“这颗是你爸那死鬼烫的……他始终是个没用的男人,窝囊,没钱,还没骨气。”(《出租屋》)有一个当代女作家也写过无爱的性史,却用了一个很有震撼性的说法:“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而吴君的作品与之相比,却完全不同,不过是随意苟且,利益互换,可谓之“一地鸡毛”,连一点刻骨铭心的记忆都不可能留下。
被吴君颠覆的还有友情。《福尔马林汤》中的程小桃与方小红,曾在共同的打工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无话不谈,相互倾诉着共同的欲望:找一个本地人结婚过日子。也正是这个共同的欲望,驱使方小红背地里做手脚、耍伎俩,最终把那个一起吃过田螺的司机搞到手。《樟木头》中的陈娟娟,遇到的是另一个方小红。她们曾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被带进那个“关押过一些三无人员和特殊职业的女性”的小镇“樟木头”。是陈娟娟用800元钱将方小红赎出来的,但陈娟娟同样的经历也瞒不过方小红。两人曾经是患难与共的好友,同病相怜的姐妹,但终因相互妒忌形同陌路。陈娟娟怎么也想不到,方小红为了报复,竟将陈娟娟不光彩的经历讲给陈娟娟的女儿江南听,导致江南从三好学生堕落为问题少女,还将母亲视为仇敌。总之,吴君笔下的人物,朋友同时又是敌手,她们之间那些琐屑庸俗的明争暗斗,惊心动魄。谁都没有真正的朋友,因而都处于孤独无助的境地。看看《有为年代》中的那个泊其吧,谁也不知道她是“死在中秋节的晚上”,“至于她为什么死,在小镇没有多少人问过,因为她实在太普通了”。是的,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他人即地狱,找不到家园,无处安放自身,在情感的世界里,除了孤独,一无所有。吴君说:“在我看来,现在是价值观最多元,人心最孤独又最浮躁的一个时期。”[4]她把这种孤独和浮躁表现到极致,深刻中带着残酷。
四 结语
“人有病,天知否?”揭露当代人的精神世界的病相,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连上帝都已死去,人的心灵早已无处皈依。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他揭露国民的病况,是为了引出治疗的希望。吴君是否也有这样的愿望呢?恐怕没有。否则她不会采取这种令人绝望的笔触来书写,不会采用非理性、非崇高、非诗意、非爱情、非英雄的写作立场。曹征路说:“吴君看到的现实实在太粗砺太原始太不优雅了,当然也就谈不上‘纯’。我相信吴君并不想启蒙谁同情谁,她只是捧出了这碗‘汤’(小说《福尔马林汤》),不管你能不能接受——让它在每一个细节里都散发着令人不忍卒读的真实和作家的主观批判精神。”[5]在阅读吴君的过程中,我曾想,为什么固执地不肯给一点暖色调、给一点安慰?但我马上又质疑自己:难道还回到理想原则上去吗?没有提供医治的办法,说明作家没有那种乐观和自信。如果吴君也像过往时代宏大叙事中的那些作家一样,向你指点一个光明的前景,你肯相信吗?
通过文化的冲突、人与城市的冲突,吴君刻画了当代人的生存困境,这毫无疑问是深刻的。深刻归深刻,吴君创作的不足之处还是有的。她的视域不够宽,看到的都是底层的、日常的生活和卑微的人群。吴君说,她之所以主要刻画这一群体,是因为“对他们的痛苦体会得更深切”。作家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人物,当然没错,可是底层生活如果不能与现代生活的其他重要领域(譬如官界、商界、知识界的生活)相互渗透,作品的意味就比较单一,人物的多样性也不够。许多人物出身相同,欲望类似,性格也难以区分开来,看得多了,不同作品中的人物容易串到一起去,真正留在记忆中挥之不去的,不多。还有,次要人物和枝节事件过多,导致有些作品有漫漶芜杂之嫌。这些情况在早期的深圳叙事中比较明显,在近期的《十二条》和《十七英里》中,已经有了不小的改善。此外,作为“深圳叙事”,深圳这座城市的都市面貌、独特风情及现代品性,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展示,以至于深圳只是作为一个揭示“现代都市内在沉疴与拷问潜在人性”的符号,缺乏城市应有的质感,也令人遗憾。不过,我对吴君的创作前景充满期待,相信吴君这种对写作有着敬畏之心的作家,作品只会越来越好。
[1] 吴君.《亲爱的深圳》跋:关于深圳叙事[M]//亲爱的深圳.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239.
[2] 洪治纲.深圳:一个理想或隐喻的符号[EB/OL].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9/2009 -09 -03/76411.html.
[3] 深圳商报.深圳的写作和生活[EB/OL].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9/2009 -09 -09/76647.html.
[4] 傅小平.吴君:由开阔走向“狭窄”[EB/OL].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9/2009 -11 -20/79401.html.
[5] 曹征路.另类的城市想象[EB/OL].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9/2009 -09 -09/766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