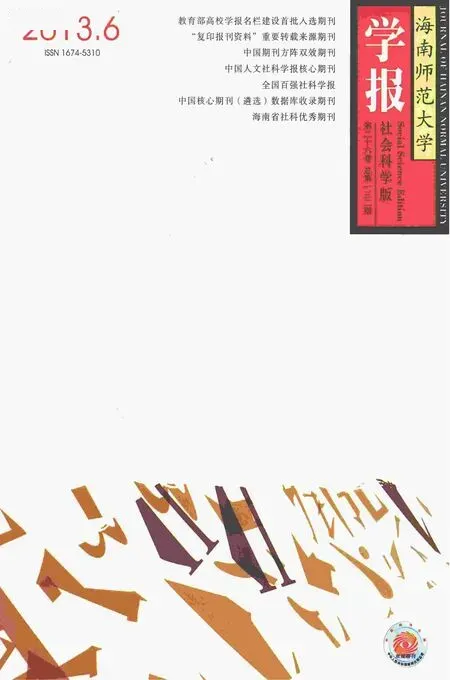一则个人和民族的成长寓言——论《我是我的神》的成长叙事
2013-04-12谢晓霞
谢晓霞
(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 深圳518060)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社会文化也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化。精英文化逐渐失落,知识分子日趋边缘化。与此同时,世俗文化浮出水面,并且以日常生活的名义堂皇地占据了这个时代的舞台中心。那些曾经闪耀着理想的光芒的强大的主体似乎已成为一个过往的神话。人们日渐为沉重的肉身所累,日渐沉沦于世俗价值所提供的感官的享乐之中。邓一光的长篇小说《我是我的神》在这个时候问世,作者以一种现实和神性写作相交融的方式再现了一个关于主体的寻找和重建的神话。这里的主体的寻找和重建既是历史中的个体的自我寻找和确认,是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也是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成长的再现。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我的神》也成为一部中国式的成长小说,它是一则关于个人和民族的成长寓言。新的历史认同和理想主义是这部小说成长叙事的主要精神支撑。
一 个人的成长与主体的生成
《我是我的神》尽管以现实主义作为主要的表达手法,然而,它给我们展现的却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命题,一个关于主体的寻找和重建的命题。正如小说题目的结构:“我是我的神”所昭示的那样,这部小说的重心之一就是困扰了哲学家和思想家若干个世纪的问题:“我是谁?”它是人类的最初之问,也是持续之问。
小说借助一段漫长而又特殊的岁月,共和国从建立到当下,通过一个在战争后期建立起来的革命家庭乌力图古拉一家来演绎这个关于主体的寻找和重建的神话。这个主体首先是一批历史中的个体,他们通过在风云变幻的历史中坚持不辍地对自我的寻找来确立他们的主体地位。其中的典型就是小说主人公,乌力家的老四乌力天赫以及乌力家的老五乌力天扬的自我寻找和确认。小说将这一对兄弟放在了共和国建立之后几十年的大背景中,让他们历经“反右”、“文革”、对苏自卫战、对越还击战、改革开放等等历史的变迁,在历史中成长,寻找并确认自我。因此,《我是我的神》可以看作是一部成长小说,这部成长小说首先记录的是个人的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无论是乌力天赫还是乌力天扬,都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新人,同时也是成长意义上的新人。在小说中,他们的形象不是像传统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是一个定型的形象,他们的形象一直处于成长和变化中。世界和历史在变化,他们也在变化,他们的变化反映着世界的历史成长,他们与世界和历史一同成长。在他们的成长中,“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1]230
作为成长小说,《我是我的神》首先是一部个人的成长史。小说中占据大量笔墨的是乌力家的老四乌力天赫和老五乌力天扬的成长。乌力天赫的成长史就像他后来经历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战争一样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乌力天赫的性格几乎是天生就具有一种理性和思辨的色彩,这使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处于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包括家庭的怀疑和反叛之中。他从小体弱多病,多思虑,后来在乌力图古拉的“法西斯教育”中变得强健,但是他不同于一般的小孩子,能把基地所有的孩子干净利索地摔到地上的他“不想当什么阿爹教养出来的英雄汉”。[2]151他也从来不是处处听父母话的乖孩子。对父母、对家庭、对周围的环境,乌力天赫始终保持着他的冷静和审视。“他眼中的家庭是那么冷漠和怪异,它由他的父亲,那个在传奇年代里获得了英雄称号的统治者凭着自己的意志建立,他是家庭的奠基者和生产者,他成功地完成了他和伴侣栖息地的选择,对家庭成员的生育繁衍、捕食和分配,并制定家庭成员的生命路线。这个生命路线包括现在的吃喝拉撒睡和今后的未来。这个统治者从来不关心他的成员在想什么,想要什么……那不是家庭,甚至连监狱都不是,而是一个巢穴……”[2]223家庭对少年的乌力天赫而言,就是他成长道路上的对手,他要战胜他们。无意中看到的美国人杰弗逊关于自由和平等的一段话不仅让他热血沸腾,还使他进一步质疑他所受到的教育,意识到“没有人关心他是谁,他想干什么”。[2]226正是在对既定秩序的反叛中,乌力天赫一步步成长。后来的散发传单、质疑“文革”、离家出走,成为特种兵、参加世界各地的多次战争,这些事件作为一个历史序列,不仅是情节的展开方式,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成长主人公乌力天赫的成长史。小说中多次提到乌力天赫的成长:“在南方,依然活着的乌力天赫快速成长着。”[2]419他是一个参加战争又质疑战争、时刻对世界、对人类、对自我保持理性和思考,又与战争和历史一起成长的个体。
这个成长过程也是我们的成长主人公哲学意义上的主体生成的过程。从乌力天赫悲愤地发现没有人关心他是谁,他想干什么开始,他实际上已经有意识地进行自我的寻找和建构。在这个自我建构中,一个强大的主体生成了。小时候质疑家庭秩序(父亲的暴力),少年时质疑社会秩序(“文革”)、参加多种战争后质疑世界秩序(人类战争)……在这个时间序列中,乌力天赫成长为一个对历史、对世界、对人类、对自己都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的强大的主体。他不是为荣誉而战的传统英雄,而是现代英雄——一个精神上自由独立强大的主体。“我已经走完了我的一生。我是说,戴着眼罩的一生。我已经结束了我的起源、成长、变迁和死亡。我该死而复生了。”[2]875复生的还有全新的自我——一个新的历史主体。
相比乌力天赫,乌力天扬的成长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普遍的象征性。少年时的脆弱顽劣,流浪挨打的狗崽子经历,长大后参军,无意中成为人们眼中的英雄,对这种英雄的告别,再次流浪,在脚踏实地的生活中找回自我。乌力天扬的成长像所有的成长主人公一样,不仅要战胜成长道路上的一个个对手:自己的脆弱、父亲的专制、环境的恶劣、社会世俗的弊端,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得经历每一个成长中的新人所要经历的精神的危机。在战胜精神危机的过程中,主人公长大成人,认识到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和作用。小时候对自己的软弱的无能为力的抗争、少年时代的犯罪、对越还击战之后的迷茫和困惑……这些精神危机就像一座座炼狱,经过炼狱的锻造,我们的主人公才能长大成人,才能找到自我。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乌力天扬不断地出走、回归,就像小说中所写的:“谁都需要破茧而出,谁都需要出走。”[2]815出走是为了最后的化蝶,为了实现生命的斑斓和壮观。当他经历了这一切,他了悟了生命本身,也找到了自我。“这个世界,有多少东西值得我们打心眼儿里敬重——安静地出生,尊严地死去,至死相爱,可是,我们总是错过它们。……生命它有自己的性子。那么,那就回来,万劫不悔地回来!”[2]829-830正如小说中所写道的,乌力天扬一直在寻找他的天使,但他也知道,他的天使不在天堂,而在地狱,他已经做好了在地狱中寻找他的“天使”的准备。小说最后,父亲进入弥留之际,乌力天扬走出父亲病房,他觉得“他就像贴着地面飞的雨燕,根本不看咄咄逼人的颤抖着的天空,迅速地掠过春天里最后一道余霞,去寻找暴风雨到来的那个方向。他那样沿着走廊走着,无声而沉着,好像他是再生了,不再需要他的父亲,不再害怕找不到自己,而且他是孩子,不断地是孩子。”[2]884
“孩子”的自我确认,也是我们的成长主人公对自己成长身份的确认。只有孩子,才会处于对外在世界的永远的好奇和探索之中;只有孩子,才会处于对自己永远的好奇和完善之中,换言之,孩子才是成长的主体。
二 民族的成长与历史的另一个维度
《我是我的神》在寓言的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一则关于民族成长的寓言。詹明信在谈到第三世界的文学时指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特别当它们的形式是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表达形式的机制——例如小说——上发展起来的。”[3]这则民族的成长寓言,在时间跨度上涵盖了年轻的共和国从建立到当下的一段历史,也就是小说一开始就提到的1949年到当下。这一段历史,在常见的教材中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从成长的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史。
这则民族寓言首先体现为一个家族的寓言。在1949年的隆隆炮声中,蒙古人乌力图古拉遭遇了美丽的国际主义战士鞑靼女人萨努娅,并在随后的1950年组成了一个家庭并先后生育和收养了一大群孩子,乌力家族由此诞生。在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乌力家族像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家庭一样,先后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事件: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反右”、对苏战争、援越战争、对越战争、“文革”、改革开放、阿富汗战争等等。在这个几乎呈线性的历史序列中,乌力家族萌芽、诞生、长大。不同于传统的家族寓言更多的建立在子辈和孙辈对父辈的认同的基础上。乌力家族的诞生和成长不仅始终贯穿着家族的两个创始人乌力图古拉和萨努娅穷期一生的“斗争”史,而且也一直伴随着作为子辈的乌力天赫和乌力天扬对父辈的怀疑、抗争和否定。
80年代的莫言在缅怀中用小说建构了一个响当当的“红高粱家族”,90年代的张炜的家族叙事也在建构家族。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写了一个家族的故事,但这却是一个对传统的家族进行解构的叙事。小说中的主人公乌力天赫从小就对父亲的专制和暴力不满,他甚至不认为自己的家是一个家,他认为那只是父母一起搭建的一个巢穴。作为巢穴的主要功能就是繁衍后代、休养生息。这里缺少的恰恰就是家对每个家庭成员的凝聚力以及家庭成员们对家的认同感。从少年开始,乌力天赫就选择了离开家庭,开始了他一个人的成长。另一位主人公乌力天扬的成长中同样伴随着与父亲的对抗和“斗争”,他几度离家出走,几度经历精神的危机,每一次的离家出走都成了一次次破茧而出的成长和蜕变。在解构了传统的家族之后,我们的主人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开始了自己的成长和自我确认。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关于传统家族解体的寓言也同时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体的成长和诞生的寓言。这种情形在“五四”时期的文学中已经出现过,当“五四”一代开始追寻自己作为主体的身份的时候,他们首先面临的就是传统的家族及其相应的伦理对他们的阻挠,后“五四”时代的写作继承了“五四”时期对传统的家族和家庭的反叛。1949年以后的政治文化结构依然指向了对传统家族和家庭的解构。《我是我的神》在成长的层面上来写这个家族故事,这注定了这个故事的设置和结局必将是对传统的家族和家的解构。
解构了传统家族,在小说中是以战争的方式诞生的作为战斗单元的乌力家族。新的个体,乌力天赫和乌力天扬式的现代英雄,也即主体诞生。这个主体,是一个不断寻找、不断追问、不断完善的主体。他在历史中前行和成长,他是历史的构成部分,历史也进入他的性格之中。在寓言的层面上,这个家族脱胎换骨式的成长故事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家族故事成功地转化为民族故事,最后又在现实的层面上转化为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故事。当然,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家”和“国”在很长的时间里本来就具有同构性。因此,在历史的向度上,《我是我的神》同时也是一个关于民族成长的寓言。这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诞生及其成长。早在晚清的许多文学文本中,知识分子就开始了对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在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少年中国说》等文本中,中国作为遥想中的现代民族国家出现,大量的晚清叙事基本上都是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到了“五四”,“个人”的想象出场,从30年代开始,“阶级”、“民族”成为想象的主体。可以说,1949年共和国的诞生,也意味着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建立在战争基础上的现代民族国家也在经历着一个成长蜕变的过程。解放战争、剿匪、抗美援朝、“反右”、“文革”、对苏自卫战争、对越战争、改革开放,这一系列的历史以时间的方式标记着中国这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从战争年代作为政治共同体的诞生,到后来逐渐发展为政治和文化共同体,到小说结尾,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建立在政治、文化、法律等等多元认同基础上的共同体。在这个成长的链条上,传统的循环论时间观被打破,代之以现代的线性时间观。小说以家族的方式展开叙事,形成的效果恰如巴赫金所说:“现代历史小说的基本任务,就是克服这一两重性:作家们努力要为私人生活找出历史的侧面,而表现历史则努力采用‘家庭的方式’。”[1]534以家族、家庭的方式展开的这个主体的生成故事也构成了对历史的另一种书写。
这种历史不同于正史,但它比正史更具有穿透历史的眼光。小说以家族史的方式展开,但它最终形成了对家族的解构。在解构家族的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个人生成。在主体的自我寻找和自我追问中,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成为历史的一种新的展现维度。
三 成长:新的历史认同与理想建构
作为成长小说,历史叙事不可避免地成为《我是我的神》的结构形式和内容依托,按照时间的线性顺序展开的主人公的成长故事同时也显现为一部特殊意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历史小说。然而,相比中国文学自上世纪50年代以至当下的历史叙事,这部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却体现出了一些明显的新质。
首先,这里的历史不再是叙事主体,它不承担揭示历史的必然性,反映事物的本质规律的任务,历史在这里成为审美的客体和主体生成的环境。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量历史小说中,小说承担着讲述革命历史,使这一段历史经典化的使命,因而,后来的研究者称其为“革命历史小说”,这类小说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4]这里的历史作为叙事主体出场,承担着揭示历史的必然性功能。如《青春之歌》对于知识分子道路问题的揭示,小说“通过林道静的‘成长’来指认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也即个体生命只有融合、投入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中去,他的生命的价值才可能得到证明。”[5]《红岩》对中国革命的讲述也意在参与革命的经典化过程。在这类小说中,个人只是展示历史的工具和手段,历史本身是那个强大的被叙述的主体,它依赖于意识形态的强势话语展开。作家在历史理性的支配下对历史进程和人物命运进行长期的社会预测和预见。《我是我的神》的情节虽然也呈现为一个历史序列,但这里的历史叙事不同于五六十年代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它不承担对历史必然性和本质规律的揭示,它本身是作品的审美要素构成之一,是审美的客体。这里的历史叙事的功能是构筑主体的精神成长史。在理想的意义上展开的主体的精神成长注定了这部小说的历史叙事是一种开放式的历史叙事,它叙述的是开放性的历史,而不是已完成的历史。
其次,这部小说的历史叙事体现出一种新的历史认同。这里所说的新的历史认同指的是贯穿整部作品的那种强烈的历史承担和历史关怀。《我是我的神》的历史叙事虽则是反本质主义的历史叙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就顺应了90年代以来的消费化的历史叙事,在新历史的幌子下游戏历史、娱乐历史和消费历史。在《我是我的神》中,伴随着小说叙事展开的,是一代人在历史中执着的自我寻找和追问。小说在父子两代人中展开,不管是从被子辈否定和超越的父辈乌力图古拉的身上,还是在成长中的子辈乌力天赫和乌力天扬身上,作家着力表达的无一例外的是对历史中的人的寻找,对历史中的人的精神的构建和追寻。换句话说,作家想给我们重新寻找的是历史中的男人和英雄,想给我们展示的是一种开放式的英雄精神和理想人格。这无疑构成了对一些新历史小说放弃历史承担和历史关怀,将历史娱乐化、欲望化和消费化的一个有力的反驳。
理想主义是《我是我的神》的成长叙事的另一精神支撑。整部小说体现出一种开放式的理想主义探索,它是一次通向理想的跋涉之旅。伴随着主人公的成长的是历史中的主体的不断地自我寻找和追问,在主体的自我寻找和追问中,新的“英雄”诞生。这些新的英雄,是一些孤独的、思考的、敢于承担的哲学意义上的“主体”。他们不仅始终在反思自我和追寻自我,而且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人类的反思和追问。在乌力天赫的身上,我们就能看到这一点,如少年时对“文革”的质疑,参加过多次战争后对战争的质疑,对人类秩序的思考等等。从乌力天扬的成长,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人对自己的生活和人生的寻找和承担,乌力天扬的那句“不能让生活干掉任何人”,同时也表达出对世俗化的抗拒。总之,由于理想主义的加入,《我是我的神》的主体探索和重建表现出一种有别于当下流行文学的鲜明的对抗意味。这就是主体重建对于主体沦丧的对抗,英雄叙事对于日常伦理的对抗。
在《我是我的神》的封底上有作者这样一段话:“如果我选择我的宗教信仰,我将选择这样的上帝——他是一种理想的道德境界,是真理、至爱、至善和感恩的结合,他将带领我走向神性生活的实现……”在日益世俗化的今天,阅读《我是我的神》,我们不仅为曾经的那段历史感动,更为人类不屈不挠地向着理想的曙光前行的激情和勇气所感动。在这则关于个人和民族的成长寓言中,不管是个人的成长,还是民族的成长,都是一种通向那充满神性光芒的理想的跋涉之旅。当历史中的英雄已经成为往事,我们该如何做一个现代的英雄,一个不断地朝着美、善和爱进行自我寻找的英雄,这是《我是我的神》所要传达给读者的重要命题,也是我们迫切需要开始思考并行动的重要出发点。
[1]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 邓一光.我是我的神[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
[3] 〔美〕詹明信(詹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M]//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23.
[4] 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2.
[5]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