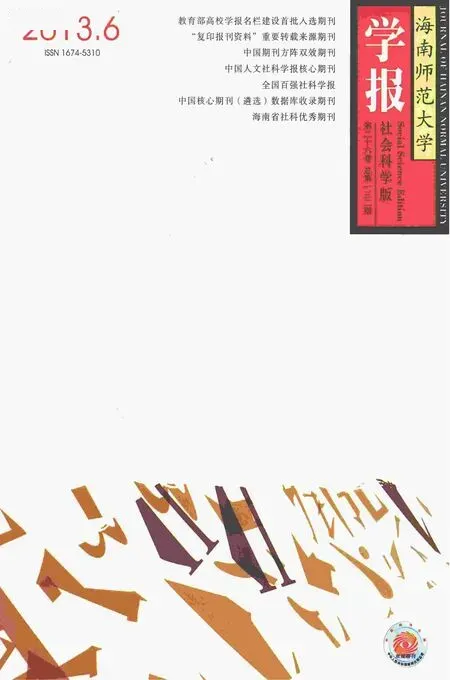《茶馆》:公共空间、私人空间、制度及人生真相
2013-04-12王建光
王建光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1957年,老舍创作了话剧《茶馆》,随后,这部话剧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搬上了话剧舞台。五十多年来,《茶馆》几乎成为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员的必修科目。可是,我们不禁要问:当我们谈论《茶馆》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些什么?在《茶馆》中,近50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浓缩于三幕剧作中,那是一步步走向崩溃的现代中国,黑暗的历史终结了,新的纪元开始了。“变”成为这种认识中的关键词,甚至可以说,它是我们认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关键词。那么,老舍在《茶馆》中是否也在思考相对“不变”的问题呢?是否也在思考超越中国问题的问题呢?或许,我们长期以来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茶馆》这一大舞台的复杂意味。
公共空间:永远的“茶馆”
每个城市都有无数的公共空间,比如,广场、车站、标志性的大街、公园、校园、酒楼、澡堂、妓院、公共汽车,等等。当我们审视这些公共空间时,市民生活一览无余,进而可以了解一个城市的性格、气质。茶馆正是典型的城市公共空间,这个公共空间中的人、事是老舍最熟悉的。“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我知道他们做什么,所以也知道他们说什么。”[1]这个公共空间是开放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可以自由进出,算命的、遛鸟的、人贩子、吃洋教的、打手、特务、乞丐、太监、说书人、女招待,等等。市民们在这里谈天说地、做生意、和解、炫富、互相挤兑,打发着日子。这是一个贫穷与富裕、善良与邪恶、美与丑并置的空间。一个乡下人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往往是在他身处这样的公共空间时产生的。同时,一个乡下人对于城市生活的痛恨,也自然是与他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境遇分不开的。开放几乎是所有城市公共空间的特点,中外没有什么差别。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这个公共空间又往往是压抑的。在裕泰茶馆,“莫谈国事”这个字条历经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北洋政府时期、抗战胜利之后等三个不同的时代,却仍旧贴在茶馆的柱子上、墙壁上,并且字还变得越来越大。何谓“莫谈国事”呢?市民可以在茶馆里说神论鬼,却不可以谈论政治,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民众,却没有资格、权利来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当然,偶尔顺着统治者的意思说上几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一旦发表自己的观点,问题就变得严重起来。第一幕中,常四爷面对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社会现实,他说到:“大清国要完!”特务吴祥子、宋恩子就将他逮捕入狱。在第三幕中,国民党市党部更是打算把裕泰茶馆完全变成监视舆情的重要站点。因此,对于那些善良的人、无心机的人,这个城市公共空间又可能是最危险的地方。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统治者以“莫谈国事”这样的字条宣告了它永远的在场性。但是,在政治生活之外,这个公共空间的主宰性力量是什么呢?黄胖子面对常四爷被逮捕时说的话极具代表性,“官厅儿管不了的事,我管!官厅儿能管的事呀,我不便多嘴!(问大家)是不是?”市民日常生活中的调解人完全无力、也无意于挑战统治秩序。所以,市民们见面热热闹闹的寒暄,看似客客气气,却是野蛮的。这是一个强者为王的丛林世界,二德子、马五爷、黄胖子、庞太监、吴祥子、宋恩子、小二德子、小唐铁嘴、小刘麻子等人尽显他们的嚣张跋扈。我们常说这部剧作采用了子承父业的人物结构,体现出老舍在话剧人物设置上的精巧性。其实,在野蛮的市民世界里,为恶者往往越来越凶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强者的地位。第二幕中,刘麻子本来与两个逃兵谈生意,却在抓逃兵的大令到来时被当作逃兵,在裕泰茶馆的门口被砍了头。对于小刘麻子来说,父亲的悲惨遭遇简直就是个笑柄。所以,他会在父亲的命运中寻到“启示”,那就是找到足够强大的后台。
开放、压抑、野蛮的城市公共空间塑造了市民的精神。一个人在孩童时代,天真烂漫,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可是,当这样的孩子逐渐长大,他穿梭于城市的各个公共空间,看到的是无情的现实人生。长辈的训导、自身的无数次碰壁使得其对他人的不幸遭遇逐渐视若无睹。
王利发 (过来)常四爷,您是积德行好,赏给他们面吃!可是,我告诉您:这路事儿太多了,太多了!谁也管不了!(对秦仲义)二爷,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常四爷 (对松二爷)二爷,我看哪,大清国要完!
秦仲义 (老气横秋地)完不完,并不在乎有人给穷人们一碗面吃没有。
第一幕中,常四爷的热情、善良瞬间便在这无情、冷漠的公共空间中消散了。冷漠往往成为市民保全自身的必备条件,善良则常常被嘲笑。
公共空间的压抑使得市民无法有效地思考政治问题、文化问题,他们不满于统治者的论调,可又自觉地接受了统治者的论调。《茶馆》中,洋烟、洋表、洋教等都成为丑陋的象征物,这与老舍的人生经历有关,也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普遍遭遇有关,但更与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的利益而散播的排外言论有关。所以,市民往往是媚洋与仇洋的结合体。他们奉行强者为王的野蛮逻辑,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过程,在他们的眼中只是强与弱的对抗,他们既痛恨强者的野蛮,骨子里又神往强者的野蛮。这种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看似与市民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却在无形中加重了他们的苦难。从小穿梭于无数公共空间的市民,往往自得于见多识广,可是他们又无法对自我进行理性的观照。他们常常谈论大问题,却无力思考大问题。在贫穷与富裕、善良与邪恶、美与丑并置的公共空间,他们仇视权贵,又艳羡权贵。他们不懂得谭嗣同的追求,不懂得秦二爷的追求,在社会的大染缸中安于庸俗的生活趣味。他们一面承受着巨大的人生苦难,一面嘲笑着更为不幸的人。
刘麻子:(凑到松二爷、常四爷这边来)乡下人真难办事,永远没有个痛痛快快!
松二爷:这号生意又不小吧?
刘麻子:也甜不到哪儿去,弄好了,赚个元宝!
常四爷:乡下是怎么了?会弄得这么卖儿卖女的!
刘麻子:谁知道!要不怎么说,就是条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里嘛!
嘲笑似乎可以平复内心的不安、惶惑、恐惧,更可以让他们在冷漠、狭隘、庸俗中永远居于胜利者的位置。因此,一个人如何从市民世界突围,是重大的人生命题;我们如何重塑城市公共空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
私人空间:走向凋敝的“裕泰茶馆”
在这部剧作中,裕泰茶馆既是一个城市公共空间,又是王利发一家人的私人空间。这种重合使得《茶馆》完整地呈现了市民的生活,同时,也呈现了城市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的挤压过程。
第一幕中,当房东秦仲义打算收回茶馆时,王利发以自己的父亲与秦仲义的情义关系来应对这个问题。第二幕中,伙计李三抱怨着工作的艰辛,可是在王利发与李三之间的拌嘴中分明可以感受到老板与伙计之间浓浓的情义,他们并非单纯的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在妻子的劝说下,王利发最终收留了康顺子和康大力,也不是基于生意上的考虑,而是基于情义。对于王利发来说,裕泰茶馆就是他的家,他苦心经营着这个家。时代流转,这个家遭遇无数挫折,可它始终有着温暖人心的东西。因此,城市公共空间的压抑、野蛮未必会导致市民精神世界的完全扭曲。可是,这个家又是脆弱的,任何大的社会变动都会影响这个私人空间。裕泰茶馆里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可是茶客们还是有意无意之间会去触碰“国事”,王利发只好小心周旋着。第二幕中,当报童叫喊着战争新闻从裕泰茶馆门口经过时,王利发无奈地问着“有没有不打仗的新闻”。裕泰茶馆还没有正式重新开业,仗还是要打起来,城里出去打仗的士兵的口粮还是要王利发这样的市民来供给。王利发颇识时务,小心经营着这个家,可无论怎样改良都无法改变裕泰茶馆一步步走向凋敝的命运。
在强者为王的城市中,任何不去遵循这一规则的人最终都得面对王利发的命运。城市公共空间的特征决定着私人空间的处境,王利发之所以选择自杀,在于他的人生哲学到头是一场空。几十年的生活中,他知道自己无力改变城市公共空间的面貌,只好一面小心适应着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则,一面勉强守着为人处世的底线。这苦心经营中可以看出普通市民生活的坚韧,又何尝没有生活的无奈呢?如果说,在王利发年富力强之时,尚能周旋着、应付着,可当他心力交瘁之时,连周旋、应付都难以为继。压抑、野蛮的城市公共空间最终吞噬了王利发,吞噬了裕泰茶馆。因此,在王利发的身上,何尝没有《骆驼祥子》中祥子的影子呢?“所有这一切却都并不意味着,假如祥子的个人人格再健全一些,他的命运悲剧就会得到任何的改变。事实上,就作品的大部分来说,作者刻意表现的正是祥子性格中的向上因素,他的爱体面、负责任,却不但不能将他从困境中救出,相反却使他沦入了更深的深渊。”[2]王利发的性格固然与祥子有所不同,可是他渴望本本分分、安安稳稳生活的理想与祥子的追求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王利发身处恶者跋扈、善者苦痛的城市,他对野蛮的生存法则的拒绝,就是其一生踉跄的原因。
因此,《茶馆》依旧体现了老舍对市民命运的深刻洞察。我们常常言及老舍在建国之后的文学创作的变化,而这种对市民命运不变的观照恰恰是《茶馆》成为文学艺术经典的原因所在。
制度的迷雾与人生的真相
从茶馆这一城市公共空间的特征与市民的精神、命运之间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老舍期望通过制度的变革来拯救市民社会这一认识的合理之处。的确,当一种社会制度能够保障城市公共空间是开放的、自由的而非压抑的、良序的而非野蛮的,市民的精神、命运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正是“五四”以来,一代代中国人追求的理想。但是,无论是在何种制度下的市民社会,对金钱、权势的疯狂追求又把人的贪婪、自私暴露无遗。这样说,并不是认为制度的变革对市民社会毫无益处,而是期望我们能从制度与个人的关系中走出来,去思考人生问题。
当我们把个人的福祉完全寄托于制度的变革时,仍旧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别人。制度越来越完善,个人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幸福。这个美丽的允诺把个人问题的解决抛给一个毫无把握的未来世界。这是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制度与个人关系的核心问题,我们曾经历这种单纯的制度信仰所带来的巨大苦难。因为,以制度问题作为充分的理由,个人的问题往往被悬置起来。为了制度、为了城市公共空间的重建,却常常牺牲市民的利益,压抑市民的精神诉求;重建市民社会时,市民却常常是旁观的。更何况制度究竟能够重建一个什么样的市民社会,又往往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此,对任何制度都保持批判性,方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前提。也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个体的独立性,保证个体拥有参与制度构想、重建城市公共空间、捍卫私人空间的神圣权利。《茶馆》中的王利发身在城市,却只能被迫地承受城市生活,他经营的裕泰茶馆就是一个城市公共空间,他却无法在其中建立合理的规则。一切只能是苦苦的等待。制度应该是充分尊重、释放个人权利,但它却常常绑架个人,而这正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问题之一。
之所以期望我们能从制度与个人的关系中走出来,去思考人生问题,还在于裕泰茶馆老板王利发的命运不只是一个中国的问题,更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命运问题。对于中国社会而言,《茶馆》呈现了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北洋政府时期、抗战胜利之后等三个时代的变迁史。但对于王利发来说,三幕剧作分别呈现了人生的三个阶段——意气风发的青年时期,惨淡经营的中年时期,苦苦挣扎的老年时期。老舍在这个层面触及了人生的真相,因为王利发所经历的这一人生历程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生命的历程,又有多少人能够改变这个普遍的命运呢?对于人而言,制度是外在的因素,我们也常常只看到这个外在因素。我们以为有了合理的制度,王利发的日子就不会如此凄惶。其实,任何制度都无法使得人们生活在静止的、乌托邦的幸福之中。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衰老就已经开始了。在这三个人生阶段中,王利发的不同处境固然与裕泰茶馆的经营状况相关联,但是,意气风发、惨淡经营、苦苦挣扎又何尝不是一个更为普遍的人生景象的写照呢?这个人生问题,怎么可能单纯地通过制度去解决呢?即便城市公共空间是开放的、自由的、良序的,私人空间是温情的、祥和的,都无法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当我们单纯地寄望于制度来解决人生问题时,制度也许会进一步扭曲人的生活。不过,这至少是一件看起来似乎有希望的事情,哪怕这希望也常常不过是哄骗自己的念想,或者是发泄自己不满的借口而已。但是,当我们直接面对人生的真相时,却常常感到悲观、绝望。当然,在人的一生中,也并非时时刻刻都在面对这一人生真相。在《茶馆》的第三幕中,当王利发与同样已届古稀之年的常四爷、秦二爷一起回首往事时,才发现每个人曾经的努力都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化为乌有,每个人只剩下衰老的身躯。此时,王利发似乎第一次真正看清了人生的真相。活下去,突然成了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对人生彻底的悲观、绝望使得王利发选择了自杀来结束自己的一生。我们已经谈及《茶馆》与《骆驼祥子》在精神层面上的延续性,“祥子的故事是一个更其绝望的故事。在我们所熟悉的俄国或法国现实主义小说中,主人公在经历一番地狱或炼狱的痛苦之后,最终趋向的,往往是精神的净化,灵魂的升华。祥子的故事则不然,这里只有堕落,没有救赎,比外在的地狱更为阴森恐怖的,是人心的地狱。”[2]王利发的故事同样是一个更为绝望的故事,因为王利发的自杀同样让我们无法释怀。因此,老舍在《茶馆》中思考的问题依旧是多年萦绕在他心头的人生问题,即当人面对人生真相时,如何才能从悲观、绝望中挣脱出来?或者说,究竟有没有可能挣脱出来?人究竟怎样来安放自己的灵魂?
我们期待制度的变革来重建一个良序的市民社会,但也需要找寻应对人生真相的方式、途径,而后者也许是人的一生中更为重要的问题。老舍认为《茶馆》的创作目的是“葬送三个时代”,他似乎以此关上了历史的大门,可是无数的人的命运还在眼前,问题似乎还是人类一直以来要面对的人生真相问题。这也许是《茶馆》这个大舞台复杂的意味所在。
[1] 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C]//曾广灿,吴怀斌.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1985:640.
[2] 邵宁宁.《骆驼祥子》:一个农民进城的故事[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