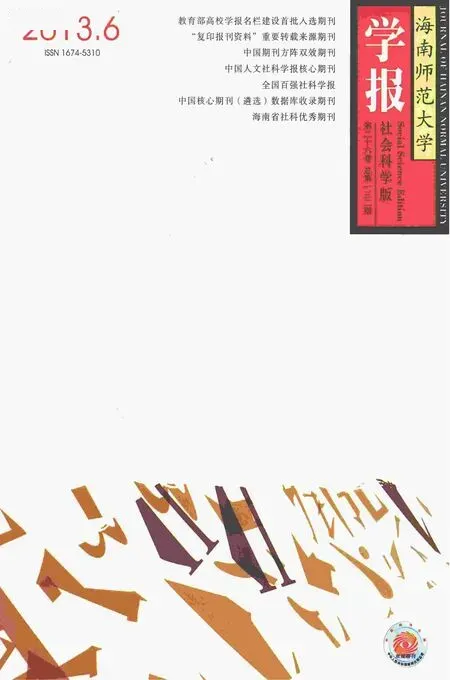论中国小说创作主体的创作原则的转换
2013-04-12李宗刚
李宗刚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离不开中国小说的创作主体的创作原则的转换。正是由于不同于传统小说的创作主体,以及这些创作主体在从事文学创作时所恪守的创作原则的转换,才使得他们所创作出来的小说,和传统小说具有了本质的区别。在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一方面,创作主体的审美情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即审美情感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转换了的审美情感促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1]另一方面,创作主体所恪守的创作原则出现了转换。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其所恪守的文学创作原则经由了以“礼”的文学创作原则为起点,经由对政治原则的认同和推崇,最后完成了对以人为本位的文学创作原则的转换,正是在此历史过程中,中国小说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
一
在传统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用来衡量一切事物(其中亦包括人)的惟一的价值尺度是“礼”。“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规范理性基础上的。它要求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成了一种绝对精神、绝对规范,人则被完全地纳入到‘礼’的固定模式中,人成了‘礼’的证明物,人的价值取决于对‘礼’的证明程度,人成了非人,人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思考力和对自我的观照力。”[2]由此说来,“礼”的创作原则是先验的绝对的,超然于人之上的,这样的“礼”恰如董仲舒所指认的“道”,具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恒久性和先验性,而人则只能成为这样的“道”的恪守者,否则的话,就会悖逆了“天道”。
正是基于对“礼”的无限推崇,致使这种原则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不仅对人的行为起着规范作用,演化为人的行为准则,而且在文学创作中,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作家创作时所恪守的基本原则,这种类似西方的那种“绝对理念”的原则,对创作起着直接的指导和规范作用。由此说来,“礼”的创作原则,从根本上说,是创作主体在进行创作时,生活的真实是怎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构建起来的文学世界里,作家要依据“礼”的原则来进行表现,只有符合“礼”的基本原则的规范要求而建构起来的文学世界,才是符合规范要求的理想世界,也才是对“载道”皈依的文学世界。这样的文学世界,在读者阅读接受时能够起到“教化”作用。这样的文学创作,便使得创作之前的“理念”得以“先行”,而至于真实的“生活”到底是怎样,则毫不影响其创作的结果。对此,我们把创作主体用来表现现实存在和理性认同的价值观中“礼的原则”称之谓“礼”的创作原则。显然,这种“礼”的创作原则是和基于以人为本的真实性原则相对立的。
正因为“礼”的原则获得了存在的绝对的先验性,致使作为“人的文学”的小说,必然打上了“礼”的深刻烙印,使得“人的文学”变成了“礼的文学”。一般说来,为了确保封建帝制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那些掌握了一定的社会话语权的大儒,制定了种种旨在规范人的行为的一套“礼”的程序,这套程序之所以能为掌握最终话语权的帝王所推崇,恰是其迎合了专制统治的根本需要,进而使得这样的“礼”的程序被纳入到了国家体制之中,获得了理念上的推崇和行动上的落实。因此,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小说创作,自然而然要被打上“礼”的烙印,成为国家意志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
基于“礼”的规范而建立起来的文学世界是和“人”的内容相排斥的。由“礼”占据着主导文化的创作原则,势必会导致创作主体在创作和艺术构思过程中,将“礼”的价值规范作为最终皈依点。也就是说,作家从“礼”的创作原则出发,完成对于现实人生的艺术取舍和加工,真实的人生在艺术观照中发生了形变,使“人”成为附丽于“礼”之上的存在物,而不再是具有自我个性乃至复合性格的活生生的“人”。当然,这样一些附丽于“礼”的原则下而建构起来的文学世界,其是否符合真实的人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符合“礼”的原则要求。
严格说来,以“礼”为指导思想的文学创作原则,和传统小说所认同的小说教化、劝诫功能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如果说教化和劝诫是身在封建体制中、掌握着一定话语权的文人士大夫之所以认同小说的内在根据的话,那么,是否能够更好地恪守“礼”的文学创作原则,则是衡量是否实现教化和劝诫的重要尺度。这种情形在中国传统小说创作中可谓比比皆是。如中国传统的言情小说《玉娇梨》,其所叙述的是才子苏友白和佳人卢梦梨在爱恋过程中的种种曲折。本来,在封建礼教的压抑下,言情小说是最能体现出“人性”和“理性”冲突的文学作品,也是最能够否定封建礼教合理性的文学作品。但是,基于“礼”的文学创作原则之上的言情小说,却是舍弃了真实的人生,先验地把那种体载着“礼”的规范要求的才子佳人的小说模式,直接搬到了其文学世界中,至于人物自身的复杂性格和丰富感情,则完全受制于是否符合“礼”的规范要求。由此所展现出来的文学形象,就成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中的“礼”的诠释物。在此,那些能够承载起“黄金屋”“颜如玉”的“书”,显然是那些诠释“礼”的“四书五经”,至于那些和“礼”背道而驰的“书”,则不在其列,甚至还被冠以“诲淫诲盗”的恶名,被打入严禁阅读和传播的冷宫。如此陈陈相因的“才子佳人”的模式,并不是从真实的人生出发,而是通过对真实人生的恪守和皈依,完成艺术上的构思和创作上的外化。这种情形便如曹雪芹所批判的那样:“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入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拔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3]5曹雪芹的这番话语,正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传统小说因循“礼”的文学创作原则所带来的必然的艺术弊端,这也是曹雪芹之所以能够超越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模式,创作出不朽的文学作品《红楼梦》的内在根源。在创作《红楼梦》的过程中,曹雪芹所恪守的文学创作原则是基于对人的理解和尊重的真实性原则。对此,曹雪芹曾经这样说过:“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在传统的晋升轨道中“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3]1。其实,曹雪芹正是基于对“礼”的道德规范的抗拒,或者说,正是“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才使得自己最终没有进入到社会正统秩序所规范的“学而优则仕”的行列中。正是基于曹雪芹对传统规范的抗拒,才使得他在创作小说《红楼梦》时,规避了以“礼”为核心的文学创作原则,以自己“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为创作对象,然后对其“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正是由于对真实人生的体察和表现,才使得中国传统小说达到了其可能企及的最高峰,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红楼梦》成为那个时代的社会史、社会心理史、经济史、政治史和文学史诸多元素的“集合体”。
然而,像曹雪芹这样不把文学创作当作“终南捷径”的作家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作家还是把文学创作当作进入国家体制的一种方式,这就使得“礼”的文学创作原则犹如一条根深蒂固的盘踞于人的意识深处的难以逾越的法则,其必然结果便是产生出“瞒和骗”的文艺。对此,鲁迅曾说过:“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4]如果说鲁迅只从国民性的角度阐述了“瞒和骗”产生的原因的话,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点,即“礼”的文学创作原则,也使得小说被迫在其虚拟的世界中进行着想象和外化,但无法触及到真实的现实人生,因为,一旦触及到现实的真实人生,那无所不在的悲剧,必然使得“礼”的文学创作原则无法施展。很多的文学作品,只能在符合“礼”的规范之下,通过人造的“大团圆”,“令人如释重负,觉得天皇毕竟圣明,好人也终于得救。”[5]这种“团圆主义”的出现,正是“礼”的文学创作原则要求的必然结果。
同样值得我们玩味的是,作为“异类”存在的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因为没有恪守“礼”的文学创作原则,才得不到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体制的认同,直到今天,有关作者的身世,依然在官方的文献典籍中难以找寻到蛛丝马迹,而《红楼梦》则被作为“诲淫诲盗”的作品,只能在民间以手抄本的形式而流传,其中的悲剧意义自不待言。
二
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着国家危机和社会危机,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说,整个国家在世界化的潮流中,被强迫纳入到了这个世界一体化的体系中,因此,国家的主权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领土的完整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救亡图存成为了时代最为关键的问题,因此,在政治层次上进行变革成为时代的主潮,而以“礼”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则失却了其所需要的历史土壤。此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体现在小说的创作中,则表现为“礼”的文学创作原则也相应地失却了一统天下的局面。取而代之的是与政治变革层面的要求相一致,在小说的创作中,则表现为小说也要服务和服从社会的政治变革这个中心点,那种以“礼”为统领的文学创作原则就被以政治原则为主导的小说创作原则所取代。
所谓从政治原则出发指导小说创作,是指创作主体的创作目的是适应其“开通民智”的政治需要,在创作中侧重于政治上的批判和启蒙,从而把人的政治内容特别凸现出来,但是,人之作为人的其他丰富内容则依然处于被抑制的状态。这种情形,主要体现在晚清兴起的政治小说创作中,代表性的人物有晚清谴责小说作家吴趼人,以及作为改良派的梁启超等。
在用政治原则处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时,它所要求的是政治上的真实。这相对于那种对现实存在采取完全排斥的“礼”的文学创作原则的情形有着质的差别。它标明晚清小说向真实性方面推进了一大步。政治小说从虚幻的“礼”的王国,终于回到了现实政治的大地之上,虽然在回归的过程中,政治小说还未寻找到真正植根的那一方土地。晚清政治小说所皈依的政治原则已经不再是一成不变的“礼”,而是从西方输入的现代意识,尤其是西方现代的政治意识。并且,在现实的政治变革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革派,就是要用西方的现代政治制度,来改革已经病入膏肓的封建帝制,进而从政治制度上能够和西方的现代政治制度相对接。从这样的政治目的出发,在晚清的小说,尤其是晚清的政治小说创作中,就出现了直面政治现实的文学,并使得小说的创作基点回归到现实中的政治真实上来。
较好地反映出小说创作中的政治原则的是晚清所出现的“谴责小说”以及梁启超所倡导的政治小说。在吴趼人所创作的“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我们可以发现,这部政治小说正如其标题所点化出来的主旨那样,它所关注的中心对象是存在于社会中的“怪现状”,即小说以突出“现状”为核心,而至于承载起这“怪现状”的“人”,则仅仅获得了载体的作用,“人”还没有成为文学创作所关注的焦点。但是,这相对于以“礼”为文学创作原则的小说而言,则具有了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在关乎理念先行还是现实存在先行上,它已经舍弃了附丽于礼教之上的文学世界,取而代之的是真实的“怪现状”,这相对于前者而言,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革。当然,因为要突出“怪现状”,作家在政治原则指导下进行的小说创作,还没有移植到对于人的真实性的艺术基点上来。但是,因为其对真实的关注,也就为“五四”时期的现代小说恪守的人的真实原则,抬高了创作的基点。这一点恰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作者经历较多,故所叙之族类亦较夥,官师士商,皆著于录……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6]286过去,我们在解读鲁迅的这段话语时,往往把解读的重点落足于后者,强化了鲁迅所“惜”的方面,而没有看到鲁迅所强化的前者。其实,在前者中,鲁迅对“谴责小说”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意味着中国传统小说创作的基点,已经开始位移到了真实的社会生活这一基点上来;至于鲁迅所“惜”的方面,则是鲁迅从现代小说创作的基本原则,尤其是从文学创作中的人的主体性方面所作出的现代解读而已——其实,如果“谴责小说”没有了鲁迅所说的“惜”的方面的话,那中国的现代小说岂不早就诞生了吗?显然,鲁迅在这里的解读,并不是从历史发展这样的纵向来进行阐释的,而是从客观存在这样的横向来进行解析的。如此说来,“谴责小说”正是依托着对政治原则的恪守,打破了那种以“礼”为创作原则的小说传统,实现了小说创作原则基点的位移,这就从点滴之处,开始了拆除传统小说基石的伟大工作,这恰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成长着的精神也是慢慢地静悄悄地向着它新的形态发展,一块一块地拆除了它旧有的世界结构。”[7]这无疑也是晚清至“五四”文学运动时小说创作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真实写照。在促成“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的众多力量中,对“礼”的文学创作原则的摒弃,恰是这个决裂历史过程必不可少的一个历史“链条”。这恰如诗人所描述的那样:“冬天来了,春天还远吗”一样,开始把创作基点转移到了政治真实之上的政治小说已经来了,那么把创作基点转移到以人为基点的人的文学上来,自然也就不再那么遥远了。当然,由于在晚清的政治小说中,并没用塑造出成功的人物形象,也没有出现具有深刻历史反响的成功之作。
在政治小说盛极一时的历史过渡时期,还有一种极力张扬人的情感的言情小说,其基本的价值趋向表现为对于“情”的特别推崇,“情”成为言情小说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但是,由于其所认同的“情”还是在“礼”的规范下而扭曲了的情感,因而其基本的创作原则还是“礼”的文学创作原则,只不过,这里的以“礼”为主的文学创作原则,更多的把笔墨用在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书写上。值得肯定的是,这对于传统的一味地拒绝“情”在文学创作中的合法性地位而言,依然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把言情小说和政治小说,都看作是中国传统小说由传统向现代形态转换的一个“链条”。
尽管言情小说的创作并没有在根本上把创作的基点转移到客观现实真实这一基点之上,依然作茧自缚一般地把那一个个的情爱故事,局限在缠绵绯恻的个人天地之中,终究难以逾越雷池半步,进而使小说创作的基点完成向人的真实世界的转换。但是,它毕竟显示了历史在转换的某些基因,这便是由于其对于“情”这一关涉到人的重要内容的透视,也就难以避免地会触及现实存在的人的情感的某些方面,从而在客观上为现代小说的进一步转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徐枕亚的《玉梨魂》。
《玉梨魂》中的男女主人公在不可自抑地坠入情网之后,又不可避免地在心理深处产生一种悖违礼法的罪恶感,并由此而竭力用旧的礼教观念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随生命而与生俱来的“情”是难以遏止的,所以男女主人公的那种由“情”与“理”所织成的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最终只能在他们的“殉情”中获得圆满解决。在此,值得我们重视的并不是作者怎样用“礼”的观念来调和矛盾,而在于作者敏锐地触及到了“情”与“理”这样一对矛盾,并且把受这一对矛盾煎熬的男女的痛苦不堪的真实情形展现给我们。①参阅李宗刚:《〈玉梨魂〉:爱情悲剧和人生哲理的诗化表现》,《文艺争鸣》,2010年第11期。这在客观上闪耀着人的情感觉醒的光芒,对促成人的情感觉醒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显然,这与传统小说中漠视“情”存在的情形有了较大的分野。至于这篇小说刊出后能够风靡一时,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恰是因为这篇小说在“礼”的重重束缚下,触及到了那些痛苦而呻吟着灵魂,这对那些有着相似境遇的读者而言,恰是“借他人酒杯,浇自我块垒”的载体,引发了读者的强烈共鸣。
如果把《玉梨魂》和传统的言情小说加以对照,我们可以发现,就才子佳人的小说范式来说,它不如《玉娇梨》,《玉梨魂》中的男主人公已不比昔日风流倜傥的苏友白,佳人亦不是待字闺阁、年方二八的妙龄少女,而是婚后丧夫的寡妇,这便在更大程度上贴近了现实生活的真实。就小说在“涕不自抑”时的诗作来说,其旖旎、其雕琢都不及《红楼梦》,但是,就爱情悲剧来看,自然也不再像宝黛的爱情悲剧那样,是由代表封建礼法的家长所制造。《玉梨魂》所展现的是在情爱意识已经觉醒、而礼法规范还如达摩克利斯剑高悬于头上时,觉醒了的个体的痛苦不堪的真实情形。这里的矛盾,已经不再是外在的,而是内化于自我心理深处的,正是在这一点上,《玉梨魂》超越了传统小说,显示出现代小说转换的曙光已经来临——其所认同的文学创作原则已经不再是“礼”一统天下的那种情形了。
三
“中国文化试图在对西方文化的领悟中寻找‘立国’的途径。受这一最本质、最核心的文化观念的驱动,小说因其特有的功能满足了文化的需要,于是,由对小说的功能发现为契机,逐步地完成了对于小说的发现。”[2]政治层次的变革以及由此对小说功能的发现,毕竟无法医治沉疴深重的现实,这使得中国小说随之进入了对人的发现和文学表现的时代。人的发现,对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此,郁达夫说过:“第一个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代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8]人的发现和人的意识的觉醒,是继政治发现之后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发现。小说正是在这样的新的文化层面上被赋予了新的灵魂——以对人的精神世界真实表现为旨归,以启蒙为已任,使得小说创作的基点发生了最深刻的转换:由现实存在的人作为文学创作的基点,彻底抛弃了传统小说中“礼”的创作基点,也抛弃了社会政治小说以政治为文学创作的基点。人,已经不再是作为“礼”的附属物或证明物而获得其存在的价值,人已经具有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其鲜明的个性已经获得了张扬,个性解放在冲决“礼”的外在规范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对此,茅盾在论述小说创作的研究对象时说过:“就是‘人’!……我于是带了‘要写小说’的目的去研究‘人’。……‘人’……是我写小说时的第一目标。我以为总得先有了‘人’,然后一篇小说有处下手。”[9]这种创作的基点与传统小说以“礼”为本、而人则附丽于“礼”之上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况且,从现代小说所认同的精神启蒙功能出发,小说创作在处理艺术和现实的关系时,也不再以超然于客观存在的“礼”为本位,而是以现实存在的人为本位。这就反映在对于真实人生的表现上,其所恪守的文学创作原则是真实性原则。这恰如鲁迅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真面惨淡的人生”的真实精神,它撕下了罩在人身上的假面具,还人生以真实,也把“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彻底地堵死,促使人从自欺欺人的“瞒和骗”中觉醒过来。所以,小说创作主体对小说从政治层次到人的层次的功能的发现,既是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历史过程,又是由对现实真实性原则的排斥到对社会现实真实性原则认同的过程。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中国小说最后完成了对现实中的人的真实性表现原则的认同之后,“人”成了小说艺术表现的焦点所在,文学是人学的现代命题才落到了实处。
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并不意味着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全部否定,而是对中国传统小说的扬弃,是一个对传统进行现代转换的历史过程,还是一个螺旋式上升发展的历史过程。由此说来,这除了包含着对于传统的文化精神的否定之外,还包含着对于传统文化中那种具有合理性存在的优质文化的肯定和继承。因为,中国传统小说创作的基本原则固然是“礼”的原则,但“礼”的原则并不是一统天下的,它是在对于其对立面的抑制中获得凸现的。因而,在中国传统小说中,还有一种以民间形式而存在的写实精神,这种写实精神,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真实性的原则,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精神,使得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中,获得了本土化的精神资源。①这种本土化的精神资源,在随后的作家创作那里,依然存在着,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便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那里获得了写作的精神资源。对此,莫言在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发言中有过说明。
写实精神作为文学的表现原则,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其发展的高峰便是《红楼梦》。《红楼梦》是对传统文化的“礼”的文学创作原则的有力反拨,对此,曹雪芹曾就其创作的基本精神有过这样的解释:“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3]4-5此处所谓“不借此套者”,恰是那些依循着“礼”的文学创作原则而来的、千篇一律的小说。试想,“礼”作为已经设定好了的法则,是亘古不变的,其所变的仅仅是人物的名称和朝代等,但万变不离其宗。而曹雪芹则依据写实的精神,对现实中“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的“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3]5正是这种围绕人的写实精神的确立,才使得曹雪芹创作出来的文学世界,具有了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并因此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鲁迅对曹雪芹这种“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写实精神,曾经给予高度的评价:“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6]234由此可见,《红楼梦》围绕着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践行的写实精神,确实为中国传统小说向现代的转换提供了最为重要的资源,这样的一种踪迹在巴金的《家》、《春》、《秋》中都有着或隐或显的传承与再造。
值得关注的是,《红楼梦》等小说中的写实精神虽然含有现代小说的某些特质,但它和现代小说所确立的以人为艺术思维中心和以人为衡量理性规范的惟一的价值尺度相比较,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主要体现在《红楼梦》在对写实精神的恪守中,并没有熔铸进现代的科学与民主意识。这点,正如曹雪芹所倡言的那样:“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五穷,实非别书之可比。”[3]6这就是说,就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的指导思想来说,尽管他通过写实精神的凸显,客观上否定了封建礼教存在的合法性,但是,就曹雪芹创作的宗旨而言,并不是对纲常礼教的全部否定,而是带有“补天”的目的,这和“五四”文学对纲常礼教的全部否定相比,其指导思想的差异自然就可以立见分晓了。但不管怎样,《红楼梦》奏出了一曲爱情悲剧,尽管它并没有完全挣脱传统理性规范对它的束缚,但其所秉承的写实精神,还是为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点。
对写实精神进一步推进的是“谴责小说”。“谴责小说”虽然存在着“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的弊端,但相对传统小说而言,它在写实精神方面有了很大的推进,只不过它并不是建立在以人的真实为基础之上的写实,而是建立在对事实基础之上的实录。至于后期的“黑幕小说”,则在更大程度上扭曲了文学创作中的写实精神。
对于写实精神如何理解,无疑涉及到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问题。有人认为“黑幕小说”是现实主义作品,《官场显形记》和《留东外史》则标志着“写实派遂进一步”,而“至黑幕小说出现,遂露出写实小说的‘真面目’”[10]他们以描写“社会的恶点”、“人类的兽性”的程度来判断写实小说的优劣,实质上是对文学的写实精神的误解。周作人曾对此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倘说只要写出社会的黑暗事实,无论技巧思想如何,都是新文学小说”,那么,“譬如大清律例上的例案汇览,都是事实,而且全是亲口招供,岂非天下第一写实小说?”[11]这就把“黑幕小说”抛开人的基点来追求所谓的实录的本质,与文学创作中的写实精神划清了界限。
现代小说正是在对于人的发现的前提下,在对于文学的写实精神的认同下,牢固地将其基点建立在以人为根本的真实性之上,由此,中国小说得以横空出世。概而言之,在此基础之上所诞生的现代小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以创作对象为本位的写实派小说;二是以创作主体为本位的浪漫抒情派小说。前者以鲁迅为代表,后者以郁达夫为代表。它们都是基于对人的真实性的认同之上的,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自我的艺术表达。
所谓写实派小说系指创作主体在创作中,以创作对象本身所具有的真实为其艺术思维的中心,更侧重的是对于现实中所存在的人进行深刻而冷峻的剖析。像鲁迅对于祥林嫂、孔乙已、阿Q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便挖掘出了这些人物形象所体载的传统文化,是怎样地把人异化为非人的,这可谓把人的魂灵深度地表现了出来。
所谓的浪漫抒情派小说,则不刻意追求客观世界的真实,而是对创作主体的情感世界进行赤裸裸的袒露,它往往把作者和人物形象熔铸在一起,主体精神世界直接投射到了对象世界中,其所强化的真实,自然更多的是创作主体情感表现的真实。对此,郁达夫曾说:“忠于内部的根本的要求,而不受环境的压迫的,是天才的气禀”,因为“人类内部有一种强有力的要求”存在而“人类可以打破环境,创造自我”,郁达夫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写实主义为基础,“更加上一层浪漫主义新味和殉情主义的情调”。[12]这种注重于创作主体的情感和个性的自由表达的创作倾向,在郁达夫那里甚至得到了极端化的推进,以至于认为“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有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13]郁达夫对此进一步论述道:“想在作品里表现一点力量出来,总要不离开实地的经验,不违背Realism的原则才可。……大家都以为我在主张所谓——len—ro—man,——除自叙的作品以外,无论如何的好作品,都是不足取的,这真是笑话。”[14]可见,郁达夫在此所认同的小说的基本原则是真实,至于是客观存在的真实还是内在世界的真实则是毋须顾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郁达夫之认同“自叙传”的观点,亦是从其能更好地完成对于真实的实现而着眼的。这种对于创作主体的凸显、对于作家的主观世界和经验世界的真实性追求,自然地赋予了作家作品以现代性的特征。
郁达夫对“自叙传”的文学观点的认同,使其文学创作折射出了“五四”时代觉醒了的那一代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发展轨迹。如果说以鲁迅为代表的人生写实派小说代表“五四”时代冷峻的社会剖析派对于社会现实认识的深度的话,那么,以郁达夫为代表的浪漫抒情派,则集中体现了“灵与肉的冲突”的情感深度,即周作人所概括的“生的意志与现实的冲突”。[15]所以,当郁达夫把这种“现代人的悲哀”揭示得如此淋漓尽致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便可想而知。故而,其代表作《沉沦》一经发表,“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使他们感受着假的困难。”[16]正是基于对人的心灵和情感世界的真实表现,才使得郁达夫的作品具有了强烈的艺术震撼力。
综上,中国小说在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历史过程中,就文学创作原则而言,其由“礼”的文学创作原则为起点,经由对政治原则的认同,最后完成了以人为本位的皈依。在此历史过程中,中国小说开启了由“瞒和骗”的“礼”的原则向表现现实人生的真实性原则的转换,并在对“人的文学”的确认中,促成了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
[1] 李宗刚.中国小说创作主体的审美情感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2).
[2] 李宗刚.论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4).
[3] 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40.
[5]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71.
[6] 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7.
[8]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卷·导言[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
[9] 茅盾.谈我的研究[M]//茅盾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10] 杨亦曾.对于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勿再编黑幕小说之意见[J].新青年,1919,6(2).
[11] 周作人.再论“黑幕”[J].新青年,1919,6(2).
[12] 郁达夫.文学概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13] 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M]//郁达夫文集:第7卷.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180.
[14] 郁达夫.《达夫代表作》自序[M]//达夫代表作.上海:春野书店,1928.
[15] 周作人.沉沦[N].晨报副镌,1922-03-26.
[16] 郭沫若.论郁达夫[C]//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9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