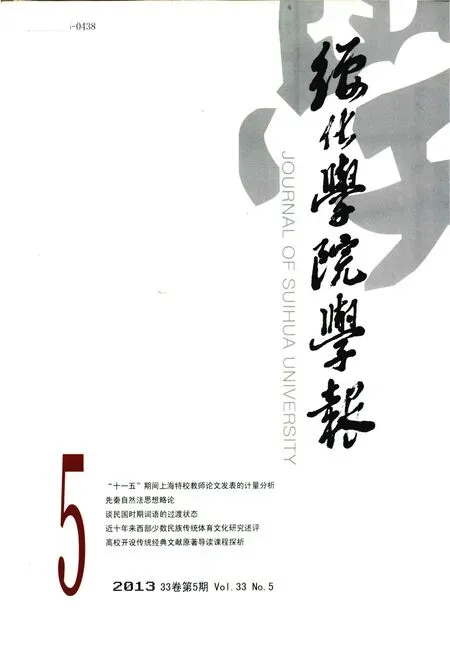经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一部力作——高明峰《北宋经学与文学》评介
2013-04-11闫荟
闫 荟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大连 116081)
经学曾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的一部分,存在于中国社会两千年之久,其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而珍贵的史料。经学所产生的影响和理论家对其所作的阐释贯穿中国文化的始终,这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烙上了经学之印。而研究儒家文化与文学之关联,第一重点是研究经学与文学之关联。因此,进一步理清经学与文学的关系,对于我们把握文学在古代的存在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经学存在的两千多年中,宋代经学的作用是突出的,是经学史上的一个高峰,这就使得宋代的文学势必会受其影响。因此,加强作为经学史之重要一部分的宋代经学的研究有其必要性,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经学的思想内涵,掌握经学对中国文学的独特影响。高明峰副教授撰写的《北宋经学与文学》(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就是这方面的一本专著。通观全书,作者用独特的视角,通过其掌握的大量北宋历史、文化资料和查阅相关的经学史原典,对北宋经学与文学的关系做了较为详细且有价值的探讨与研究,而该探讨为宋代经学与文学关系之研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平台,在文学与经学关系研究领域留下了崭新的一笔,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从中我们也感受到作者文学素养之浓厚与治学态度之严谨。因此汪俊先生在该书的序中写到:“此书博考经籍,高屋建瓴,在理论上对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作了总体探讨和准确把握,梳理北宋一朝的经学发展脉络,揭示其与文学发展的互动面貌和演进规律,探讨了宋人经学新风对文学内容、风格、形式的影响。”这段话无疑是对全书的整体概括。总而言之,高明峰副教授在《北宋经学与文学》一书的写作中,“为了求真而不避繁难,可见其问学之笃实”,该书也是经学与文学关系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值得一读。
从具体内容来看,《北宋经学与文学》一书共分六章,按照时间的顺序从中晚唐到北宋熙宁、靖康年间,详细论述了经学与文学的密切关系。
要讨论经学与文学的关系,首先要了解并掌握经学的基本含义。在第一章绪论中,作者指出所谓“经学”,指的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包括字句的注释、义理的阐发等。笔者认为,这一阐释作为本书的开头,使读者更加明确“经学”一词的涵义,同时也让读者在阅读伊始对本文的主题“经学与文学的关系”有更加明确的理解。
随后作者又向我们提出了谈经学与文学的关联,应当讨论的三个问题:经学与文学的关系、经学与文学的关系得以实现的途径、对经学与文学关系的基本看法与评价。通过论述,作者向我们展示了研究的客观态度与清晰思路,而这“三个问题”的解决也为下面经学与文学关系的具体研究论述做了理论铺垫,体现出极强的逻辑性。而提到经学与文学的具体关系,书中写道:“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受制于经学,要时常迎合经学,又不断地发现、挖掘自身的特质,表现出对经学的疏离和突破。经学与文学这种紧密的联系,既制约了文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演进。”作者通过以上简短的话语就对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的说明,这是作者逻辑和概括能力的体现。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经学与文学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二者相辅相成,可以说是既统一又对立。
研究价值是一个课题的骨力支撑,而在《北宋经学与文学》这本书中,作者认为“经学与文学的关系”这个课题有其自身的研究价值,并对该价值作出了介绍:“从经学方面来说,这本身可以算是经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文学方面来看,它有助于具体、客观地把握文学生成和演进的原生状态,展示文学发展丰富的历史面貌,同时也有助于深层的揭示文学理论背后的思想文化内涵,阐述文学理论的逻辑生成与变迁。从综合研究的方面来讲,它既可以丰富经学研究,有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对于纯粹的、单一的经学研究或文学研究来说,都是一种突破。”笔者认为,作者从经学、文学与综合研究三个方面对该课题的研究价值作出了介绍,说明该课题具有特殊的价值,而这些都是研究经学与文学关系领域中必不可少的。当然,这些价值在《北宋经学与文学》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并成为该书的闪光点之一,因此该书有着很强的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不仅向我们介绍了该课题的独特价值性,还对其研究现状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研究过程中,作者对从“六经”诞生起至今有关经学与文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认为宋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多属个案研讨而少整体观照。而高明峰副教授的《北宋经学与文学》就为我们弥补了这个遗憾与缺失,并为我们提供了此领域精研谭思的成果,从中可见此专著之必要性与重要性。
以上都是对“经学与文学的关系”这一课题的整体概括与论述。在第二章开始,作者进行分期论述。书中共分为四个时期:中晚唐时期;北宋庆历以前;庆历、熙宁间;熙宁、靖康间。作者对不同时间段的经学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要讨论宋代的经学与文学关系,就必须要了解掌握与之相关联的中晚唐时期的经学与文学各自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因此,作者在《北宋经学与文学》的第二章中探究了“安史之乱”以后在经学方面的新风及与之相关的在文学领域引起的新变。该探究为下面章节关于北宋经学与文学关系问题的展开提供了参照,也丰富了我们对存在于不尽相同的时代背景下的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的认识。
高明峰副教授认为,中晚唐经学的新风与文学的新变,是当时所兴盛的“儒学复兴”风气下的产物,也可看做是复兴儒学的重要表现与内容。这是作者向我们介绍的中晚唐经学的新风与文学新变产生的主要因素,而这种新风、新变也相应地显示出与该因素相符的新特点。因此,笔者认为,作者对背景、相关因素的介绍有其必要性,可见作者思路的缜密与清晰。
再者,中晚唐所体现出的经学新风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舍传求经、以己意解经;二是原经求道、依经立义。在论述这两方面时,作者举啖助、赵匡《春秋》学派和韩愈、李翱等人的经学为例,通过理论联系实例的方式,对以上两个不同学派各自的主张进行详细论述,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握中晚唐时期经学新风所表现出的独特性。
“这种经学新风,不仅在经学领域产生了普遍影响,也从根本上造就了文学的新变。”这是一句承上启下的话,而作者通过这样一句简短的话直接将主题转入到另一个论述内容中,从中可见作者写作的巧妙之处。随后,作者认为这种新变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在文学创作和批评方面,要求以“六经”为典范,要求文以明道,要求诗以讽喻,突出强调文学对现实的干预作用。二是在文学风格方面,或奇诡,或浅切,都与经学新风有着深层联系。作者同样结合最具代表性的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等人的讽喻诗风展开了详尽论述。总之,笔者认为,第二章对中晚唐经学的新风与文学的新变的论述是非常有必要的,它不仅增添了本书的完整性,还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与掌握本书的主题:“北宋经学与文学的关系”。
从第三章开始,作者对本书的主要内容“北宋经学与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期而具体论述。在论述伊始,作者首先对北宋经学与文学的演进背景从经济与政治两个方面作了简单的介绍。随后,作者以“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为分界点,将北宋的经学发展大致分为如下三期:庆历以前是过渡期,承中有变;庆历至熙宁前,是变革期,主要功绩是破汉学;熙宁以来直至北宋灭亡,是自立期,主要功绩是立宋学,出现“荆公新学”、“苏氏蜀学”、“二程洛学”等鼎足而立的学派。与此经学演变相关联,文学的进程也显示出相应的变迁。以上是作者对后面内容的一个概括介绍,让读者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本书论述的整体走向。一本书的思路是否清晰是影响其成功的重要因素,而高明峰副教授在本书的论述过程中对主题走向与整体思路进行了显明的梳理介绍,这体现出作者的“问学之笃实”。
首先是北宋庆历之际,在政风、士风和学风上都表现出过度的性质,较多地沿袭唐五代以来的陋习之风,但承继中亦有新变的因素在内。这是对该时期政风、士风和学风整体风貌的总结,同时也引出下文对经学与文学新面貌的论述。作者认为,经学与文学也呈现出诸多相应的面貌,其主要的特征,即是均表现为守旧(因袭)与革新的并存。在论述经学方面,作者从官方组织编著或认可的经学著述和私人经学著述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其中着重介绍了以柳开、王禹为代表的,以“复兴古道、古文”为任务的私人经学著述,作者通过介绍这两个人在经学方面的重要贡献,来进一步论述庆历以前的经学风貌。而在文学方面,作者从诗、文、词、赋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从而得出:这时期的总体面貌是因循守旧多于创新变革。本小节作者通过对经学、文学两个方面在北宋庆历之际的特点进行逐一论述,揭示出本时期经学、文学的总体面貌,可以说是由点及面,详略得当。
作者为更好地引出下章内容,在本章结尾处留下了伏笔。作者认为:虽然在庆历以前,经学与文学在柳开、王禹等人的努力下,已经开始表现出一些具有革新性质的特点,但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文坛上,紧接着出现的杨亿、刘筠等人的西昆体风靡一时,柳、王等人开创的复兴古道、古文的运动,限于才力,不能够彻底的扭转局面。以古文取代骈俪之文,这样的任务只能由后面的人来完成了。笔者认为,这一段话的论述,勾起了读者的好奇之心,自然而然将读者是视线引入到下一章节中,为后文作了铺垫。同时,这一写法也增添了全书的流畅性,增强了全书的逻辑性。
值得庆幸的是,像欧阳修这样的后来人并没有让前人失望,他们在继承前人遗产的基础上进行不断革新,体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作者在文中指出,庆历、熙宁间的经学,其特点在较为彻底地“破”汉学,而庆历以来的经学新变,其主要方面在于疑传惑经的盛行和通经致用的取向。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突出代表是有“宋初三先生”之称的胡瑗、孙复、石介三人所身体力行并通过教学而广为传布的“明体达用”之学。
沿着“宋初三先生”开辟的路径,庆历以来的经学面貌豁然一变。当然,其主要方面是前边已提到的疑传惑经的盛行和通经致用的取向。作者对这两个方面内容分别列举出了其代表作品与人物,前者是刘敞的《七经小传》,而后者是以李觏为代表。就庆历、熙宁间的“疑传惑经”来说,是由欧阳修导之于前,刘敞承之于后,而就实际成绩和影响来说,则刘敞似更值得注意,这或许也是作者选刘敞作为其代表的主要原因。而在庆历之际,范仲淹等人掀起一股改革之风,终于形成“庆历新政”这一高潮。与现实变革有关的是,在经学领域也呈现出强烈的通经致用,以经学干预政治、服务政治的色彩。这种取向最为突出的代表是李觏及其《周礼致太平论》。通过作者的具体分析,我们足以了解当时学者们通经致用的情况。
经学面貌的新变也渗透到了文学的领域中,促进了这一时期文学面貌的新变。简要地讲,庆历、熙宁间的文学是初步奠定了宋代一朝之文学的面貌,体现出了宋代文学自身的诸多特征。而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欧阳修、尹师鲁兄弟、苏舜钦、梅尧臣等。在书中,作者通过对这些人在古文、诗歌两方面的主要成就作详细的分析,揭示出这时期的文学新面貌:力行古文、以文为诗。随后又向我们介绍了产生这种文学新面貌的现实背景。通过介绍,我们可以得知,这时期的文学面貌是与当时的经学新风密切相关的。经学新风影响了文学的内容、风格与体式。除此之外,作者还对庆历、熙宁间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的经学与文学做了单独的讨论,这样既有助于较好地把握欧阳修的文学风貌和学术成就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做是研究庆历、熙宁间经学与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富有代表性的个案。
到熙宁、靖康年间,经学是沿着前人开辟的路径继续推进的。在本章节的开始部分,作者就向我们指出了熙宁、靖康年间的经学实绩和文学面貌。本时期的经学除了在疑传惑经和经世致用方面更推进一步之外,在性命之辨方面也开始重视起来,而这两个方面,正是此期经学的主要内容。能够体现以上经学内容的代表人物,又都能自我树立,自成一派,分别形成了所谓的“荆公新学”、“濂洛理学”、“苏氏蜀学”等。这些自我树立的、独重义理的经学流派,构成了熙宁、靖康间经学的总成绩。而这时期的文学面貌也呈现出与学术相应的特色。换句话说,就是一派有一派之文学,而这样各自成派的文学,即组成了当时文坛的基本面貌和整体走向。这些具体展示了经学与文学的联接,但这种联接也受到了社会环境的诸多制约,主要表现于纷繁复杂的党争和改弦更张的科举两方面。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作者又分设荆公新学与文学、苏氏蜀学与文学、二程洛学与文学三节,进行具体而深入的个案研讨,评述其经学成就与特点,掘发其经学与文学的内在关联。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王安石、苏轼等人的学术建树,更能深化我们对其文学特质的理解。
就本书的论述方法来看,作者为了让读者更加明确的了解所论述的内容,皆以理论联合实例的方式进行讨论研究,避免了一味的理论论述引起的枯燥乏味,增添了本书的趣味性和论证的说服力。除此之外,文献基础的扎实、研究视野的开阔也都为本书增色不少。
总体而言,高明峰副教授《北宋经学与文学》一书,紧扣经学与文学二者,点面结合、时空交织、勾勒与分析并举、宏观与微观互证,既展示出北宋经学与文学的互动演进,又阐述了北宋经学与文学互动中的诸如制约因素、逻辑成因、主要途径等重要命题。大体实现了作者“在整体上既做到丰富经学史的研究,又为文学史的研究开辟新径”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