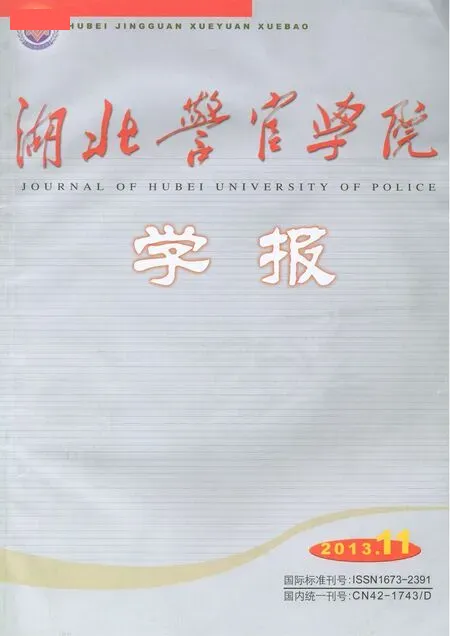诈骗罪与非罪的界限
2013-04-11王栋
王 栋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北京 100025)
诈骗罪是一种多发型犯罪,也是司法机关办理较多的案件类型。本文拟通过对诈骗行为等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的探讨,试图对欺骗行为、错误认识、交付财物行为等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并考察几种常见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以此分析诈骗罪罪与非罪的界限。
一、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诈骗罪与盗窃罪、抢劫罪一样,是转移罪。但是,盗窃罪、抢劫罪是夺取罪,以违反占有人的意思而转移占有为要件,而诈骗罪是交付罪,以基于占有人的意思而转移占有为要件。[1]通说认为,诈骗罪的基本模式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实施欺骗行为,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对方基于该错误认识交付财物,进而造成损失。
二、诈骗罪客观构成要件的界定
(一)欺骗行为
在实践操作中,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主要通过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来区分。即有欺瞒行为的情况下,行为人“通过非法占有,取得被占有财物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从而改变财产的所有权,使财产所有人在事实上永久、完全丧失财产的所有权。”[2]就可认为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诈骗罪。
【案例1】甲为一工厂老板,向乙借款,担心乙不会借款,就编造了其父住院需要手术费的理由,并允诺在1年之内还款。后因工厂被淹毁,甲无法归还欠款。事后查明,甲在3年内资金都用于扩大产能,不可能按时还款。
【案例2】甲为一工厂老板,向乙借款,称所借款将用于扩大产能。因担心乙不会轻易借款,就向其允诺高额利息,并写下借条,后甲无法归还。事实上,甲平日沉迷于赌博,工厂及其他财产都已出售,身无分文,所借钱款也都用于赌博。
通常认为,虽然上述两则案例中甲都有虚构事实的行为,但是只有案例【2】中的甲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诈骗罪。其区别在于,一般认为该民事欺诈行为是“当事人采取欺诈方法,旨在使对方当事人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即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这个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利益。”[3]故民事诈欺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其实,两则案例中甲的欺骗行为也是不同的,案例【1】中的甲只是民事欺诈行为,案例【2】中的甲才是诈骗罪的欺骗行为,包含了其隐瞒要将钱款挥霍的内在事实。
诈骗罪的欺骗行为,主要包括虚构事实和隐瞒事实等。诈骗中的“事实”应指现在或过去的具体过程或状态,应具有可以验证其为“真”或“伪”的性质,不但包括客观的“外在事实”,也包括兼及主观的“内在事实”。[4]此处“内在事实”的欺瞒,是指行为人欺骗、隐瞒或误导的某种内心既存的心理状态。此种“事实”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在欺骗行为中主要表现为行为人非法取得被害人财产的内在意愿。虽然“内在事实”是主观的意愿,但是其仍为客观构成要件中的“事实”要素,也就是欺骗行为中的“隐瞒事实”,不应与主观故意相混淆。因此,编造理由借贷的行为不是诈骗罪的欺骗行为,而行为人隐瞒其将钱款挥霍或不愿还款的内在事实才是诈骗罪的欺骗行为。
(二)错误认识
实践中,一般不认为恋爱中和交易中的欺骗行为构成诈骗罪,因为为了保持正常的生活和经济发展,我们不得不容忍类似的欺骗行为。而事实上,这两类行为中的部分情况并不仅仅是因人们观感上的理由不构成诈骗罪,而是其客观上本就不符合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案例3】甲女为一美女,乙男和丙男同时在追求甲女。甲女看上两款价值不菲的首饰,就分别向乙男和丙男虚构另一方赠送其昂贵礼物发起攻势的事实,让乙男和丙男为其购买首饰。乙男和丙男为了不输给对方,就各自购买了首饰送给甲女。事后,二人发现上当受骗。
【案例4】甲为一卖古字画商人,向收藏家乙高价出售一幅自称为元代名家的字画,乙仔细鉴别后认为该画并非元代字画,而是出自明代另一名家之手,认为以该价钱买入十分划算,遂买入该画。实际上,该画为当代仿品,价格很低。
上述案例【3】中,甲女确实为了取得价值不菲的首饰而虚构事实,使乙男和丙男都陷入错误认识,处分了财产,造成乙、丙财产的损失,但是我们一般不认为甲女构成诈骗罪。案例【4】中,甲商人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对于此两则案例中甲女和甲商人为何都不构成诈骗罪,并无过多的学理解释,通常认为相对人(即被害人)具有过错,行为人能诈骗成功不具有普遍的意义,不能因此而认定行为人构成诈骗罪。这样的解释显然不具有说服力,是否构成诈骗罪不能因为相对人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而有所区别。
实际上,此两则案例不构成诈骗罪,是因错误认识部分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诈骗罪中的错误认识是指引起或维持相对人某个与事实不符的主观想象(或认知),是相对人主观上的想法与客观的真实情形产生不一致的现象,包括相对人对于事实核心部分任何不正确的、不符真相的认知或想象。[5]上文已经提到,并非所有欺骗的行为都是诈骗行为;同理,并非所有与事实不符的想象,都是陷入错误认识。诈骗罪的本质是让受骗人自损财产的犯罪类型,因此,无论是行为人所实施的欺骗行为,或相对人所陷的错误认识,都必须蕴藏某种直接招致财产上损失的特性。[6]案例【3】中乙男和丙男赠与行为的对象是甲女,是为了讨甲女的欢心,对这一点,乙男和丙男并无任何错误认识。但是,此二人处分财产所陷入的错误认识是因其在女孩子面前争强好胜的错误动机引起的,并不是因甲女欺骗行为而引起,所以甲女并不构成诈骗罪。在案例【4】中,乙并不是因甲商人的欺骗行为而陷于错误认识,其错误认识的产生是基于对自身专业知识的自信,甲商人欺骗行为产生的错误认识和乙陷入的错误认识两个要件之间缺乏必要的因果关系,所以甲商人并不构成诈骗罪。综上,当错误认识的不同而切断了欺骗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因果关系时,行为人就不构成诈骗罪。
(三)基于错误认识的处分行为
一般情况下,诈骗罪和盗窃罪、侵占罪等犯罪的区别仅仅是犯罪个别化的问题,理论上虽有较大争议但是对实务操作影响不大。然而,在追诉标准对这几种犯罪的入罪金额要求不同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区分就有了实务上的意义。
【案例5】甲将乙约在某餐厅吃饭时,声称需要借乙手机打电话。乙将价值4000元的手机递给甲后,甲假装拨打电话,并谎称信号不好,一边与“电话中的对方”通话,一边向餐厅外走,然后趁机逃走。[7]
【案例6】甲在商店购买相机,将一台价格4000元的手机装入一个相机盒子中,结帐时店员乙只收取了甲一台相机的钱,而未发现其藏在盒子中的另一台手机。
对上述两则案例,如果认定甲的行为为盗窃行为就可以入罪,而认定为诈骗行为则因达不到追诉标准而不能入罪。因此,其行为构成何罪,在实务中进行探讨就有了必要性。
通常认为被害人是否具有处分财物的意思和行为,是区分诈骗和盗窃的客观标准。[8]对于“处分行为”的理解,主要有“所有权转移说”、“占有转移说”和“持有转移说”。对于“处分行为”,笔者更倾向于在实务操作中采用“持有转移说”,即被害人认识到将某种特定财物转移给对方,即使只是暂时的持有也能认定具有处分行为。上述案例【5】中,乙已经将手机转移给甲,认识到甲对该物的暂时持有,所以就可以认为乙对该手机具有处分行为,甲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但是,由于手机价值只有4000元钱,甲并不构成诈骗罪,这样的认定更符合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同时,就诈骗罪而言,老百姓一般认为行为人利用一定的手段进行欺骗,使得相对人遭受损失就应该构成诈骗罪,而不是盗窃罪。学界和实务界不能为了迎合精致理论的要求就忽视普通人的认识,将骗手机、调包的行为都认为是盗窃行为而不是诈骗行为。
而对于“处分意思”,主要有“缓和处分意思说”和“严格处分意思说”两种。实务操作中,处分者究竟该认识到哪些内容、认识到何种程度是很难考查清楚的,而且相关规定中也很难对此进行列举或归纳,所以,笔者更倾向于“缓和处分意思说”。即“被骗者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把某种财产转移给对方占有,而根据自己的自由意思作出此种决定,就应该认为具备了处分的意思内容。至于所处分的财产的性质、数量、质量、价值等,则不一定要求其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
如果采用“缓和处分意思说”,上述案例【6】中,店员乙没有认识到甲将手机藏在相机盒子中,并不知道在盒子内有两种产品,但是其同意甲将商品拿走,表明其具有处分的意思和行为,所以甲的行为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但是由于没有达到诈骗罪的入罪金额,所以甲不构成诈骗罪。
综上所述,对诈骗罪处分财物的行为和意思采用“持有转移说”和“缓和处分意思说”可以适当地将诈骗罪范围扩大,对于某些既可以认为是诈骗行为又可以认为是盗窃行为的情形,这样的认定对行为人更有利,也符合刑法的从轻原则和谦抑性原则。但是,以帮被害人的财物施法为名,取得被害人财物,在施法过程中进行调包,将调换后的财物再交还被害人的,通常不认为被害人具有处分财物的意思和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窃取的行为更加明显,也更符合社会认知,应认定为盗窃罪。
三、结语
通过对诈骗罪的三项构成要件进行分析,笔者对诈骗罪与民事行为之间进行了区分,阐述了某些民事行为不构成诈骗罪的理由,这样可以避免刑罚的滥用。
同时,笔者对诈骗罪采取相对缓和的理解,适当将某些既包含窃取又包含骗取的行为统一认定为诈骗罪,这样可以提高这些行为的入罪门槛,符合刑法谦抑性的原则。但是,这种缓和的理解不应走向极端,将无意识的处分行为都认为是诈骗罪,使得诈骗罪成为一个“口袋罪”。对诈骗罪的理解还应结合其侵犯财产犯罪的属性,在其成立范围上和其他犯罪找到平衡点。
[1][日]山口厚.刑法各论[M].王昭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86.
[2]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886.
[3]熊选国.论诈骗犯罪与民事诈欺行为的界限[J].法学评论,1990(1):49.
[4]林钰雄.刑法与刑诉之交错适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67.
[5]甘添贵.体系刑法各论(二)[M].出版社不详,2000:293;林山田.刑法各论(上)[M].出版社不详,1999:405.
[6]林钰雄.刑法与刑诉之交错适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90.
[7]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97.
[8]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至五庭.刑事审判参考(2008年第3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