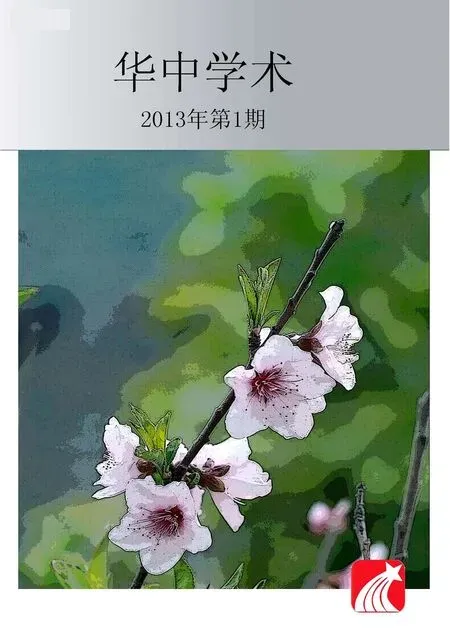从两个文本看赵树理大众文学思想的特色
2013-04-10王先霈
王先霈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
从两个文本看赵树理大众文学思想的特色
王先霈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以“五四”为开端的中国新文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革命文艺,在其发展历程中都有一个从头贯穿的线索,那就是文艺的大众化。在新文艺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行者中间,在无产阶级革命文艺队伍内部,文艺要大众化,这是一致的,至于怎样才是大众化,如何实现大众化,则是一个历经反复探索并不断产生争议的问题。赵树理被认为是文艺大众化的一位卓有成就的实践者,他的作品受到热情赞扬,也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指责以至于嘲笑;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他关于文艺大众化的思想在他所属的体制之内遭受到的更多是冷遇、碰壁。为什么一位曾经被树为旗帜的作家,他付出真诚努力所得的却多是挫折和苦恼呢?看来,要从外在环境和赵树理本身两个方面寻找原因。本文试由“赵树理方向”提出之时他所写的《艺术与农村》和“文革”被审查批判时所写的交代自述《回顾历史,认识自己》这两个前后跨越二十年的文本,对赵树理大众文学思想的独特之点及其深刻性和局限性作一探讨[1]。
1947年夏,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座谈会,提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实应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2]这是赵树理正式地进入文坛主流的一个辉煌的开端,座谈会后,《人民日报》特约赵树理撰文,谈农村文艺运动。赵树理文章的题目是《艺术与农村》,这篇文章语调平和,立论平易稳健,只是表达自己对于文艺性质和作用的看法,而没有正面展开对文艺方向、方针的宏观问题的论述,与那些赞誉颂扬他的文章、讲话相比,官方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淡薄,很值得咀嚼品味。1966年,赵树理已经被当作“文艺黑线干将”,失去人身自由,那年冬天他写了一个检查交代性质的自述《回顾历史,认识自己》,重新梳理毕生文学道路和文艺观点,在那样极不正常的气氛中,依然信守历来的基本信念。在自述的末尾,他郑重地声明:“我自参加革命以来,无论思想、创作、工作、生活各方面有何发展变化……始终是自成一个体系的。入京以后,除在戏改方面受了些感染外,其他方面未改变过我的原形。”这些话是符合事实的,赵树理的大众文学思想,也是有个性而不雷同于他人的。这一头一尾两个文本,正可以作为我们理解、把握赵树理大众文学思想的切入点和标本。
他在《艺术与农村》这篇文章中说,“农村有艺术活动,也正如有吃饭活动一样,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农村人们艺术要求之普遍是自古而然的”。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赵树理在论证文学艺术工作的出发点的时候,不是像当时其他许多人那样,不是首先讲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文艺作为革命政党宣传和组织工作的一种工具的特性,而是讲文艺欣赏是出自人的本性的一种自然需要。文艺欣赏、文艺活动,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农民和城里人、和知识分子一样,有文艺欣赏的权利,欣赏什么、怎么欣赏,有他们自己应该尊重的选择。从这点看,就显示了他和革命政党领导者,和革命文艺运动主流、权威之间的有意味的差别。我们试来比较一下,瞿秋白被称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学大众化的最早的一个倡议者和鼓舞者”[3],他主持制定、由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发的《俱乐部纲要》中指出:“俱乐部的一切都应当为着动员群众来响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每一号召的,都应当是为着革命战争。”[4]他比赵树理早得多就注意到大众文艺要利用“旧式体裁”以适应不识字和识字很少的民众,但他这样做,是为了让革命政党的主张通过文艺为群众所接受,所以,他说,“革命的大众文艺因此可以有许多不同的题材。最迅速地反映当时的革命斗争和政治事变,可以是‘急就的’、‘草率的’。大众文艺式的报告文学,这种作品也许没有艺术价值,也许只是一种新式的大众化的新闻性质的文章,可是这是在鼓动宣传的斗争之中去创造艺术”[5]。瞿秋白的看法在“五四”新文艺运动的先驱和革命的领导人中有相当的普遍性,在他们中若干人宣传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的热情里,有时候不自觉地带有对普通民众文化上和审美上的轻视。赵树理不是这样,他认为,农民虽然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农村中文盲众多,但农民的艺术欣赏能力未必很低。他说,“一个文盲,在理解高深的事物方面固然有很大限制,但文盲不一定是‘理’盲、‘事’盲,因而也不一定是‘艺’盲”,有的不识字的农民,“甚至精通了某种民间艺术”[6]。这是一个很精彩的观点,人的艺术感受力、鉴别力,与他的学历及书本知识的多少,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许多大文学家、大艺术家,都乐于和善于从民间艺术吸收营养,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更是有必要了解、学习并努力满足农民的艺术审美兴趣。
赵树理可以说是做革命宣传工作出身的,他早年写的那些文字没有保存下来,据他在自述里回忆,那些小作品“特点是有战斗性”,足见他是充分认同革命文艺的工具性的,他后来的整个创作道路也证明这一点。但与此同时,他又承认并重视文艺还有超越功利的审美功能。他在《三里湾写作前后》中曾提及,旧时代文艺的欣赏者,要求轻松的小趣味,并“不打算接受什么教育”[7]。这里实际上是指中国曲艺的古老传统,中国的曲艺是由勾栏瓦子、茶楼酒肆里的艺人和农村里的负鼓盲翁创造并不断推进的,《水浒传》里白秀英的父亲白玉乔说,“只凭女儿秀英歌舞吹弹,普天下服侍看官”。文艺家是“服侍者”,服侍观众、读者。不仅仅是茶馆里的闲人,一般的读者大多也不是首先为了受教育而走进剧场或捧起小说来。恩格斯在《德国的民间故事书》里指出,民间故事的使命,首先是让因艰苦劳动而疲惫不堪的农民得到快乐和慰藉[8]。西方文学也有类似的传统,菲尔丁在《汤姆·琼斯》中说,作家的写作,不应当是阔人施舍粥饭;作家好比饭馆老板,人家出了钱来吃饭,你就要合乎他的口味[9]。菲尔丁说的是“饭馆老板”,赵树理经常讲到的是群众艺术需求的“供给者”,他们应该尊奉读者大众为文艺的主人,以虔敬之心服务,而不应摆出俯就的姿态。赵树理在《艺术与农村》里讲到,一般人都有“唱”的冲动, 如果没有可唱的东西, 在实在憋得吃不住的时候,就唱几句地方旧戏来出出气;群众翻身以后有了土地,土地不但能长庄稼,而且还能长艺术,物质食粮可以满足最基本的需要之后,精神食粮的要求也就提高了一步。没有可唱的东西即是审美的匮乏,改变匮乏的责任在关心和热爱群众的文艺家。
作家应该做的是去体会、揣摩接受者的口味,而不是强制接受者适应他自己的口味;更不应以为只有自己的口味才是纯正的、高雅的,下层接受者的口味都是浅陋低俗的。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发言里他指出,群众文化馆和按照文化馆的订单创作的作家都以为,只要有了连他们自己也不认为是艺术的东西,既不艺术又宣传不好政治的东西,群众就足以娱乐了,他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判。赵树理反对的是那种施舍的心理和做法,他一直反感以为群众会满足于简陋的、缺乏艺术性的作品的观点。1943年,他写过一篇《平凡的残忍》,起因是有同伴嘲笑他把金针海带当作山珍海味,他激愤地说,没有尝过珍馐佳肴而吃南瓜喝酸汤,“并非万古不变的土包子”,“也不是娘胎里带来的贱骨头”,“贫穷和愚昧的深窟中,沉陷的正是我们亲爱的同伴,要不是为了拯救这些同伴出苦海,那还要革什么命?”[10]这篇短文显露出终其一生郁积于心的情结,那是一种基于农民本位思想的情绪,是对于任何轻视农村人的言行的强烈愤懑。
赵树理提出,不能把普及和通俗混为一谈,他甚至认为,“俗”字是上流社会轻视和侮蔑劳动人民的字眼[11]。他多次提出,中国的文艺界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五四”新文艺运动开创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新文艺传统”,另一个是“未被新文艺界承认的民间传统”[12];到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里,则说:“中国现有的文学艺术有三个传统:一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的传统,旧诗赋、文言文、国画、古琴等是。二是‘五四’以来的文化界传统,新诗、新小说、话剧、钢琴等是。三是民间传统,民歌、鼓词、评书、地方戏曲等是。”虽然赵树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文学界占有重要位置,1956年,周扬在报告里把他与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并列,称为当代语言艺术大师,但赵树理本人却宁愿自外于这个系列。“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这是我的志愿。”“新文学的圈子狭小得可怜……新文学只在极少数人中间转来转去,根本打不进农民中去。”他把大多数作家的创作,称为“交换文学”[13]。赵树理觉得,文艺界的多数人是不承认民间传统有延续的价值的,不相信民间传统能产生杰作,民间传统无力争取到文坛上的地位,而他所继承和发扬的正是这个“不被承认”的传统,他始终不懈地要为这个传统的延续而努力。进城之初,他领头发起成立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编《说说唱唱》,接受林庚教授的邀请到燕京大学讲授民间文艺课,这都是一些很有益的工作。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在政治上和审美上的错综的矛盾中,他这几个方面的工作未能如他所愿,而且难以为继。
赵树理的两个传统或三个传统之说,大体适合文学艺术的整体,比较适合于戏曲和曲艺,而他本人是小说家,就小说而言,三个传统是否能构成平行并列的体系,那是一个问题。在中国古代,抒情文学长期占据正宗地位,文人独立创造的叙事文学作品远不如民间留下的遗产之丰厚。20世纪中国文学为了启蒙和救亡的目标,急需小说这种文学体式,作家们主要是借鉴欧洲小说,鲁迅、冰心、叶绍钧、巴金、茅盾、郁达夫等莫不如此;即使是乡土文学派的鲁彦、许钦文等人也是自觉借鉴俄罗斯、东欧和美国小说,从张爱玲等人的作品里可以看到《红楼梦》的影响,但更多地也还是靠拢18、19世纪欧洲小说的范式。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革命根据地,说唱文学拥有数量不小的接受群体,革命根据地有些作家的小说借用了说唱文学的一些叙事方式,但进入50年代,情况逐步发生变化——看小说的日渐增多,听说书的则日渐减少,而且在国家工业化带来农村文化生活变化的背景下,这是一种持续的趋势。赵树理对这个大趋势很不敏感。正是有鉴于此,他后来回忆到,1951年“胡乔木同志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要我读一些借鉴性作品”,胡乔木、周扬开了书单子,让他读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那时与赵树理过往密切的严文井回忆说:赵树理原来就读过不少“五四”时期的文艺作品和外国作品的译本,“我这才明白,老赵并不是一个‘土包子’,他肚子里装的洋货不少”。但是,赵树理是一位农民本位主义者,他多次明确宣称,他就是为农民而写作,他的作品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目标是适合农民的审美趣味,他心目中的农民,是远离现代城市文化的农民,他的小说创作乃是承续民间说书的渊源。他认定“说唱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统。小说要能说,韵文要能唱”[14]。他并不愿意像欧洲作家那样写小说,周扬在1962年大连会议上说:“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他对农村有自己的见解,敢于坚持,你贴大字报也不动摇。”严文井说,“我觉得他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有些像狂热的宗教徒”。由于这种宗教徒似的坚持和执拗,于是,他和当时中国大多数小说家,与当时文艺界的多数人,就发生了重大的分歧。
赵树理一方面承认民间的文艺有粗浅的一面,另一方面并不以为民间的文艺就都是低水平,他说:“农村从业者既是靠戏吃饭,其独到之处,也有许多值得做戏运工作的同志们重视的,千万不要抱‘放下你的一套来学我的一套’之痛快想法。”[15]“有些人误以为中国传统只是在普及方面有用,想要提高就得加上点洋味,我以为那是从外来艺术环境中养成的一种门户之见。”[16]近年有些论著谈及50年代初赵树理与丁玲等人的分歧,即所谓“东总布胡同与西总布胡同之争”,其中虽然确有人事纠葛的因素,但更根本的却是艺术理念的差异,如赵树理所说,“两个艺术传统中培育出来的人,在艺术兴趣上往往是不相入的”[17]。赵树理与丁玲的审美趣味不同,与胡乔木、周扬也不相同。本来,人和人之间审美趣味的差异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作为个人,保持自己的趣味、尊重他人的趣味就是。而作为一个以写作为职业,在文艺创作中寄托自身生命价值的人,如果感觉到个人审美趣味与文学界主流趣味、社会主流趣味的相斥,就会产生惶惑和困扰。正是这种艺术趣味上的冲突,使赵树理进城后几十年感受到深深的痛苦。如果是在一个很宽松的环境里,赵树理的艺术追求,作为一种风格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但他所处的并不是平静宽松的时期,艺术趣味的差异和政治运动中的波澜反复搅在一起,制约了赵树理艺术上的探索。《回忆历史,认识自己》里说:“老的真正民间艺术传统形式事实上已经消灭了,而掌握了文化的学生所学来的那点脱离老一代群众的东西,又不足以补充其缺。”“我在这方面的错误就在于不甘心失败,不承认现实。”不能说这都是赵树理的错误,但他却不能不承受由此带来的苦果。
赵树理说,“能理解知识分子以外的广大群众欣赏艺术的心理状态的人太少”。其实,真正能够深刻理解他的创作心理的文学批评家也不是太多。极端者,如美籍文学史家夏志清对赵树理的评价:“故事写得很笨拙”,“是一种民间幽默的粗糙尝试”,“完全摆脱欧化的左翼传统,嘻嘻哈哈为党做宣传”,“故意迁就工农兵读者的水准”[18]。从中可以看出不同文化环境、不同艺术传统中的文人审美上的隔阂如何之深!捷克汉学家普实克说得比较客观:“夏不大能够领会那些娴熟地运用了民间说书传统的作品的特殊魅力。”[19]理性的文学研究家,还是应该尊重自己趣味范围之外别种艺术风格存在的权利。
造成赵树理创作道路坎坷、挫折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作品的社会内容。他从来都很明确,他的创作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他把自己的小说叫做问题小说,“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20]。他这样做,是主动地自觉地使自己的创作成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成为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这也是他早期受到重视和表扬的原因。可是,问题小说,问题提给谁,作品中对于解决问题的答案,是站在谁的立场?在《回顾历史,认识自己》中,讲到粮食统购,赵树理有一段话:“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是矛盾的——在县地两级因任务紧张而发愁的时候,我站在国家方面,可是一见到增了产的地方仍吃不到更多的粮食,我又站到了农民方面。”也就是说,在农民面前他是政府立场,在领导面前他又是农民立场。他在几十年中所思所想、所说所写,也都有这样的两个方面。这后一点,就会为领导所不喜,乃至为环境所不容。《回顾历史,认识自己》里说,“检查我自己这几年的世界观,就是小天小地钻在农村找一些问题唧唧喳喳以为是什么塌天大事”。这显然并非由衷之言。关于农村、农民、农业,他曾有一些切中时弊的精当看法。1948年在《人民日报》连载的《邪不压正》,他说,“我写那篇东西的意图是想写出当时‘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知所趋避”,“‘土改’中最不容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21]。这是从土地革命到60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都存在而解决得并不好的一个问题,能够看出并在作品中反映反映这个问题的作家在80年代以前则极为罕见。1959年他给中央负责人写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提出的意见与上级的想法大相径庭,信被批转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协会找了一些人开会帮助他改变认识。严文井回忆说,“老赵虽然处于孤立的地位,却也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让”。历史证明,赵树理的意见是正确的。关键还不在于谁正确,而是在于文艺作品除了向大众宣传上级制定的方针政策之外,是不是还应该向社会、向领导反映下层大众的呼声?这是文学的大众性的一个核心问题。古人谈到文艺的作用时也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赵树理想用他的小说将下情上达,这是他被冷落的主要原因,也正是他的可贵之处。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和做法,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挖掘、分析和总结。
注释:
[1] 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四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年,第1360—1364页。
[2] 《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关于这次座谈会的报道。
[3]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序》,《瞿秋白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2页。
[4] 刘云主编:《中央苏区文化艺术史》,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07页。
[5] 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瞿秋白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19—20页。
[6] 赵树理:《供应群众更多、更好的作品(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赵树理文集》第四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年,第1522—1523页。
[7] 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四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年,第1490页。
[8]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第401页。
[9] 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第512页。
[10] 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四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年,第1358—1359页。
[11] 赵树理:《彻底面向群众》,《赵树理文集》第四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年,第1617页。
[12] 《普及工作旧话重提》中“两个传统及其关系”、“两种艺术境界”、“两种普及的前途观”诸节,见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四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年,第1543—1548页。
[13] 李普:《赵树理印象记》,《长江文艺》创刊号,转引自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8—19页。
[14] 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03—304页;又参见严文井:《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中国作家》1993年第6期。
[15] 赵树理:《对改革农村戏剧的几点建议》,《赵树理文集》第四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年,第1395页。
[16] 赵树理:《从曲艺中吸取养料》,《赵树理文集》第四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年,第1611页。
[17] 赵树理:《普及工作旧话重提》,《赵树理文集》第四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年,第1545页。
[18]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8页。
[19] [捷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49页。
[20] 赵树理:《当前创作的问题》,《赵树理文集》第四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年,第1651页。
[21] 赵树理:《关于〈邪不压正〉》,《赵树理文集》第四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年,第1437页。
【主持人语】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建设与发展实际上是在两个领域中展开的,一个是理论接受的领域,表现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译介、理解、阐释以及运用;另一个是文艺实践的领域,表现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境中对发生在创作和批评中的各种问题的论争。前者因为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和文艺观念有着直接的联系,成为人们研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发展演化的主要对象;后者却因为是发生在文艺实践中的具体事件,涉及个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因此常常处于理论研究的边缘,有时候甚至被忽略,以至遮蔽了研究这些事件对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所特有的意义。这种意义是指,这些具体文艺问题的论争往往产生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实践中所遭遇的现实问题,它们和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有关,而论争的发生又是因为在基本原理中没有现成的答案,反映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认识。所以研究这些文艺论争本身,特别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展开更深入的反思,便成为我们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历史发展的绝好材料,并为中国形态的当代建构提供有益的参照。这次发表的两篇论文,正是从这两个方面讨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问题的。特别是关于赵树理的一篇,不仅让我们认识到实证性研究对梳理历史经验的重要性,而且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思考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问题。(孙文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