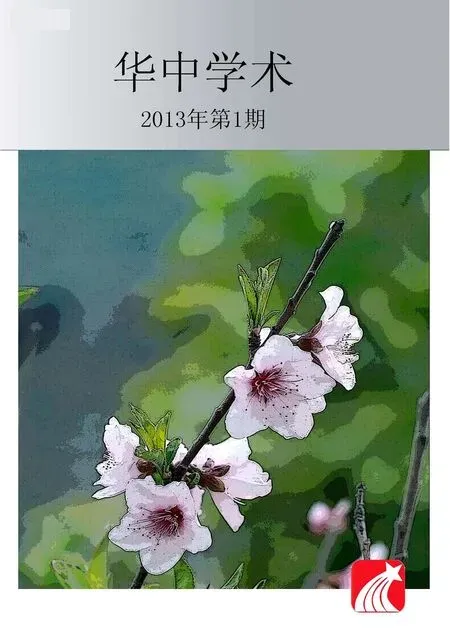难忘昙华林
——怀念我的导师石声淮先生
2013-04-10何新文
何新文
(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昙华林”,一个美丽而富有画意诗情的名字!这条坐落在武昌城区花园山北麓的历史文化老街,留存着许多历经沧桑的古老教堂、医院、民居、城墙,隐没着一百五十年前西方传教士设立的文华书院;还有不少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场所,清末民初以来政要与文化名人的旧居、公馆,更有许多华师学子耳熟能详的国学大师钱基博的故居朴园,私立华中大学“半居街市半居乡”的学苑公寓“华中村”,如此等等。昙华林的古韵遗风,珍藏着大武汉的城市文脉,也珍藏着百年华师的根脉渊源,是令无数老华师人梦魂牵绕、怦然心动的地方。
而昙华林带给我的美好回忆和永生难忘的情愫,则缘于我的导师石声淮先生(1913—1997)。三十多年前的1979年,即将大学毕业的我带着几分兴奋、几分敬畏,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跟随导师石声淮教授攻读先秦汉魏六朝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记得第一次来到昙华林,是那年暑假去先生寓所接受面试。走近华中村14号那栋上下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门前有几棵枝叶繁茂的高大朴树,顿时便觉有一阵清凉袭来。进得门来,踏着十余级木板楼梯上到二楼,然后向左沿着走廊进入先生的书房。书房不大,却十分整洁简朴,摆放的书也没有我先前想象的那样多,只见一两个不大的书架上摆放着一些线装及平装的书。身材高瘦、精神矍铄的先生,就坐在书架前面的书桌前。几句寒暄后,他老人家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线装书,打开书本指着其中一段没有标点断句的原文及注释文字让我读。读完后,又指着书页上“杜氏注”三字问我这“杜氏”是谁?好在我准备考研时已在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韩珉老师家里翻阅过线装的《十三经注疏》,便回答说“可能是西晋注《春秋左传集解》的杜预”,心想刚才读过的那段文字就应该是《春秋左传正义》的原文和注疏吧。于时,先生露出微笑,说了一句“那好吧”,这次面试也就算完成了。昙华林的初次拜访,给我留下了幸运、愉悦的感觉。
在面试以后不久的9月下旬,学校通知我们正式录取的四名研究生与导师见面。石先生是省内外知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他博闻强识,谙熟古代文史文献,而且英语、德语很好,又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是校内外闻名的“活字典”、“活辞海”,在省内古典文学界颇负盛名。记得考上研究生后,我原来学校的老师、武汉师范学院的张国光、李悔吾教授曾对我说:“石先生是名师,考上他的研究生不简单,你可要认真学习哦!”两位老师的叮嘱,更增添了我对先生的敬畏感。但在我后来的记忆里,被称为“名师”的先生,倒没有什么名师的派头。他是一位造诣深厚的学者,自有一种博雅和善的风范,而且也不乏幽默和风趣。那一天,我随佘斯大、邓云生(即唐浩明)、周禾三位师兄去中文系拜见导师,一见面先生便说:“我看过你们的试卷,很短的时间却要写那么多文字,还真不容易,要是我可能还考不上我的研究生哦!”一句风趣的话语,立即引来同学们轻松的笑声,刚开始有点紧张的气氛也变得随和了。
自那以后,去昙华林的次数便多了起来。从1979年下半年起,直至1982年7月毕业前夕,在读研的三年时间里,先生几乎每周都要在昙华林华中村14号他的书房里给我们讲课。听课的人,除我们四名同学外,有时也还有华师中文系及校外的教师或进修访问的学者,如周伟民、唐玲玲、涂光雍老师等就时常来“旁听”。大家如约来到昙华林,在先生的书房里,品尝着钱钟霞师母准备的茶水,听先生用地道的湘方言为我们讲课,从《周易》、《诗经》、《左传》、《国语》、《国策》、先秦诸子,到汉赋、《汉书·艺文志》,南北朝乐府诗歌,有时还讲唐诗如白居易《长恨歌》、李商隐《无题》诗等。每次一讲就是一上午。
先生对于先秦典籍烂熟于心,对于《史记》、《汉书》,六朝文史、唐宋诗文,也非常熟悉。听先生讲课,可谓是一种高雅的艺术享受。他一般不看教材,而是以他独具特色的长沙话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如坐春风。对于原文,他总是直接诵读,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倒背如流;讲解的时候,则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记得刚开始给我们讲《周易》,无论是《易经》还是《易传》,都是先生在前面一边背诵一边讲解,我们几个同学忙着在后面寻找、翻阅他讲读的内容,还往往应接不暇。
同时,先生又极富音乐与绘画素养。上课时,他曾经按照古韵用抑扬顿挫的长沙话唱诵屈原《离骚》,吟诵李商隐的《无题》、《锦瑟》诗;在讲解《离骚》“跪敷衽以陈辞”、“驷玉虬以乘鹥”、“搃余辔乎扶桑”,《国殇》“车错毂兮短兵接”等诗句时,又随手在黑板上用粉笔画速写,简单几笔就会勾勒出一些古代服饰、器物的形象或人物的行为状态,以解释“跪敷衽”、“驷”、“搃”、“车错毂”等词语,所画人、物神形毕肖,直观形象,易懂易记,让我们兴趣盎然,印象深刻。
讲完安排好的内容后,一般总要留约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让大家提问。这时候,能够较多地提出问题的,常常是知识渊博的大师兄“老佘”和能言会道的“老邓”(当时我们都这样叫,虽然三十岁刚出头的他们并不“老”)。如果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问题,我们就和先生闲聊一会,然后再与先生和师母告别离开。
先生的课上得好,深受学生欢迎,除开他渊博的知识、深厚的功底、多才多艺的素养、熟记背诵等专业功夫之外,还与他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关爱学生的崇高师德和循循善诱、科学得当的教学方法有关。听很多同学讲,石先生总能够记住学生的名字,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认真履行教师职责的风范;每次上课,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进行准备,讲课虽不带书,但总带着一些用中文或英文写的卡片,上面写满先生精心设计的授课内容。此外,还把他写的《中国文学先秦之部小结》、《左传概述》、《北朝民歌》等讲义给我们抄读。看得出他对授课、备课有多么重视。
先生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也有独到的特色。先生强调背诵经典,背书是他的基本功课。他告诉学生,背书也是有方法的,背书要先在初步理解的基础上反复朗读,边读边加深理解,理解透了也就背会了。“会背书者背结构”,是先生的经验之谈。文章篇下有章,章下有段,段有层次,层次由句子组成。由句到层,由层到段,由段到篇章,这其中有步骤有规律,掌握这规律和步骤,就比较容易背熟,而且记得牢实。他授课,也重视结构。1980年6月2日,先生专门讲授过一次“怎样备课”的问题。他说备课的步骤:一是要通读课文,要达到三个目的,即了解课文的大致意思、结构,弄懂并标记主要的字眼;二是重点分析文章的结构,搞清楚课文的上下前后关系、主从关系、因果关系、层次关系,文章的线索,时间线索、事物发展线索、矛盾发展线索等,这样便于记忆。如讲贾谊的《过秦论》(上),着重分析结构:前后两个半篇,前半是写秦始皇以前,从诸侯到帝王;后半是写秦始皇时代,从帝王到灭亡。先生说,讲课不能只讲第一段、第二段,而应该交代清楚全文的整体结构,交代清楚段与段之间的关系;三是通过文章的结构分析而得出课文的主题思想;四是总结写作特点,而首先还是应该总结结构上的特点,如此等等。在讲《长恨歌》时,他也强调:“讲长作品的诀窍,就在于把握整体结构。”他以李白《秋浦歌》第十六首为例说:“秋浦田舍翁,采鱼水中宿。妻子张白鹇,结罝映深竹。”此诗是说一家人妻离子散,种田的去打鱼,晚上不在家,妻子也得出去打鸟。为什么能够看得出此意来呢?就是因为掌握了诗的总体:田翁 + 妻子 = 家。
先生治学严谨,又秉持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述而不作”(或许应该是“厚积薄发”)的学术传统,反对轻率立言和华而不实的文风。他不轻易著书立说,论文也写得不多,可谓是惜墨如金。即便有所论著,也常常是从考证入手,细读文本,深入分析文本内容、探寻作者原意,并在充分占有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十分审慎地形成自己的观点、得出自己的结论。因而,也往往能得出不同常人的新见胜义。如先生长期致力于《周易》研究而且很有心得,但也只发表有《说〈损〉〈益〉》、《说〈彖传〉》(上中下)、《说〈杂卦传〉》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先生的这些论文,大都送我们学生每人一份。这些文章论点明确,考证精详,文风朴实,文字简洁洗练,持论平允审慎,绝无主观臆断、浮华无根之病。尤其令人感慨的是,送给我们的这些已经发表了的论文,先生又进行过认真的校读,改正了或出于原文或出于印刷的一些讹误。仅以我手上保存的这篇刊载于《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的《说〈彖传〉》(下)为例,经先生亲笔校改的文字就有6处,如将《大畜》卦《彖传》之“利有攸往”改正为“利涉大川”,在“《左传·昭公十八年》春王二月”之后补上“乙卯”二字,将“成”字纠正为“或”,还有一处是改正单括号“)”打错的地方。这些细微的错讹,年近七十高龄的先生仍然一一检出、逐个改正,可见他对发表过后的文章是又一次地认真通读并且校核过全部引文的!这是一种多么严肃认真、细致踏实的学术精神,这又何尝不是一个真正学者人格的生动体现。试想一下,我们今天年轻的学者,还有几人能有先生这般的执著和耐心。
除先秦典籍外,先生对宋代大文学家苏轼的诗文词赋有着特别的喜爱和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先生与唐玲玲教授一起合撰有《苏轼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和《东坡乐府编年笺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二书。其中《东坡乐府编年笺注》的编写,历时八年之久,在已有朱祖谋《东坡乐府》及龙榆生《东坡乐府笺》的基础上,对列入的苏词348首(其中编年241首、未编年107首)详加考证、勘误、注释和补充,书后又列有《各本题跋》、《东坡词评论》、《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东坡词版本简介》四个附录。全书考订精审,资料丰赡,注释详细,与享有盛誉的朱本、龙本相较,也可谓后出转精。如书中所列《皁罗特髻》(采菱拾翠)一词:
采菱拾翠,算似此佳名、阿谁消得。采菱拾翠,称使君知客,千金买。采菱拾翠,更罗裙、满把珍珠结。采菱拾翠,正髻鬟初合。真个、采菱拾翠,但深怜轻拍。一双子、采菱拾翠,绣衾下、抱着俱香滑。采菱拾翠,待到京寻觅。
全词81个字,却有七句“采菱拾翠”,占全词字数三分之一以上。但这“采菱拾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龙榆生《笺》只引《楚辞》“涉江采菱”及《洛神赋》“或拾翠羽”等资料交代出处,并没有说明在这首词中是什么意义,读者仍然难以理解整首词的内容。而本书的笺注,既注意词中典故成语的来历和具体字、词、句的解释,更注重全首词整体意义的把握。笺注者细读全词,从词中“似此佳名、阿谁消得”和“一双子”两句分析,“采菱”和“拾翠”当是这“一双子”的“佳名”,而不是成语典故;又引《苏轼文集》卷九十五《与朱康叔》第十五首“所问菱、翠,至今虚住”文句,作为“菱”、“翠”为妓妾名的佐证。从而得出结论说:“此词应是咏两个(‘一双子’)被知府或知州(‘使君’)买来的妓妾,一个取名采菱,一个取名拾翠。她们服饰华丽,皮肤香滑,除京城外,别处无从觅得。苏轼受她们的主人请托,作这首词。词中七次提到她们的‘佳名’:‘采菱’和‘拾翠’。”这样一来,这首仅见于苏轼所填且难以解读的《皁罗特髻》词,就清楚明白、迎刃而解了。在此书中,像这样从文本具体内容出发,注重整首词意的理解,且发前人所未发的胜义,俯拾即是。故著名学者周振甫先生看到此书以后,曾于1990年12月13日致信石声淮先生,并高度评价道:“尊笺于系年及注,皆胜龙《笺》,后来居上。考订既精,笺注复详援据,非博稽详考者不能为。据尊笺,据以读苏词,可以窥苏公之经历与心曲,尤为可喜。”
先生不仅以这种严谨、朴实的学风律己,而且以此来严格要求他的学生。在这方面,我们几位同学大都有终身难忘的体会。可能在先生心目中,著书为文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非有真才实学且具真知灼见者不能为。因此,他不轻率立言,不赞成研究生忙着发表论文,也从不催促我们写文章,反而还告诫大家不要学某些人没有什么心得却喜欢“干喊干叫”,所谓胸无点墨,却好自矜夸。记得我们进校后,华中师范学院《研究生学报》就创刊了,编辑部的同志多次向我们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约稿,但大家谨遵先生教训,都不敢造次为文。直到临近毕业的那年,想到本专业也不好在这份研究生自己创办的内部刊物上留下令人遗憾的空白,几位师兄才怂恿我(理由是我岁数最小,先生或许不怪),瞒着先生草写了一篇题为《从文学史的角度略谈〈易〉卦爻辞》的文章送到编辑部,在1982年8月的第3期上发表出来:这是三年来我们“79级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在上面发表的唯一的一篇文章。学报出来时,已经是毕业之时,我们都要离开先生而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了。
对于文章的文风,包括遣词造句等细节,先生也要求严格。他见不得那些鬻声钓世、为文造情之作,见不得那些刻意追求华丽辞藻之文。甚至于大家论文初稿中出现诸如“积淀”、“冒天下之大不韪”之类的词句,先生也颇为不满,要求改掉。我当时用钢笔手写的硕士学位论文《〈左传〉写人艺术略论》的开题报告,共17页,经先生审阅后,不仅每一页都有他用红笔修改的文字或批语,而且这些批语、修改文字及标记符号多达七十多处!这些批改文字,虽然其中也不乏肯定之词,但主要还是指出不妥或错误之处。如:(1)对于援引《左传》原文或其他文献不规范之处,则批示要“标明某公某年”、“举出篇名”、“注明篇章”;(2)对于提法不妥或举例不当之处,则批示“不是如此”、“说得很含糊”、“我读不懂”等等,有的地方还会一连提出三四个反问来反驳你的不妥之说,有时当然更会提醒和补充很多我不知道的资料;(3)对于文稿中出现的文字错误,除了直接改正之外,有时也会提出很严厉的批评,如第11页,我的原稿将晋文公夫人“文嬴”误写为“文赢”,先生就批示说:“‘嬴’,这个字不是‘笔误’,而是不肯翻书,贪安逸!”读着这样外表严苛却内涵温润的文字,我至今仍为自己的无知、粗疏、慵懒,给年迈的先生带来太多的辛劳、麻烦而深感愧疚!但是,稍可庆幸的是,正是先生如此这般的严格要求、悉心指导,使我如醍醐灌顶、彻底醒悟。先生的言传身教,不仅指导我顺利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而且促使我时刻保持警惕,在此后从教为学三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心怀敬畏,脚踏实地,孜孜追求。先生仰之弥高的学术品格、教泽风范,弟子虽不能仿佛其万一,但无数晚生后学确已在先生如炬的目光注视下不骄不躁、努力前行,先生所留下的无比珍贵厚重的精神财产,已成为我辈终身受用取之不竭的万斛泉源。
毕业之后,没有机会再聚集在昙华林先生的书房里听课了。但华中村那座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仍然是我们师兄弟和先生团聚的圣地。我和佘、周二位师兄约定(有时还有从长沙赶来的唐浩明),每年至少一次或两次去那里看望先生。门前的朴树依然茂盛,先生也还是那样的温和博雅,嘘寒问暖,记忆犹新。就这样,十多年来从未间断,一直持续到先生迁居桂子山华师本部的新居为止。此后,真的再也没有去过昙华林了。再后来,也就是十五年前,与孟子同寿高龄的先生又驾鹤西去……
寒来暑往,春秋代序。前行不歇的历史风雨,变幻不定的时代烟云,并没有冲淡或遮挡我对昙华林的怀念和记忆。前年暑假,趁着在省中医院住院的机会,我又一次来到了阔别已久的昙华林!沿着重新修建的那条老街,走走停停,寻寻觅觅,只见一幢幢仿造得“古色古香”的新近建筑树立在街道两旁,却再也找不到我曾经熟悉的“昙华林”的身影。此时此刻,一种莫名的感伤涌上心头。然而,就在我凝神遐想之际,那曾经镶嵌着“华中村14号”门牌的小楼,小楼门前那高大挺拔的朴树,楼上书房里那温暖如春的点滴情景,还有先生、师母轻盈的姿态与笑貌音容,又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升腾在我的心中。
难忘昙华林!难忘华中村14号那座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