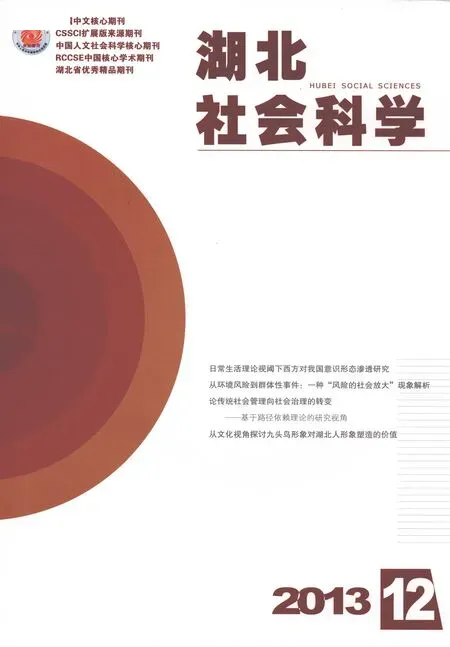论庄子的象、言与“大美”
2013-04-10王唯茵
王唯茵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无锡 214153)
庄子在《齐物论》中曾说道:“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道为昭显之“道”,其“道”也就远遁于外了,论辩的“言辞”总有它所到达不了的地方。这也就是在说明,言“象”、立“言”不足以来表达“大美”。因为“大美”的超越性已然不是言“象”、立“言”所能够把握的。
一、“大美”与象
“象”作为主观的视象,与心相关,作为心的一种显现。既然是显现,便有虚实之分,即显现的可以为实相,也可以为虚相,二者无主次、高低之分,只是显现的方式不同。将“象”纳入到“大美”的视域关联中,可以分为两个面向来观入与理解之,试图将显现于心的具象穿越虚无的美感视觉,这两个面向即是:显于象与隐于象。
(一)“大美”显于象。
在关于庄子对“大美”的描述当中,以“象”称美为一贯的手法,通过对象的比拟与描述来映衬“大美”。“大美”无形无相,既不可以以一种具象的特征将自身的美映衬出来,也不可以通过外在的陪衬物自我显映于差异化的显现之中,它唯有借寓言故事来加以说明,这一点类似于周易“以卦言事”。按照“以象附之”的比拟与阐释,即是说明,象有显现“大美”的能力,“大美”可以为象所呈现,此呈现是作为呈现“有象之象”而呈现出来,而不是作为“无象之象”而隐喻其中,“有象之象”是具体的呈现也就是指“可见之象”。此种“可见之象”与“无象之象”相区分,它彰显自身可以显化“大美”的属性特质。
庄子在形容大椿树的“大美”说:“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庄子·逍遥游》)[1](p11)很显然此种显现“大美”的方式是通过一种具象的表达而实现的,“八千岁”表达不只是时间上的跨度,而更是在对大椿树绵延不绝生命之美的一种礼赞,春秋各为“八千岁”这样很具体地将大椿树“大美”的形象从虚中抽取出来而幻化为一种实在。比如还有对栎社树之“大美”的刻画:“其大蔽数千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庄子·人间世》)[1](p170)同样,通过“数千牛”、“百围”、“十仞”、“十数”这样的近于生活经验的表达,将抽象的“大美”还原为一种生活经验,毋庸置疑能让“大美”在生活经验的层面回归到真实、具体。庄子诸如此类的通过侧面的“象”来描述“大美”的事例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出来,因为所有的事例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是:通过“有象之象”的呈现来还原“大美”的轮廓。
“大美”通过“象”来映衬,那么“象”自身是否可以尽“大美”?答曰:不足以尽“大美”。“象”不足以尽“大美”在于:其一,“象”作为有形的事物表达,它只是暂时的,而暂时的事物转瞬间即为化为无,故而它自身还构成不了“大美”;其二,构成“大美”事物的特征不外乎在于其自身的抽象性、不确定性与超越性。抽象性指的是它不是一种具体美的表现,具体美的表现一般都是“小美”,而抽象性的美才算称得上是“大美”,也只有抽象性才能激发观者想象的思维,而“大美”也一般与观者的想象有所关联,这样无疑使得抽象性的事物更接近于“大美”;不确定性指的是构成“大美”的事物往往不拘泥于单一的形式,而“象”作为单一形式的展示,所以不足以尽“大美”,所谓“大音稀声,大象无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超越性指的是构成“大美”的事物往往具有超越现实的能力,现实的东西按照柏拉图来讲,都是不美的,只有抽象的“美的理念”才是“大美”的,因为现实美的事物都是对“美的理念”的一种模仿与分有,既然是分有与模仿,无疑其层次没有抽象美的理念之高。所以象作为一种现实的事物,它不可能具“大美”。
对于象作为“大美”的映衬与表达,虽则其自身不足以构成“大美”,但在对待“象”时不可固执其中,因为如上文所讲的那样,它本身就是暂时、片面的。庄子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1](p756)又接着说:“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1](p756)在这里,乐与悲伤作为“象”语的表达,它转化逆来,可为什么庄子会“悲”,因为它感叹世人为“象”所固执,即为“物逆旅耳”。这些“象”无论在物,还是在人都是作为一种瞬间存在的形式而存在着,所以说在对待“象”上不要固执其中。在看到“象”呈现“大美”的同时,也要警惕“象”自身的虚无化的特征。
(二)“大美”隐于“象”。
所谓“大美”隐于象,“隐于象”即是说明“大美”无象,但“大美”无象并不是在说“大美”的虚无,“大美”作为隐于象它自身区别于无,因为它是“有”,此种“有”是作为“象外之象”而存在的。“象外之象”似有若无,但绝对不是虚无。
庄子言“物我并生”、“物我为一”,这种“为一”、“并生”本身即是对“大美”其共在状态的一种表达,说明“大美”是作为共在而敞开自身的。天地万物流逝不定、变化不居,因此其敞开于万物之上的“大美”也变化莫测,在不同的形式上显现着道化万物的内在力量。“大美”隐于万物,作为“象外之象”而显映之、变幻之。
庄子所描绘的人物当中,并非个个相貌俊美,也有一些人物相貌奇丑,身体残疾,比如在《庄子·德充符》篇中,叔山无趾、兀者王骀、支离疏等人物不是面貌狰狞,就是身体欠缺,但是这些庄子所刻画的人物形象虽然有失“大美”形象,但他们个个备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正是因为他们自身内在德的修养之境界高,此种境界就是一种无形的“大美”,此种“美”无关乎“象”,它也超然于象之美。正如庄子所说的“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1](p217)有“德”才有内在的修养品格,才有“大美”的显现,这样自然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所以与之相比,外在的相貌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综上所述,“大美”在显于象的同时,也隐于象,它若有若无,有显有隐,时虚时实,它显化于有无、虚实、显隐之间。可以说“大美”已然超越了“有象”与“无象”的边界,是作为“象为之象”而呈现出。
二、“大美”与言
“大美”不显于“言”,其原因有二:其一,言自身的限制使其无法所言,二是“大美”不言因其“道”的超越性。
(一)不显于言。
庄子在《天道篇》有曰:“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1](p488-489)
世人所贵者为书,因其书中之言,言之所贵即为意,但意却不可以转述,即“不可以言传”。世人贵于言,而后立著成书。庄子以“道”为贵,而世人却贵于言。在庄子看来,“言”是末,而“道”为本,语言只是一个表象,除此无它。
由此而观之,“大美”作为“道”之本的体现,它隐斯于言语的表象之中,它切入生活的意蕴之中而无法言及。所以庄子有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知者不言即深知言语的穿透实力不足以穿越“大美”的意象的表达,那些为语言所传导的也不是真正的“大美”之境。
此外,所谓“辩也者,有不见也”,言的本质在于“知”,此知作为“知向”而不是“知得”。“知向”在于意会与体悟,而“知得”在于理论建构与逻辑梳理。庄子说:“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1](p1069)所谓“判”与“析”作为“知得”而呈现出,用“知得”去探求“大美”必然有失。
综上所述,由于言自身的局限与欠缺穿透的能力以及人取“知得”的理性逻辑,无法言及“大美”之美。“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庄子·则阳》),[1](p914)言与知都无法超越于具象的物象之表达,所以,“大美”无法为“言”所切中。
(二)无需言。
“大美”的无须通过语言的通道而呈现出,因为“大美”无需言。庄子曰:“至言去言。”(《庄子·知北游》)[1](p765)“至言”的“大美”是“去言”的。庄子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天地”、“四时”、“万物”以无言的方式而运行之。此种无言的方式更好地传达出了朴素“大美“的呈现无关乎其它而只关涉到寂静无声的言语。
同样的道理,“言”作为人的活动,它与自然的“言语”相区分。即是“言非吹也”(《庄子·齐物论》),[1](p63)自然的“言语”是纯粹的无目的性的言语,它与任何企图无关涉,但作为人活动的“言语”与人内心的目的是相联系的,语言也同时建立起人存在的根基,建立了是非曲直的标准。在孰是孰非中各自相互争执中,“道”已经藏匿,“大美”隐没。《庄子·列御寇》篇有言:“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1](p1045)如果人能回归到一种无所为并且对自然万物不实施干预的话,融入天地万物的并生之中,即万物即我的境界,那么“大美”何需言。
三、“大美”超象绝言
以“无象”而言“大美”,以“象”而言“大美”,或以“无言”言“大美”,这些表达都含有一种悖谬的性质,因为“大美”超象而绝言,如何企图通过“无象”而言“大美”,以“象”而言“大美”,或以“无言”言“大美”都是“大美”的一种偏失,“大美”不是可以通过逻辑推理或者分析可以把握的。越是固执于“大美”的寻求,就越会停留于“象”的层次,从而产生滞待。当我们产生滞待的那一刻,所谓的“大美”早已逃之夭夭。所以,我们捕捉“大美”的前提是要破除“象”的显化与“言”的表达,也只有超越“象”与“言”,才有可能认识到把捉到“大美”。
(一)象罔得其全。
何为“象罔”?他只是庄子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在庄子的《天地篇》有记载:“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1](p944)
这个故事记载的是关于黄帝遗失“玄珠”而复得的这么一个故事。首先黄帝下令“知”去寻找,但“知”“索之而不得”。后黄帝派“离朱”去寻找,但“离朱”还是“索之而不得”。尔后黄帝派“喫诟”去寻找,但“喫诟”还是“索之而不得”。最后,黄帝让“象罔”再次去寻找“玄珠”,出奇意外的是“象罔”找到了黄帝遗失的“玄珠”。
其实这个故事暗含了很多的“道”于其中,故事中的“玄珠”即是对“道”的一种隐性表征,也可以作为“大美”而隐含之,“知”即是“智”也,“朱”即是颜色,“离朱”即是指形色,“喫诟”指谓的是“辩言”,而最后所谓的“象罔”即是“无象无言”的引入。故事虽则简单,但是蕴含着庄子深刻的智慧与见解,后人郭庆藩释曰:“象罔者,若有形,若无形,故曰眸而得之。即形求之不得,去形求之亦不得也。”意思即是说,“象罔”得“玄珠”于有形与无形之中,在有形与无形当中“眸而得之”,此“眸而得之”并不是遵循某一特定的方向,而是在于其自身之境界。境界的层次提高了,故而易求得“大美”。
通过“象罔”来呈现“大美”,在庄子的文本中不乏其陈,如庄子所描述的“无极之野”、“大莫之国”、“六合之外”等,其实都没有逃离“象罔”的指引。庄子将“大美”之境置于一种无限的时空之中,那种试图通过理性之思而进达所谓的“大美”之境界都是徒劳的。
“昔者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尧曰:‘然则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尧曰:‘胶胶扰扰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为哉?天地而已矣。”(《庄子·天道》)[1](p475-476)
舜曾经问尧,天王如何用心治理天下?尧回答说,“不敖”、“不废”、“苦死者”、“嘉孺子”、“哀妇人”。舜的回答是,这样作是“美”,但不算“大美”。尧就问,如何才称得上“大美”,舜就回答道:“天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尧感叹道:你是与天相结合,我却与人相结合。所以,庄子说,天地向来都尊为大,尧帝与舜帝都以天地为“大美”。
尧之用心都是有其“象”,此象在舜看来,都是小象,算不上“大美”;而天地安宁于恒常,无形似有形,显于无象之中。但正因为其无形而有为,所以“天德而出宁”,其源于“大美”;昼夜有经,其经在昼夜具象之外而显化,云雨相生,四时运行。所以,“大美”无象,却表达于“象”,此“大美”之象以超然于象本身而作为“象外之象”而呈现出来。
(二)得意而忘言。
庄子对语言保持有一种戒备,以至于他对语言保有否定的态度。但《庄子》本身就是由语言而构成的。“大美”不能为语言所传达,庄子却借用语言的这一工具来达到“大美”之境界。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1](p944)
庄子所讲的这个故事很好地解答了“言”与“意”之间的矛盾。“荃”就是指捕鱼的篓子,也就是说,鱼篓是用来捕鱼的,捕到鱼了之后鱼篓就没有多大的作用;兔网的作用是用来捕兔,捕到兔子后兔网也就没有什么大的作用;言语是用来理解“意”,理解了“意”,“言”也就自然遗忘了。所以庄子借此故事是在告知对“意”的领会与理解虽然借助于“言”,但不是执泥于“言”,此种“意”即是对“大美”的一种表征,太执着于“言”,就会“错失”“大美”。
庄子在否定语言的同时,也借用了其语言这一通达的工具,通过其“无端崖之辞”来达到言说这一目的性,但言说的目的不在言说之中,也不在言说之外,而是“破言”,以“言无言”的方式去叩开“大美”的窗户。对于这些真正能得意而忘言的人,又何必与其言说?故而庄子有叹:“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综上所述,“大美”显于象,又超然于象,有无相生。在其显现时,表现于具象之中,在其隐失时,又超于象外,化为“象外之象”。“大美”超绝于“言”,对“大美”的洞见必须超脱于言语的限制。因此,只有超象绝言,直指世界的本体,以“道”通观万物,才能领悟“大美”之境。
[1][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