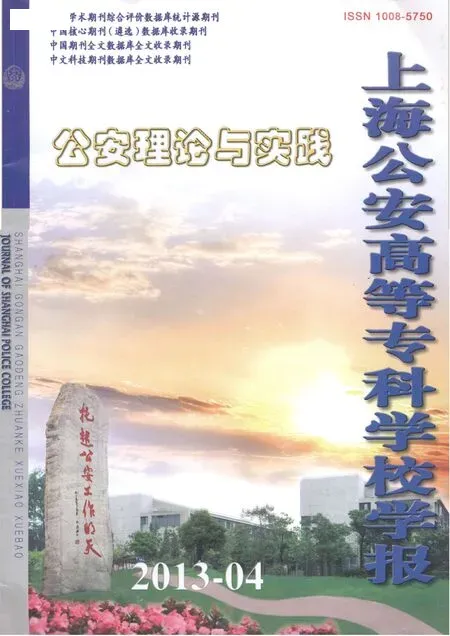儿童性侵案件侦审问题与对策
2013-04-10庄忠进
庄忠进
(台湾警察专科学校,台湾 台北)
儿童性侵案件侦审问题与对策
庄忠进
(台湾警察专科学校,台湾 台北)
儿童性侵害案件因其特殊性质,固难以在被害人身上采到完整或具体之证据,惟如检警人员善尽调查、查证、搜证、采证、举证与论证之能事,依旧可以将犯罪者绳之以法。为求提升侦办儿童性侵案件的能力,侦查人员宜精进有关儿童认知与心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取得询问儿童的专业认证。检警机关应建构本土性的性侵害被害儿童标准化的询问作业及供述效度评估量表,针对不同类别之性侵案件,归纳出犯罪者类型、犯罪者特质、犯罪手法、相对伤痕、对应证据、被害者类型、被害者年龄、被害情境、可疑征候、被害后之异常行为与心理反应等等,彼此之间的对应、甚至因果关系,至少应制定检核表,以利受理与侦查。关于儿童被性侵案件,似宜将儿童再细分为幼儿园阶段与小学阶段两类,以符侦审需要。
儿童;性侵害;猥亵;侦审
一、前言
台湾地区《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员会保护数据库系统》统计数据显示:儿童及少年遭受性侵害①指对于未满十二岁之人为强制性交或猥亵。人数,2009年为4684人,2010年为5630人,2011年为7025人,就与前一年比较,约分别增加20%与25%,幅度相当惊人。复因儿童性侵害案件具有:低度被揭发率、不易搜证与举证、被害儿童记忆与回忆未必可靠、供述易受诱导扭曲、是否遭受性侵害与身体或心理有无创伤反应并无绝对关系、被害儿童往往翻供、供述内容不够具体等等(庄忠进,2012),导致儿童性侵害案件之审判,不管有罪与否,均引起极大争议,甚至有检察官直接行文质疑:你相不相信孩子(吴维雅,2007),公然挑战审判结果。因此,如何解决幽微难懂的儿童性侵害案件,不但是妇幼安全的重大议题,更是侦查实务上的一大挑战。
二、所面临的问题
儿童性侵案件侦审之所以引起争议,大多在于难以取得实体证据而必须以被害儿童供述及其异常的身心或行为反应,作为起诉的唯一证据,即便辅以专家证人对被害儿童身心状态进行衡鉴,审判结果亦经常难以预测,甚至出现两歧的结果(吴维雅,2007)。
造成此等现象可能之原因,就侦查而言,大致有案发之后数月甚至数年后被害者才提出指控,导致证据湮灭,甚至不知从何处着手搜证;被害者关于遭受性侵害的供述受到诱导或暗示;猥亵几乎不会留下任何实体证据;非暴力性的强制性交,即便有伤痕,亦可能因为事过境迁而自愈或复原(李建璋,2011)、年幼儿童不知②例如,加害人以提供看电视、打计算机或玩游戏的机会,对智能不足的国中一年级女生进行猥亵,该女生不仅不认为受到侵害,甚至于案发后接受保护期间,犹频频私下打电话给加害人(嘉义市网络团队经验分享,台湾地区防暴联盟,2013)。、不认为③2012年5月间,台北市发生某国中十七位男同学遭受性侵案件,因为加害狼师系以带学生郊游烤肉、给零用钱等方式拢络被害人,并以照顾与管教之名,帮学生按摩与检查身体为由,借机对弱势家庭出身的学生手淫、口交或肛交,案发后大多数表示受到伤害,却有位被害者因受到狼师的照顾,而不认为受到性侵害(台湾地区防暴联盟,2013)。、甚至误以为受到性侵害;儿童回忆不全甚至错误(陈慧女、陈美燕,2004);为免受到二度伤害或产生诱导,侦查阶段不能过度询问;吊诡的是,为求真相而积极询问,亦可能会造成虚伪供述(庄忠进,2012)等等。就审判而言,大致有法官对于儿童认知发展与创伤心理或行为所知有限、甚至误解,例如,儿童翻供、供述前后矛盾、供述欠缺逻辑性等等,所为指控往往被法官认为系出于虚伪①如果是成年被害人,推定为虚伪供述应可接受;但认为儿童供述必须具备逻辑性与合理性始可采用,实属过度要求。(刘贞汝,2011);儿童是否有创伤症候群或性侵害适应症与有无遭受性侵害并无必然关系,过度依赖专家证人进行审判缺乏学术依据等。
三、因应对策
以供述为侦审依据所面临之问题,固有属于本质上难以克服者,例如,强制猥亵的案件几无实体证据;然亦有因侦查过程受到暗示、诱导或污染、侦查意识不足、论述举证不全、认知偏差或错误者,实有待透过严密的侦查流程或制度,担保或补强儿童供述的正确性,以供起诉审判之参考。
(一)再确定供述是否受到污染或诱导
当查无实体证据时,就逻辑论证而言,只能回头检查有无干扰因素导致供述错误,从确定否证事实不存在去推定待证供述为真(黄光国,2001)。除了查明有无不正动机②例如,母亲为离婚而唆使女儿诬指父亲性侵等等。外,应就以下三个方向,查明供述有无受到污染或诱导。
1. 犯罪如何被揭发或发现?
性侵案件如何被揭露,是判断供述正确性的重点。布朗(Brown)认为揭露是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可能开始于相当戏剧性的一步③④例如,母亲帮女儿洗澡时发现阴部有挫裂伤、老师发现学童玩弄性器官等等。,也可能是一系列的尝试、试探或暗示的过程⑤网络时代,愈来愈多妇幼安全案件,系被害者于脸书、网络、聊天室等分享时,慢慢揭露(台湾地区防暴联盟,2013)。。因此,儿童有准备的叙说、过于完整的揭露,通常系受到诱导或唆使,并非真实,特别是被害者为学龄前儿童年纪愈小者。
当被害人主动诉说时⑥一般而言,这类被害人殊少会独自径向司法警察报案。,则应查明向谁诉说⑦对象包括任何可能污染供述者,例如,最先受理的基层警察。?两人具何种关系⑧有无信任到向其述说的程度。如被害者向素不关心他(她)的母亲诉说父亲对其性侵,再由后者向警察举发形同陌路的丈夫性侵其女儿,供述可靠性就要存疑。?并了解诉说经过、内容与方法、听闻者如何记录或记住供述内容?听闻时作何反应⑨例如,母亲听到女儿诉说遭家庭成员性侵时,何以迟未举发?何以直到本件才举发?有无质问谁是嫌疑人?如何质问?是否过度质问?如不质问,原因何在等等,均要查明。?如果曾向多人诉说,查明供述内容关于被害的关键问题是否一致?如果是被人察觉,应查明如何察觉?察觉后作何反应或处置?有无询问被害人被害经过?如果有,如何询问?被害者如何回答?有无做成纪录?余类推。
2. 案发后多久被揭发或发现?
即使无阻挠因素,案件愈晚被揭发,儿童记忆愈模糊,最后甚至只能记住印象极其深刻者而已。至于有无其它因素干扰而延迟举发或揭发者,应设法了解以供判断是否确实被害。一般而言,遭受陌生人暴力性侵者,即使身体外观并无伤痕,除非精神受到严重创伤⑩关于妇幼安全案件之发现、揭发或掌握,实务工作者的顺口溜是:“法官知道的不会比检察官多,检察官知道的不会比警察多,警察知道的不会比社工多,社工知道的不会比三姑六婆多。”(引自洪淑姿检察官经验分享,台湾地区防暴联盟,2013)。狗尾续貂,可以再加上“三姑六婆知道的不会比上帝多”。而不想、不敢言说,应该不会迟未向他人反应或被揭发,因此,这类案件隔了一段时间,父母才诉请警察侦办,真实性容或存疑;然而,加害者如具血缘、亲属、教养、辅导、教育、照护、安置等等关系者,被害人可能受到加害人或利害关系人①例如父亲性侵儿女,母亲胁迫被害人不得报案。胁迫或恐吓、为了维护家人名誉、顾及被害人前途或名誉、年幼不知遭受性侵、受到利诱等等而迟未、甚至数年后才报案或被揭发②国小三年级女生遭受继父性侵,迟至国中二年级接受性别平等教育后,方确定遭受性侵而向同学诉说因而被发现(新北市网络团队案例分享,台湾地区防暴联盟,2013),亦属正常反应,均必须设法查明原因③不报案的情形,尚可能包括被胁迫、恐吓,甚至利诱、哄骗,不一而足,均应查明。复如,亦须查明是否有不报案的家庭动力因素(陈慧女等,2004)。,不宜径行认定指控为虚伪、甚至当作无罪判决的依据(张玮心,2012)。例如,非经诱导却能想起被“记忆检所禁制”(Retrieval Inhibition)所压抑的多年前被性侵害之记忆,先决条件是出现强力的提示线索,如果查明属实,指控通常为真(李明译,2002)。
对家庭内的性侵案件,除了安置辅导被害人外,社工人员应兼协助④社工师的专业远比司法警察更适宜在任意侦查阶段处理这些事情,且可在安置辅导被害人的过程中同时进行;惟因社工师并无侦查权限,仅能定位为任意侦查的辅助角色。侦查员访视家庭氛围及成员互动状况,了解案件揭发过程是否有其它与案件无关的因素或诱导询问、有无可能导致被害者反复指控等,用以辅助证明指控的可靠性。
3. 儿童有无受到不当询问
严格来说,应该查明自性侵案件被揭发迄被害人进行“减述作业”⑤系指对于未满十八岁或智能障碍不能完全陈述的性侵害被害人,为了避免过度询问造成二度伤害或诱导,当警察初步受理后即交由社工评估如需进行减述作业,则会在检察官主导下,对被害者进行询问,询问过程则全程录音或录像。当以本份笔录当证据时,被害者即可不用出庭接受交互诘问,称为减少重复陈述作业,简称减述作业。然而,亦有法官认为性犯罪属重罪,行政规定无权剥夺被告的诘问权,依旧会请被害人在隔离或变声、变装的情况下,出庭接受交互询问。时,儿童到底与那些人接触过?他们如果曾经问过被害人,查明如何提问,是否让被害人处于感到自在的环境或情境,并向其表示被问及之事件可以自由陈述,包括可以回答“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或“我暂时不想回答”等。使用开放式问句还是封闭式问句(吴维雅,2009),如果是封闭式问句,到底用于哪些问题之询问?在何状况下使用⑥例如,针对何种年龄的被害者使用?或在儿童无法回答问题或答非所问、感到害怕或觉得羞耻而无法回答或不敢回答时使用?还是一直都用封闭式问句,苟真如此,供述正确性就有问题。?被害儿童如何回答?等等,都要逐一查明,以确保供述未受暗示或诱导,最后,则要考虑询问人员的专业性与实务经验。
就笔录而言,要回头检视有无诱导者,至少包括最初受理的警询笔录⑦妇幼专责人员以外警察如有询问的情况。、社工人员访谈笔录、医疗诊断之问答纪录、发现儿童遭性侵而向警察检举之人的笔录、其它曾与儿童接触过之人的访谈笔录、甚至“减述作业”的询问过程与笔录、以及所有询问过程的录音录像纪录。必要时,应再向制作笔录、纪录或供述者确认整个问话过程、所用语句或态度,以确定有无暗示、诱导或不当询问者。
(二)查无其它因素造成异常心理与行为反应
被性侵儿童如果出现性虐待症候群或创伤后压力症候群⑧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症状,请参阅美国心理学会的DSM(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DSM-IV-TR)诊断手册(Gaffney, 2012)。实务上,出现的症状有:遭男性成人性侵的十八个月女童不愿陌生人帮其更换纸尿布。玩游戏时,玩具丢到女性前面,幼童会前去拿取,丢到男性前面,则畏惧不敢靠近。换成另一位男性时,女童亦出现相同反应(洪淑姿检察官案例分享,台湾地区防暴联盟,2013);国小三年级女生遭受性侵,慢慢验生出抗拒学习、非行行为与注意力不集中的征候(新北市网络团队案例分享,台湾地区防暴联盟,2013)。,因为创伤已形成永久记忆,即使事件已经远离,负面情绪或行为依旧会反复出现;惟就因果关系而言,起诉前应再确定此创伤是否有可能系与创伤经验无关的压力事件⑨压力事件所造成的情绪反应比较轻微,会随时间与治疗而减轻。持续对创伤事件的过度反应,会造成无法分泌足够的可体松(Gaffney, 2012)。所造成。
因为这已是未搜集到足够物证下的最后侦查,比较不会担心嫌疑人会湮灭证据。基本上,可就儿童的生活、学习与家庭方面,有无出现可能导致其出现类似被性侵的异常心理或行为反应的压力事件,例如,因学业或生活事件遭受严厉斥责、体罚或羞辱等等。
(三)评估供述内容之真实性
不管内容分析效标法(Criteria Based Content Analysis,简称CBCA)(庄忠进等,2012)或陈述效度评估法(曾春侨,2008)。现行评估供述内容真实性的指标,大致可分成两大判准,十大指标。两大判准指的是内在充分性与外在契合性⑩指的是供述是否有效,只能由供述者本身及其内容去探求,可视为建构效度;外在契合性,指供述是否可靠,由外在证据可判断,可视为效标效度。,十大指标分别是:(1)语气坚定性,如指控态度愈坚决,语气愈明确,供述愈可靠;(2)内容具体性,如指控内容愈详细,表达愈有条理,供述愈可靠;(3)态度自然性,如指控时情绪与肢体语言愈切合被害情节,供述愈可靠;(4)整体一致性,如前后内容愈没有矛盾,供述愈可靠;(5)情节合理性,如双方互动过程愈符合经验法则,供述愈可靠;惟因性犯罪者常有异常心理,被害情节的合理性,应从加害者角度看待;(6)对象特殊性,如愈能指出加害者身上的特征、罕见的犯罪手法或言行,供述愈可靠;(7)动机利他性,如愈是咎自己且愿意原谅犯罪嫌疑人,供述愈可靠(高忠义译,2000);(8)偶发意外性,如愈能指出案发时的突发或并发事项,供述愈可靠;(9)案件重复性,如性侵害具有重复性,除非遭受严重的暴力侵犯而无法掩饰者外,儿童如仅指控一次被害,可靠性较低;(10)外在对应性①外在对应性只是外在契合性的一个指标,其它指标亦可抽出外在契合性,例如,被害者供出加害者的身体特征经查符合者,身体特征即属外在契合性的一个因素,余类推。,如愈能找到客观存在的证据、愈能符合客观情境,供述愈可靠。
虽然霍罗威茨(Horowitz)等人证实CBCA的信度(Reliability)为0.84,台湾地区研究却显示:九岁以下儿童之供述,只要核心问题无显著不合事理或矛盾之处,并非不可信(张玮心,2012);内容愈详细愈可能受到诱导(李慧瑜,2004);家庭内性侵案件被害儿童过于激烈的反应或求救,并非正常;突然被性侵,惊慌失措、恐惧害怕,无法记住细节,严重者甚至失忆(庄忠进等,2012);儿童是否能同理或原谅加害人颇值怀疑;儿童对于与他本人或家人有影响或关系的加害者之指控,经常反复不定;儿童关于遭受性侵害之揭发,通常并非及时而具体;儿童关于被害日期与时间的陈述,因为缺乏参考坐标②例如,幼儿园儿童遭性侵当日为其生日或园庆日。小学生遭性侵之日为其考试或毕业旅行之日。,可靠性不高③事实上,即使是一般的性侵案件,仍有为数不少者难以评估案发时间,被害人甚至无法陈述被性侵害的过程,例如,被害人因药物或酒精作用无法确定是否遭性侵、被害人因智能不足或其它因素无法清楚陈述歹徒犯罪过程,或案发时间相隔过久无法正确估算(粘凯俐等,2007)。,年纪愈小愈不可靠,遇害次数愈多愈容易搞混④因此,询问时应注意查证,如无法确定,不宜明确纪录,以免被加害者利用为不在场之证明。。因此,被害儿童供述是否可靠,就现行的内容分析法,判准不是内在充分性,而在外在契合性,凡与此有违且超出合理忍受范围者,宜推定供述为假,例如,所指控的犯罪手法与被指控对象惯用者不符。至于仅能依靠外在契合性而非内在充分性判断之原因,或许在于认知及表达能力不同,而这又与年龄有密切关系。
因此,除非能将儿童再细分为七岁以下与七岁以上、十二岁以下两类,并依据认知发展程度、案件性质、被害反应等等,律定本土性的陈述内容量表或效标,现行内容分析效标法或陈述效度评估法,并不适用于性侵害案件被害儿童供述正确性之判断⑤在日本的司法审判实务上,针对所谓痴汉行为的审判,对于被害者供述的证明力判断,逐渐形成以下基准:具体性与详细性,越具体与详细,就越显示被害的可能性高。自然性,即就一般情况,被害人的供述是否流畅,而无造假的可能。合理性,即供述内容就客观而言,是否合理。主观的感受性,一般而言,对于被猥亵或骚扰者,其被害感受深,自会流露在陈述过程中。主观的确信性,即被害人的主观确信高,代表其被害并非虚构。上述基准,虽是目前实务运作常用者,但非绝对,且因其内容仍属空泛,欲达于所谓超越一般人合理怀疑的有罪证明度,仍需辅以证人指证补强(吴景钦,2010)。然而,这个标准或许适用成年被害人,却难以适用性侵害的被害儿童,其次,儿童性侵害案件又殊少目击证人,日本司法界的补强方式,其实难以适用儿童性侵害案件。。例如,台湾地区法院85年度上诉字第5041号判决主文略以:“被害人于案发时未满12岁,原应不解男女间性事,惟其于警讯时,却能明确指称被告与其发生性关系时之过程与细节,且被害人与被告并无宿愿,而其所指诉之事实又关系其一身之清白,是被害人断无不顾自身名节而胡乱指控之理。”若参考台湾地区法院92年少连上诉字第218号判决理由,本项判决亦可能被推翻。毕竟,发生过程与细节之陈述,如被告不承认、无重复性可参考或无录像照片等佐证,属于内在充分性之判准,审判者如无外在契合度可供判断,不同审级法官要加以推翻,实属轻而易举⑥例如,相反论点可为:被害人于警讯时,虽能明确指称被告与其发生性关系时之过程与细节,但此等指控,不无套用从媒体、网络或电视所看到之色情影片,或受到他人诱导所致,并非全然可信。。其次,未满十二岁是否就不解男女间性事⑦以网络如此发达、A片这般泛滥的年代,国小四、五、六年级学童未必完全不解性事。、有无宿怨皆属于外在契合性之判准,如无相关证据证明或反证推翻,法官何能认定?至于一身清白与名节,不知未满十二岁者如何看待此等空泛而抽象的名词,而审判者又焉知儿童对此之认知与感受?
(四)涉嫌程度查证
1. 类型化判断
类型化是认识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对性犯罪者可就特质、手法、心理状况、触发条件等等进行类化侦查。例如,格罗斯(Groth)等人就性行为的特异性与心理需求,将性犯罪者分成迷恋型(fixated)与退化型(regressed)两类。迷恋型①典型者如恋童症者。的特性是持续且强迫性地喜欢儿童,犯罪系出于预谋而非环境压力。犯罪者会藉由利诱、照护②例如,藉提供义务课后辅导的机会,反向性侵儿童。、教育、辅导、信仰等等与被害者建立联系关系。退化型则常见于成年后因失业、婚姻破裂、滥用药物等。
外在压力或挫折而引发,犯罪者常有寂寞、孤单、焦虑、低自尊与低自信等负面情绪或认知,他们倾向于侵害易于接近的对象。
如果格罗斯(Groth)分类适用台湾地区,就侦查角度而言,似可作以下的侧写:受理儿童疑似遭受性侵案件时,如发现被指控对象于案发前,确实遭遇重大挫折或压力事件,且过去并无性侵前科,则被害指控并非无据。这种退化型的犯罪者,因为低自信与低自尊、不具良好的社交能力,通常是在封闭的生活圈内性侵易于接近之儿童,虽然受害人数相当有限,但会重复侵害特定对象③例如,自己子女。;如果查无重大挫折或压力事件,但被指控者有良好的机会或能力可接近被害者,推定属于迷恋型者,所为性侵害绝非仅止于本件,犯罪时间亦非肇始于本件而已,因其具有良好的掩护,例如,隐身于教会、托儿所、幼儿园或假冒善心人士,受害者通常远多于退化型。单一受害者仍会重复被害。这类犯罪者对于如何接近与诱导被害人、甚至选定犯罪目标,通常有一定的步骤④例如,伪装大善人,设法取得儿童信任、甚至家长信任。、方式⑤例如,以糖果或礼品引诱,以教导功课接近。告诫、甚至威胁不得将两人关系告诉他人。与标准⑥例如,选定缺乏父爱或特定身材长相的被害儿童。2012年5月间,台北市发生某国中十七位男同学遭受性侵案件,被害者大多出身经济条件较差之家庭(台湾地区防暴联盟,2013)(郑雅方译,2009)⑦2012年5月间,台北市发生某国中十七位男同学遭受性侵案件,这位狼师系以体育社团教练身份在校兼课,也曾在小区的另一所小学兼课,为小区颇具知名的热心人士,并自称为牧师,许多受害学生自国小即认识这位狼师。他系以带学生郊游烤肉、给零用钱等方式拢络被害人,并以照顾与管教之名,帮学生按摩与检查身体为由,借机对学生手淫、口交或肛交,部分学生受害时间甚至长达三到四年。这是典型的娈童症犯罪样态。受害者家境普遍不佳,虽大多数表示受到伤害,却有位被害者因受到狼师颇多照顾,而不愿意对其指控(台湾地区防暴联盟,2013)。。
至于在公开场所向陌生儿童暴力性侵害者,就侦查角度而言,区分性犯罪者类型帮助不大。
2. 犯罪手法调查
儿童性侵案件因其特性与犯罪者特质,经常会重复发生。因此,除了伤害严重致无法掩饰者外,即使是单纯的退化型性侵案件,亦殊少仅有一、两次即被发现者。是故,当被害期间长达数个月、甚至数年,儿童却仅供认几次被害,非有相当理由,可靠性就值得怀疑。其次,性犯罪者常为累犯,犯罪手法会因经验累积而趋于固定,甚至出现罕见的签名⑧例如,出现某些与完成犯罪无关却与满足犯罪者心理需求有关的举动或仪式行为。特征,非遇重大挫折不会改变(庄忠进等,2012)。因此,嫌疑人如有犯罪前科,则指控有其依据;如有相同犯罪手法,则指控可能为真;如有签名特征,推定指控为真。如果同时有多人受害且手法雷同,则指控应该为真⑨例如,父亲性侵国小六年级女儿及其两位同学,引自2012年12月21日苹果日报。。因此,对于指控是否为真,除了清查嫌疑人前科素行外,亦要就其生活圈或工作场域所接触的儿童或少年,今昔有无因故而不敢⑩如受到胁迫而不敢举发。、不能 、不想 举发或提告之被害人,此种被害者愈多,被指控对象涉案程度愈高。再者,因为犯罪手法趋于固定,因此,当儿童指陈的被害情节与嫌疑人惯用手法显然不同时,供述可靠性就要怀疑。
3. 犯罪机会调查
当有能力与动机的人,在无监督者在场时遇到被害人,犯罪就极可能发生。性是人的基本驱力,当犯罪行为尚未显露时,除有前科者外,实难从外表看出谁是狼人。实务上,性侵儿童之人,固有酗酒、失业、感情或事业挫折者,亦不乏一定社会经济地位之人(庄忠进,2012),因此,侦办时并不需特别考虑动机问题,更不应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认为某种特定身份或职业者不会性侵儿童。再则,除需以特殊工具凌辱、掌控、玩弄被11如智能障碍而不知举发。
12如得到好处而不想举发或和解而不想提告者。害者的宰制型犯罪者外,任何后青春期之人都有性侵他人之可能性。因此,儿童性侵害案件是否可能发生,决定于两种状况,一是被指控者在两人非日常活动的处所与被害儿童在一起,此种情况大致已脱离监控,推定指控可能成立;二是两人在日常活动的处所出现,此时必须监控者恰巧不在场,犯罪才有发生之可能①十八个月女童因母亲无力抚养而将其委托男性友人照顾,某日因陷于昏迷而送医院急诊,小儿科医师发现女童全身多处瘀伤、脸部有对称性捏伤。经超音波检查发现,腹部瘀伤对称之腹部内的小肠已经断裂发炎,造成严重之腹膜炎。住院治疗期间,医护人员发现其阴部开口明显,经会同妇产科医师诊疗确定处女模五点与七点钟方向有裂痕,判定受到性侵害。本案仅有验伤证明,并无被害者供述;然因查明仅照顾者有机会接近女童,且照顾者接受询问时,辩解之词与女童身上伤痕形成样态不符,检察官认系狡辩卸责而提起公诉,后经判决9年6月有期徒刑定谳(洪淑姿检察官经验分享,台湾地区防暴联盟,2013)。。
因此,从侦查观点而言,就要去查明加害者与被害者有无可能因时空交会而在一起②如果缺乏时空接近性,亦即出现所谓的不在场证明,除非间接正犯,应无犯罪可能。,前述第二种状况同时要调查交会时有无监控者在场。侦查的要领,主要是以时间为轴,依序查明其行踪与活动,再比对两人有无可能在被指控的时间点交会。因为儿童对于日期与时间的记忆可能发生错误,交会时地容许一定范围的出入。当有交会而无正当性,指控就非无据,如再加上监控者不在场,指控就可能为真。
追查个人在时间轴上的行踪,可供依据者愈来愈多,诸如:手机通讯、手机定位、行车纪录、消费纪录、交通纪录、监控录像、医疗纪录、上网纪录、询问人证、双方交往或互动纪录等,可谓不胜枚举,且会随数字科技之发达,可追查者将愈来愈多,侦查人员必须与时俱进,懂得运用。
4. 诬陷可能性调查
台湾地区法制系以追诉犯罪为原则,检警机关侦查犯罪必须详为调查嫌疑人有利与不利之证据。当儿童性侵害案件查无具体证据证明涉有犯罪时,就有必要反向查证有无不正动机而胡乱指控或为诬告者。不正动机可能直接起因于被害者本身,亦有可能出于以儿童被害为工具,达到特定目的影武者③唆使儿童指控父亲性侵而达到离婚、取得赡养费之目的。,皆必须设法查明。
研究显示:儿童或少年④此处不单指儿童而已,还包括少年。境外这种资料是否适用台湾地区,有待验证。未受诱导或教唆而说谎者,其情形有:(1)报复被指控对象的处罚;(2)模仿最近看过的影集、电视剧或影片;(3)虚拟真实指控,幻想自己是被指控对象喜爱之人;(4)患有精神疾病⑤曾有胡乱指控的纪录(张玮心,2012)。;(5)兄弟争宠或与继父母子女争宠而虚拟被害,以引起父母的关爱;(6)为逃避课业或生活压力而指控压力来源者(张玮心,2012)。台湾地区亦曾有六年级学童因听闻曾被乱伦的同学表示安置中心生活舒适,想要逃离恶劣的居家环境而诬指父亲乱伦者⑥2012年12月19日妇女新知总干事姚淑文小姐亲口告知的工作经验。。
侦办儿童被性侵案件,系以宁可信其有的态度进行。因此,就时机而言,非有具体的反证或情报,侦查初期不会先就有无虚伪指控询问被害人或检举人,以免引起反感;同理,通常也是查无可疑时,才会反向就有无被诬告询问被指控者,以免过早询问有无被诬告而促使被指控者知所收敛、伪装或灭证(郑雅方,2009)。就技巧而言,查明有无诬告,大多旁敲侧击,迂回探问,非不得已,不会开门见山询问。
(五)提前请专家证人协助
当儿童性侵案件缺乏具体物证时,法官通常选任临床心理师或精神医师以专家证人的身份,辅助判断儿童供述真假及是否出现压力事件症候或创伤后压力症候,以为定罪科刑的参考。有些研究认为:只要儿童未受到暗示或误导,可以透过严谨的诊断判断是否受到性侵害⑦判定发生性侵害并不等于认定谁是犯罪者。。
就逻辑而言,法官必然认为他们远比其它人更具有解读儿童供述意义与异常身心的专业。既然非君莫属,唯汝是赖,则争论他们的专业性,目前并无意义⑧因为也找不到其它合适的专家证人。何况,除了同行外,甚至也无人可以判断他们的专业性。。在此所要探讨者,乃审判时始借重专家证人,万一各审级的专家证人一致认为儿童为虚伪指控,致使法官为无罪之判决,则要如何回复被告名誉与身心所受的折腾?退求其次,如果专家证人衡鉴结果相异,又将陷法官于两难抉择的困境。因此,何不提前于侦查阶段就引进专家证人协助判断,一则作为发动搜索监听等强制处分的依据;二则当作提起公诉之凭借。其实,警察机关办理性侵害案件处理原则第三点早已规定:对于心智障碍或其它陈述有困难之被害人,应给予充分陈述之机会,详细调查,必要时得洽请台湾地区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相关专业人员协助。就本文观点,此所谓的专业人员宜为临床心理师或精神科医生而非社工师。陈述显有困难之人,除身心障碍者外,指约为九岁①这个界限仅是原则或学理探讨,仍应依个案状况决定。亦有论者认为应为七岁以下。以下被害人(陈慧女等,2004)。
实务上,2010年9月起,高雄市妇幼安全团队开始试办“早期鉴定”,当妇幼队警察简要受理儿童性侵案件后,即由社工评估如需“早期鉴定”,则报告检察官委托相关领域的精神科医师进行,目的有四:(1)协助检警制作幼童或心智缺陷之性侵害被害人笔录;(2)鉴定被害人在遭受性侵害后的立即创伤;(3)鉴定被害人智力状况及表达能力、年龄与证词的可信度;(4)协助被害人复原。
经过几近三年的试验,因为个案数量不足,尚无法有意义评估是否有助于显著提升起诉定罪率。衍生的问题则有:(1)不易找到有意愿有热诚的精神科专业医师,特别是以委托鉴定的方式实施,依法须以专家证人身份出庭接受反对询问,更令精神科医师望而却步;(2)当精神科医师以专家证人身份出庭时,除了面临诉讼攻防外,对照亦可申请委托其它精神科医师进行鉴衡,而当精神科医师鉴定结果两歧时,法官又将陷入两难。有鉴于此,亦有认为精神科医师可以“协助办案”而非“专家证人”身份,于检察官询问被害儿童时,在旁观察并解释儿童身体讯号的意义,给予检察官必要的协助,甚至对儿童进行认知与创伤衡鉴,评估受到性侵害的可能性,让检察官据以发动强制处分或向法院申请搜索票或监听票,藉以取得实体证据②本文认同这个论点。(台湾警察专科学校,2013)。
(六)测谎的必要
台湾地区法院对测谎结果的采用,早期较持肯定的态度,代表性判决为台湾地区法院92台上2282号判决略以:“测谎机关的鉴定报告,形式上若符合测谎基本程序要件,包括:(1)经受测人同意配合,并已告知得拒绝受测;(2)测谎员须经良好之专业训练与相当之经验;(3)测谎仪质量良好且运作正常;(4)受测人身心及意识状态正常;(5)测谎环境良好,即具有证据能力,如其符合待证事实需求者,始有证明。”近几年则出现相反观点,代表性的94台上1725号判决略以:“测谎结果不具科学的再现性,生理反应之变化与有无说谎间,尚不能认为有绝对的因果关系,是测谎技术或可当作侦查之手段,尚无法作为认定有无犯罪事实的基础。”台湾地区关于测谎用于法院审判之研究发现:“性侵害案件”测谎结果被法院采信比例为73.1%。测谎系确立无辜者清白之良好验证工具(罗时强、黄富源、廖训诚、曾春侨,2005;蔡俊章、罗时强、曾春侨、2009)。是则,透过对嫌疑人的测谎及测后晤谈,辅助是否对缺乏明确物证的性侵害案件起诉,似乎亦值得考虑。此外,既然类似罗夏克墨渍心理测验③台湾地区士林地方法院91年度少年诉字第23号判决,系依据心理谘商师透过分析少女所画的自画像、家庭图、房子、树、人、玫瑰花丛等绘画内容,分析少女确实遭性侵害。可用于审判之参考,则美国实务上常用投射与解离的心理防卫机转来判断是否涉案④观点为:行为语言往往出于潜意识或下意识,是可以被解读的。供述分析包含很多语言与结构的要素,兹以使用名词、动词与形容词来分析。被控弑子的父亲抗辩说:my story is never change。story意旨创造出的故事,因此,my story is never change完全不同于 I told what happened,前者意涵虚伪的陈述。说谎者必须不能前后矛盾,所以不会使用直接或明确的字词。其次,是被告用child这个字,而非被其杀害的女儿名字,用这个没有温暖、没有关怀的名词,表示一种疏离。第三是,用hurt 表示没有殴打三岁女儿致死,表示在降低事件的严重性。将个人行为从事件中抽离。因此,就有可疑而必须更深入讯问。本案有重复的瘀伤可证明。最后,用that这个表示有空间距离的形容词,也是想从事件中抽离出来。总言之,这句话表示父女不亲,父亲会持续忽略与虐待女儿(Adams, 2004)。的嫌疑人供述内容分析法,或亦可作为参考。
(七)因果关系的担保
嫌疑人是否犯罪,通常系现场、加害者与被害者三者间,透过物证建立连结关系(庄忠进等,2012)。当儿童性侵案件缺乏可供连结的物证,而仅能依据被害人的供述及其异常的身心与行为进行起诉审判时,即使供述内容为真、异常行为或身心反应确为遭受性侵所致,依旧难以连结嫌疑人。换言之,到底是谁对其性侵,终究只能依赖儿童的指证,这与非被害人身份的目击证人之指认,并无本质上之不同(庄忠进等,2012)。因此,当无证据可供连结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时,有无必要进行列队指认,乃有考虑之必要。台湾地区92年少连诉字第8号判决有罪的一种理由,是认为儿童乍见被告时产生畏缩反应⑤美国审判实务认为:儿童对于提及嫌犯或嫌犯靠近时,出于本能反应地产生畏惧逃避的退缩行为,供述推定为真。如果自然的亲近或接近,甚至于快地靠近,供述为假(张玮心,2012)。如果这个论点成立,当儿童确定遭受性侵害却未指明特定的嫌疑人时,则日常生活中接触之人如有使其退避三舍者,即可认定为犯罪者。苟真如此,当儿童被性侵时,曾经与其有不愉快经验之人,特别是其日常生活可能接触者,将极有可能随时沦为犯罪者。;然而,社交逃避或畏缩既然是创伤后压力的一种症候,被害者遇见类似身材长相者、甚至长相可怖可惧或不信任之人,即有可能产生相同之反应,若以此认为这些人即是加害者,是一种逻辑的谬误。因此,单以儿童对某人有退缩反应①疑似遭受性侵害的18个月大幼童玩游戏时,当玩具丢到女性前面,幼童会前去拿取,丢到男性前面,则畏惧不敢靠近。换成另一位男性时,女童亦出现相同反应(洪淑姿检察官案例分享,台湾地区防暴联盟,2013)。或仅实施之单一指认,就认定具有因果关系,似有斟酌余地。
四、结论
儿童性侵害案件因其特殊性质,固难以在被害人身上采到完整或具体之证据,惟如检警人员善尽调查、查证、搜证②特别是利用科技搜证。、采证、举证与论证之能事,仍有可能将犯罪者绳之以法;侦办儿童性侵害案件如万不得已仅能依被害者供述及其异常心理与行为作为起诉依据时,鉴于台湾地区迄无判断儿童供述正确性之量表或指标,创伤后压力或性虐待适应症候群只是一种行为或心理表征而非病因,其与遭受性侵害未必有因果关系,刑事司法人员又普遍对儿童认知与被害心理与反应缺乏认识,无法对供述能力有限的儿童进行有效的询问。因此,提起公诉前,仍宜再对儿童供述是否受到污染与诱导、儿童指控是否出于不正动机,进行查证与确认,并借儿童心理专家衡鉴被害儿童供述之可靠性、及其异常心理或行为反应与遭到性侵害两者间的因果关系,以求周延,必要时,给予嫌疑人有接受测谎证明无辜的机会或列队接受被害者指认的余地,期达勿枉勿纵。
为求提升侦办儿童性侵案件的能力,侦查人员宜精进有关儿童认知与心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取得询问儿童的专业认证。检警机关应建构本土性的性侵害被害儿童标准化的询问作业及供述效度评估量表③美国法院检验儿童证言可信度之方法有:(1)先假设儿童供认遭受性侵害之证述为真;(2)儿童描述被告性侵害的样态(犯罪手法等核心内容)是否前后一致;(3)儿童陈述内容有无出现超现实情节;(4)就儿童与被告之关系,确定儿童有无说谎之动机;(5)警察或社工有无诱导询问被害人;(6)案件系儿童主动向师长、父母、朋友或医师供认,还是被动地为其中之人所发现(张玮心,2012)。第1点可当侦查参考,似不宜作为审判依据。其它各点,似均可当作编制检测表或量表的项目或指针。,并针对不同类别之性侵案件,归纳出犯罪者类型、犯罪者特质、犯罪手法、相对伤痕、对应证据、被害者类型、被害者年龄、被害情境、可疑征候、被害后之异常行为与心理反应等等,彼此之间的对应、甚至因果关系,至少应制定检核表,以利受理与侦查。其中,因为儿童开始就学后,认知表达能力会大幅提升。关于儿童被性侵案件,似宜将儿童再细分为幼儿园阶段与小学阶段两类,以符侦审需要。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Concerning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ild Sexual Assaults
Zhuang Zhongjin
(Taiwan Police College, Taibei, Taiwan)
Because of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 sexual assaults, it is difficult to collect intact or specific evidences from the victims. But if the prosecutors or police do well in investigation, checking, searching for, collecting, giving evidences and testification, the criminals will be brought to justice. In order to improve abilities to investigate the child sexual assaults, the investigators should learn knowledge about the children and their psychology and get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s regarding child enquiry. Procuratorates and police agencies should set up local standardized enquiry procedures and offer assessment forms so as to target different types of sexual assaults to determine the criminal type, features, modus operandi, injuries or scratches, related evidences, victim type, age, details, suspicious signs, abnormal behaviors,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and so on, whether they are matched or not, their cause and effect, examination forms, which will facilitate the case disposal and investigation. Furthermore, after the children begin schooling, their cognitive and expressive capabilities will be greatly improved. When it comes to child sexual assaults, it is better to further categorize kids into kids at kindergartens and at elementary schools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investigation.
Child; Sexual Assault; Molestation; Investigation
D631.4
A
1008-5750(2013)04-0050-(08)
10.3969/j.issn. 1008-5750.2013.04.010
2013-07-02 责任编辑:何银松
庄忠进,男,台湾警察专科学校刑事科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