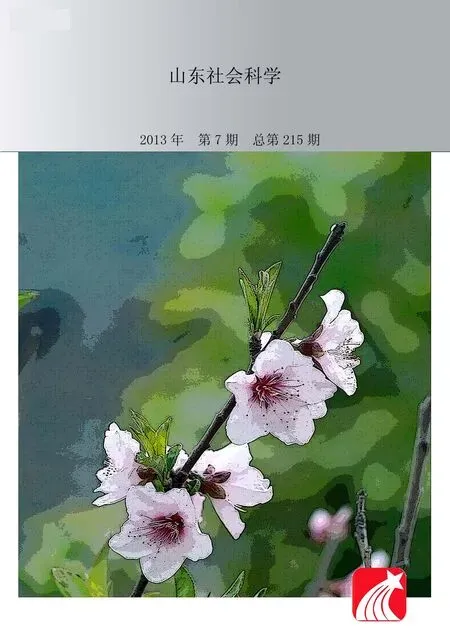“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与“从后思索”
2013-04-07何中华
何中华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0条中写道:“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在这里,马克思从“立脚点”的意义上比较了新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差别,所以这段话可谓是理解实践唯物主义的一个要枢。恰当地解读这一论述,对于深刻领会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意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怎么理解马克思所谓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才恰当?
“人类社会”的原文是“die menschliche Gesellshaft”,翻译成“人类社会”,似乎未能特别地标示出它的特定历史内涵,因为从汉语语境看,人自从脱离动物界开始,就进入了“人类社会”。而马克思在这里的意思,却不是一般地刻画这个意义上的“人类社会”,而是特指人性化了的社会。所以,朱光潜先生主张将它译作“人性的社会”[注]朱光潜:《美学拾穗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另据纪玉祥先生考证,“在《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引者注)中,menschlich有两种基本含义,其一表示领属关系,可译作‘人的’或‘属人的’,其二在特定意义上使用的,menschlich即指gesellschaftlich(社会的),在这种情况下则应译作‘人性的’或‘人道的’”[注]纪玉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部分译文商榷》,《历史唯物主义研究》1987年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页。。现有的译法(即译作“人类社会”),实际上不过是在第一种意义上翻译的,而按照马克思的特定语境,“menschliche”其实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的,所以将“die menschliche Gesellshaft”译作“人性化的社会”似乎更为贴切和准确。
而马克思所谓的“社会的人类”,其德文是“die gesellschaftlich Menschheit”。恩格斯在把《提纲》作为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附录发表时,将它修改为“die vergesellschaftete Menschheit”。问题在于,恩格斯的修改同马克思的原有表述是否在语义上相当?纪玉祥先生认为两者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并指出:“恩格斯把原稿中的‘社会的人类’改为‘社会化了的人类’,表面看来似无区别,实际上其意义是不同的。vergesellschaftete是由动词vergesellschaften变化而来的,它有‘社会化’、‘国有化’、‘成为共同所有’等含义,显然是同生产资料公有制问题相联系的。”而“‘社会的人类’和‘社会化了的人类’是不同的,前者虽然同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有联系,但主要是同马克思的早期异化学说相联系,后者则同《共产党宣言》以后著作中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问题相联系;前者强调的重点是消除异化,后者强调的重点是消灭私有制”。据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恩格斯的修改反映的是他同马克思自《宣言》以后的观点。”[注]纪玉祥:《关于恩格斯对〈费尔巴哈论纲〉的修改》,《哲学研究》1982年第10期,第36页。也就是说,恩格斯的这个修改不过是依据马克思后来更成熟的思想作出的。其实,马克思在《提纲》之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提出了“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的基本观点。这里所谓“积极的扬弃”,是同马克思所批评的那种“粗陋的共产主义”试图“抽象否定”而非历史地否定“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相对而言的,因为这种抽象否定不过是在前私有财产水平上进行的,所以马克思说“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9-80页。。这种“扬弃”只能是消极的扬弃,而不可能是通过历史本身的成熟而实现的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正是在《手稿》中,马克思把“私有财产”同“异化”内在地联系起来,他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这里的‘私有财产’,其德文词是‘Privateigentums’——引者注)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所以,我们不能说马克思在《手稿》中谈论人的异化时,没有从本质的意义上涉及私有制及其超越问题。而晚于《提纲》的《共产党宣言》提出的“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hums”(消灭私有制),亦可译作“扬弃私有财产”。显然,它同《手稿》说的“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是完全一致的,唯一的差别仅仅在于,《手稿》所谓的“扬弃”更多地还是一个相对抽象的命题,随着马克思研究的日益深入,它到了《宣言》那里已经获得了更为具体的内涵。所以,应该说,恩格斯的这个修改能够更清晰地传达出马克思的原意,即指理想的社会中的人。这可以在《资本论》第3卷描述马克思心目中理想社会即“自由王国”时所刻画的“人”的性质及其历史内涵那里得到某种佐证。马克思说:“社会化了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页。所谓“社会化了的人”,其原文为“vergesellschaftete Mensch”,这个措词恰恰同恩格斯的修改相一致。基于以上考察,有理由认为“社会的人类”就意味着“合乎人性的人”[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此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社会的人类”中的“社会”的涵义。马克思在《手稿》中写道:“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这样就意味着它是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的真正实现和完成。人的自然化是指异化的扬弃,因为异化是人的非自然化,本己才是自然的,而异化是他然的,即由异己的他者外在地规定的状态。人的自然化无非就是人的自然而然。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谓的“社会”,只能是共产主义。[注]有学者早就指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社会’”,“同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并不是一回事”,它“实际上是指马克思当时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纪玉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部分译文商榷》,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1987年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页)。应该说,这个诠解是准确的。因为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显然,这样的“社会”只能是作为未来目标而存在的理想规定。
“市民社会”同“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作为新旧唯物主义各自的“立脚点”,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是空间范围的不同,而只是时间维度上的不同。“市民社会”是现在进行时的,而“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则是将来时的。“市民社会”是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存在着的事实,而“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则是应当存在而事实上尚未来临的一种应然的规定。马克思的“自由王国”就是将来时的,不把“资本主义”置于此种参照系中,就无从理解它的本质。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通过《提纲》第6条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得到更深切的体认。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此所谓“现实性”(Wirklichkeit),并非指现存之物所具有的性质,而是一种应然的规定。因此,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在新唯物主义立脚点的意义上被揭示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现实性”,其德文词也是“Wirklichkeit”。马克思分明是说,在宗教异化的关系中,人的本质是没有“现实性”的。它获得现实性的条件,只能是人的本质与实存的统一,亦即人的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而对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维度而言,这当然只是未来的可能性而已。因此,马克思所谓的“现实性”应该在黑格尔意义上被领会。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指出:“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注][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页。请注意,此所谓“现实的”,黑格尔用的德文词是“wirklich”。他进一步阐释道:“除了理念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现实的。所以最关紧要的是,在有时间性的瞬即消逝的假象中,去认识内在的实体和现在事物中的永久东西。其实,由于理性的东西(与理念同义)在它的现实中同时达到外部实存,所以它显现出无限丰富的形式、现象和形态。”[注][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页。诚然,黑格尔拒绝了彼岸性,认为“哲学是探究理性东西的,正因为如此,它是了解现在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的,而不是提供某种彼岸的东西,神才知道彼岸的东西在哪里,或者也可以说(其实我们都能说出),这种彼岸的东西就是在片面的空虚的推论那种错误里面”[注][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页;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序言》里,也有类似的说法。。但马克思所提示的那个作为“彼岸”之规定的“自由王国”,不同于黑格尔这里所说的“彼岸的东西”。因为前者并非宗教意义上的“天国”。在马克思看来,“天国”只是“幻想的现实性”,而不是“真正现实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资本论》所揭示的“自由王国”,才是人们“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
在《提纲》第6条中,马克思批评了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这种“抽象物”是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具体规定相对而言的。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而作为“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人的本质”只有成为历史的结果才是可能的。人只有在自身的全面发展中,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本质因为异化而丧失了的全部丰富性。这样的“人”,才是《手稿》中所谓的那种“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原始的丰富性只有经过历史本身的抽象所造成的贫乏之后,才能实现历史地复归。这正是“人的本质”获得“现实性”的过程。费尔巴哈之所以把“人的本质”了解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是由其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所决定的。因为立足于“市民社会”,费尔巴哈“没有对[人的]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从而造成了对人的抽象化理解。在《提纲》第7条中,马克思揭露道,“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亦即属于作为“旧唯物主义”立脚点的“市民社会”。与此完全不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则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所以才能把“人的本质”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旧唯物主义同市民社会的关联性,昭示了唯物主义的世俗基础和意识形态性质。它导致的一系列理论后果是:(1)感性直观性,如费尔巴哈的经验视野及其静观的立场;(2)人的自然性,如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对肉体感受性的推崇;(3)人的抽象性,如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揭示仅仅注重人的自然本性;(4)非批判性,即满足于“解释世界”而非“改变世界”,局限于对事物的“正确理解”。不过,也应该指出,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观在其适用的范围内无疑是恰当的和有效的,但一经超出这个范围,其局限性就暴露无遗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同费尔巴哈在人的本质问题上所秉持的不同观点,不是一个对错和是非的问题,而是一个对人在不同历史维度上的性质作出刻画的差异问题。
二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之所以必须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说到底乃是由马克思所特有的“从后思索”的运思方式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写道:“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页。其实,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已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这不过是“从后思索”的一种象征或隐喻的说法罢了。马克思说:“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他还提出:“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如果说“地租”是“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的标志,那么“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标志着“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其实,“从后思索”乃是贯穿于马克思早年和晚年思想的基本方法。青年马克思在实际的运思过程中就已经贯彻着这种方法了,只是没有如此明确地将其刻画出来罢了。例如他指出:“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却不是民主制的真理。……从君主制本身不能了解君主制,但是从民主制本身可以了解民主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页。晚年的马克思在给俄国学者丹尼尔逊的信(1878年4月10日)中写道:“现在我首先应当告诉您(这完全是机密),据我从德国得到消息说,只要那里现行的制度仍然像现在这样严格,我的第二卷(指《资本论》——引者注)就不可能出版。”因为“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第二卷。这一次的现象是十分特殊的,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因此,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5-346页。显然,马克思是否出版《资本论》第2卷,并不完全取决于写作完成与否,更根本的则取决于历史本身的成熟。与此相对照的是,空想社会主义何以会陷入“空想”?从客观方面说,就是由于历史的不成熟,或者说历史没有给它提供“从后思索”的条件和机会。在此意义上,我们不能把它的空想的性质归咎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的主观错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4页。。马克思的历史叙事为什么要从资本主义经济入手,并且从资本主义最发达、最成熟的英国开始呢?表面上看这是出于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的需要,实则有其更深刻的方法论原因,即它是“从后思索”的要求。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而现代社会就是那种“已经发育的身体”。
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实践唯物主义坚持“从后思索”的运思方式,这在马克思的思想建构中有着诸多的体现。第一,马克思在其哲学的语境中,始终致力于人的个体与类的矛盾的彻底解决,而不是停留在知性对立的意义上去拯救个人或者是类。那种对于马克思思想中缺乏个人地位的指责,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种指责本身就折射出指责者囿于资产阶级狭隘想象的局限性。而人的个体与类的矛盾的最后解决,是将来时的。第二,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或者像恩格斯说的,“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4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自己的学说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然而,资产阶级学者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他们贫乏的想象力实在无法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有限范围。因为他们无从想象,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普遍的懒惰问题赖以产生的前提已不复存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及其动力从而不再依赖于利益的刺激和诱惑。因此,私有制的消灭与普遍的懒惰根本无关。显然,只有立足于共产主义,才能突破资产阶级的狭隘想象力的束缚。第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关消灭“资产阶级权利”和“平等”本身被历史地超越的思想,同样显示出其中贯彻的“从后思索”方法的致思取向,因为马克思是以共产主义为参照系来看待平等诉求及其历史暂时性的。[注]参见何中华:《“平等”问题的历史规定及其超越——重读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从后思索”中所谓的“后”,究竟是实然意义上的“后”,还是应然意义上的“后”?答案是,二者兼而有之。就过去时而言,“从后思索”不过是“密纳发的猫头鹰”;就将来时而言,“从后思索”则又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高鸣”的“高卢雄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密纳发的猫头鹰”象征的是实然意义上的“后”,而“高鸣”的“高卢雄鸡”象征的则是应然意义上的“后”。在直接的意义上,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方法固然是由哲学本身的反思性质决定的,是这种反思性质的要求和体现。但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它归根到底又取决于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及其特点。由人的这种独特的存在方式引申出来的研究方法,究竟是实证的、经验的(归纳),还是思辨的、先验的(反思)呢?只有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过去”能够充分地规定“未来”,从而由“过去”就可以推知“未来”,经验归纳才能成立并有效;但这个假设完全无视并剥夺了人的存在的历史生成性质。人的存在不是预成的,而是生成的。这种生成性使人的存在内在地具有开放性,它表征为向未来敞开着的可能性。正因此,人才成为宇宙中唯一能够“犯错误”的存在物。在这里,“犯错误”应该在积极的意义上被领会,因为“犯错误”是人的一种“能力”,它表明人具有借助于自己的感性活动超越自然界赋予其限制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使人事先无法充分地预期自己的活动结果及其效应。这恰恰是人之所以“犯错误”的存在论原因。而马克思所秉持的那种“从事后开始思索”的方式,就是由人的存在的这种非预成性决定的。人的历史本身是人以其实际地存在现实地生成着的过程,由此决定了只有通过已然的和将然的“结果”,才能以反思的方式重建并再现人的存在本身的生成史。
问题在于,这种“从后思索”所采取的反思姿态,同马克思所一贯主张的从现实的历史和历史的现实出发是否不相侔?在马克思语境中“反思”的条件是什么?任何可能的反思都只能从先行有效的思辨的前设出发,但马克思却把这种前设理解为历史的完成状态(不过是通过反思先验地把握到了的而已)。然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却批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对人性的揭示存在的错误,揭露了“人”在观念层面上被抽象化的原因,指出:“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普通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以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问题在于,这些意识形态家们不正是“从后思索”的吗?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在马克思看来却是不可接受的呢?这种做法同马克思的致思取向的本质差别究竟何在呢?马克思认为,他们的做法是一种“本末倒置”,因为如此这般,历史的结果就被当成了历史的先验尺度,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意识形态的颠倒。它的致命的局限在于:一是把形式上的先验性误认为是真实的先验性,二是它的人性论前设并未建立在对人性的历史生成的“研究”基础之上。与此不同,马克思的叙述方法是以研究方法为绝对前提的。马克思的参照系固然具有历史的超越性,但它本身却要以历史为基础才能成立并得以展现。这虽然看似吊诡,但却正是历史的辩证法。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通过回顾经济学演进的历史,揭示了经济学的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即由具体到抽象和由抽象到具体。后来,在1873年写的《资本论》第1卷“第2 版跋”中,他对此又作了进一步论述,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24页。观念地再现材料的生命,仅仅是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罢了。但是,这种“先验的结构”决不同于黑格尔意义上的先验性,它只是“好像是”,并不是思辨哲学的那种真正的先验的规定,并不像黑格尔那样“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9页。。因为马克思的这种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黑格尔却错误地把这种精神上的“再现”当成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了。“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是时间在先的,而“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才是逻辑在先的,因此看上去才“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恩格斯说过:“历史有它自己的步伐,不管它的进程归根到底是多么辩证的,辩证法往往还是要等待历史很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50页。即使作为反思形式的辩证法本质地掌握了历史进程的逻辑,那么这种应然意义上的“从后思索”的结果,也不得不“等待”历史的来临。显然,这种“等待”,既意味着“辩证法”对历史本身的反思性的把握带有某种先验的意味,同时又意味着“辩证法”归根到底从属于历史而不是相反。这正是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同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的本质区别所在。
可见,马克思在《提纲》中得出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应该在“从后思索”的意义上被理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费尔巴哈对“人”的把握不能“从后思索”,只能从现存的状态出发来加以思考并得出非批判的结论,马克思却能够超越费尔巴哈的局限而做到“从后思索”进而得出革命的和批判的结论呢?这种本质的差别究竟取决于什么呢?我们只有从哲学原初基础的分野中,才能得到恰当的解释。由于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费尔巴哈不得不从感性直观出发,他所看到并揭示的不过是抽象的人和静态的现存事物本身。从费尔巴哈这个个案身上,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的那个论断:“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每个人其实原本都已先行地处在历史中了,但因为意识形态的遮蔽和欺骗,人们不仅在主观上疏离了历史,在客观上也远离了历史。这种疏远,并不是说人们可以超出历史之外,而是说他仅仅以非批判的方式介入历史,不再采取一种自为的和自觉的姿态创造历史,从而沦为历史的旁观者。费尔巴哈就是一个例子。马克思在哲学原初基础意义上确立了感性活动的优先地位,从而能够解构意识形态的陷阱,回到历史本身的本真处。这种对真正历史性的发现,注定了马克思对“从后思索”方法的选择,并由此决定了他的历史叙事不是直观的,而是内在地蕴含着一个反思的层面。作为原初范畴的“实践”之奠基,赋予马克思哲学以“历史地思”这一具有历史纵深感的运思方式。马克思所建构的“人的存在的现象学”,通过历史性在哲学语境中的真正复活,同“从后思索”方法之间发生了内在的勾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