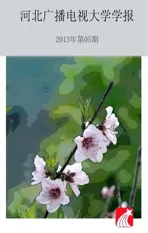试论《左传》的天人思想
2013-04-07赵君
赵君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河北 石家庄 050071)
试论《左传》的天人思想
赵君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河北 石家庄 050071)
春秋时期的天人关系出现了极大的转变,完成了由天命中心论向人本主义的过渡。《左传》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思想转变,体现了春秋时代在敬奉天道的基础上,以“德”为基础,将“敬天重人”和“保民重民”结合在一起,高扬人道的价值,理性地构筑天人关系,并且对后世影响深远。
春秋;《左传》;天人思想;人本思想
天人关系在春秋时期面临着观念上的突破,并成为神事向人事转化的价值依据。本文以《左传》为史料,考证由天命中心论向人本主义的过渡。《左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较为完整的编年体史书,以史实解《春秋》,为述者之冠冕。其内容丰富、取材广博,是春秋时期典籍之最。《左传》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起,依次经过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十二公,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比《春秋》多记了13年,共记录了255年的历史。“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刘知几《史通》),它客观地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非常时期的社会面貌,是对纷乱的春秋时代的记录,它以生动的笔触描绘春秋诸侯的金戈铁马、雄心壮志,也反映了那个大时代的社会文化;从观点上看,《左传》高扬人道的价值,突破《春秋》尊王正统思想的束缚,体现了春秋时代在敬奉天道的基础上,理性地构筑天人关系,表现出比较进步的历史观点。
一、敬天重人
殷周奴隶主统治时期天神或上帝是天地间的最高主宰,有神论的天命思想在当时占统治地位。自然现象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种种活动都受到天或上帝的意志力掌控。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权威的衰落和诸侯国政治危机的加深,敬天尊神的观念也发生了动摇。一方面,秉承西周“以德配天”的传统,确立“天命”,即王权在当时道德的约束下统治世俗社会的实用天人观。《左传》讲“天之所废,谁能兴之”,作为意志主宰的“天”对个人、家族乃至国家的存亡荣辱都至关重要,仍然拥有绝对的权威;另一方面,时代的巨变瓦解着敬天尊神的传统天命观,天和人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由天命中心论逐渐向以“人”、“德”为主的人本主义转变 。《左传》在保持对天命和“神”敬畏的同时,往往更注重“人道”,强调“人”的作用。钱钟书先生说:“盖信事鬼神,而又觉鬼神之不可信、不足恃,微悟鬼神之见强则迁、唯力是附,而又不敢不扬言其聪明正直而壹、凭依在德,此敬奉鬼神者衷肠之冰炭也。玩索左氏所记,可心知斯意矣。”在当时不能完全否定鬼神的历史背景下,利用鬼神之说扬善赞德,这与破除迷信无关,而是人与神位置的变化。例如:
十一年春,齐、卫、郑、宋盟于恶曹。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
斗廉曰:“郧人军其郊,必不诫,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我以锐师宵加于郧,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斗志。若败郧师,四邑必离。”莫敖曰:“盍请济师于王?”对曰:“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又何济焉?”莫敖曰:“卜之?”对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遂败郧师于蒲骚,卒盟而还。郑昭公之败北戎也,齐人将妻之,昭公辞。(桓公十一年)
在这场战争中,莫敖担忧,提出占卜通过神来决吉凶,斗廉则分析敌情,成竹在胸,精心策划,战胜了敌军,再次强调了人为的作用。又如:
郑厉公自栎侵郑,及大陵,获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请纳君。”与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杀郑子及其二子而纳厉公。
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公闻之,问于申繻曰:“犹有妖乎?”对曰:“人之所忌,其气焰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 (庄公十四年)
申繻没有否定妖,但更强调“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在《左传》中,成败得失通常是以各种形式的神意作解释的。清代学者汪中在《左氏春秋释疑》中指出《左传》在记述天道、鬼神、灾祥、卜筮和梦的时候都“未尝废人事也”。又如:
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鷁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僖公十六年)
叔兴根据时事作了预测,但他明白,国君问得不恰当,陨星和风向都是自然现象,与吉凶无关,吉凶是人的行为来决定的。之所以迎合国君,只是因为不敢违背他而已。
《左传》中重人道的倾向是建立在“天命”的基础之上的,认为“聪明正直”的“神”是“依人而行”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只有“民和”了,神才会“降之福”,从而把“天命”和“人道”统一起来。《左传》更加注重人和人事,把天和神作为虚设和外壳,走出了西周时期的天神的神秘,注重现实,推崇理性。
二、重民保民
《左传》表现了强烈的以人为本的思想,表现在以人而非以神为目的,其中敬天礼神的目的是为了“重民保民”,将百姓置于神灵之上。桓公六年时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百姓不同心,鬼神便没有了主人,祭祀和福佑也是没有用处的。春秋时期空前重视“民”的价值,在国家强弱、霸业更替以及民众反抗中表现出巨大的作用。例如: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庄公十年)
曹刿认为只有“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才是“忠之属也,可以一战”。说明只有民心的向背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又如: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左传》中立君为民是当时流传的一种思想认识,邾文公认为:“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邾文公把利民与利君统一起来,认为利民就是利君,他认为“命在养民”,“命”是国君的使命;而个人的生命短长,不过是时间问题,所以他坚决迁绎。《左传》赞扬这位国君知道为君的使命,对此只作了两个字的评论:“知命”。
另外,春秋以后诸侯为了争霸,战争频繁。《左传》写战争的胜负,很少涉及战场的厮杀,往往从国君是否能争得民心、顺应民意上找教训。例如: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既败,王使谓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孙伯曰:“得臣将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将以为戮。’”及连谷而死。(僖公二十八年)
城濮之战中楚师大败,楚国的荣季认为:“ 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 民本思想虽然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是当时的进步思潮。
三、德为根基
《左传》中的“德”是天道奖惩人道的判断标准,以此来突出天命神鬼的道德性和目的性,同时对世俗社会提出“以德配天”的要求 ,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天道观。在处理国家政事上,《左传》更重视“仁德”的作用。例如:
公曰:“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弗听,许晋使。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冬,晋灭虢。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僖公五年)
当时晋献公向虞国借路攻打虢国,虞侯把对神灵祭祀的虔诚作为自己发动战争的挡箭牌,认为神灵一定会庇佑他。宫之奇借《周书》讲:“上天没有亲近的人,只辅助有德行的人。”又说:“祭祀的谷物没有芳香,光明的德行才有芳香。”又说:“百姓不能改换祭物,只有德行可以充当祭物。”神所依据的,就只在于德行了。
楚国大夫屈完面对强大的诸侯联军,不畏强暴,对齐侯说:“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僖公四年)那种“河山之固,在德而不在险”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致力于德行的建设才是巩固霸主地位的关键因素。
另外《左传》对社会异常现象也用“德”来解释。《左传》“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返也”。全书记载了大量作为天道、人道相互作用的社会现象及与之相关的占卜预言,强调的是“天”、“德”、“人”关系,重点突出“德”的重要性。人有没有知天奉天、配德以承天命和灾异发生、各种事件的吉凶有关,例如“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而且《左传》通过弘扬“德”,超自然现象成为工具达成主观目的。春秋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超自然力量自此打破神秘,例如,晋国发生日食,晋国君王问吉凶于大臣文伯,文伯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昭公七年)
《左传》中天道成为独立于人道之外的一种超自然而又并非无目的的至高力量,“德”是天道和人道的联结纽带,对世俗社会起到更有力的约束。天道影响人道的判断标准是“德”,实际上肯定的是人的作用,表面上天道支配人道,但事实上的决定权掌握在人的手中。
[1]孔颖达.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李索.左传正宗[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3]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4]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5]钱钟书.管锥篇[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7]龚留柱.春秋弦歌:左传与中国文化[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TsoChuanon the Philosophy of Heaven and Human
ZHAO Jun
(Hebei Radio & TV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71, China)
There has been a great chang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man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heaven-centered theory to humanism was accomplished.TsoChuandeeply manifests this change. It shows that people then advocated the value of humanity on the basis of the heaven worship, with “virtue” as the foundation, combining “worshiping heaven and respecting human” with “respecting and benefiting people”, rationally constru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 It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ages.
the Spring-Autumn period;TsoChuan; the heaven-human philosophy; humanism
2013-07-28
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开放大学的文化使命与传统文化经典教育》(SQ122011)
赵君(1977-),女,河北沧州人,文学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汉文化研究。
I206.2
A
1008-469X(2013)05-006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