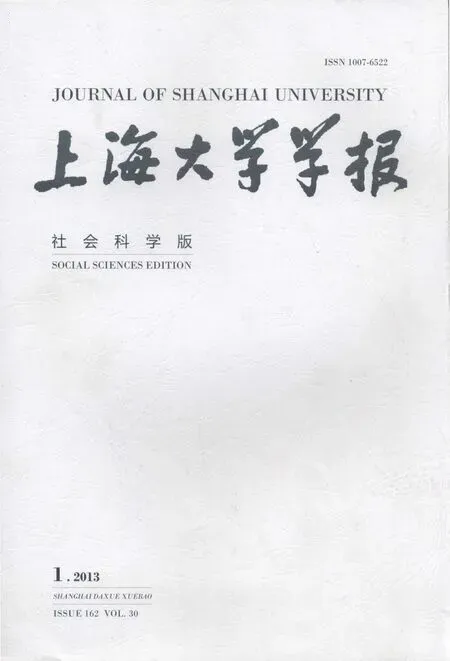文化资本与角色转变——基于清末民初时期画家群体的知识社会学研究
2013-04-07黄剑
黄 剑
(湛江师范学院 法政学院,广东 湛江524048)
一、中国近代美术史中的一个社会学议题
中国清末之前的画家一直游走在社会边缘地带,绘画还不是一种体面和正当的职业,在当时的职业观念中,专职的画家总是容易和“工匠”群体联系在一起,在社会分层结构体系中处于较低的位置。至于文人画家,他们的主要身份还是文人或士,决定他们地位的主要因素还是功名或官职。如果一位文人画家没有功名或官职,即使绘画水平再高,他的社会地位也是十分尴尬的;如果有人看中了某位画家的绘画才能而想把他引入社会上层,就必须给他一个功名或一官半职,有了正式的名分后他才算居于正统。历史上大部分文人画家仍与其他文人一样,必须遵循当时唯一的社会流动路径:科场题名,进阶仕途,对绘画只能抱着玩乐的态度。只有少数画家科场不顺,仕途坎坷,绝望于功名,唯有以画抒情言志,甚至卖文鬻画赚取钱财,最终因画而名闻天下。
清人唐岱在《绘事发微》中有关于画家社会地位的评论:“画家得名者有二。有因画而传人者,有因人而传画者……因人传画者,代代有之,而因画传人者,每不世出。盖人传画者,既聪明又富贵,又居丰暇豫,而位高善诗,故多。以画传人者,大略贫士卑官,或奔走道路,或扰于衣食,常不得为,即为也不能尽其力,故少。”[1]从中国的正史记载情况来看,那些所谓的“因人传画者”,大都能入本纪或列传,而那些“因画传人者”,则多不见传,主要身份是职业画家的人物是不值得立传的。只有那些具有一定政治身份的画家才会出现在正史记载中,他们要么有较高的官衔,要么有功名,或者在文学方面有很大影响,而且关于他们的绘画才能也只是轻描淡写。
清末民初以来,画家群体逐渐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活跃在中国的文化界,例如举办画展,开办美术学校,创办美术刊物,参与各类社会活动等等。那时画家职业已经逐渐获得社会的认同,画家也已经承担起相应的社会使命,出现了首批以绘画为专门事业的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家。那时已经涌现出不少极富盛名的杰出画家,他们和其他文化精英一样,深受社会各界推崇和尊敬,甚至可以进入上层社会。画家社会地位与角色随着当时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个转变历程超越了艺术史的研究范畴,可以成为一个社会学议题,其中的社会机制值得我们探讨。
涉及这段时期的美术史研究对这个社会事实并未做专门的分析和交代,因此把这段美术史重新纳入到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中进行补充性的研究,理出其中的社会条件和机制,是很有意义的。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深入地探讨这样一些问题:绘画活动是如何从自娱遣兴的“末技”成为一种独立和系统的文化门类的,绘画知识的形态和价值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历程,而与此同时,画家的社会角色如何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二、知识的正当化:意义与价值的重建
任何文化知识体系的价值都与社会的认可程度密切相关,其功能和价值直接决定着自身能否成为一种文化资本,而给拥有者带来相应的社会地位。民国之前的绘画作品以及绘画知识一直只是文人们抒情言志或者雅集助兴的手段,并没有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体制中取得正统地位,文人们一般视之为“余事”,因此绘画作品及其知识的功能和价值并没有被当时主流社会所认可,因而难以成为一种有效的文化资本为画家带来足够体面的社会身份。绘画的社会地位与文学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不如书法高,其原因就在于文学、书法与科举考试能力密切相关,而绘画技能则与科举考试这条正途没多大关系,这也是文人们长期以来一直把绘画看作是一种自娱遣兴的“末技”的主要原因,专事绘画则被认为是不务正业而难以登大雅之堂。
清末民初以来,受到西方美术思想影响的中国画家逐渐把绘画的功能提拔到较高的程度,并且适时地把美术活动融入到新文化运动当中,从而为美术活动注入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继“文学革命”的口号提出之后,“美术革命”的口号也随之产生,吕澂和陈独秀在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1 号)上最早明确提出了“美术革命”的口号。民国初年的画家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积极思考中国美术变革的问题,他们试图在批判传统绘画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美术革命是对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界革命的响应,自然而然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蔡元培在1919年12月1日的《晨报》发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明确地把美术看作是新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术活动应当是和新文化运动相呼应的。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如康有为、陈独秀、吕澂等,通过批判中国传统绘画而开启了新美术运动的序幕,他们都开始重新评估中国美术的价值。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康有为就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一文中表达了对中国传统绘画的不满:“中国画至国朝而衰弊极矣。岂止衰弊,至今郡邑无闻画人者。其遗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笔如草,味同嚼蜡,岂复能传后,以与今欧美、日本竞胜哉?”他“卑薄四王,推崇宋法,务精深华妙,不尚士大夫浅率平易之作”,预言中国画改革趋势必为“合中西画而为画学新纪元”。[2]21-25
正如当时的画家所宣扬的那样,绘画对于个人和社会都具有非凡的意义。近代著名山水画家胡佩衡在当时的《绘学杂志》发表了《美术之势力》一文,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美术的意义:“文化上之势力、道德上之势力、教育上之势力、工业上之势力。”[2]52-53刘海粟指出,美术和每个人的人生都积极地关联着,可以使人们摆脱物质的束缚,从而获得美的人生:“美术是导人独立的天使,能使人支配物质,能使人从束缚的状态升到自由的状态,因为他是赤裸裸的天使,他的信仰是即善即美。”他又说:“要注意启迪一般人美的感,使他们尊重自己的内心生命,发达他们创作力,他们就自然渐实现美的人生。”[3]“美术救国”的口号是效仿“文学救国”之后提出的,它把美术的意义上升到推动国家进步的高度。1918年10月6日的《申报》刊登刘海粟的《组织美术会缘起》一文,他强调:“美术者,文化之枢机。文化进步之梯阶,即合乎美术进步之梯阶也。物穷则变,所穷者美,所变者亦美也。美术之功用,小之关系于寻常日用,大之关系于国家民性。”
美术革命借着新文化运动把美术活动纳入到了新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中,中国绘画也因此获得了新生,从传统意义上的“余事”和“技艺”转变为一项独立的文化事业,和文学一样,可以承当起“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使命。中国画家也融入了新式知识分子的阵营当中,顺应了历史潮流,取得了文化活动的正当性。当时的很多学者和美术家都赋予了美术与文学、戏曲等同样的地位,在新式知识分子和美术家的宣传鼓动下,美术逐渐从历史的后台走向了前台,从边缘走向了主流。因此,绘画才能不再仅仅是画匠谋生的手艺,或是文人墨客娱乐消遣的产物,其意义被充分地阐释出来,其价值也被充分地加以提升,成为一类功能独立的文化资本,赋予画家更加独立而崇高的社会角色。
三、知识的学科化:由“技”到“学”的嬗变
绘画要摆脱仅仅是“技巧”、“技能”形态,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文化门类,其“知识型”必须要进行质的转变。绘画知识的生产、解读、运用与传播必须依据一套权威的、自主的、统一的内部法则来进行,与规则有关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只能为少数的专业精英所掌握。艺术精英借助特有的艺术法则对文化资本进行操作,实现其知识形态上的学术化,画家也就成为一种专业型的知识分子群体。画家的文化资本在形式上更加规范与精致,其内容更加深刻与复杂,这类文化资本就成为一般人无法企及的知识和技能,文化资本的稀缺性也因此得以生成和保持。
中国绘画史传承了各家的画论,涉及绘画的技法、原理、史传、品评、鉴藏、著录等,但在近代以前,这些绘画知识处于不关联、不系统、碎片化的杂乱状态,大多是文人们品评和交流的杂记,并没有把绘画上升到独立而系统的学术型态。清末以来,在西方美术理论的影响下,中国的一些画家和美学家开始了中国美术理论的建构,把传统的绘画技艺上升为现代形态的文化门类,有了相对独立的、系统的理论知识作为支撑,中国的绘画被推进到规范化、专业化的发展路径之中,而中国的画家也摆脱了“画匠”的角色,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家。
在一些美学家和画家的自觉努力下,近代中国美术由起初的致用型技能逐渐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理型学术体系,特别是美术的理论化过程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使中国本土的画学与西方的现代美术得以衔接起来。借助现代学术的形式,中国美术摆脱了传统的“技”的地位,上升为“学”的高度。西学东渐的风潮使得西方的现代美学理论和艺术理论逐渐传入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绩者包括王国维、蔡元培、李叔同、林文铮、朱光潜、丰子恺、吕澂、黄忏华、腾固、傅雷、倪贻德等人。王国维在19世纪末到上海接受了西方新学的影响,他后来陆续把叔本华、康德、尼采、席勒等人的哲学、美学、文艺等思想介绍到中国,让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美学这门学问。蔡元培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另一位创始人,并较为系统地提出了美育理论。朱光潜是一位职业的美学家,这方面的著述相当丰富,他批判地研究了西方一些重要的美学流派和美学思想,把西方美学和中国的传统艺术与美学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系。
清末民初时期,中国画坛呈现出空前的活跃局面,画家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支独立的生力军在发挥着作用。从欧洲、日本留学回来的画家成为中国画坛的新生力量,并迅速掌握了美术场域的话语权;而传统画家则不再把“学而优则仕”作为唯一的信念追求,而是大大方方地做起了职业画家。北京、上海、广州是当时中国画坛的中心,尤其是当时“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的兴盛成为了研究那段绘画史的典型范例。吴昌硕、王一亭、陈衡恪、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张大千、李叔同、李毅士、陈抱一、汪亚尘、朱屺瞻、关良、倪贻德、吴法鼎、李超士、王远勃、蔡威廉、林文铮、潘玉良、庞薰琹、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画坛名家均是活跃于那个时期。此外,那时美术学校兴起,有官办的,也有画家自己办的;美术社团林立,有的画家身兼好几个社团的成员;美术期刊也十分丰富,大多是进行学术理论探讨。俞剑华在1928年所作的《现代中国画坛的状况》形容当时的画坛盛况说:“如雨后春笋,万尖齐茁;如雨后夏山,万壑争流;如千军万马之杂遝;如笙管笛箫之迭奏。”[4]
画家队伍的壮大、美术机构的发达、美术思想的活跃等等这些文化现象促使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建构出一个美术场域,它是由其中的利益攸关者构成的一个社会空间。他们之间有各种利益博弈关系,也有权力等级结构,他们的活动大体遵循一种统一的、内在的场域逻辑,其成员对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的争夺主要是依据特定的、权威的艺术法则来进行。美术场域特定的逻辑和法则是其区别于其他场域的标志,也是保证其独立自主的重要依据,它可以保证美术场域自主地运作和发展,而抵制来自外部力量的干扰。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关于人体模特的道德论战,是在以刘海粟为代表的美术界与以孙传芳为代表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正面交锋。此次论战体现了美术场域的独立自主性,以及中国画家社会地位的上升,有效地捍卫了艺术法则的自主性、正当性和纯粹性,论战过程本身的意义远大于其胜负结果。
统一、稳定、规范的场域逻辑和艺术法则也是设置准入门槛的需要,这样可以在纷繁复杂的绘画从业者中区分出艺术与非艺术、专业与非专业、内行与外行、“匠”与“家”,这也是艺术精英群体进行自我标榜、自我区隔、自我维护的重要方式。进入民国之后,“艺术”、“学术”这些词便经常出现在画家的演讲和文章当中,美术的学术化意味着绘画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手艺”,而是上升为一种具有理论内涵的学问,画家也因此摆脱了“技艺操持者”的身份。随着绘画知识由“技”到“学”的转变,那些具有一定艺术修养的专业画家和一般的艺匠就有了明显的界限。艺术素养不是普通从业者所能掌握的,它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具有了稀缺性,其分配格局的落差也造成了绘画从业者群体内部身份的区隔,从而真正发挥了资本的作用。
汪亚尘曾在《申报》发表《美术家》一文,把画家区分为“职工”和“美术家(艺术家)”。他指出,靠画画谋食的职工没有创作的自由,要么为帝王将相所雇用,要么受民间市场摆布,他们只是普通的画工,缺乏个性和艺术修养;而真正的艺术家在社会上占有一个较高的位置,他们不会为金钱而失掉个性,他们为了艺术而不息前进,探索真正的艺术。汪亚尘批评那些只掌握了绘画皮毛功夫的人“不图实际”,明明是一般的画工,非要自称是艺术家,他认为只有“耐心地修养真挚的艺术”,热爱艺术,有了“充分的修养”,才配称真正的艺术家。[5]吕澂在倡导美术革命的时候,表达了对上海商业绘画的不满和蔑视,他站在纯美术的立场揭示了此类绘画的“伪艺术”面目,此类画“面目不别阴阳,四肢不成全体”,不符合美术解剖学原理,不能使世人培养其“美情”,根本不能和纯美术相提并论。因此这类画根本不能称作艺术,其制作者也只能称作“画工”而已。[6]
四、知识的神圣化:艺术偶像的打造
经由专业化过程之后,绘画知识和技能成为美术场域特有的产物,这类知识的价值只能在美术场域进行生产,并最终要在其中接受检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艺术场域具有炼金术一般的机制,能够赋予艺术品和艺术家神奇的魅力和价值,这都是艺术场域特定的逻辑法则和其中的共同信念所发挥的作用。专业化促使绘画知识成为画家特有的文化资本,维护了其基本的稀缺性特征,而且这种文化资本可以转换为符号资本和经济资本,进行自我增值。布迪厄所说的符号资本是指由个人的权威和声望所产生的利益,饶有意味的是,这种资本并不直接与赤裸裸的物质利益相关联,而往往以非利益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无形的资本形式。画家的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是一对相互依存、相互建构的资本形式,绘画作品的价值最终是借助美术场域的“炼金术”而获得,话语权拥有者的“共谋”以及由此形成的集体信念可以点石成金,把画家文化资本的价值推向极致。一旦被赋予超凡脱俗的神圣性,绘画作品可以变为某种“圣物”,画家也可以因此成为偶像。
绘画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也是一种担负着崇高社会使命的事业。纯粹的艺术家是一种表现性社会角色,和功利性社会角色不同,他承担着引导和表现社会文化价值观、推动人类精神发展进步的社会使命,因此社会对画家的基本评判就是高尚而神圣的。蔡元培在阐述他的美育思想时就强调要提高艺术在生活中的地位,提出美育代宗教说,希望艺术能在满足人类情感、超拔人类精神方面发挥独当一面的作用,艺术家也因而充当着“全人类精神生活上之农夫”的角色。林风眠指出,“艺术家原不必如经济学同政治学一样,可以直接干涉到人们的行为”,但是“只要他们所产生的所创造的的确是艺术品,如果是真正的艺术品,无论他是‘艺术的艺术’或‘人生的艺术’,总可以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精神深处”。①参见林风眠《艺术的艺术与社会的艺术》、《我们要注意》,均收录于朱朴编选的《林风眠艺术随笔》,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刘海粟指出:“在混浊的社会里,美术可以安慰人们的杂乱和悲哀,可以超拔人们的绝望和堕落,不是供奉少数人的叹赏为满足。”[7]
画家符号资本的积累还在于其人格魅力的展现,纯粹艺术家的品格应当是超凡脱俗、淡泊名利的,其艺术活动不应赤裸裸地和世俗利益联系在一起。林风眠在《艺术家应有的态度》一文中介绍说:“无开心论是康德论美的精华,就是说,当一个艺术家在创造他的作品的时候,第一应该把世间的一切名利观念远远地置之度外,然后才能到生命深处,而直接与大自然的美质际会。”[8]对世俗利益的拒斥是艺术场域基本价值取向,布迪厄把这种规则称为“颠倒的经济逻辑”,它建立在符号资本的本质上,意思是艺术家虽然在短期内牺牲了物质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他却获得了学术声望等象征性利益(即符号资本)。布迪厄指出,纯艺术的反“经济”的经济建立在必然承认不计利害的价值观、否定“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这种纯艺术的生产从长远来看,除了艺术家自己的要求之外,不承认别的要求,它朝积累符号资本的方向发展。②文中引号中的“经济”特指物质利益,没有打引号的“经济”泛指任何形式的利益,包括符号资本。参见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刘晖译,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第175页。
艺术家的超凡之处还在于其比普通人具有更热烈的情感、更卓绝的创造力和更鲜明的个性,普通的画匠是难以具备这些品质的,只有那些具有天赋和历经磨炼的人才有可能具备这些品质,因此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才气和灵感而显得独一无二。艺术家具备天然的禀赋和资质,还要敢于抛开世俗的偏见而见人之未见,发人之未发,自从在“模特事件”中被人谩骂为“艺术叛徒”之后,刘海粟便常常以此自居,并把自己和胡适并称为“两个叛徒”。他曾于1925年1月撰文《艺术叛徒》,称颂荷兰的后期印象派画家梵高:“他实在是创造时代的英雄,决不是传统习惯的牺牲者,更不是社会的奴隶,供人揄扬玩赏。伟大的艺人,只有不断的奋斗,接续的创造,革传统艺术的命,实在是一个艺术上的叛徒!”[9]
职业画家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之后,那些非常优秀的画家受到人们的尊重甚至崇拜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他们被冠以“天才”、“大师”、“泰斗”等头衔,受到类似于著名作家、著名学者那样的礼遇。巨大的声望和权威使他们的个人特质被赋予了很强的传奇色彩和象征意义,他们不再仅仅是某个具体的社会个体,而是被强烈地符号化。中国古代社会尽管有达官贵人推崇和珍藏画家绘画的现象,但是画家本身却没有被给予很高的社会地位,而到了民国时期,人们对艺术作品的崇拜和追逐就往往会转移到作者身上,社会尊敬和崇拜艺术家本人已经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了。那些极富盛名的杰出画家绘作品在当时已经受到社会名流的追捧,他们举办个人画展都会有学界、政界、商界的名流前来捧场,有的还会亲自撰文对其加以介绍或称颂。
艺术偶像是艺术场域运作的产物,偶像的打造使得人们的热情从艺术作品扩展到作者本身,以至于人们不再关注具体的作品内容,而是更关注作者名字作为一种偶像符号所承载的权威和名气。于是对作品的追逐逐渐导致了对作者的追捧,作品的神化创造了作者的神化,文化资本可以脱离实质内容进行价值的自我增值。因此著名画家的签名就具有了神奇的力量和价值,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典型案例就是法国画家杜尚的装置艺术品《泉》,他的签名可以让工业成品“化腐朽为神奇”,这是对艺术界符号崇拜现象最直接的诠释和讽刺。而在中国美术界此类现象也屡见不鲜,符号资本的积累让某些画家具备了一种“点石成金”的神奇能力,仅仅凭借他们的签名就可以让某件作品价值倍增。为了满足人们追逐名家珍品的需求,以及画家获利的需要,中国美术界甚至出现了请人代笔的事情。吴昌硕晚年的作品中有一部分就是由他人代笔的,他的弟子赵子云经常为其代画,而他的题画诗常常请沈石友代作,据郑逸梅回忆:“吴昌硕作画忙不过来,所有题画诗动辄请石友代为。囊年昌硕大弟子赵云壑,搜罗他老师的遗墨,曾得昌硕与石友书札数十通,装之成册,十九是请石友题画的。”[10]
[1]黄宾虹,邓实.美术丛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257.
[2]郎少君,水中天.20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
[3]刘海粟.美术和人生[N].申报,1925-01-18(1).
[4]周积寅.俞剑华美术论文选[C].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63.
[5]王震.汪亚尘荣君立年谱合编[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6:54-55.
[6]吕澂.美术革命[J].新青年,1918,(6):84-85.
[7]袁志煌,陈祖恩.刘海粟年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44.
[8]朱朴.林风眠艺术随笔[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143-144.
[9]沈虎.刘海粟艺术随笔[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65-168.
[10]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97-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