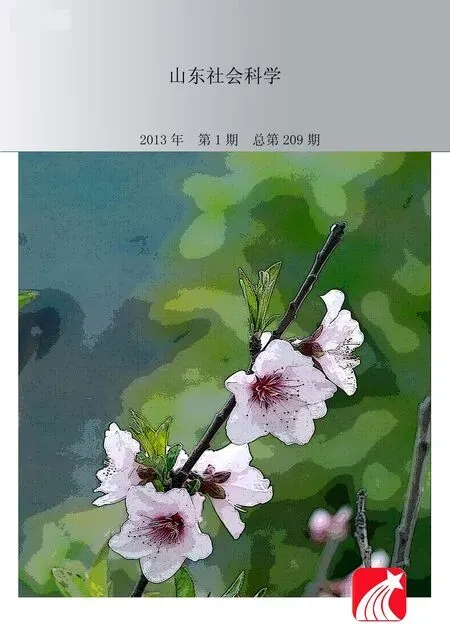当代文学批评的社会历史观问题
2013-04-07赖大仁
赖大仁
(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文学批评在根本上是一种文学评价,文学评价并不仅仅关乎文学中的价值,更关乎文学批评的价值立场与价值观念。恩格斯在评论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时,批评作者进行文学批评的“调和主义”倾向,指出:“任何一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只是同整体的比较当中决定的”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24页。。对文学的评价,不管是对于一个作家的评价,还是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评价,或者是对某种文学现象的评价,都不可能从它自身得到说明,而是需要放到一定的结构系统及其价值关系中,从比较的意义上才能得到较为确切的认识和较为切实的评价。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任何价值都不是单一的,都无不关联着一定的价值系统,都不过是在这个彼此关联着的价值坐标系统中的某个维度上显现出来的价值。因此有学者认为,“从价值学来说,文学批评的价值体系就是文学批评的价值理论或价值学依据,就是说文学批评可以从文艺学,即文学原理的角度来研究,价值学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文学批评的研究,它既要尊重文学的一般规律,又要将之纳入价值哲学的系统。文学批评的价值体系来自文本价值实现的要求对主体与文本对话的一种驱动,并表现为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①毛崇杰:《颠覆与重建——后批评中的价值体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从文学价值论的一般意义而言,不同维度上显现的文学价值构成彼此关联的文学价值系统,而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与不同的文学价值维度相对应的文学价值观念,也构成一种彼此相互关联着的文学价值观念系统。通常的文学批评及其文学评价,便是在某种文学价值观念的支配作用下,从某种文学价值维度着眼进行的。
一、文学批评的社会历史观问题探讨
在文学批评的价值维度及其价值观念系统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关于文学的社会历史观问题。把文学艺术看做自然的摹仿或社会生活的反映,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艺观念,也曾经是影响最大、流行最广泛的文艺观念,至今也仍然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自古以来人们大多相信,文学艺术反映社会生活(包括历史生活),并不是纯客观的反映,其中包含着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生活的认识评价,当然也就会反映出人们的社会历史价值观。首先,从文学创作方面来看,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文学的作用就是再现生活、说明生活、对生活下判断。这就是说,作家反映生活,必有一个对生活的认识、理解与判断的问题,其中的是非曲直、善恶美丑,以及生活是否合理、是否社会的进步、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等等,都需要有作者的认识理解,否则就既无法“说明生活”,更不可能“对生活下判断”。而从文学批评方面来看,对于文学中所描写反映的社会历史生活,是否站在正确的价值立场、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生活、是否具有认识价值、能否起到“生活导师”的作用,等等,都是文学评价中无可回避的问题。而文学批评要对文学反映社会历史生活作出价值评判,当然不能没有进行评判的价值观念。文学批评所关涉的这方面的文学价值观念,可以统称之为“社会历史价值观”,其中所包含的具体内涵,主要关涉以下一些方面的问题。
(一)真实性价值观
应当说,凡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无论是描写现实生活,还是叙写历史人物故事,都首先有一个真实性的问题,如果文学作品对生活的反映缺乏真实性,那就几乎没有多少可取了。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几乎把真实性视为文学的第一要素。按高尔基的理解,“对于人和人的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②[俄]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63页。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名言,则更是众所周知:“在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3页。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充分肯定果戈理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倾向和写作态度,就在于他们能够“按照真情实况来再现生活与现实。文学就从这一点在社会的眼里获得了重要的意义”④[俄]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502页。。
人们之所以看重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性,是因为真实反映生活关联着的是文学的认识价值,如果文学对生活的描写不真实,那么它的认识价值必然大打折扣。因此,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把真实性作为评价那些着重反映社会生活面貌的文学作品的重要价值尺度,应当是合乎逻辑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应当如何理解文学的真实性?是否把生活现象搬进文学作品,就自然具有了文学的真实性?就必然具有文学的认识价值?显然这是一种极为简单直观的理解,实际上并非如此。对此,俄国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有一段话阐述得极为深刻,他说,“我们还要求文学具有一个因素,缺了这种因素,文学就没有什么价值,这就是真实。应当使得作者所从而出发的、他把它们表现给我们看的事实,传达得十分忠实。只要失去这一点,文学作品就丧失任何意义,它甚至会变得有害的,因为它不能启迪人类的认识,相反,把你弄得更胡涂。”“然而真实是必要的条件,还不是作品的价值。说到价值,我们要根据作者看法的广度,对于他所接触到的那些现象的理解是否正确,描写是否生动来判断。”⑤[俄]《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362页。这就是说,作为文学价值的真实性,一方面来源于对生活现实真情实况的真实再现,另一方面还包含着作者对生活的正确认识理解和判断,对于描写历史生活来说,则是要求包含“历史理性”在其中。否则,倘若作者自己都对所反映的生活认识不清,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以其昏昏又岂能使人昭昭?这样的文学又如何能给读者提供有益的认识和启示?所以文学真实性看似是一个外在性的评价尺度,实际上具有很值得探求的价值内涵。
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对于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历史)的真实性,其实也不能笼而统之一概而论,其中仍有不同的层次内涵。笔者以为,至少可以从这样几个层面着眼来加以考察和评价。一是生活现象描写的真实性,包括人物、故事、场景和描写,要求从情节到细节都具有生活的逼真性,真正富有一种生活的质感,其中尤其不能忽视细节的真实。从上面的引述可知,恩格斯理解现实主义文学,是把细节真实作为基本要求来看待的。巴尔扎克也曾说过,如果一部小说在细节上不真实,那就毫不足取。故事与细节的真实虽然是最表层的真实,但如果没有相当厚实的生活素材积累,没有认真严谨的创作态度,仅仅凭着想象去编故事,那也是很容易“穿帮”的,倘若如此那就会影响整体上的文学真实。二是写出生活氛围的真实性(对于历史题材写作来说则是历史氛围的真实性),也就是要求写出这个时代生活的整体气氛,将所描写的人物、故事、场景都融入这种如雾气般浓厚的生活氛围之中。如果说生动的人物故事具有打动人的力量,那么真实的生活氛围和历史场景则更具有一种感染人的力量,达到生活氛围的真实无疑是一个更高的要求和境界。三是写出社会生活变革发展趋势或者历史潮流的真实性,要求把潜藏在人物故事背后那种社会历史变革发展的必然性表现出来。恩格斯在评论拉萨尔的历史剧《济金根》时曾说过:“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8页。文学创作不能仅仅停留在写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做了什么,更需要去追问和洞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驱动和支配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从哪里来的?如果能够把这种社会生活变革发展的趋势以及历史的必然要求写出来,应当说是一种更深刻的、更具有本质意义的真实性,当然也就更具有认识意义和文学价值。
(二)人民性价值观
自从俄国民主主义者提出文艺的“人民性”范畴以来,就一直成为人们衡量古今文艺作品的历史进步意义的一个重要尺度。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同样也把文艺的人民性纳入了自己的理论视野。列宁曾经提出,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页。。这里实际上涉及如何认识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文学在反映社会历史生活时,显然对此无法回避,这就是一个“人民性”价值观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到文学批评时,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页。这里所谓“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实际上也是提出了一个“人民性”价值观的问题。这不仅在认识和评价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时有这个问题,而且在当代文学批评中,同样也会涉及这方面的问题。
从当代文学批评的角度而言,当代文学作品所关涉到的“人民性”及其价值内涵,也许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当代文学创作反映社会历史生活,究竟是坚持人民史观还是英雄史观的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是人民史观,认为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变革社会的实践活动,形成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而历史上出现的英雄人物,是只有在这个时代需要的时候才产生的,也是只有顺应这种时代潮流,在人民革命或社会变革的实践中才发挥其作用的。因此,描写社会历史变革发展的大事件,理应写出这种时代发展的大趋势,社会变革的大潮流,人民的普遍愿望、要求和人心向背,以及人民参与社会变革的巨大热情、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从而把英雄人物置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加以表现,这样才能写出真实的社会历史生活,也才能对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和恰当的艺术表现。然而实际上,在新时期以来相当一些文学作品中,特别是一些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往往抛开或模糊了这种历史观,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英雄史观:写古代历史只见帝王将相,写现代历史也只有英雄豪杰;将一些主要人物描写成可以凭着个人欲望和意志,独往独来、颐指气使、呼风唤雨、主宰一切的历史创造者和救世主,而普通民众则只是软弱可欺、俯首听命、等待拯救的群氓。在这样的描写中,“人民性”便无从谈起,其社会历史观也必然会被扭曲。
其二,在当代大众文化兴起的背景下,“人民性”是否要改变为“公民性”的问题。这里涉及对“人民”概念如何理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历来把“人民”理解为社会的主体、历史发展的先进力量和根本动力。据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莱希特曾为“人民”下过这样的定义:“人民即指那些不仅全力以赴于历史发展中的人,而且人民中事实上还是把握历史发展、推动历史发展、决定历史发展的人。人民,在我们看来,就是创造历史的人,也是改变自身的人。”①转引自[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页。国内学者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的“人民性”范畴,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它的广大性,二是它的革命性。前者是在范围上显示人民的广泛性,后者则是在内质上凸显人民的先进性。②参见严昭柱:《关于文艺人民性的思考》,《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6 期。然而据说有论者提出,应当从“公民性”的意义来理解和重建文艺的“人民性”,认为公民是现代人的普遍身份,现代语境中的人民落到实处时就是公民,真正的人民性既以公民性为始基,又以公民性为指归,只有学会以公民性为本位和尺度,才能找到建构文学的人民性的方向,创造出真正的人民文学。而这种“公民性”的内涵,其实也就是作为个人而存在的“个体性”。笔者认为,在当今时代条件下,重视文艺的大众化、平民化发展趋向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放弃应有的价值理念,用“公民性”取代“人民性”,无异于消解了其中的先进性价值内涵。我们主张坚守真正的文艺“人民性”价值立场,就是既要肯定其广大性,即充分尊重和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艺审美需求,同时又要倡导其先进性,坚持用来自人民的先进思想与时代精神,引领人民的精神生活。如果说在当今文艺大众化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还应当有核心或主导性的价值观,那么就应当坚守这种“人民性”价值观。③参见赖大仁:《文艺“人民性”价值观》,《人民日报》2007年4月19日第9 版。如果放弃和丧失了这种价值理念,那么当代文学批评就更容易走向迷乱。
(三)关于“历史观点”的理解
众所周知,恩格斯曾提出文艺批评的“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这里的“历史观点”,显然是针对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生活,以及所表现的社会历史观而言的。那么恩格斯所说的“历史观点”究竟是什么含义,其中体现了什么样的社会历史价值观?仍值得认真研究探讨,这对于我们建构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体系,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按笔者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历史观点”,绝不同于一般所谓“历史主义”,而是具有唯物史观的特定含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唯物史观在文艺批评中的具体化。在通常情况下,我们认识历史、分析问题时,只要将现象和问题放到特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具有某种历史意识、历史眼光、历史视野等等,就可以说具有了一定的“历史主义”态度。而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历史观点”,除了上述基本含义之处,还要求洞察人物事件所关联着的那些历史条件和现实关系,把握人物事件所处的历史潮流,从历史的必然要求与其实现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中,才有可能对人物事件作出正确而深刻的分析评价。这种“历史观点”,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对文艺现象深刻观照的特殊要求。
具体就其中所包含的价值内涵而言,我们认为又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历史理性”精神,就是文艺作品反映社会历史生活及描写人物事件,并不只是按照事实本身来描写,而是要求包含对历史发展潮流和发展规律的正确理解与把握;二是在这种社会历史生活的反映描写中,应当体现历史进步的价值观。这也就是前面引述毛泽东所强调的意思,除了追问这种反映描写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还要追问一下它在历史上有没有进步意义?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进步意义?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观,而更多体现为一种价值观。如果说文学创作需要有这样的自觉意识,那么文学批评就更需要有这样的历史眼光加以审视与评判。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的历史悲剧《济金根》的批评,并不是指责它描写了济金根这个历史人物,以及他领导骑士暴动失败这个历史事件,不是责备作者没有正面描写农民革命,而是批评作者没有把济金根及其骑士暴动放到当时的历史潮流中去认识理解,没有写出济金根及其骑士暴动失败的真正历史根源,而是对此作了违反历史理性的主观唯心的理解和描写。其结果,一方面是没有正确反映历史发展潮流和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并不能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和理解历史,无益于人们吸取经验教训推动历史进步。再如恩格斯驳斥格律恩等人对歌德的评价,也是因为格律恩等人只是从所谓抽象的“人的观点”评论歌德,结果只能是导致对歌德的歪曲评价。而恩格斯主张用“历史观点”评价歌德,则是要把歌德还原到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与现实关系中去,这样才能真正认识歌德及其创作的积极和消极方面,从而起到促进社会变革进步和人性解放的历史作用。还有后来列宁评论托尔斯泰,同样是把托尔斯泰及其创作中体现的思想学说的矛盾,放到俄国农奴制改革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潮流中去认识评价,既揭示产生托尔斯泰及其思想学说的历史条件,又辩证地阐明了他的艺术成就及其意义,以及“托尔斯泰主义”可能带来的危害。这种历史评价的着眼点,仍然在于揭示历史发展潮流和发展规律,以及推动社会变革发展的意义。
从这种“历史观点”来看,我们的当代文学创作显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一些“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的文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只强调还原性、原生态地真实“呈现”社会历史生活,而无意于表达对生活的认识评价,实际上放弃和消解了“历史理性”。而我们的文学批评,也同样在不断弱化“历史观点”,实际上也是在放弃和消解“历史理性”。其结果,只会带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社会历史观的更大混乱,这个问题的确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当代文学批评的社会历史观评析
描写社会历史生活的文学作品,一方面是一定社会历史生活的反映再现,另一方面又无不表现出作者对这种生活的认识评价,即无不表现出一定的社会历史观。因此,从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的维度来认识评论文学,包括对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社会历史观及其价值取向加以认识评析,应当说也是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为历来的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所重视。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社会历史批评也历来是具有重要地位的文学批评形态,在我国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甚至还是占主导地位的批评形态。不过随着当代文学批评的变革转型,在一些人看来,社会历史批评似乎已经过时,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其实这种看法是偏激片面的。正如王元骧先生所说,“只要我们承认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那么,要全面而正确的认识文学作品,社会学的研究总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文学研究中最基础的工作。只有建立在这一基础研究的工作之上,其他文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如文化学的研究、美学的研究、心理学的研究乃至符号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发挥它们自己的特长和优势,而不至于脱离基础研究而走向片面和极端。”①王元骧:《探寻综合创造之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3-74页。这种认识显然是更为客观公允的。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从文学观念到批评方法可能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往往将文学中的“社会历史”因素简单化,如简化为单一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或阶级斗争因素等等,把文学当做某种经济学或政治学的教科书,文学研究成为变相的社会学研究,文学批评也成为简单的“政治批评”。如果说在过去的某些历史阶段上,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具有其历史合理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些东西则会失去它的现实合理性。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指出:“……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失去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从我国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变革发展来看,作为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现代转型,即逐渐打破原来政治化批评模式的桎梏,将其他文学批评如人学批评、文化批评等因素融合进来,尤其是受到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新潮观念的影响,不断走向开放性发展。由此带来的变化是,一方面,社会历史批评的视野及其意义阐释空间更宽阔了;而另一方面,作为此类文学批评形态之根本的社会历史观念本身,则又往往变得模糊混杂起来。
从一个时期以来描写社会历史生活的创作实践及其文学评论来看,尤其是那些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包括改编)及其评论阐释,所表现和张扬的社会历史观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值得加以观照与评析。
一是注重文学的想象虚构性而颠覆历史的真实性。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把文学看成是社会历史生活的真实反映,首先注重的是文学反映生活的真实性,这是一切文学价值的基础,如果文学缺乏真实性,那就谈不上别的意义价值。后来新历史主义的文学观不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更为注重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便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传统文学的真实观,文学对社会历史生活的描写因此变得扑朔迷离,文学批评也难以对这种文学描写的真实性及其意义进行确切的把握和评价。及至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流行开来,历史真实性的观念则更进一步被彻底颠覆,正如麦克黑尔在论及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特点时所说:“后现代主义者虚构了历史,但通过这样做,他们意在表明,历史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虚构的形式。”③[英]布里安·麦克黑尔:《后现代主义小说》,转引自王岳川主编:《中国后现代话语》,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在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历史本身并无所谓真实性可言,通常人们所看到的所谓历史,都不过是文本的历史,而文本又不过是某些人按照自己的认识和意图书写的,因此这种历史的文本自身就是不可靠、不真实的。特别是作为文学中的历史书写,就更是一种虚构的文本形式,更不必拘泥于历史真实。既然如此,作为文学批评也就不必以历史真实作为评判此类文学的价值尺度。在这种后现代文学观念的影响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有一些历史题材的写作,如某些新历史小说,已不像传统的历史写作那样,致力于在考证历史事实和搜集生活素材方面下工夫,而只不过是把某种社会历史背景或某些历史大事件的框架移用到作品中来,在这种历史背景和事件框架之中,在想象或幻想中虚构自己的历史故事,表达自己对某种社会历史生活的理解。在此类写作中,作者也许并不在乎所描写的生活事件与人物有多大程度的真实性,而更注重的是借此表达的思想观念,因而就更多成为一种观念化或理念化的写作。而对于此类作品的评论,也往往把阐释评价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作品表达的观念或理念上,而对于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则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也许可以说,作为当代社会历史写作及其文学批评,比以往更为注重对社会历史生活意义的开掘,强化对社会历史的认识理解即历史理性的表达,这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问题在于,反映社会历史生活的真实性毕竟是此类写作的基本要求和重要特性,并非可以忽略不计置之不顾。应当说历史真实性是表现历史理性的基础和前提,如果失去了历史真实性这个条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历史理性又将何以充分表现?如果过于强调社会历史书写的想象虚构性,过于消解此类写作的历史真实性,就难免走上歧路。从一个时期以来的社会历史写作及其文学批评来看,在这方面的确存在一些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
二是张扬历史事件的偶然性而颠覆历史的规律性。这可能主要来自西方“新历史主义”思想观念的影响。新历史主义为了颠覆以往机械僵化的“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必然论”观念,反其道而行之,以另一种极端的方式,提出“历史偶然论”,认为历史并没有必然规律可言,历史发展是由各种不可预测的偶然因素促成的,历史过程也完全是由一系列偶然事件构成的,有时候某个关键性历史人物的一个偶然性的动机与行为,就有可能改变历史的面貌与发展进程。这种观念往往特别为文学家们所乐于接受,其原因也许在于它与文学本身的某些特性恰相吻合。因为文学作品描写社会历史生活,恰恰在于写个别性和特殊性的事件,以及写出人物的独特个性,因此某些偶然性的生活事件以及人物的个性冲突,就往往成为构织作品情节的最好元素。记得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偶然是最伟大的小说家”①[法]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转引自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68页。,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也许正因为如此,国外一些新历史主义写作特别热衷于张扬偶然以颠覆历史。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我国近一时期也有一些作家和评论家,以这种新历史主义观念为时尚,不断标举所谓“新历史”写作或“边缘化”写作策略。在一些被称之为“新历史小说”的作品以及同类型的影视作品中,热衷于写情节的偶然性和事件的突发性,以及人物的个人动机与偶然性行为所造成的矛盾冲突及历史转折,给人带来的阅读观感,除了历史的扑朔迷离和命运的变幻无常,并不能给人以深刻的历史认识与启示。这种以偶然性颠覆历史规律性的写作,所表现的是一种非理性的社会历史观,这与唯物史观是恰相背离的。唯物史观并非不承认某些历史事件的偶然性,而是认为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是辩证地统一于历史过程之中,一个历史过程虽然包含着若干偶然性事件,但在其背后,仍然有某种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因素在发生作用。文艺作品当然可以选取某些偶然性的生活事件作为创作题材,但仍然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它写出偶然性当中所包含的某些必然性的东西,以及个人的偶然性行为动机中所包含的历史动机。恩格斯在批评拉萨尔的历史悲剧《济金根》时,并不是批评他写了济金根领导骑士暴动并最终失败这样一个具有相当偶然性的历史事件,而是批评他没有写出这个事件背后深刻的“历史根据”,没有写出济金根个人动机背后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历史潮流。如果无视社会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根据,无视这种历史潮流的作用,而是仅仅着眼于描写这个偶然性事件本身,为写偶然而写偶然,除了让人感到扑朔迷离和命运无常之外,并不能给人提供更多一点历史认识与启示,那么它的意义价值何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在批判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必然性的消解倾向时说:“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历史是朝着某种既定目标平滑地展开的。但是每一个人都相信历史的目的和意图,相信被它们的特殊目标所定义和指导的构想。”历史具有其真实性,“至少,这是一种最低程度上的意义,即历史是一种必然性的而不是一种‘随便什么都行’的事情”②[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0页。。应当说,历史发展过程中无疑存在各种偶然事件,但任何偶然都是历史必然性进程当中出现的偶然,都是可以通过历史理性来加以认识和解释的偶然。真正的文学写作理应建立在历史理性的基础上,无论是写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都能为人们理性地认识和理解历史提供某种启示和借鉴。倘若文学写作仅仅只是热衷于写偶然性事件,甚至不只是为写偶然事件本身,而是为颠覆历史,张扬非理性的社会历史观,从而导向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那就更将贻害无穷,不能不引起充分关注。
三是将历史戏剧化而遮蔽其中的是非善恶。文学艺术创作不同于历史记录,而是一种艺术创造,无疑需要进行艺术加工,将普通的社会历史生活编成引人入胜的文学故事,乃至追求戏剧化的艺术效果,这都是无可厚非的。不过问题在于,即使是在文艺创作中,社会历史也并非可以无原则地随意阐释,尤其是社会历史斗争中所包含的是非善恶美丑,也并不是可以随便抹去的。然而从近一时期某些文艺创作及其评论来看,却是过于将社会历史生活戏剧化,一味追逐所编写的故事热闹好看,而并不顾及这些故事所关涉的是非善恶。比如,在一些新历史主义者看来,阶级斗争观念早已过时,用这种观念来认识判断历史是非也已经不合时宜,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所谓“历史还原”,即还原历史争斗的事实本身,至于这种争斗的原因与是非,则似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这种观念的影响支配下,一些文艺作品不管缘由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大写各种各样的人间斗争,诸如君王霸权之争、宫廷王权之争、朝野势利之争、军阀派系之争、党派利益之争;还有各种各样的明争暗斗,为统治地盘而斗,为权力而斗,为财富而斗,为情色而斗,为帮派私利而斗,为满足种种个人私欲而斗等等。有的甚至把我国近现代的改良与革命的斗争,以及民主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与军事斗争,也都归入这种历史争斗的模式之中加以描写。而在各种大肆铺张的描写与渲染中,人们看到的是形形色色密室里的阴谋算计,战场上的血腥搏杀、明枪暗剑的无情中伤、处心积虑的残酷陷害、人面鬼胎的权术角逐。这样的描写看上去是所谓“历史还原”,即还原为争斗的事实本身,好像并没有对此作出什么历史解释,然而其中实际上仍然包含着某种认识判断,这就是把一切争斗的根源都归结为人的欲望与野心。既然凡人都有欲望与野心,并且也都是在这种欲望与野心的驱使下加入争斗行列的,那么彼此就都只是为各自的利益而争斗,无所谓君子与小人、英雄与流氓,充其量不过是胜者王侯败者寇而已。倘若如此,无疑将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再如,在有些人看来,历史无非是个各色人等表演的大舞台,每个历史人物登台表演都各有动机,而这一切又都可以说根源于人的本性。历史活剧中的表演虽有成败荣辱之别,然而在人性展示的意义上则可同等视之,并无善恶高下之分。这种观念在那些写封建王朝宫廷斗争、朝野纷争的作品与评论中比较常见,反正都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人物,无所谓好人与坏人;他们的恩怨争斗,无所谓是非对错;他们的种种言行表演,都根源于人之本性,无所谓善恶高下。还有的写现代共和革命题材的作品,创作者力图在“人性”的深度上加以开掘,为某些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挖掘“人性”的根源和依据,似乎任何历史人物,不管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如何,他的行为都自有“人性”上的根据与合理性;而且从“人性”的方面看,无论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还是封建统治者与军阀,在人性上都各有弱点和可称道之处。于是一场历史斗争也就转化成了历史人物的“人性”表演或展示,历史的是非善恶也就在“人性论”的观念中消解了。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人性论”观念的影响,一些为历史人物翻案的文学创作也就层出不穷,而文学创作上的这类翻案文章,往往不是重在历史事实方面,而恰恰是着眼于“人性”方面。即便是某些历史上有定论的大奸大恶的历史人物,好像也可以撇开其历史评价而在“人性”的意义上加以开掘,似乎历史烟云早已消散,是非善恶也已模糊可以不必计较,唯有“人性”是可以超越历史时空而彰显意义的。这种以“人性”展示来遮蔽和消解历史是非善恶的价值导向,无疑将使社会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陷入深重的误区。在笔者看来,虽然历史上的各种纷争错综复杂,但并非没有基本的是非可辨,这里起码还有一个“人民性”的标准,即人民的普遍愿望或人心的向背、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等等。站在这个立场上,就不能说历史是笔糊涂账,也不难判断各种历史争斗的是非。问题只在于,我们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是否把这种人民性的价值立场根本抛弃了。
四是将历史游戏化而消解历史理性。众所周知,一个时期以来,在历史题材创作领域,除了“正说”历史(比较严肃的历史正剧的创作)、“另说”历史(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另类”解读和演义)之外,十分流行的就是“戏说”历史,也就是借历史来游戏娱乐搞笑。此类创作之所以风行,也许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不必花工夫去研究历史和考辨史实真伪,也不必表现严肃的主题和追求多高的艺术境界,无非是拿历史来开玩笑游戏一番搞笑取乐而已,创作可以比较轻松随意,又不必承担历史责任,自标“戏说”,等于是告诉读者观众:此为“野史”而非“正史”,因此别把我当真,也别跟我较真,游戏而已。二是具有广阔的消费市场。说不清是游戏化的创作培育了读者观众的观赏趣味,还是读者观众的游戏化观赏趣味刺激了此类“戏说”创作,总而言之,在当今文化艺术普遍游戏化、消费化的语境中,那些认真严肃的艺术创作,显然没有这些戏说搞笑的东西更有市场。在这种市场导向下,“戏说”成风也就不足为奇了。本来在一个审美趣味多元化的时代,某些题材(如无案可稽的野史之类)拿来戏说搞笑一番似无不可,但问题是在“戏说”成风之后,不仅民间野史被“戏说”,而且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也被拿来“戏说”,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戏说”历史中所有意或无意传达出来的历史观念: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历史既非悲剧,也非喜剧,而只是一场闹剧,是一场没有导演、没有规则、也没有意义的游戏。所以在那些“戏说”类作品中,真实的历史背景被抹去了,严酷的现实苦难被淡化了,各种矛盾斗争也都游戏化了,各色人等打打闹闹、哭哭笑笑,皆是在玩各种误会巧合的游戏,到处皇天乐土、其乐融融;游戏中的君主臣民个个都天真有趣、风流多情、可亲可爱,使人误以为古代封建社会原来是如此温情的人间乐土!这真可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种“闹剧”般的“戏说”方式无疑是对历史的嘲弄,并且在这种调侃游戏中将导致对历史意义的根本消解,如此“戏说”下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将在“逗你玩”的游戏中悄然丧失。“戏说”类的历史剧或其他文学作品,也正是在这种“逗你玩”的文学游戏中,把应有的历史感和历史理性玩丢失了,剩下的就只有娱乐搞笑本身。这必将走向彻底的历史虚无主义,造成对读者观众、尤其是对历史知之不多不深的青年读者、观众的严重误导,其反历史主义的负面作用不可低估。而当今文艺理论批评界,却似乎对这种历史游戏化的现象见怪不怪、听之任之,有的甚或在历史普及化的名义下为之推波助澜,这显然是一种有害无益的误导。
此外,在当代社会历史写作及其文学批评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宣扬英雄史观、帝王史观的现象。比如一些作品专写历史上某些颇有作为的帝王故事,写他们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歌颂他们超人的智慧谋略和文治武功,以及追求建功立业、励精图治的人格精神。然而在不知不觉中,封建王朝被粉饰了,封建帝王被美化了,封建皇权意识也在无形中被歌颂和强化了,与此同时,则是封建专制统治的残酷社会现实被掩盖了。也有一些历史题材的作品,虽然也写到封建时代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写到某个朝代的天灾人祸及百姓的苦难,但主导方面却是在颂扬封建王朝的君臣们如何忧国忧民、心忧天下、情系百姓、爱民如子,与民同甘共苦,乃至舍身为民请命,解民倒悬,其境其情,无不令人感动,因之这些君臣的形象都显得十分高大。有人评论说,这些作品揭露贪污腐败,歌颂清官明君,符合老百姓的愿望和为群众所欢迎,因此效果是好的。我们认为对此需要作辩证分析。应当说就封建社会的范围而言,显然明君清官比昏君贪官好,老百姓能得到更多一些好处,在无法改变封建专制统治、还不可能实现人民民主的社会条件下,老百姓也只能把愿望寄托在一些清官明君身上,这并不难理解。古代的许多文学作品正是表达了百姓的这种愿望,因而为人民群众所欢迎,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进步,是各种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最根本的动力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包括生产劳动实践和反抗乃至推翻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斗争。至于某些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能顺应民意和历史发展潮流,励精图治,以求国泰民安,虽然从动机和出发点来说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基业,但与那些暴君昏君的误国害民相比,显然能给百姓带来一些好处,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文学作品以此为题材,并在艺术上作某种肯定性的描写再现,本无不可,不过有一个宏观把握和度的把握的问题。然而一些作品过于夸大某些封建帝王的历史作用,极力渲染歌颂他们如何以盖世无双的文韬武略治国平天下,开太平盛世,给天下百姓带来福祉,并让百姓们由衷地感恩戴德、山呼万岁;有的作品甚至充满激情地歌颂“煌煌天朝气象万千”,还有的作品干脆代封建帝王抒情“我还想再活五百年”等等,则无疑是英雄史观、帝王史观的借尸还魂,表现出一种历史倒退的价值立场。
上述种种,归根结底是社会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是否需要坚守唯物史观和历史理性的问题。应当说历史既有喜剧,也有悲剧,更有正剧,无论何种历史形态,都需要真实地加以呈现,并且以历史理性加以烛照和表现,给人以历史启示。倘若我们的社会历史观本身出了问题,扭曲或消解了历史真实与历史理性,那么文学中的历史就都将变成不可理喻的闹剧,由此也就必将走向彻底的历史虚无主义,造成对读者观众、尤其是对历史知之不多不深的青年的严重误导,其反历史主义的负面作用不可低估。有鉴于此,当今坚守唯物史观立场,倡导重建历史真实性和历史理性应当说是极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