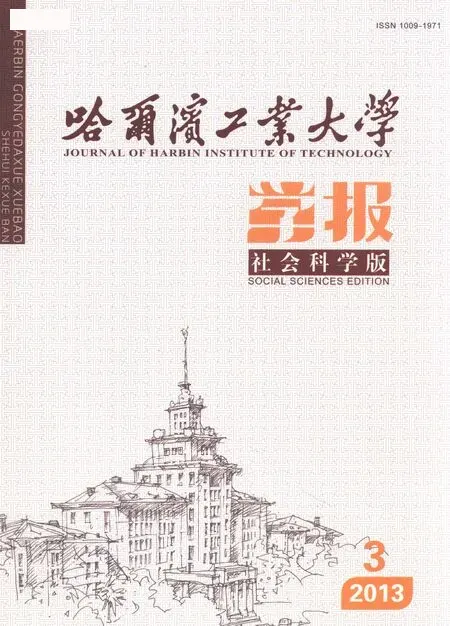书写的相似:语境、主题与手法——中国创作界对福克纳的接受
2013-04-07朱振武
郭 宇,朱振武
(1.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2.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444)
作家莫言曾说,他“这种年纪的作家毫无疑问都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因为在80年代以前中国是封闭的……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学被翻译进来,我们有一个两三年的疯狂阅读时期,这种影响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从而不知不觉地就把某个作家的创作方式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来了。”[1]20作为20 世纪 80 年代被译介的一员,福克纳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如莫言、余华和赵玫等知名作家都曾承认福克纳对自己有影响。这种影响有其接受上的偶然因素,但也是一种必然结果。本文将主要以莫言、余华和赵玫三位当代作家及其作品为例,考察中国创作界对福克纳接受的必然性。
一、语境的相似
“文学是一个与时代同时出现的秩序”[2],因此历史的推演和社会的变迁必然会对文学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创作界接受福克纳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文学环境与福克纳的创作语境有很多相似之处,而很多中国作家又与福克纳有相似的文学创作追求。这种相似的书写环境是中国创作界接受福克纳的基础,并使对福克纳接受的文学事实成为一种必然。
相似的书写环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时代背景方面,中美两国都处于历史变革期,在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下,人们的心态都发生了变化。福克纳生活的年代正是奴隶制衰退、资本主义工业化兴起并逐渐走向鼎盛的时期,同时也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时期。福克纳面有战争创伤,但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传统南方人在面对现代化时所受到的情感和心理上的冲击。他们精神上所依赖的旧传统从某种层面上来讲对于那些南方人无异于信仰般的东西,失去了旧传统也就意味着信仰的失落,也对他们造成了集体性的和创伤性的心理阴影。福克纳身为其中一员也同样遭受了这样的心理创伤,因此产生了悲观的心境,其前期作品中表达的那些比较悲观的情绪体验是个证明。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也处于转变时期,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那段历史成为了中国民众集体性的创伤心理体验。这种创伤情绪一直蔓延到20世纪80年代,因此中国创作界的文人们在创作时就带着这样的情感体验。同样的过渡社会现实,同样的创伤心理,这些相似性成为中国创作界对福克纳及其作品产生高度认同感的基础,也最终使福克纳的接受成为一种必然。这种相似性就像绳索一样将中国创作界与福克纳牵引到了一起。
其次,中美两国的文学大环境也具有相似性,都处于一种变化时期,这推动了中国创作界对福克纳的接受。20世纪初的美国文坛在经历了多年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后迎来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文学审美追求呈现出明显的“向内转”倾向,因此带动了文学创作中形式方面的革新。作家们不再拘泥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也不再仅仅关注外部客观世界,更多的是将目光投向了人的内心世界以及如何表达内在的情绪。在此文学创作背景下,福克纳更加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和意识流动,因此注重对创作手法的不断创新与尝试,进而找出最有效的表达方式。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中国文学要往何处走,该怎么走,这些成了学者们思考的主要问题。新时期的中国文学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因为此时的中国文学是在国际文化文学的影响下成长的。改革开放政策给各种文化文学以大量涌入国门的机会,使得国际文化对文学所表现的现实生活,对中国人的政治观和社会发展史观,以及思维方式等多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3]。除了外来影响,本国的历史经验也是影响新时期文学走势和接受的重要因素。中国文坛呈现出“向内转”的文学倾向,描写内心感觉、注重主观化抒情的创作追求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并渐次促成了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等文学流派的勃兴。另一方面,文学上的每次创新几乎都是从对形式的创新开始的,西方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再到现实主义是这样,中国古代历史上从唐诗到宋词再到元曲也是这样。因此,20世纪80年代,莫言、余华和赵玫等部分文人也将目光锁定在形式的创新上。如何更好地表达内心真实成为一部分作家关注和思考的主要方向。他们这一时期的作品在内容上关注人自身及其生活,在形式上则尝试用新鲜的话语方式进行表达。他们的努力促进了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等文学潮流的产生和发展。文学发展趋势的相似性对福克纳和中国当代作家催生了相似的心理状态和文学追求,这影响了中国创作界对福克纳的认同与接受。
最后,创作者个人与福克纳有共同的文学追求与审美取向。在创作内容上,他们都致力于对人性的发掘以及对影响人性变化的生活的展示。福克纳一直都将表现人性视为创作的第一要务。他曾说:“我主要是对人感兴趣,对与他自己、与他周围的人、与他所处的时代和地域、与他的环境处在矛盾冲突中的人感兴趣”[4],所以作为作家,尤其是渴望成为作家的青年人应该集中精力探索人性的奥秘。他如是说,也是如是做的,从第一部小说《士兵的报酬》到收关之作《掠夺者》,福克纳无一不是在暴露形形色色的人性,有好的,但更多的是对失落的人性的探索。而造成人性失落的原因则是福克纳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同其他许多南方作家一样,其作品“深刻地反映出在社会巨大变革冲击下人们在旧的意识形态解体过程中的痛苦和思考,它所涉及的不仅是生活方式、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念、精神面貌。”[5]因此,人所处的生活环境对人性的变异产生了怎样巨大的影响作用成为了福克纳作品中重点表现的一个方面。“他以浓重的笔墨描写‘约克那帕塌法县’的演进,再现出南方的兴衰史。……他笔下的美国南方历史是人类经历的一个缩影。”[6]而关注历史和历史中的人成为福克纳笔下的重要命题,但是他的探索却又绝对不是单纯地对他所熟悉的南方社会的探索,他实际上是在寻找人类的本质。
中国创作界中的许多作家也与福克纳有着相同的审美诉求。莫言、余华和赵玫不仅赞同福克纳的创作观念,而且他们自己在创作中也刻意寻求对人性以及现实与人的关系的表达。莫言的《红高粱》用“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率性行为批判与反思现代人的种的退化与人性的脆弱;而余华的《现实一种》所显现出的那种人性的冷漠更让读者不寒而栗;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则表现了女性所受到的人性压抑。这些从不同角度出发对现实生活的探讨不仅有关人性,更重要的是对当下生活的反思,正如福克纳对人性的考察也是为了展示现代化文明对南方古老传统的冲击一样。因此,中国创作界与福克纳又产生了相似点。这种相似令中国创作界欣赏并接受福克纳,甚至借鉴和融合他的文学思想与观念。
另一方面,在创作形式上,这些中国作家都追求形式的创新与实验,起到了先锋作用。作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福克纳将意识流这种题材运用得炉火纯青。在《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通过这种文本构建方法将白痴等人错乱复杂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又不失表达上的逻辑性。为了将每个人物的心理流动都完美完全地展露出来,福克纳还多次使用多角度叙事的创作方法。在《我弥留之际》这部篇幅不长的长篇小说中竟然出现了十五个人物的心理独白,这些不同角度的心理独白共同帮助福克纳完成了对真实生活的表达。此外,福克纳喜欢用结构构筑意义,令处于不同层面的故事在交汇时产生更多的意义。意识流式的表达和多角度叙事是福克纳在形式实验方面比较成功且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手法,同时这些实验性的创作也成就了福克纳,使其跻身于现代派的代表作家的行列。中国部分作家也希望在形式方面有所突破,许多人选择了拜福克纳为师,仿效并吸收福克纳的创作技巧。莫言的《檀香刑》、余华的《兄弟》以及赵玫的《高阳公主》等作品就分别吸取了福克纳的不同表现手法。比如在《檀香刑》中,莫言就使用了多角度叙述,故事是由六位叙述者共同讲述完成的。又如赵玫的《高阳公主》,整部小说中穿插了大量的主人公的心理活动。除此以外,贾平凹也是如此,他从未停止过在创作形式上的实验与探索,他的《秦腔》中疯子引生的第一人称限制性叙述让我们一下子就想到了《喧哗与骚动》中白痴班吉的表述。这种在心理上对文学观念的认同以及在实践中对写作手法的仿效推动了这些作家对福克纳的接受。
由上观之,中国创作界接受福克纳时在时代背景、文学环境和个人追求等方面有高度的契合点使中国创作界对福克纳的接受成为一种必然。
二、主题的相合
中国创作界认同福克纳的创作观念,并积极地借鉴和学习,进而将受到的影响潜移默化到自己的作品中去。在这一接受过程中,这些作家接受福克纳时在文本中显示出许多相似性,他们的文本中分别传达出与历史意识和苦难意识等内容相关的东西。这不是福克纳接受中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必然选择。
福克纳关注人、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环境,为了最大限度地阐释自己的思考,福克纳利用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以小见大”,将自己对历史的理解置于区域性的生活之中,将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理体验和人生经历投射到美国南方那块难以割舍的地域之上,“始终背负着沉甸甸的南方历史感和文化意识”[7]。通过对约克纳帕塔法县中的人们为了生存与进取所作的努力和挣扎进行的描述,福克纳重现了人类生存的历史图景。他一生都致力于描写南方,在他创造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王国中,康普生、麦卡斯林、塞德潘、沙多里斯和斯普诺斯五大家族的悲喜人生交替上演。福克纳笔下的南方历史是通过个人化、内隐化和象征化进行表达的①虞建华曾指出福克纳小说的历史意识的表达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南方的历史通过个人化进行表述,比如从某一家族成员的视角发现家族史的某一侧面,进而折射出区域历史的进程;二是南方的历史通过内隐化表达,比如历史的压迫和负重,在其小说中表现为人物焦躁的情绪、突发的暴力和怪异的举止;三是南方的历史通过象征表达,比如《喧哗与骚动》中的昆丁将家族或南方的没落与妹妹的失贞联系在一起。具体参阅《历史与小说的异同:现实的南方与福克纳的南方传奇》,载《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6年第5辑,110页。,因此其历史意识更多地带有南方地域的文化和心理的色彩。这样一种混合着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历史意识使福克纳的作品流露出对逝去的传统无法挽留和延续的失望与痛苦以及对历史无法改变和抗拒的无奈与绝望。如《喧哗与骚动》中的昆丁,他因为无法留住时间和保住妹妹的贞洁而最终绝望地选择了自杀,他企图以这样的方式来阻止历史的前进,这当然是徒劳的。福克纳借此表达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悲观不安的情绪,以及时间的不可抗拒和历史的不可阻挡。
中国创作界也像福克纳一样对历史意识进行了自己的独特解读。同福克纳一样,中国创作界也选择了将历史放置于区域性的生活之中。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余华的南方小镇和苏童的风杨树等都表达了特定地区中的人及其生活,并传达出浓厚的历史意识。他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文学选择,原因之一就是由于福克纳的影响。在这一方面,莫言最具代表性,他的高密东北乡就是受到了福克纳的启发。他曾说“读了福克纳之后,我感到如梦初醒……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尤其让我明白了,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受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启示,我大着胆子把我的‘高密东北乡’写到了稿纸上。”[1]40因此,莫言在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中第一次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一字眼,开始了他的家乡系列小说的创作之旅。虽然像福克纳一样,莫言也选取了通过区域性的故事来展现自己对历史的态度和思考,选择了返回历史与民间,然而其中也有不同之处,福克纳的返还更添一种对必然走向没落的旧南方的留恋之情,对破败与衰亡的描写是福克纳为旧南方献上的一曲悲怆的挽歌,而莫言的返还则是试图重新寻回民族的精魂。前者的历史充满了消极的情绪,后者的则是乐观的。福克纳不仅帮助莫言发现了“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帮助他完成了寻根文学运动的过渡。中国文学是以寻根文学为分界线开始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文学从文以载道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走向了更为纯粹的审美立场。福克纳的小说鲜有明显的政治批判的痕迹,更多的是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出发,在描画历史中探索对生活和人性的表达。他把他对人生与人性的认识都融入到了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历史与生活之中,他通过强化文本中的历史意识来表达对人类灵魂的终极关怀。在福克纳的历史意识的影响下,莫言的文化认知和文化批判也从历史的立场出发,他将高密东北乡的历史与文化交融在一起,讲述了一个个的民间传奇故事。
这种接受有其出现的必然性成因,而这一成因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的乡土文学传统密切相关。一方面,费孝通的关于“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8]这一对中国性质的判断早已为世人所公认,而这种乡土性质也对文学产生了影响。不仅促使作家创作乡土小说,也在接受外来文学时会更易倾向接受具有乡土因子的文学。另一方面,自五四以来,鲁迅就开创了中国作家创作乡土小说的传统,使其之后的许多作家都关注乡土文学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中国创作界的文本与福克纳的作品一样,其中都充满了对苦难的表达。与苦难的生活相左的是暴力、死亡和性等,这些极端的生命状态表达了福克纳对美好人生的强烈向往。由此观之,福克纳在创作时也受到了反向作用心理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创作界会接受他的原因,因为在创作时出现了共同的心理倾向。福克纳揭露南方的罪恶,不是因为他恨这片土地,但他却偏偏描写了南方的诸多的不美好之处,这正是因为太过热爱,他才会不惜一切地暴露其短处,进而唤起固执的人们将家园建设得更好。关于对待苦难的态度福克纳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忍受苦难是非常重要的核心点。在福克纳看来,忍受苦难是人的一种优秀品格,显示出了人性的坚忍与顽强。“福克纳在其所有作品中都关注人类能够忍受什么、敢于做什么、能够完成什么这样的问题”[9]。在小说《我弥留之际》中,福克纳就集中笔墨描写了人类可能遭到的大部分苦难与痛苦,比如洪灾和大火这样的天灾,还有生老病死伤残孕育等产生的疼痛。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人类必将战胜一切险阻的坚定信念。《喧哗与骚动》也同样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尽管它更多的是在揭示奴隶制必将走向毁灭、资本主义工商业兴起的历史必然趋势,但是最后一部分的叙述者女仆迪尔西却表现出了坚韧顽强的品质,她是摇摇欲坠分崩离析的康普生家族中唯一散发温暖的人。最后这个家族变得破败不堪,但是迪尔西这一人物却传递出作者仍留有希望的心情,迪尔西身上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可以抵抗困难生活并获得新生。
中国创作界也充分探讨了关于苦难的内容。在这方面,余华对福克纳的接受最为突出。像福克纳一样,余华也着力表现人所遭受的苦难,在他的后期作品中这一点尤为突出,如《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等就都将关注点投射到了人民苦难的生活上,同时也突出表现了人在逆境中的顽强。《活着》的主人公富贵经历了丧母、丧妻、失女,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等多种悲惨的事件,在每一次重温温情的时候都会面临失去亲人的痛苦,即便命运如此作弄富贵,但是他没有被击倒,而是坚强地活了下来。余华意在强调对于苦难要学会忍耐,活着就是一切。在忍受苦难这一点上,余华与福克纳极其相似,使得余华特别对福克纳的写作手法赞赏有加。因为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正是源于同样的内容表达的需要,才出现使用相同表达形式的文学实践。余华正是这样积极学习并运用了福克纳的一些创作手法。对福克纳的接受不仅令余华成为了先锋文学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同时也帮助余华在90年代实现了他文学创作上的转型。
三、手法的相似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创作界正处于转型时期,单纯的社会历史审美早已不符合他们的创作观念,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不能满足他们对文本表达的需要,多年以来被压抑的文学文本渴望进行发自内心的真实倾诉,文学“向内转”成为一种趋势,对外部社会的写实表述渐渐转向对内部心灵世界的描摹。因此,对新鲜话语表达模式的追求也随即成为主潮,如何表达内在的心灵世界成为中国创作界一部分作家的文学使命。在外国文学和文化的冲击下,福克纳的诸多实验性创作手法成了作家们借鉴的对象。学习福克纳的写作方法和技巧变成了一些中国作家有意识的实践追求。因此,中国创作界特别关注福克纳作品中有关心理描写等方面的叙事手法,进而将其融会贯通到自己的创作中去。这里将以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檀香刑》、余华的《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以及赵玫的《高阳公主》等作品作为文本依据,具体论证中国创作界对福克纳在形式技巧方面的接受。
意识流是福克纳小说创作中的重要题材之一,①李维屏在其讨论英美意识流小说的专著《英美意识流小说》一书中指出,“在现代小说中,意识流是指小说的内容或题材(the subject matter),而不是指创作技巧或作品本身,所以不能混为一谈”。具体参阅李维屏《英美意识流小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5页。而多角度叙事则是福克纳创作中最具特色、运用得最成功的带有实验性的文本建构方法之一,它们使作为作者的福克纳跳出了作品,最大程度地还原了人物的心灵世界;使人物可以自由地表达真实的内在情感。李文俊在其早期的评论文章中曾指出:“福克纳是人的内心活动的挖掘者和表现者。……在许多情况下,他是通过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来塑造人物与表现时代精神的”[10]。
这种成功的文学实践恰巧契合了中国创作界的文学需求,因此意识流和多角度叙事成为中国创作界在形式方面接受福克纳的主要内容。
福克纳的意识流赋予人物以主观能动性,强调了人物的主体性,即便是一个白痴也有话语权利,也可以尽情地表达自我。《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虽然是傻子,但是他对姐姐凯蒂的喜爱,以及极其不愿让凯蒂失去树的香味的心理都得到了完全的展现。白痴傻子这类人的想法原本是不被人重视的,在一般的作品中,他们都处于失语状态,没有人关心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或者根本没办法知道他们的内在情感。意识流这种叙事手法则解决了这一叙事难题,它成功地把跳跃的思维、流动的心理、杂乱无章的非理性的情感世界呈现出来,并使这一切记忆碎片的拼接变得合情合理。然而反映内在心理并非福克纳的终极目标,通过使用意识流这种题材表现人物的所思所想进而影射出现实境况才是最终的目的。因为“意识流小说的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着重表现西方人的复杂心态与悲观情绪,通过揭示那个痛苦的‘自我’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11]。在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话语权利变相丧失,“有话难讲”是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文本和人性都遭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扭曲和压抑。新时期的到来为心理倾诉打开了一扇窗,而如何表述内心世界、如何将各种苦难的经历和碎片化的记忆杂糅在一起则是作家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福克纳的意识流则恰巧提供了解决的途径,使许多作家都把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作为学习仿效的对象,从而使福克纳在中国的接受成为必然。另一方面,中国创作界对福克纳的接受又并非是简单的植入。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遗传影响,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不可能被完全抛弃,因此从中国最早的意识流手法的实践者王蒙开始,中国的意识流小说就与西方的意识流小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西方的意识流因为受到了非理性思潮的影响,所以有着突出的非理性特征,毫无章法的心理轨迹随处可见,中国的意识流则是具有理性特点的心理流动,思维跳跃的同时也遵循逻辑上的顺序。而“将福克纳的意识流创作方法解释成与以‘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相一致,这种将陌生的‘熟悉化’的解说话语无疑减少了对作品接受的心理难度”[12]。这也是为什么在众多的意识流大家中,福克纳得以脱颖而出并得到了更多的中国作家的仿效的重要原因。
从文本方面具体观之,莫言的《檀香刑》和赵玫的《高阳公主》等多部当代作品都显现出理性的意识流的影响痕迹。《红高粱》选择了第一人称“我”作为故事的叙事者,讲述了“我爷爷”、“我奶奶”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和抗日事迹。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感情线,一条是一起打鬼子的事件线。我的思维在这两条线之间来回跳跃,一会是野性的爱情,一会是民间的抗日。通过意识的流动,叙述者将回忆完全展现出来,还原了故事的全部,也还原了人物的心理。赵玫的《高阳公主》虽然没有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但是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也充分表现了人物的心理。高阳在每次事件中的想法,以及她有关情感的心理变化都在意识流的表现形式中得到了彰显。高阳作为女性,她的命运被操控,人性被压抑,她的内心充满了绝望的反抗情绪,同时她也将想法付诸实践,她摒弃没有感情的丈夫,大胆地向她真正喜爱的丈夫的哥哥示爱,她以行动抗议压在她身上的种种不公平。赵玫细腻地刻画了高阳不停变化的心理状态,塑造了一个在爱欲和命运中挣扎的女性形象,还原了作为人的女人真实的内心世界和情感需要。意识流的功用不仅仅是帮助中国作家找到了表现心理的途径,更为重要的是,“就叙事文学而言,新时期的叙事艺术革命是以‘意识流’这个舶来品为突破口的。站在文学发展意义的角度上,意识流则扮演了中国当代文学叙事艺术由外部社会历史的描摹到对内部意识结构和复杂人性的抒写的历史性转递的角色”[13]。
通过运用多角度叙事这一表达方式,福克纳一方面完成了对创作手法的实验性的探索,另一方面也达成了对故事的真实性的构建。多角度叙事是福克纳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技法,使故事的叙述增加了立体感和层次感。在运用多角度叙事的作品中,故事不再是单一地被讲述出来,而是通过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得到呈现的,像《喧哗与骚动》和《押沙龙,押沙龙!》就都选取了4个人物充当叙述者,在他们或一致或冲突的表述和回忆中,凯蒂与塞得潘的形象得以建立,他们的经历也得到了完整的呈现。作者通过这样一种实验性的叙事革新手法还原了故事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福克纳的另一部多角度叙事的作品《我弥留之际》将这一技法运用得更是淋漓尽致。该书共分为59节,每一节就是一个人物的心理活动,有19个人物进行了内心独白,他们各自从自己的个性视角介绍故事的一个部分,最后共同向读者勾勒出了本德仑一家的故事。这几部多角度叙事的作品在艺术上秉承了福克纳一贯强调的“实验性”,探索了叙述角度的多样化的可能性。它们都没有一个从一而终的叙述者来统摄全局,而且也没有任何描述与介绍性的批注标示与旁白语言,仅仅依靠不同人物的内心独白来构建小说,作品呈现出语言狂欢的面貌。通过这样一种尝试,福克纳探讨了有关真实性的问题,所谓客观的“真实”其实很难保证,但是遵从内心的真实却往往更容易实现。在瞬息万变的历史长河中,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里,历史的真实性其实是建立在内心的真实性的基础之上,要进一步还原真实的历史,首先要做到内心的真实。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正寻求创新,为了挣脱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束缚,许多作家开始转变文学观念,突破了传统小说将重点放在“写什么”上面,转而注重“怎么写”,关注形式的创新,这种文学创作追求后来成了先锋文学的滥觞。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福克纳的影响极大,他的实验性技法为一部分先锋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提供了参考与模仿的范本,多角度叙事被一些作家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如莫言的《檀香刑》和余华的《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等。像福克纳一样,莫言也尝试用不止一位叙述者来讲述故事,在《檀香刑》中,他设计了6位。但是莫言的多角度叙事不似福克纳那般彻底,并非通篇都是人物独白。在《檀香刑》中只有开头和结尾两部分使用了多角度叙事方法,而作为主干的第二部分仍是通过传统的第三人称叙述来完成的。莫言使用多角度方法是为了弥补客观叙述的不足,做到外聚焦与内聚焦相结合,达到既有客观的事件描述、又有主观的心理独白的目的,进而呈现更完整更真实的故事。在《檀香刑》中,莫言传达出这样一种观点,故事的真实性并非来源于外在世界的表象,每个人内心的所思所想才是真实的所在。余华的《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的多角度叙事虽然也受到了福克纳的影响,但是又与福克纳不一样,与莫言的也有所不同。在这个短篇小说中,读者通过仔细阅读,可以看出故事具有三个层次:一是“我”遭遇了一系列事件,如车祸、手术、遇见外乡人,以及我的梦境中的女孩;二是外乡人患了眼疾之后移植了因车祸死亡的少女杨柳的眼球;三是由外乡人转述沈良讲过的有关谭良和10个定时炸弹的故事。余华通过多角度叙事以及频繁地转换视点使得这三个层次相互穿插在一起,常常令读者分不清叙述者是谁,事件的时间顺序完全被打乱,由此作者构建了一个叙事迷宫。余华正是通过这种非理性的没有结果的叙事完成对真实性的探讨。真实性正是存在于非理性之中,反而观之,理性的世界中其实并无真实可言。由此,余华以其先锋的姿态抨击了现实的不可靠性。然而,太过非逻辑的叙事也使得余华的小说形式有余而深度不足,这一弊端在余华90年代的转型创作中得到了改变。
综上所述,福克纳关于构建自己的文学王国的创作观念以及对新的写作手法的探索与尝试都得到了中国创作界的关注。而这一接受有其必然性成因,即社会历史的外在变迁、文学发展的内在需求、本国文学传统的承继以及作家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文学追求的相似使中国创作界和福克纳之间形成了接受与影响的关系。这一接受的结果使中国当代文学顺应了时代的抒发心声的需求,也促进了当代文学进程的演进,并且与西方乃至世界文学更加靠拢与融合。
[1]莫言.小说的气味[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
[2][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32.
[3]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4-9.
[4]FAULKER W.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Gwynn,Frederick L and Blotner,Joseph Leo,eds[M].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Virginia University Press,1995.
[5]毛信德.美国小说发展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319.
[6]常耀信.精编美国文学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208.
[7]虞建华.历史与小说的异同:现实的南方与福克纳的南方传奇[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6,(5):104.
[8]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1.
[9]BROOKS C.William Faulkner:First Encounter[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94.
[10]李文俊.约克纳帕塔法的心脏——福克纳六部重要作品辨析[J].国外文学,1985,(4):20.
[11]李维屏.英美意识流小说[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15.
[12]查明建.意识流小说在新时期的译介及其“影响源文本”意义[J].中国比较文学,1999,(4):68.
[13]吴锡民.意识流:转递中的中国当代叙事艺术之反省[J].江苏社会科学,2003,(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