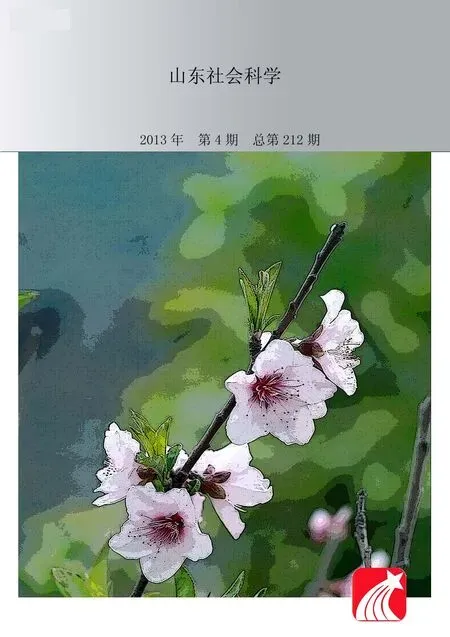论阿多尔诺否定的道德哲学构想
2013-04-07周爱民
周爱民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伴随着当代实践哲学的转向,阿多尔诺的道德哲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针对阿多尔诺否定的道德哲学思想,人们发出这样一种普遍的质疑:否定的道德哲学能否为我们提供某种规范?或者说它在何种意义上能够为我们提供某种规范?如果把阿多尔诺的道德哲学置于当代规范伦理学的讨论框架中,我们确实很难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即使从他著作的片断表述中我们或许能够寻找到某种肯定的答案,但这也可能会误解他的道德哲学。在此,我们不想在当代规范伦理学的语境中继续展开这一讨论,而是把阿多尔诺的道德哲学置于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比较中,即从亚里士多德的肯定的道德哲学与阿多尔诺否定的道德哲学的比较中,具体探明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宣称道德哲学必须具备否定性的维度。本文将首先从“道德”(Moral)与“伦理”(Ethic)的区分入手来考察亚里士多德与阿多尔诺的道德哲学中的核心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指出,尽管阿多尔诺拒斥使用“伦理”概念,但他使用的道德概念其实与亚里士多德使用的伦理概念所要处理的问题仍是相同的,他们的区别仅在于解决问题的视角不同。最后,我们将具体指出怎样的理论因素最终决定了这种视角的差别,以及阿多尔诺否定的道德哲学将面临怎样的问题。
一
在论及如何准确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时,邓安庆教授指出:“在我们日常的意义上,伦理学是研究是非善恶的道德学问……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现今日常用语中关于道德或伦理的用法,就无法理解这部著作。”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正如邓教授强调的,在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时,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个文化史的事实,即古希腊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Moral)一词。亚里士多德所使用的“伦理”(ēthos)一词,远比现代道德一词内涵丰富得多。因此对这两个概念作些考察就显得非常必要,它将是理解阿多尔诺否定的道德哲学的理论前提。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中,亚里士多德把伦理学的最高目标定义为追求至善。他认为人类每种活动都有一定的目标、意图或目的,它们就是各种各样的善。他坚信一定存在着“纯粹因其自身之故而被追求”最高的善,其它各种因其自身之外的原因而被追求的善都以它为最终目标。由于亚里士多德认为无穷后退不可能,因此这种至善必然存在。正如西季威克所指出的,如何确定最高的善与其它种类善的关系是希腊思想家们自始至终所争论的问题。[注][英]亨利·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128页。
亚里士多德断定这种至善就是幸福。这里的幸福不是一般所理解的“某种抓得着、看得见的东西,例如快乐、财富或荣誉”,相反它们都最终以追求幸福为目的。[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3-44、53-54页。那么幸福究竟意指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论述存在一定的张力关系。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一章中,他在粗略考察了三种不同的生活形式中的前两种后,即追求享乐的生活和政治的生活,认为尽管在政治的生活中德性被认为是最终的目标,但德性自身并不完满。一方面拥有德性的人甚至一辈子都不实行它;另一方面拥有德性的人也会遭受困难和最大的不幸。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被称为幸福的。而到了该卷第六章中,它把幸福规定为“灵魂合乎最杰出、最完善的德性的活动”。[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在此,幸福与德性的实现活动被等同起来。然而当我们仔细考察了他对灵智与明智的区分,进而在此基础上展开对合乎德性的生活与思辨生活的划分后,我们才能真正把握这种张力关系。
在该书第六卷第六章中,亚里士多德对灵智的界定只有寥寥数语,但是他的表达是清楚的,即灵魂中只有灵智是与科学的第一原理相关的,其它的都与此无关。关于明智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则花了相当大的篇幅。他所说的明智主要是指一种实践智慧,“它是在涉及对于人或好或坏事情上的一种与正当的尺度相联系的行动的品质”。[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页。在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明智不是仅仅从个人的角度权衡某种事情对于自己的利弊,而是同时也要具备权衡整个城邦利益的视角,所以他认为“说一个不懂得如何齐家治国的人却懂得处理好他自己的事,这也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页。
灵智是人类灵魂中最高贵的部分,这种最高贵部分的实现的活动就是思辨活动。但由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观,他认为这种活动不是人之为人的活动的全部,人性中还包含其它的组成部分,如情感、欲望等。因此,这种活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似乎只是一种理想,是我们要不断地朝之努力的方向,但作为人而非神,我们永远也无法达到。与这种神性的活动相对应的就是人的活动,也就是人的伦理德性的完满实现,明智与此相关。虽然明智属于理智德性,但它与伦理德性密切相关,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德性因为明智才变得有序。[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46页。那么人的幸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这些组合而成的整体的德性的完满实现。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政治生活中的德性不能与最高的幸福相等同,因为这种活动并不是灵智的活动,它至多涉及到明智。而“灵魂合乎最杰出、最完善的德性的活动”就是灵智的活动,也就是思辨的生活才是最高意义上的幸福。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伦理概念所包含的核心意蕴就是探讨什么是最终的善,或者说什么是最终意义上的好生活。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就是一种目的论的伦理学。如利科指出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概念与近代意义上(以康德为代表)道德概念的差别就是目的论与义务论的差别。[注]Paul Ricoeur,Oneself as Another,trans.Kathleen Blamey,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2,pp.170-171.
在《道德哲学问题》中,阿多尔诺却坚决拒斥这样的伦理概念,主张使用道德哲学而非伦理学。他认为“伦理”一词明显是对道德领域所发生的问题的回避,他的论证主要分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阿多尔诺认为由于道德一词是从拉丁词“mores”演化而来。“mores”的本意是指某种处于一定历史地理环境中的集体所形成的风俗习惯。在德语中与之对应的就是“Sitte”,因此关于道德的哲学在德语中也被称为“Sittenlehre”,即关于“Sittlichkeit”的学说。这其中包含了一种和谐假设,即个体的正确的生活能够依赖于这种共同的规范。
其次,由于道德首先意指一种特定共同体中由于历史地理因素而形成的风俗习惯,它本身也就包含着特定的历史性因素。那么显然,如果与之对应的历史共同体瓦解的话,这种风俗也一定会相应地受到影响,或者说,如果这种普遍规范所依赖的实体性内容不存在的话,那么个体正确的道德生活便无法再依赖于这样的道德规范,由此就会导致这种道德规范与个体之间产生一定的张力关系。阿多尔诺认为当今的社会状况就已经反映了这个问题,即共同体的力量膨胀到我们常常必须被强制地与共同体保持一致。因此,坚持在这种意义上使用道德概念时,我们必定会遭遇这种张力关系,用阿多尔诺的话来说就是个体与普遍之间的张力关系问题。[注]Theodor W.Adorno,Problem der Moralphilosophie,Frankfurt/M.:Suhrkamp1996,S.33.
最后,如果人们用伦理概念取代道德概念的话,以上的张力关系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被悄悄地遮蔽了。阿多尔诺认为从希腊文ēthos演化而来的“伦理”(Ethik),在一般意义上指的是“本性”(Wesensart),与此非常接近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品质”(Charakter)。它们都是指一种正确的生活或好生活就是使我们的本性或品质完全实现出来。只要我们按照我们自身的本性或品质去行动,使之完全实现,那么我们就达到了一种正确的生活。在此,我们关注的仅是个人的自我实现,而非个人的实现与他人、社会之间的张力关系。因此,阿多尔诺认为个体与普遍之间的张力关系在此就被完全回避掉了。[注]同时,阿多尔诺也强调这种纯粹的自我同一性就是一种死亡。See Theodor W.Adorno,Metaphysics:concept and problems,ed.Rolf Tiedemann,trans,Edmund Jephcott.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08-109.由于阿多尔诺的辩证法主张直面矛盾,对矛盾本身展开分析,他必然强调用“道德哲学”(Moralphilosophie)取代这种意义上的伦理学。
这里需要注意阿多尔诺所谈论的道德与康德意义上“道德”(Moral)用法的差别。在《道德形而上学探本》中,康德虽然认为古希腊把“EthiK”划为哲学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是正确的,但他把“Ethik”理解为关于自由的法则的学说,它也可被称为“Sittenlehre”。显然,康德已经改变了古希腊意义上“Ethik”的含义了。康德对“Sittenlehre”又作了进一步的划分,即划分为形而上学的部分和经验的部分,前者称为道德(Moral),后者称为“实用的人类学”(practische Anthropologie)。排除了经验部分而只对“Sitten”的形而上学部分进行考察被康德成为“Moralphilosophie”。[注]Immanuel Kant,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Hamburg,F.Meiner 1999,S.3-10.然而,阿多尔诺在使用“道德”(Moral)时则主要侧重作为普遍性的道德规范与它的历史性内容之间的张力关系,他认为道德哲学就是对这种张力关系的分析。
但现在的问题是:坚持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伦理概念是否就意味着个体与普遍之间的张力关系会被遮蔽掉呢?
二
《尼各马可伦理学》确实很少触及阿多尔诺所阐发的在一种错误的社会中个人如何过正确的生活问题,但这并不表明亚里士多德只从个人出发谈论人自身的自我实现问题,因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伦理学只是政治学的一个部分。这表明,在亚里士多德意义上谈论伦理必然要与个人在城邦中的实践活动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个人德性的实现必然与城邦的构成相关。因此麦金泰尔强调,只有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语境中,我们才能正确理解他的伦理学。[注]Alasdair Macintyre,Rival Aristotles:Aristotle against some Renaissance Rristotelians,in Ethics and Politics,selected essays,Volume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3-26.
个人与城邦之间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柏拉图《理想国》所谈论的核心问题。柏拉图认为要认识什么是正义,或个人怎样做才是正义的问题,就必须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城邦的正义。[注][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7-58页。从亚里士多德对个人与城邦之间关系的论述来看,他并不认同柏拉图的诸多结论,但两人所强调的个人的德性只有在一个好的城邦中才能得以实现的观点却是相同的。那么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好的城邦是一种怎样的城邦呢?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继续沿用了《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关于善的讨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各有一善,这种善就是它们各自追求的目标,那么城邦也有自身所追求的至善,它的目的就在于追求最优良的生活。因为城邦是由人构成的,而人的最终目的在于获得幸福,所以城邦就必须确保其公民获得最高的幸福。亚里士多德进而认为这种幸福的获得只有在最优良的政体当中才存在最大的可能性。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把好的城邦等同于优良的政体,他认为理想城邦的建构只能在优良政体之中才可能。亚里士多德对优良政体的论述围绕两个维度展开:第一,存在于理想城邦中的理想政体。就理想政体中的公民品德而言,这又分为两种情况。如果这个理想城邦是所有自由人组成的联合体,即公民都是善人,那么善人的品德就是好公民的品德。一个善人(好公民)就应当具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个方面的才识,即“他应该懂得作为统治者,怎样治理自由的人们,而作为自由人之一又须知道如何接受他人的统治”。[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7页。否则即使是理想城邦,拥有一个最良好的政体,好公民的品德也是不需要完全等同于善人的品德的,这是由每个公民不同的职分所决定的。例如,明哲此时就是统治者应当具备的品德,而“信从”则是被统治者应当具备的品德。[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8页。第二,就现实的城邦生活可以实现的最好政体而言,亚里士多德首先区分了政体的类型,[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78页。随后他根据其伦理学的观点指出,现实城邦中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优良的政体。从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来看,在这种政体下,中庸就是善德的表现,公民的中庸与节制使其可以顺从理性。由于政体是尽可能由相等而同样的人们组成,城邦团结而又平安。
综上所述,理想与现实中的优良城邦均需要公民具有一定的善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德源于天赋、习惯与理性三端,公民可以经由自己习惯的训练养成一部分才德,这部分才德构成了建立优良政体的基础。另一方面,在理想的优良政体中,立法家可以通过教育方针的制定,对公民进行理性方面的启发和引导,从而使公民养成另一部分的善德。这是由于最优良的政体就是一种善的城邦,以促进善德为目的,而这种城邦集体的善肯定内含各个个别的善德。[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90-391页。从这一角度看,亚里士多德对城邦与个人之间关系的分析具有一种辩证的结构:一方面,城邦的善只有在公民的善德基础上才可能;另一方面,公民善德的养成也需要在善的城邦之中才可能。
那么从何种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对伦理的阐发最终遮蔽了个体与普遍之间的张力关系呢?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明显看到,他对城邦的善与个体的善的界定都是从一种目的论的视角出发的。从这种目的论的视角出发,公民与城邦之间在最终目的上是一致的,不存在相互的敌对状态。因而,公民的德行与城邦制度安排之间的张力关系就被排除出主要的讨论范围之外了。例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民品德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专职品德与共同品德。[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3页。专职品德是每一个公民在城邦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承担的不同职分决定的,因而公民在专职品德上是存在差异的。共同品德则是特定的政体对其全体公民的要求。亚里士多德假设在优良的政体中专职品德与共同品德二者是统一的,不会出现张力关系。但在我们看来,即使在最优良的政体中二者之间也会出现一定张力关系。因为在最理想的城邦之中,亚里士多德也坚持认为这种城邦的维系需要所有人各司其职,公民的品德就在于努力完成自己的职位,然而每种职位所要求的各种品德是各不相同的,即使它们并不相互矛盾,但由于人们坚守自己的职位发挥自己专职品德时,一种共同的品德或一种普遍的品德就很难形成。卢卡奇对物化劳动的详细阐发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注][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48-152页。另外,在一种恶的城邦之中,即使人们仅仅发展自己的专职品德也会是一种恶,在此意义上,汉娜·阿伦特把它称之为一种“平庸的恶”。[注][美]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是明显注意到个人与普遍之间的张力关系的,在此意义上他的伦理概念与阿多尔诺的道德概念所要处理的问题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二者的不同仅在于解决问题视角的差异。由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的形而上学观限制着他,使他只能从肯定的方面建构个体与普遍之间的关系;而阿多尔诺的形而上学观则把他导向了一种否定的道德哲学,即从否定的角度解决个体与普遍之间的张力关系。
那么,阿多尔诺的形而上学观究竟如何直接导致他采取了区别于亚里士多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呢?对此问题的回答直接涉及到道德哲学在何种意义上必须具备否定之维。阿多尔诺的论述与他对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有关。我在下文将指出,若阿多尔诺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是合理的,那么他就能在此基础上宣称道德哲学必须具备否定之维。
三
早在《哲学的现实性》中,[注]该文已由复旦大学王凤才教授译出,目前尚未发表(据悉,将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本文对其有所借鉴,在此表示感谢。阿多尔诺就已经表达了对宣称能够把握总体现实存在的哲学的失望。他断言任何哲学都不能够把握现实总体。当然这不是一种独断式的宣言。在该文中,阿多尔诺考察了新康德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等20世界上半叶诸多哲学思潮。他认为这些思潮在把握现实总体方面最终都失败了。例如,被他推崇的现象学也被认为存在着最深层的矛盾,即用主体哲学相同的范畴去努力赢获它曾经所反对的用这些范畴所达到的客观性。在阿多尔诺看来,这个矛盾导致胡塞尔只能以先验观念主义为起点,理性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最终只能诉诸“理性的判决权”(Rechtsprechnung der Vernunft),尽管他认识到不可推论的给予性(unableitbaren Gegebenheit)概念的重要意义。[注]Theodor W.Adorno,Gesammelte Schriften Bd.1-Philosophische Frühschriften,Frankfurt/M.:Suhrkamp 1973,S.327.英文翻译参见,The Adorno Reader,ed.Brian O’Connor,Blackwell,2000,p.26.
通过对这些哲学思潮的批判性考察,阿多尔诺认为哲学在当代的可能性就在于它是一种解释(Deutung)。这种解释不是赋予对象以“意义”,也不是呈现对象世界背后的本质世界的过程,而是像解谜一样,通过对象的不断组合、排列使现实自我呈现的过程。“真正的哲学解释不是偶遇一种早已位于问题之后的固定的意义,而是顷刻之间照亮它,并同时毁灭它。”[注]Theodor W.Adorno,Gesammelte Schriften Bd.1-Philosophische Frühschriften,Frankfurt/M.:Suhrkamp 1973,S.335.等待解释的问题的答案并非像传统哲学中躲在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世界,而是已经寓于问题之中,问题本身已构成答案,后者被找到前者也就同时消失。很显然,阿多尔诺是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它所包含的理念世界的思想。
这种批判在其《形而上学:概念和问题》中得到进一步具体的发挥。在其中,阿多尔诺认为形而上学真正的发端肇始于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主要特征在于其肯定性,也就是说,通过形而上学,存在不再被当做我们理性或概念无法把握的东西,概念本身就已经是存在的诸多范畴。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就是一种本体论,“本体论作为存在的基本的构成性概念只是意味着思维的基本结构被提升到存在的诸范畴”。[注]Theodor W.Adorno,Metaphysics:concept and problems,ed.Rolf Tiedemann,trans,Edmund Jephcott.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99.它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表述为,具体的质料是无规定性,单独通过这些质料,我们无法形成真理性认识,真理性的认识必须依赖于一定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内在于质料当中,它是质料朝向其运动的最终目的,质料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内在于其中的形式。所以,阿多尔诺认为“正是理念或者本体的理智的领域比经验的领域更现实的观点形成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核心”。[注]Theodor W.Adorno,Metaphysics:concept and problems,ed.Rolf Tiedemann,trans,Edmund Jephcott.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37.相对于神学,形而上学的批判性在于,虽然物质世界内含着朝向一种更高意义的存在,但是这种合目的性能够被理性所把握,在根本意义上理性的诸范畴与存在是同一的。
然而,阿多尔诺认为,不可改变的就是真实的并具有实体内容,而流变则是低级的、可鄙的、欺骗性的,这种从柏拉图以来的观点,在当今社会中,从一种辩证的立场看,应当被抛弃。他认为如果按传统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奥斯维辛以及诸如此类的伤痛,我们就是非人性的,即“断定生存或存在自身内就有一种积极的意义并且朝向一种神圣的原则在面对这些受害者和他们遭受的无穷的痛苦时将是一种纯粹的愚弄”。[注]Theodor W.Adorno,Metaphysics:concept and problems,ed.Rolf Tiedemann,trans,Edmund Jephcott.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01-102.因此,在他看来,形而上学的意义世界与内在物质世界的和谐已经被打破,如果继续宣称我们拥有一个有意义的目的世界将是一种意识形态欺骗的手腕。
阿多尔诺强调,对待形而上学的这种态度,不光是面对苦难的一种主观的情感反映,它同时具有一定的客观内容。这种形而上学的经验在当代社会中所对应的客观内容就是:在现代生产逻辑下,任何个体都是可替代的、无足轻重的;虽然我们具有一定的形式民主,但是整个社会都以普遍性的名义被操纵在少数人手中,社会的强制从表面上看并非是某个个体强加于我们之上的,因为我们无法找到施加强制力的个体,我们面对的总是普遍的大众。[注]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philosophical fragments,ed.Gunzelin Schmid Noerr,trans.Edmund Jephcot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24-126.个体的无助不仅体现在这种社会结构中,而且也体现在社会运行所遵循的客观原则当中。这种原则从根本上剥夺了我们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体验。随着启蒙祛魅进程的展开,一切承载意义的对象都被消融进主体自身,启蒙凭借着内在性原则,一切客观性都被纳入主体之中,这样的主体仅仅是抽象的、空洞的自我同一性。在现代社会中,主体的这种抽象的自我同一性原则被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称为“自我持存”(Selbsterhaltung)原则。如若任何人宣称在自我持存原则之外仍然有某种更高的意义世界,或者这种抽象的原则之外仍然有它无法包纳的生活内容,他将不仅被排斥,而且在由这种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中他也将无法存活。[注]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阿多尔诺对此作了生动而精辟的分析,See Theodor W.Adorno,Minima Moralia:reflections on a damaged life,trans.E.F.N.Jephcott,Veso,2005,pp.21-24.
正是对形而上学和现代社会的这种批判,阿多尔诺坚信任何忽略这些维度进行形而上学式的慰藉都将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操纵。因此,在这种错误的社会中,宣称一种正确的生活能够直接被给予我们的道德哲学也将是虚假的。在这一层面上,阿多尔诺认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在此,阿多尔诺并非宣称反对一切文化、一切道德规范,而是要强调,在面对奥斯维辛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应该反思一种正确的生活是否可能。这种反思并非试图重新提供某种理想,而是考察我们是否以及为什么要在一种苦难的生活中继续生活下去。[注]Theodor W.Adorno,Metaphysics:concept and problems,ed.Rolf Tiedemann,trans,Edmund Jephcott.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10-111.在阿多尔诺看来,道德哲学因此将致力于:“奥斯维辛和所有与此类似的一切不应再次发生”。[注]Theodor W.Adorno,Metaphysics:concept and problems,ed.Rolf Tiedemann,trans,Edmund Jephcott.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10-111.阿多尔诺认为这是道德哲学唯一的一个绝对命令。这个绝对命令就像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无法通过逻辑的论证得来,但是他不认为这样的绝对命令是一种非理性主义或者一种直接给予我们的自然法则。尽管如此,这种绝对命令仍然面临着规范性基础何在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规范性基础是什么,它如何能够为自身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我们将在下文对此具体展开论述。
通过以上的说明,我们已经阐明了形而上学在现代社会的遭遇,换句话说就是传统形而上学在现代社会的失败,使得阿多尔诺在理论上彻底反对它。正是这种反对,导致他与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肯定的道德哲学传统分道扬镳。如果阿多尔诺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以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界定是准确的话,那么在此层面上,他把道德哲学界定为否定的,即对一切遭受苦难的人、一切社会的恶的一种扬弃就是合理的。
四
为了准确把握阿多尔诺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合理地提出区别于康德的新的绝对命令,我们必须再次回到阿多尔诺的哲学,不过他是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展开相关讨论的。阿多尔诺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论述,与他对形而上学的论述始终保持着一致性。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知道阿多尔诺坚持概念与对象的非同一性,在对理论与实践的论述中他同样坚持认为,理论与实践应该保持一定的张力关系,在道德行动中尤其如此。
当然,阿多尔诺晚年对此问题的思考与他青年时期的论述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虽然他的核心思想基本保持终身未变。在《哲学的现实性》中,他强调解释哲学所获得的答案不仅是在理论上取消问题,而是最终要通过实践来完成,即哲学解释最终要导向实践,而在《道德哲学问题》中,他却对这种关系重新进行了论述。
首先,他区分了实践(Praxis)与日常意义上的实践(Practischen)的区别。他认为道德实践(Praxis)概念是指康德意义上的“我们如何去做”,而不是我们如何灵活地处理各种事情的实践(Practischen)。然而,阿多尔诺认为即使“我们如何去做”的实践也会在现实中容易以一种歪曲的形态呈现出来,即过度强调行动的层面而忽视理论的反思,甚至放弃思想。在此意义上,阿多尔诺坚决反对简单的行动主义,在他去世前创作的最后一篇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文章中,他甚至激进地认为,思想就是一种行动,理论就是一种实践形式。[注]Theodor W.Adorno,Critical Models: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trans Henry W.Pickfor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297.
其次,在道德行动中,即使正确的理论反思也无法确保行动就是道德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阿多尔诺认为这种距离是由道德实践的本质决定的。他认为在道德实践中存在一种“自发性”(Spontaneität))因素,它无法由理论推论出来。由于无法用概念清楚地界定它,阿多尔诺用一种对“恶”的抵抗(Widerstand)来呈现这种自发性。他认为我们在面对巨大的恶时,即使我们在理论上并不清楚它的根源以及我们是否能够成功地消除这种恶,但我们仍可能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对这种恶的抵抗中。这确实无法被理论清楚地规定,阿多尔诺也称它为道德实践中一种“非理性”因素。
最后,在阿多尔诺看来,这种“非理性”并非完全的非理性或反理性,它的生成也需要理论的中介。他认为,如若没有从理论上对这种恶的现象的反思,这种恶的破坏性或不可忍受性也无法得到清楚的认识,因此一种不妥协的抵抗也就无法产生。在《历史与自由》中,阿多尔诺对此作了一番生动的描述:当法西斯政府的警察敲开民众的家门进行突然检查时,如果他们对这个刚刚掌握国家机器的组织没有进一步的了解,仅仅把这个突然检查视为与其它时刻的检查毫无区别时,那么他们也就无法体验到对此有着深刻洞察的人的家门被敲开时那一刻的恐惧。[注]Theodor W.Adorno,History and Freedom:lectures 1964-1965,ed.Rolf Tiedemann,trans.Rodney Livingstone,Cambridge:Polity press,cop.2006,pp.19-28.
因此,阿多尔诺强调即使正确的道德实践无法完全由理论推出,二者无法被同等,但我们也必须坚持理论的反思。如果我们丢弃或丧失理论的反思能力,把直接性的对象当做真理或沉沦于日常生活之中,那么在他看来,我们在间接的意义上就会是恶的“帮凶”。另外,在这种恶的社会中,如果我们试图采取一种追求个人的善的生活,或采取一种逃避式的“退隐山林”的生活,这也是一种恶。[注]Theodor W.Adorno,Minima Moralia:reflections on a damaged life,trans.E.F.N.Jephcott,Veso,2005,pp.37-40.在此意义上,阿多尔诺指出,在一种错误的生活中,正确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阿多尔诺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阐发主要包涵两个方面:对社会的恶进行不懈的理论反思;正确的实践活动并非完全由理论推出,它有着自身的自发性。我们认为,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能够完全支撑他所提出的新的绝对命令。一方面,对恶的不妥协的反思,是由他的否定的道德哲学所决定的。它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直接提供给他人一种善的生活方式,道德哲学的规定只能是否定的。所以,我们只能从否定的层面提出某种道德规范。另一方面,道德实践的“自发性”要求这种规范不能够完全由理性提供,非理性的内容必须被纳入,道德规范必须包含非理性的内容。前一个方面说明了我们能够提出某种绝对命令,尽管只是否定的。后一个方面指明了这种绝对命令的内容。如前所述,这种内容就是对恶的抵抗,即“奥斯维辛和所有与此类似的一切不应再次发生”。这种抵抗并非完全来自理性,它的一部分内容来自非理性。阿多尔诺指出,非理性部分的因素主要来自我们本能地厌恶对身体施加伤害。[注]Theodor W.Adorno,Metaphysics:concept an dproblems,ed.Rolf Tiedemann,trans,Edmund Jephcott.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16-117.显然,阿多尔诺在此试图把道德哲学中形而上的内容置于一种身体的感觉。
以上的论述指明了在其理论与实践的结构中,阿多尔诺所提出的绝对命令与其整个否定的道德哲学框架并不矛盾。但是仅从他对绝对命令内容来源的分析来看,这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注]目前学界对阿多尔诺道德哲学规范性的质疑也主要集中于这一方面。See Fabian Freyenhagen,Moral Philosophy,in Theodor Adorno Key Concepts,ed.Deborah Cook,pp107-112.例如,如果道德规范的基础是基于这种直接的情感反映,即使这种反映已经通过理论的中介,那么它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些人(虐待狂或受虐狂)在面对身体的伤害时所具有的强烈快感;另外,以身体感觉为基础的道德哲学又如何面对道德普遍主义的反驳呢?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把阿多尔诺主张道德规范中存在非理性要素的思想直接等同于他赞同道德认识不需要反思,只需直接性的道德冲动。[注]施威蓬豪伊塞尔就把阿多尔诺的绝对命令置于这种道德冲动之上。See Schweppenhäuser,Gerhard,Ethik nach Auschwitz:Adornos negative Moralphilosophie,Hamburg:Argument1993,S.190,转引自Manuel Knoll,Theodor W.Adorno Ethik als erste Philosophie,Wilhelm Fink Verlag,2002,S.12-13.对此,门克(Menke)区分了两种反思:作为对道德规范构成过程的反思和道德构成性思维(morally-constitutive thinking),即对道德评价具有重要意义的行动的方面和后果的反思。蒙克认为阿多尔诺并没有否定前者,而只是批判后者,因此不能简单地就把阿多尔诺的道德哲学置于一种直接的无反思的道德情感之上。[注]Christoph Menke,Virtue and Reflection:The Antinomies of Moral Philosophy,Constellations Volume12,No1,2005.当然,阿多尔诺否定的道德哲学是否能够在当代规范伦理学的语境中成功地为自己辩护仍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在此,我们只想再次强调,如果阿多尔诺对现代社会和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合理,那么他就能够合理地在自己的道德哲学框架中提出规范性要求。正如王凤才教授指出的,批判理论在其第一期发展中,政治伦理向度仅处于边缘地位,[注]王凤才:《蔑视与反抗:霍耐特承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314页。用阿多尔诺的话来说就是,道德哲学只是否定辩证法其中的一个“模型”(Modell),[注]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ktik,Frankfurt/M.:Suhrkamp 1970,S.3.因此若要准确理解他所提出的规范性要求,我们就必须首先恰当地把握他的哲学尤其是他的否定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