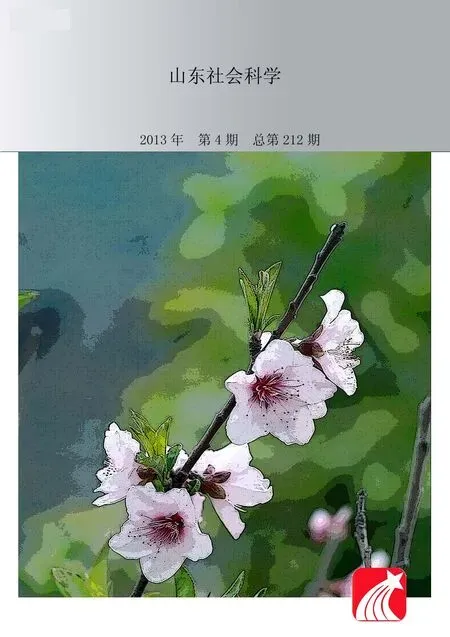南希·弗雷泽关于全球化时代公共领域的构想
2013-04-07贺羡
贺 羡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043)
南希·弗雷泽是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哲学、政治学教授,是英美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理查德·罗蒂赞赏她对当代左翼所面临的问题的分析,认为她是美国最受关注的哲学家之一。注Kevin Olson(ed),Adding Insult to Injury.Verso,2008,p.69.她与哈贝马斯、阿克塞尔·霍耐特、查尔斯·泰勒等人的论争推动了女性主义理论、批判社会理论和正义理论的发展。
公共领域理论是哈贝马斯商谈政治理论的基础,也是其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以下简称《结构转型》)中大致勾勒出了这一理论的基本轮廓,提出了“公共领域”概念,而后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进一步发挥。公共领域是个体讨论公众事务或共同利益问题、形成公共舆论的社会生活领域,它一方面通过让国家对公民负责,为政治统治的合理化设计出一种制度机制,另一方面设计了特定的对话互动,指出讨论应该向所有人开放,参与者作为伙伴进行商谈,“开放准入观念是公共性规范的核心含义”。注Nancy Fraser,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in Craig Calhoun(ed.),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Cambridge,MA:MIT Press,1992,p.118.公共领域作为公共舆论的生成空间,应该是包容的、公平的。公共性应当质疑那些不能经受批判检验的观点,并保证那些可以经受检验的观点的合法性。此外,公共领域还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整合公共舆论的载体,它应把市民社会意识转化成表达这种公民意志的国家行动。“这两个观念——公共舆论的规范合法性和政治有效性——对民主理论中的公共领域概念至关重要。没有它们,这个概念就失去了其批判力量和政治立场。”注Nancy Fraser,Transnationalizing the Public Sphere:On the Legitimacy and Efficacy of Public Opinion in a Post-Westphalian World,in Theory,Culuture﹠Society,2007(24),pp.7-8.在哈贝马斯看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正是这样一种结合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形式,只不过现在还是一个未完全实现的理想。然而弗雷泽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与开放平等的公共性理想是相违背的:基于性别、阶级、种族偏见的排除规则把一部分人阻挡在政治生活之外,并且这种准入也只对民族国家中的公民才适用。弗雷泽认为,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概念以“民族国家”为核心范畴,隐含了一个威斯特伐利亚[注]“凯恩斯—威斯特伐利亚架构”(Keynesian-Westphalian frame)指战后民主福利国家鼎盛时期正义争论的国家领土基础,大致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哈贝马斯把现代性政治话语的起源从法国大革命向前追溯到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和作为战争结束标志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又称《1648年和约》,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分别在德意志的奥斯纳布吕克和明斯特同瑞典人和法国人签署的和约的统称,它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各邦国与帝国之间的宗教信仰问题、各封建等级同帝国和皇帝之间的关系问题、德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问题等。因此,它实际上是把宗教和约、国内和约和国际和约融为一体,不但为神圣罗马帝国,也为欧洲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秩序。哈贝马斯认为,“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带来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而民族国家在现代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中一直都是一个核心范畴。弗雷泽并不关注此条约的实际成就,而是用这一词来指一种政治想象,即它作为相互承认的主权领土国家体系塑造了世界,这种想象体现了战后第一世界关于正义的争论架构。参见曹卫东:《曹卫东讲哈贝马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73页;Kevin Olson(ed),Adding Insult to Injury.Verso,2008,p.273,注1以及Nancy Fraser,Reframing Justiceina Globalizing World,in New Left Review,2005(36),p.2,注1.的政治想象,即有界政治社群及其领土国家的框架。然而在全球化时代,这个框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已无法应对诸多跨国问题,因此应予以超越。
一
在《重新思考公共领域》一文中,弗雷泽认为,公共领域在产生之初就是男权主义的,它把女性排斥在公共辩论之外,这一点可以从“public”与“pubic”的词源联系上得到印证。除了性别排斥,早期公共领域中还存在阶级排斥,“仁慈的、平民的、专业的、文化的俱乐部和社团网络都不是对所有人开放的。相反,它是一个训练场,终究是资产阶级男性阶层的权力基础,这些男性把自身视为一个‘普遍阶级’,并准备宣称他们是进行统治的合适人选。因此资产阶级形成过程暗含了市民社会特定文化和联合公共领域的阐述”。[注]Nancy Fraser,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in Craig Calhoun(ed.),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Cambridge,MA:MIT Press,1992,p.114.哈贝马斯认识到了性别排斥与公共领域从贵族向资产阶级转移有关,但他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充分考察,有关某一阶级的公共领域,他也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所以弗雷泽认为“鼓吹准入性、理性和地位等级悬置的公共性话语本身就是作为一种区别策略出现的”。[注]Nancy Fraser,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in Craig Calhoun(ed.),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Cambridge,MA:MIT Press,1992,p.115.
此外,哈贝马斯把公共性与地位之间的关系想象得过于简单了,他借助“中立化”对地位差别存而不论,把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理想化,没有对其他众多的非自由主义的、非资产阶级的竞争公共领域进行考察。事实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公众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众,与资产阶级公众同时产生的还有大量其他公众,如民族主义公众、精英女性公众和工人阶级公众等,它们从一开始就反对资产阶级公众的排斥规范,阐释不同类型的政治行动和公共演讲规范。例如,十九世纪北美女性即使没有投票权,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参与公共生活,因此那种认为女性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的观点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它依赖于具有阶级和性别偏见的公共性观念,认为表面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公共诉求才具有公共性。因此,有学者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既是一种乌托邦理想,也是一种统治工具。然而,弗雷泽并没有完全否定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作用,而是在批判其四个建构假设的基础上,发现了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观念的一些相应因素:
第一个假设是,公共领域中的对话者忽略地位差别,似乎以平等的身份进行商谈,假设社会平等不是政治民主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在没有任何正式排除的情况下,社会不平等也可以影响商谈不平等,弗雷泽引用了一个对男女共同参加会议的观察: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被打断、发言更少、更容易被忽略或得不到回应。在这种情况下,商谈变成了统治的面具。风尚和礼仪支配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对话非正式地把女性和平民阶级成员边缘化、阻止她们作为平等伙伴进行参与,即使她们取得合法参与的资格,仍然会受到妨碍。对社会不平等存而不论并不能促进参与平等,相反它更有利于社会统治群体。
第二个假设是,竞争公众的多样性增长是背离而不是趋近更广泛的民主,单一的综合公共领域比多元公众更可取。事实上,分层社会的基础制度框架在统治/从属的结构关系中产生了不平等的社会群体。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可能完全实现公共辩论和商谈中的参与平等。如前所述,社会不平等使公共领域中的对话过程向统治群体的利益倾斜,特别是只有一个单一综合公共领域时更是如此。这时,从属群体成员不会再有相互商讨其需求、目标和策略的场域,也将失去那些不受统治群体监管而进行交往的场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太可能找到合适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只能保持沉默,结果在综合公共领域中就不能表达、捍卫自己的利益,掩饰统治的商谈模式就不太可能被揭示出来,这种模式把弱者吸纳进虚假的“我们”。弗雷泽认为,参与意味着用自己的声音说话,同时通过方言和风格来构建、表达自己的文化身份,包含多元竞争公众之间争论的安排比单一的综合公众能更好地推进参与平等理想,她将这些非正统的公众称为“亚反公众”(subaltern counterpublics),他们可以在“主流公共领域”中有效地表达自身观点和利益。因为这些占主导的理解和交流手段使边缘的和被排除的群体处于劣势,所以他们不得不创造自己的“亚反公众”来重新命名他们遭受的不正义,“从属社会群体的成员创造、传播反话语来塑造对其身份、利益和需求的相反理解”[注]Nancy Fraser,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in Craig Calhoun(ed.),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Cambridge,MA:MIT Press,1992,p.123.,其增长能够提高从属阶层的参与。弗雷泽把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所提出的概念(如约会强奸和性骚扰)的发展和普及当做这一方面的典型。同时她强调,亚反公众并不总是有效的,其中一些显然是反民主的、反平等主义的,甚至那些带有民主和平等主义意向的公众有时也在实践非正式的排斥和边缘化模式。“只有那些为了反抗主流公众排斥而出现的反公众,才有助于拓展对话空间。原则上,先前不受质疑的假设将得到公开讨论。一般而言,亚反公众的增加意味着话语争论的扩大,在分层社会中是一件好事。”[注]Nancy Fraser,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in Craig Calhoun(ed.),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Cambridge,MA:MIT Press,1992,p.124.总之,不管在分层社会还是在平等主义社会中,多元公众比单一公众更能实现参与平等理想。
第三个假设是,公共领域中的对话应该囿于关于共同福祉的商谈,私人利益和私人问题的出现总是不受欢迎的。这涉及到公共领域的界限问题,即公共性之于私人性的界限。哈贝马斯关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论述的核心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私人个体”商谈“公共问题”的对话场所,公共成员通过商谈能够发现或创造一种共同利益。在对话的过程中,参与者由利己主义的私人个体转变为能够为了共同利益而共同行动的、具有公益精神的集体。这里的“私人”和“公共”有若干不同的意思,“公共”意味着:与国家相关的、对每个人开放、关注每个人、涉及共同福祉或共享利益。“私人”则意味着:涉及市场经济中的私人财产、涉及亲密的家庭或个人生活包括性生活。这样看来,私人利益在政治公共领域中没有合适的位置,至多它们是商谈的“前政治”起点,在辩论过程中最终被转化和超越。在政治话语中,“公共”与“私人”的划分经常把某些利益、观点和主题非法化而为另一些保留商谈的空间,使自身利益和群体利益相抵触,使参与者(尤其是那些相对无权的人)无法弄清其利益,隐含了资产阶级的、男权主义的偏见。因此,一个持久的公共领域观念必须容纳被资产阶级、男权意识形态视为“私人的”、不允许公开讨论的利益与议题。
第四个假设是,起作用的公共领域需要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作出严格区分。根据“市民社会”的不同表达,对这个假设也有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如果市民社会意味着私人调节的资本主义经济,那么坚持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就是捍卫古典自由主义。弗雷泽认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不能促进社会经济平等,最终需要实现某些政治管制的经济整顿形式和再分配(如市场社会主义)。第二种理解是,“市民社会”意味着非政府或“亚级”社团的联结,它既不是经济的也不是管理的,而是“聚集起来形成公众的一群个体”,那么市民社会应该与国家相分离,这确保了更大范围的检验。这些“个体”不以任何官方身份参与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作为国家的对应物、非政府话语意见的非正式鼓动实体。在资产阶级观念中,公共领域的超政府特征赋予它所产生的“公共舆论”以独立、自由和合法性的光环。因此,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观念认为(联合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明显分离是可取的,它促进了弗雷泽所谓的“弱公众”,其话语实践只存在于“意见”的形成中,不包括决策制定。如果这种公众话语向决策制定扩展,那么将威胁公共舆论的自主,因为公众将有效地成为国家,失去对国家的批判话语监督的可能性。但当考虑议会权威时,这个问题就变得复杂了。自从自治议会在国家中行使公共领域职能时,就出现了一个主要的结构转换,弗雷泽称自治议会为“强公众”,其话语既包含意见形成又包括决策制定。议会是运用国家权力话语权威的场合,最终产生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策(或法律)。随着议会自治的实现,(联合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界限模糊了。不可否认,议会自治的出现以及(联合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界限的模糊代表了一种民主进步,公众意见的力量得到强化,代表它的实体被赋予把这种“意见”转换成权威决定的权力。因此,一个合理的公共领域观念应该同时考虑到“强公众”与“弱公众”,并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理论化。
综上所述,弗雷泽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不足以批判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存民主,必须对公共领域批判理论进行重构,为此她提出了四项任务:第一,批判理论应该说明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不平等腐蚀公众商谈的方式;第二,它应该阐明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平等如何影响公众之间的关系、公众如何被有区别地赋权或分割,以及某些公众如何被迫孤立并服从其他公众;第三,它应该揭示在当代社会中如何能够广泛地讨论某些被标识为“私人的”利益和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解决途径;最后,它应该说明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些公共领域的过度软弱如何剥夺“公众意见”的实践力量。
二
在《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研究在两个层面上同时进行,一个是经验的和历史的,另一个是意识形态批判的和规范的。在这两个层面上,公共领域被概念化为是与有界政治社群和主权领土国家(经常是民族国家)共存的。无疑,这一直不是完全明确的。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论述至少依赖六个社会理论假设:(1)在公共领域的领土基础方面,把公共领域与在边界领土之上运用主权的现代国家机构联系起来;(2)在公共领域的参与主体方面,把公共领域讨论的参与者视为一个有界政治社群的伙伴成员;(3)在公共领域讨论的主题方面,把公共领域讨论的首要主题设想为对政治社群的经济关系进行适当安排;(4)在公共领域的交流方式方面,把公共领域与现代媒体联系起来,使交流超越距离,把空间上分散的对话者集中到一个公共场所中,然而,哈贝马斯暗地里通过关注国家媒体尤其是国家出版和国家广播把“公共性”领土化;(5)在公共领域的交流媒介方面,默认公共领域讨论是完全可理解的、在语言上是清楚明白的;(6)在公共领域的渊源方面,把公共领域的文化本源追溯至十八、十九世纪的印刷资本主义的信件与小说。它把这些资产阶级风格归功于创造一种新的主体立场,通过它个体把自身预想成公众成员。这六个假设都存在于政治空间的威斯特伐利亚架构中。
在《结构转型》中,公共性是与现代领土国家和国家想象联系在一起的,哈贝马斯没有质疑现代领土国家民主化过程的威斯特伐利亚框架,而是预想了恰好处于其中的民主商谈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民主需要通过公共交流的领土边界过程、受国家语言的引导、通过国家媒体转述产生一个国家公共舆论的实体。……它有助于把国家政治统治理性化,应该保证威斯特伐利亚国家的行动和政策反映国家公民在对话中形成的政治意志。因此,在《结构转型》中,公共领域是(国家)威斯特伐利亚民主的关键制度成分。”[注]Nancy Fraser,Transnationalizing the Public Sphere:On the Legitimacy and Efficacy of Public Opinion in a Post-Westphalian World,in Theory,Culuture﹠Society,2007(24),p.11.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概念在其深层概念结构中完全是威斯特伐利亚的,“只有近年来,一方面由于后冷战的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由于与‘全球化’相联的跨国现象增强的显著性,它才在跨国框架中反思公共领域理论中变得可能且必然”。[注]Nancy Fraser,Transnationalizing the Public Sphere:On the Legitimacy and Efficacy of Public Opinion in a Post-Westphalian World,in Theory,Culuture﹠Society,2007(24),p.8.事实上,哈贝马斯在《包容他者》中已经指出,民族国家正受到内部多元化与外部全球化的双重挑战,全球化的趋势使民族国家内在主权的局限性充分暴露出来。一个民族国家想要捍卫其内在主权的话,就很难加入到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当中;而要投身到这个进程中去,民族国家就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把自己的部分主权让渡给全球化的机构。面对这一困境,哈贝马斯尝试为民族国家寻找新的合法化理由,以便顺应全球化大潮,即走向一种“后民族国家”的世界格局。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这种新的世界政治共同体就是一种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其基础是建立在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基础上的全球公民社会。然而,匈牙利作家皮特·艾斯特哈茨(Peter Esterhazy)指出,哈贝马斯构建的“后民族格局”“不过又是一个超级大国(欧洲国),一个寻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欧洲民族国家’”[注]曹卫东:《曹卫东讲哈贝马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威斯特伐利亚框架的窠臼。
因此,弗雷泽试图重构公共领域概念使之适应后威斯特伐利框架,后威斯特伐利亚框架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全球政治框架。在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中,公共领域溢出了国家边界,形成了不再以共同的语言、出身、血缘以及地域等为基础的“跨国公共领域”。事实上,弗雷泽对后威斯特伐利亚框架的构想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她对《结构转型》的批判分为两种:一种是合法性批判,另一种是有效性批判。前者关注市民社会中的关系,主张《结构转型》模糊了剥夺一些名义上为公众成员的人作为公共辩论的完全伙伴、与他人平等参与的能力的系统障碍的存在;后者关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主张《结构转型》没有指出剥夺政治力量在对话中产生的公共舆论的系统障碍的全部范围。然而,两种批判仍然导向有界政治社群的商谈民主前景,它们继续把公众与领土国家公民等同起来,其目标都是要在现代领土国家中使商谈民主更进一步。
在《公共领域的跨国化》(2007)一文中,弗雷泽修正了上述批判的理论前提,指出“不管问题是全球变暖还是移民、女性还是贸易协定、失业还是‘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目前公共舆论的变动很少停留在领土国家边界内。在许多情况下,对话者没有构成民众或政治公民。她们的交往通常既不存在于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中,也不通过国家媒体传播。此外,辩论的问题通常就是跨领土的,既不能被置于威斯特伐利亚空间中,也不能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国家得到解决。”[注]Nancy Fraser,Transnationalizing the Public Sphere:On the Legitimacy and Efficacy of Public Opinion in a Post-Westphalian World,in Theory,Culuture﹠Society,2007(24),p.14.这对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公共性的讨论也同样适用,哈贝马斯在这本书中集中考虑有效性问题,它把法律当作交往权力转化成统治权力的适当工具,区分了权力的正式的民主循环与非正式的非民主循环。在前者中,弱公众影响强公众,最终控制国家机器;在后者中,私人社会权力和根深蒂固的官僚利益控制法律制定者、操纵公共舆论。“哈贝马斯承认非正式循环通常胜出,他在这里提供了关于民主国家中公共舆论有效性缺陷的更完整论述。”[注]Nancy Fraser,Transnationalizing the Public Sphere:On the Legitimacy and Efficacy of Public Opinion in a Post-Westphalian World,in Theory,Culuture﹠Society,2007(24),pp.13-14.“哈贝马斯支持社会整合的后民族主义形式,即‘宪政爱国主义’[注]有学者将其译为“宪法爱国主义”,而哈贝马斯用这一词表示德国人对于目前宪法制度的普遍认同,因此译为“宪政爱国主义”更贴切。(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其目标是剥开国家主义的包裹,解放民主国家。但是在这里他实际上赞同一种更加纯粹的威斯特伐利亚公共性观念,因为他赞同一种更具有排他性的领土观念。”[注]Nancy Fraser,Transnationalizing the Public Sphere:On the Legitimacy and Efficacy of Public Opinion in a Post-Westphalian World,in Theory,Culuture﹠Society,2007(24),p.14.
三
在这种情况下,理论界出现了“跨国公共领域”、“流散公共领域”、“全球公共领域”这样的表述。弗雷泽认为,目前跨国公共领域的出现可以被视为另一种“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但在她之前,学界对这种新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论述还很不充分。她为了澄清问题、提出可操作性的公共领域批判理论,主张回到威斯特伐利亚公共领域理论的六个建构假设上来,认为这些假设都是反事实的:
(1)在公共领域的领土基础方面,现在的领土国家(不论贫富)都与国际组织、政府间网络和非政府组织分享许多关键的管理职能。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相对较新的功能,如环境监管,而且也适用于传统功能,如防卫和治安。这些组织现在的确被霸权国家所掌控,然而运用霸权的模式已不同于以往:霸权不是求助于排他的、不可分割的国家主权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它越来越通过解体主权的后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来运作。因此,公共领域理论的第一个前提在经验上是站不住脚的。
(2)在公共领域的参与主体方面,当今的公共领域与政治成员身份不能共存。由于移民、迁徙等现象,现在每个国家领域内都有非公民,对话者经常既不是族人也不是伙伴公民。因此,他们的观点既不代表共同利益也不代表任何民众的普遍意志。
(3)在公共领域讨论的主题方面,外包、跨国企业和“离岸商业登记”(offshore business registry)使基于领土的国民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只存留于观念上。由于布雷顿森林资本控制的全天候(24/7)全球电子金融市场的出现,国家对货币的控制现在非常有限。调控贸易、生产和金融的基础规则应由跨国机构来制定,它们向全球资本而不是向任何公众负责。
(4)在公共领域的交流方式方面,“分众媒体”(niche media)变得丰富多样,它们致力于使国家权力的运用服从于公共性检验。即时电子、宽频和卫星信息技术绕过了国家控制,使直接的跨国交流成为可能。所有这些发展标志着交流设施的“解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
(5)在公共领域的交流媒介方面,当语言群体在地域上是分散的、更多的言说者会多种语言时,许多国家事实上是多语言的。同时,英语作为全球商业、大众娱乐和学术界的通用语得到巩固,所以单一国家语言的预设就不再成立了。
(6)在公共领域的渊源方面,由于文化混杂性与混合化、全球大众娱乐的出现、视觉文化的崛起,哈贝马斯认为支撑公共领域对话者主观立场的那种民族文学,不再能为团结提供共同的社会想象了。
总之,对公共舆论的每个构成因素而言,公共领域逐渐成为跨国的或后民族的,先前威斯特伐利亚国家公民交往的“谁”(who),现在经常是一个分散对话者的集合,而不能构成一个统一的民众。在跨国社群中,先前植根于威斯特伐利亚国民经济中的交往的“什么”(what),现在已经遍及全球,然而并不体现在同样广阔的团结与认同中。曾经存在于威斯特伐利亚国家领土的交往的“哪里”(where),现在被解域为网络空间。曾经依赖于威斯特伐利亚国家出版媒体的交往的“如何”(how),现在涵盖了断裂的、重叠的视觉文化的广阔跨语言连结。曾经对公共舆论负责的主权领土国家,现在是公共与私人跨国权力的不规则混合物,既不能被轻易识别也不能被认为是应负责的。
那么,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框架的跨国公共舆论如何能够在规范上具有合法性、在政治上具有有效性呢?弗雷泽从下述两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首先考虑规范合法性问题,这涉及到两个标准:包容的范围和参与平等的程度。前者关注“谁”被授权参与公共讨论,后者关注参与者“如何”互动。按照包容标准,讨论必须在原则上对所有受决策结果影响的人开放。威斯特伐利亚框架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参与平等标准,而忽略了包容标准。然而在全球化时代,公民身份不再能够代表受影响的人了,一个人的生存条件不再完全依赖于政治社群的内在构建了,而是越来越多地受到其他外在的和非领土结构的制约。面对这个问题,弗雷泽起初采纳“所有受影响者原则”(all-affected principle),认为所有潜在受到决策影响的人都应该作为伙伴参与共同事务的商谈,但是在《非常规正义》一文中,她认为“所有受影响者原则成为蝴蝶效应的‘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的牺牲品,它把所有人都变得受一切事物的影响。它不能识别道德相关的社会关系,在抵制它试图避免的一刀切全球主义时遇到麻烦。因此,它不能为决定“谁”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标准。”[注]Nancy Fraser,Abnormal Justice,in Kwame Anthony Appiah(etc.),Justice,Governance,Cosmopolitanism,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Reconfigurations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Humboldt-Universitat zu Berlin,2007,p.135.她转而提出“所有从属者原则”(all-subjected principle),“根据这一原则,所有从属于特定统治结构的人都有一个与之相关的、作为正义主体的道德立场。把人们变成正义伙伴主体的既不是共同的公民资格或国籍,也不是共同拥有抽象的人格,也不是因果相互依存的纯粹事实,而是都从属于一种统治结构,这一结构为他们/她们之间的互动设置了基本规则。对于所有统治结构而言,所有从属者原则使道德关怀的范围与受影响的范围相配。”[注]Nancy Fraser,Abnormal Justice,in Kwame Anthony Appiah(etc.),Justice,Governance,Cosmopolitanism,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Reconfigurations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Humboldt-Universitat zu Berlin,2007,pp.135-136.这些统治结构不只局限于国家,还包括能制定强制规则的非国家主体,因此,所有从属者原则为后威斯特伐利亚公共舆论的合法性提供了评判标准。
其次考虑政治有效性问题。在公共领域理论中,当且仅当公共舆论被政治力量所调动,使公共力量负有责任,保证后者的实施反映了市民社会经过深思熟虑的意志时,它就是有效的。这涉及到两个标准:转化标准和能力标准。根据转化标准,市民社会中产生的交往权力必须首先转化成具有约束力的法律,然后再转化成行政权力。根据能力标准,公共权力必须能够执行在对话中形成的意志。前者关注从市民社会到公共权力的交往权力流动,后者关注行政权力实现公共计划的能力。过去的公共领域理论假定,公共舆论的接收者是威斯特伐利亚国家,它应该被民主地构建,因此没有阻断从弱公众到强公众的交往流动,能被转化成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同时,威斯特伐利亚国家具有运用这些法律的必要行政能力,以便实现其公民的目标并解决相关问题。因此,威斯特伐利亚国家被认为是实现公共领域有效性的转化标准和能力标准的适当工具。尽管威斯特伐利亚框架刺激了对转化标准的兴趣,但却模糊了能力标准,它只强调国家公共领域产生的交往权力是否足够强大以致影响立法、限制国家行政。相应地,讨论集中在什么应被当做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民主权力循环,而没有过多讨论国家监管塑造公民生活的私人权力的能力,举例来说,一些理论家认为,经济实际上是国家的,民族国家能够以国家公民的利益对其进行调控。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如果现代领土国家不再拥有调控其经济、保证其国家环境完整、为其公民提供安全和福利的行政能力,那么应当如何理解公共舆论有效性的能力标准呢?这个问题涉及到国际法和跨国机构的权责问题,是后威斯特伐利亚框架不可绕过的具体问题,虽然弗雷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当前的公共领域理论也只提供了少许线索,但是疑问本身就指明了进一步研究的目标,即如何创造新的跨国公共权力,并让它们对新的跨国公共领域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