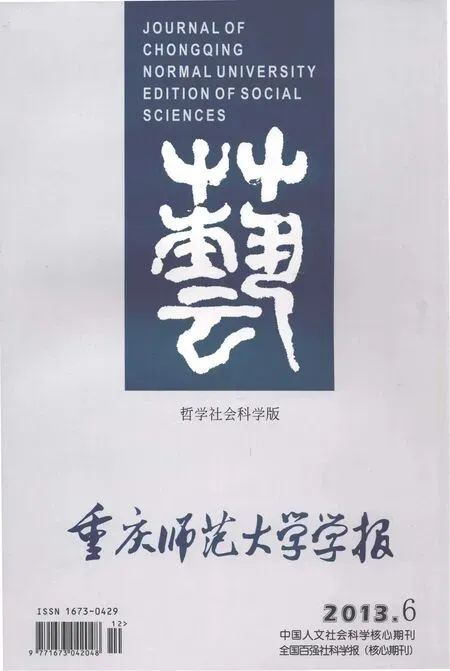漠视与推崇——从《革命军》看邹容对日本和西方的态度
2013-04-02常云平
常云平 张 周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晚清留日学生的对日态度基本可以分为推崇、中立和反对三种。如李喜所指出,“中国留日生对日本的印象从总体上讲是很好的,也是较客观的,基本将日本视为中国人的榜样,而去学习研究和加以介绍”[1]。孔繁岭认为中国近代留日学生对日本的态度是“爱恨交织”,但同时又“多数反日”[2]。周建树则提到部分湖南籍留日学生已将日本视为“东亚之祸源,中国之威胁”[3]。然而,在西学受到晚清各界普遍推崇的大环境下,留日学界是否存在着漠视日本与推崇西方并存的态度呢?答案是肯定的,晚清最为流行的《革命军》基本成稿于邹容留学日本期间,但该书在大篇幅论述西方的同时仅仅提及日本六次。为什么一个留日青年的代表作在推崇西方时如此漠视日本?本文试图从邹容的个人经历和《革命军》的内容出发来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解释邹容漠视日本与推崇西方并存的原因。
一、被漠视的日本
邹容在留日期间完成的《革命军》一书,对当时中国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革命的目的以及革命后建立什么样的制度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奇怪的是,作为一部留日学生的代表作,与日本相关的内容在书中屈指可数,远不及其他留日学生对日本的关注程度。
从《革命军》的内容来看,全书言及日本一共六处,且从未以独立内容呈现,仅仅作为支撑邹容观点的众多事例之一而存在。如为了证明在满族奴役下“汉官威仪”和“唐制衣冠”已“扫地殆尽”,邹容描述了国人在外国受到普遍歧视的状态:“拖辫发,著胡服,踯躅而行于伦敦之市,行人莫不曰Pigtail(译言猪尾)、Savage(译言野蛮)者……又踯躅而行于东京之市,行人莫不曰チャンチャンボッ(译曰拖尾奴才)者”。[4](226)为了证明汉族自古具有优越性,他又大肆渲染汉族文化的活力和汉族的生存能力:“汉族者,东洋史上最特色之人种……自古司东亚文化之木铎者,实惟我皇汉民族焉。日本、朝鲜亦为我汉族所蕃殖。”[4](239-240)“我皇汉民族起自黄河东北一带之地,经历星霜,四方繁衍,秦汉之世已布满中国之全面,以中国本部为生息之乡。降及今日……其流出万里长城以外、青海、西藏之地者,达一千余万之多。更进而越日本之境,或侵入北方黑龙江之左岸俄界,或达南方,进入安南……更进入太平洋,侵入布哇、美洲合众国……逾南洋侵入吕宋、爪哇、浡泥及澳洲、欧洲者,亦不下三四百万。”[4](242-243)与这些观点一致,“日本人”与“朝鲜人”、“暹罗人”、“西藏人”等一道被邹容纳入了“中国人种”的范畴。此外,邹容还通过列举一系列具体的事例来证明汉族的劣根性和奴隶地位,指出:“满洲人入关,称大清朝顺民;联军破北京,称某某国顺民;香港人立维多利亚纪念碑,曰‘德配天地’;台湾人颂明治天皇功德,曰‘德广皇仁’……”[4](244-245)“法国议院中,无安南人足迹;英国议院中,无印度人足迹;日本议院中,无台湾人足迹”[4](252)。可见,《革命军》中涉及日本的言论既无法反映当时的日本国势,也没有体现作者明确的对日态度。
与同时期留日学生的言论相比,《革命军》对日本的关注程度也要逊色许多。1905年以前,留日学生大多把日本作为中国的师法对象,因而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持肯定态度。湖南籍留学生周家纯对日本国势的蒸蒸日上就感慨良多:“自入长崎以来,流连异土,百感交集,及达东京,益怦怦不能自持者,非有他也,吾侪种族若朝鲜、若交趾、若缅甸、若阿富汗、若俾路直等,大抵颓然不振,或已澌灭无遗,或犹仅保残喘,其铮铮佼佼尚契黄种之旗,以招展于世界而不堕黄人之绪者,在西则为匈牙利,在东则惟日本而已”[5]。新式教育在日本的兴盛也受到留学生的广泛关注,乃至出现了“日本学校之多,如我国之鸦片烟馆,其学生之众,如我国之染烟瘾者”[5]之类的比喻。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还毫不隐晦地承认受到日本书籍的影响:“自居东以来,广览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6](188)1901年,留日学生章宗祥编写的留日工具书——《日本游学指南》出版,该书极力向有志留学的国人推荐日本,指出与留学欧美相比,日本同时具有“文字同”、“地近”、“费省”等三大便利和“有当时维新之历史,足为东洋未来国之前鉴”的条件,所以“资本一而利十者,莫游学日本若也”[7](148)。随着1905年“留日学生取缔规则事件”的发生和日本对华侵略的加剧,留日学生的对日态度逐渐产生分化,反日主张开始增多。当时陈天华就已经发现了留日学界对日态度的分歧,他在《绝命辞》中指出:“近人有主张亲日者,有主张排日者,鄙人以为二者皆非也。”[8](174)但无论是亲日、排日还是中立言论,其所表明的对日态度都远比《革命军》中的涉日言论要明确得多。
与日本在书中受到漠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代西方得到了邹容的极力推崇,并占据了《革命军》较大的篇幅。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受到推崇。邹容把近代西方的启蒙思想当作欧美先进文明形成的根本因素,指出“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4](201)。同时,他站在近代西方启蒙思想的高度来理解“政治”和“国民”的内涵,认为“政治者,一国办事之总机关也,非一二人所得有之事也”[4](237);“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4](247)。此外,一些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学说还被邹氏应用到对未来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中,由此提出了“各人权利必需保护。须经人民公许,建设政府,而各假以权,专掌保护人民权利之事”;“无论何时,政府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迨其既得安全康乐之后,经承公议,整顿权利,更立新政府,亦为人民应有之权利”[4](257)等设想,希望依照启蒙思想中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学说”来组建和更替未来的中国政府。
第二,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及其革命者受到推崇。邹容在《革命军》中高度评价了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认为英、美、法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善良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4](198-199)。同时他认定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
二、受推崇的西方
是“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购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一切权利,为国民增幸福”的“文明之革命”,指出以“除祸害而求幸福”为目的的文明革命应当受到同胞们的“顶礼膜拜”。[4](233)除此以外,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也为该书所称颂:“一时所谓革命之健儿,建国之豪杰,流血之巨子,其道德,其智识,其学术,均具有振衣昆仑顶,濯足太平洋之概焉。”乃至邹容对这些革命者直接发出了“吾崇拜之,吾倾慕之”的表白。[4](235)值得一提的是,邹氏对广大无名革命者的崇敬之情丝毫不亚于其对革命领袖的崇拜:“若华盛顿,若拿破仑,此地球人种所推尊为大豪杰者也。然一华盛顿、一拿破仑倡之,而无百千万亿兆华盛顿、拿破仑和之,一华盛顿何如?一拿破仑何如?其有愈于华、拿二人之才之识之学者又何如?有有名之英雄,有无名之英雄,华、拿者不过其时抛头颅溅热血无名无量之华、拿之代表耳”[4](235)。由上观之,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者的历史作用得到了邹容的极大肯定。
第三,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受到推崇。邹容对西式制度的推崇主要是通过中西之间的一系列对比来完成的:首先,中西之间的言论自由程度有着天壤之别,“外国工人有干涉国政、畅言自由之说,以设立民主为宗旨者;有合全国工人立一大会,定法律以保护工业者;有立会演说,开报馆,倡社会之说者”,而中国则“杀一教士而割地赔款,骂一外人而劳上谕动问”;其次,中西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存在较大差异,“外国之富商大贾,皆为议员,执政权,而中国则贬之曰末务,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再次,中西之间在司法层面的差别也十分明显,“文明国中,有一人横死者,必登新闻数次,甚至数十次不止。司法官审问案件,即得有实凭实据,非犯罪人亲供不能定罪(于审问时,无用刑审问理)”,而“吾同胞每年死于贼满人借刀杀人滥酷刑法之下者,不知凡几”[4](217-219)。相较下来,中西制度孰优孰劣已是显而易见。邹容对西方制度的推崇还反映在其对未来中国的设想中。他希望未来中国能够仿效美国的选举制度来组织政府和议会:“区分省分,于各省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行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又举一人为副总统,各州、县、府举议员若干”[4](256)。以西方制度作为未来中国制度的榜样,足见邹容对近代西方制度的青睐。
三、漠视日本与推崇西方并存的原因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体现了漠视日本和推崇西方并存的态度。表面上看这一现象并不符合邹容留日学生的背景,但只要通过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其必然性。
其一,日本的近代化是通过学习西学、效法西制实现的,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接触的近代观念实质上源于西方。有学者曾指出,“中国在输入西洋文化的过程中,日本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中国从日本间接获得不少西洋文化”[6](160)。的确,产生于近代西方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思想在成稿于日本的《革命军》中多次得到体现。邹容明确指出驱除满人是为了“恢复我声明文物之祖国”,“收回我天赋之权利”,“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4](232)在说明“平等自由之大义”时,认为“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4](236)并没有君与臣的差别。在邹容设想的未来中国里:“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4](257)甚至在黄帝子孙效法的榜样方面也以西方的历史人物华盛顿和拿破仑为代表。可见,邹容虽留学日本,但在言论、出版相对自由的环境下接受更多的是近代西方的知识,这一点从他“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4](201)的感慨中得到了充分表现。
其二,邹容在日本的留学时间较为短暂,对日本的兴起尚缺乏全面的了解,同时日本的国际地位在邹容留日期间也尚不能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邹容在1902年9月至10月之间抵达日本,第二年3月即因为与张继等人剪掉南洋学监姚煜的辫子而被迫归国[9]。不足一年的留日时间使得他对日本的了解不可能全面。此外,从他“早脱满洲人之羁缚,吾恐英吉利也,俄罗斯也,德意志也,法兰西也,今日之张牙舞爪以蚕食瓜分于我者,亦将迸气敛息以惮我之权威,惕我之势力”[4](230)的假设中我们可以得知,日本在邹容眼中并不能与上述国家相提并论。事实上,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日俄战争前并不被列强当作世界性的强国对待。西方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虽在明治维新后有所修改,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直到1911年才得以恢复。《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日本即因为俄国、德国和法国的干涉,被迫放弃了条约明文规定割让给日本的辽东。后来更是只能通过与英国结盟来与沙皇俄国争夺。直到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在西方列强中赢得了国际声望,日本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主义集团一员[10](264)。
其三,邹容撰写《革命军》的主要目的是鼓励四万万同胞革命,而日本在政治上的保守不符合宣传革命的需要。邹容认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4](198)1688年英国革命、1775年美国革命和近代法国的三次革命符合上述标准,因而在书中多次出现。实际上,只要是与革命尤其是民族革命相关的内容,就会在邹容书中有所体现。例如,“十三洲之独立,德意志之联邦,意大利之统一,试读其革命时代之历史,所以鼓舞民气,宣战君主,推倒母国,诛杀贵族,倡言自由,力尊自治,内修战事,外抗强邻。”[4](234)甚至连爱尔兰这个并不属于列强的民族也被邹容拿来当作反抗异族统治成功而取得自治地位的例子。反观这一时期的日本,1889年公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明确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皇位按皇室典范之规定,由天皇男子孙继承”;“天皇神圣不可侵犯”。[10](220)天皇是国家的元首、陆海军的统帅,内阁的权力高于议会,只对天皇负责,日本人民被称为“臣民”,臣民享有的的选举权受到性别、财产等条件的限制。所有这一切,都与邹容在书中提出的“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儆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4](256)的社会理想相去甚远。
余 论
既然邹容在《革命军》中推崇的对象是西方,日本受到了漠视。那么,是不是日本因素在邹容创作《革命军》的过程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呢?当然不是,邹容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不知不觉地受到日本因素的影响。例如,他在书中提及最多的“革命”,就是接受日本人用原出于中国古籍的“革命”一词表达英文“revolution”涵义的结果,否则,邹氏对“革命”的理解恐怕还停留在“汤武革命”的层面,而《革命军》这样的书名就更无从谈起了。
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革命军》本身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对日态度的著作,其漠视日本的态度在当时的留日学界具有典型性而非普遍性,这是由邹容短暂的留日经历、内心对强国的向往以及宣传革命的主观目的等因素所共同决定的。至于其对西方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日本在晚清中国西学东渐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早有学者指出:“日本确是欧美新思想传入中国的一座带有中介意义的‘桥’,而留日学生则充当了真正的架桥铺路人。”[1]留学生赴日,入的是西式学堂,西式学堂传授的主要是西方新知,可以想见,邹容长时间处于这样的学习环境之中,又怎么能不产生对西方的推崇心理呢?
一国文化的生命力往往随国家实力的消长而消长。近代以来,中日传统文化在以炮火为后盾的西方文化面前都处于劣势。所以,近代中日两国都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来改变国家的弱势状态。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摆脱了民族危机,清王朝却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屡屡碰壁。尤其是甲午战争日本击败清政府,日本的实力超过中国已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文化也开始展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但是,此时的日本文化已不是日本的传统文化,而是夹杂着许多近代西方因素的文化。留学生赴日的目的也正是要学习这部分本质上源于西方的文化。从这一大背景下考察,留日学生中出现漠视日本与推崇西方并存的态度也就不足奇怪。
[1]李喜所.甲午战后50年间留日学生的日本观及其影响[J].社会科学研究,1997,(1).
[2]孔繁岭,申在文.简论中国近代留日学生的特点[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3]周建树.辛亥革命前后湖南留日学生的日本观[J].船山学刊,2011,(4).
[4]周勇.邹容集[M].重庆出版社,2011.
[5]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6]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7]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8]郅志.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M].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9]周勇.革命军中马前卒——百年辛亥忆邹容[J].红岩春秋,2011,(5).
[10]王仲涛,汤重南.日本史[M].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