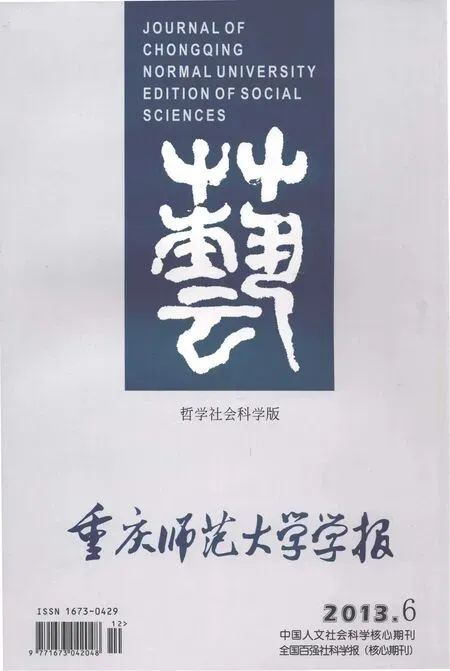语言的文学性使用及其意义增殖效应
2013-04-02贾玮
贾 玮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海德格尔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近代唯心论、洪堡、现代语言科学与语言哲学等对于语言的理解,指出西方思想正在逐渐走出将“语言”理解为“存在者”的迷途,并独树一帜地借助荷尔德林的诗作阐明语言对于存在的“道说”,这就是所谓的“走向语言之途”[1](237-271)。作为承继胡塞尔传统的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思想也经历了这种转变。特别是,胡塞尔后期对语言的强调,其实已经指明了现象学趋向语言的发展方向。庞蒂对于“身体主体”的建构则为“主体”趋向“语言”这一方向提供了具体化的路径。
一、言语表达对于个体生成的奠基
美国学者列文指出:“梅洛-庞蒂严厉批驳那些无视说话主体的关于语言的哲学理论……但是捍卫说话主体决不是要回到康德、笛卡尔式的主体。”[2](82)梅洛-庞蒂对于语言的拓展研究其实是进一步走出意识主体的必需及建构“身体主体”的必然取向,因此,关注“说话主体”,就是从“身体”出发对笛卡尔、康德哲学中在“意识主体”统摄下的语言观念进行分析,即对于传统意识哲学所设想的意识、语言、表象三者的关系进行重新梳理。梅洛-庞蒂所批驳的“无视说话主体的关于语言的哲学理论”,正是以笛卡尔、康德为代表的哲学家对于语言的论述思考。当然,这些论述往往只是只言片语,不成体系,但对后世的语言学理论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依循大笛卡尔主义的理性主义传统、康德等人的哲学构架,人们拒绝给于语言全部的哲学意义,语言成为一个无需花费太多心思的中介,“语言如同万能的工具一般存在于此”[3](6)。梅洛-庞蒂所点明的正是对于语言一贯的错误认知,但也就此切中了意识哲学传统的根本症结,即并没有给与语言以真正的哲学地位,语言被迫下滑至手段-技术领域。
语言内蕴着“自然”与“文化”的沟通,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洞悉人的历史性生成之谜,更为重要的是,“语言”(le langage)与“言语”(le parle)的区分,使得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有了几乎全新的入思角度:索绪尔强调了语言对于言语的深层次制约,但又积极肯定了言语的独特与独立。梅洛-庞蒂并没有简单停留于这一区分。索绪尔强调其研究是只讨论“语言的语言学”[4](42)。这种对言语活动的有意忽视,显然放弃了对个体生成的审视,当然也为现象学家们,特别是庞蒂留下了巨大的探索空间。在其论述中,庞蒂积极尝试否弃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等等的严格区分,这是“回到活的语言”的必然要求,“回到生活世界,尤其是由客观化的语言回到言语”[5](81)。“如果说从横断面考虑,语言是一个系统,它也必定在其发展中才会如此”[5](79),但从语言的实际经验出发来思考,就会发现活的语言是在历史中绽裂为多维度。这一系统必然在每一环节都包含有未经思考的事件能够进入其中的裂缝,交流、表达由此发生裂变,思想、意义由此得以衍生,这就是语言内藏的偶然性陷阱。因此,言语与语言、历时与共时的区分只是从静态、制度方面的设想,而非“语言现象学”所探寻的“活的语言”。事实上,这正是语言学与语言哲学(或曰语言现象学)之间的差异,也即索绪尔与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家的不同:后者较为关注语言的使用,而前者则习惯于从静态对语言进行分析。
言语,或者说活着的、正在进行的语言活动,确保了个人相对于历史的独立性。人来到世间,作为某种人类传统的必然继承者,很难说是完全的“新生”,但从第一声啼哭起,他或她却又开始了一种全新的表达,“就是把事物中意义与价值激发了出来”[6](436)。即我们的“赋意能力”(sinne-gebung)从此得以展开。这是我们的表达带给我们的真切自由,我们对于世界的赋意不是被封闭在已有的习惯和过往的历史积淀之中,而是不断涌现和开放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表达是赋意行为,即对于历史积淀的创造性把握。当然不可能回避对于语言、文化传统等等的继承,但是内蕴其中的未来向度,却使得个体不再完全被过去所奴役,具有决定性向自我实现的逾越,“每个现在再次证实它所追逐的一切过去的在场,预测了一切将来的在场,而且根据定义,现在并不封闭自身,而是向未来和过去超越”[6](420-421)。正是在未来与过去的交汇迸裂中,每个个体在当下才得以确立起自己。
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不仅意味着对于历史的隐秘传承,更是一个新的场域参与到世界之中,并积极参与先于他的其他场域。这种交汇重叠正是这个新生命必然负荷承载的普遍性,于其中,这一新生命开始了对于积淀意义的创造性把握。这是个体生命活动的承诺:因为意义积淀“只是一个趋向”[7](27),但并不封闭固守,而是期待每次看似相似却又绝不相同的创造性把握。如同一个未完成的作品的继续发散展开,他必须接受他人同样的索取与给予,所以说“赋意不仅仅是离心的,这就是为什么历史的主体不是个人。在普遍生存与个体生存之间、在所得与给予之间有着一种交换”[6](450)。个体生命对于世界意义的再次创造其实就是一次生存的投射,这种意向性的投射促使我们去创造未来,“我们每个人必然在绝对个体意义和绝对普遍意义上,都是隐匿的,我们存在于世,正是这双重隐匿的具体承载者”[6](448)。这可以说是知觉模糊性必然的升华式延伸。人在生活、历史中开始了自己的生命,人的意志当然也就不是纯粹的和完全自主的,它不得不受制于生存条件错综复杂的制约而具有了某种模糊性。但历史从未就此湮没人的意志与自由:每个个体对于意义的再次激发,正是我们不妥协于普遍性的确证,“因为这种有意义的生活,这种我所是的自然与历史的确定意义,没有限制我进入世界,反而是我与世界交流的手段”[6](455)。我们借助对于意义的承载与又一次激发实现着“处身于世”。
我们的表达使得我们甚至与自己有了深深的隔阂,而这种隔阂将在生命持续的表达中不断加深,进而升华:我们每个个体正是这样不断生成,我们承载着历史,我们分担着他人,但是却没有被历史和他人完全裹挟或者压制至“无”。每个个体通过其表达实现了对于意义的再生成,这也正是其生命活动偏离更大于继承的冒险,个体与普世存在于这样的表达中获得交流。我们通过赋意活动进入历史,并与所处处境的相互交织进而促成了历史的延伸。借助表达,我们与历史发生了交流,并不断拓展历史,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得以形成的耕耘模式。
身体共有着“自然”与“文化”。人的身体是“一个自然”,但是它带有各种象征意义,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并塑造人类文化世界。当我们进入世界,我们作为“身体-自然”绝非完全世界性的,但它决定了我们向着世界的召唤与开放。处身于世,就是使得世间万物随之成为主体,与其相互交流,对话,这就是主体间性的形成基础。文学,这种独特的言语现象,因此绝非再现现实或者为作家传情达意那般简单,而是通过与语言艰苦角力叩问了文化与历史的成形。
二、文学对于语言的含混的展现
前言表明《符号》这部专注研究语言符号的著作是“庞蒂与萨特进行对话的明确延续”[8](43),因此可以进一步说“梅洛-庞蒂的整个语言学思考的最初动机是回应萨特的《什么是文学》”[9](297)。萨特看重的正是文学特别是散文对现实的干预作用。他并不认同,甚至可以说敌视绝缘于现实、追求极度自律的唯美主义宣言及其文学追求,“我们应该既揭露英国在巴勒斯坦与美国在希腊推行的政策,也揭露苏联流放政治犯”[10](271)。因此,语词本身在萨特看来并不值得深究,即使其能带来审美与愉悦:“语词是透明的,目光穿过词语,那么在词语与目光之间塞进几道毛玻璃便是大谬不然。”[10](83)
支撑这一所谓的“介入-实践文学”的显然是一种语言工具论,也就是说,正是认定语言可以作为传达思想、意义的高效工具载体,萨特才将“文学”(散文)视作介入现实的必然通途。这种文学观其实是对前文谈及的笛卡尔、康德、早期胡塞尔等人视语言为意识的工具这一理论的进一步阐发和使用。针对战后法国乃至欧洲的现状,对于意在关注当下、思入现实的萨特而言,这一思路正是其力图针砭时弊、唤醒一代人的又一创见,因为他明锐地意识到“我们的语言还带有纳粹入侵的印记”[10](269)。此举其实也借机提高了文学的地位,进而动摇了哲学的权威:海德格尔后来批评萨特是在用文学方式来作哲学。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许正是萨特“想要的”。萨特希望哲学摆脱形而上学的桎梏真切关注现实,但哲学传统,或者说传统的哲学思考方式不可能如此“直达现实”。文学,准确地说,萨特所看重的散文似乎能更好地诀别形而上学传统,披露现实种种。但是,这种与形而上学的决裂是徒有其表的,因为文学至此并没有跨出再现论与表现论的桎梏。
梅洛-庞蒂则相信文学与形而上学在现象学视域中有着更为深刻且不同于以往的关系,因为现象学对于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使得哲学开始专注于对世界经验的描述。小说,特别是优秀小说对于世界(这也正是胡塞尔渴望的生活世界)的成功摹写已经使形而上学传统相形见绌。随着对于语言的关注,文学,这一特殊语言现象进一步表明:一、语言绝非思想的外表;二、语言有其难以被征服的沉默[11](43-45),这其实是对于“言语有一种意义”的理论的进一步展开。
第一,文体对于意义的初步重建。
梅氏认为,一部作品的意义首先不是通过其思想,而是通过语式、叙述形式或文学形式的变化表现出来。简言之,就是需要关注一部作品得以显现的形式。“在能够传达我们的某一独特思想的种种不同表达中,唯有一种是最好的。我们并不总是能够在说或写中与之相遇,但是它存在着确是无可质疑的。”梅氏认为法国作家让·波朗(Jean Paulhan,1884-1968)的这一名言值得反复思考,因为它表明了一个可能经常被忽视的真实,即表达形式之于表达的决定作用。在梅氏看来,文体这一表达形式对人类的众多文化活动都存在着根本的限定:“一部难懂的哲学著作至少向我显示某种‘文体’——斯宾诺莎的、批判主义或者现象学的,文体是著作的意义的最初显露,当我深入这种哲学思想的存在方式,再现哲学家的语气和风格时,我开始理解一种哲学。”[6](179)显然,梅洛-庞蒂于此所说的“文体”是诸多表达的“存在方式”,因此,一支乐曲、一幅绘画等等“如果真正说出某东西”,终究会获得认同,也就是说,“终将分泌意义”。在散文和诗歌中,我们似乎容易忽视这一表达形式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因为我们直面的是言语,我们也习惯于认为我们是通过它获得小说、诗歌的意义,这种认识又强化了语言是思想、意义的工具这一观念。但是,调色板上色彩或乐器的天然声音显然不足以形成一幅绘画的绘画意义和一支乐曲的音乐意义。这一事实提醒我们,从一部小说、一首诗歌获得意义绝非仅仅依靠单个言语及其组合就可以达到的。这些言语作为小说、诗歌存在的方式才是至关重要的,是这一存在方式成功实现了这些言语的融通、重组,使得它们成为一部小说、一首诗歌。“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与其说是由词语的普通意义所提供的,还不如说是归功于对于可接受意义的改变。”[6](179)
值得注意的是,梅氏于此提出我们具有获得调色板上的颜色、乐器的天然声响等等的“自然知觉”。与之相应,显然应该有一种使我们获得绘画意义、音乐意义、文学意义的能力,这种能力确保我们将言语重构为小说,将色块、线条理解为绘画,即梅氏所发现的人类行为独特的“格式塔”。成功的表达之所以能感染读者,甚至使其摆脱初始的厌烦情绪,正是在于这种“文体”对于读者的“深层次召唤”:文学的交流,不是作家对于所谓的先验意义的摹写,继而,读者直接获得这种意义。读者获得意义,表面看来似乎只是依循言语直达意义,实际上这一获得意义的过程其实要复杂得多。意义的获得需要更为隐蔽的“格式塔”展开运作,即读者从某一特定文体获取小说、诗歌、绘画等意义的结构能力。因而,文体“这种人类的语言学关系有助于理解象征与制度产生整齐秩序的平常关系”[11](45)。
第二,伟大的散文对于含混多义的守护。
梅洛-庞蒂对于“文体”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对于文体的惯常理解,其中也包括萨特对诗歌和散文的划分:“我们称为诗歌的东西或许不过是卖弄自律并就此得到认可的那一部分文学。所有伟大的散文也是对意指工具一种创新,从此这种工具将按照一种新的语法被运用。平庸的散文习惯于接触符号中已被文化安置于其中的含义。伟大的散文乃是获取一种到现在为止尚未被客观化的意义,并使它能被说同一语言的所有人理解的艺术。”[11](45)
梅氏在此对散文这一概念进行了拓展,也从更为深广的角度阐发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梅氏之所以看重文体,是因为他所关注的是一种表达方式是否能使表达趋向成功。一旦这种表达实现了对未被表达出的意义的成功表达,即使得“沉默经验”浮出历史地表,都可以归入梅氏所说的“伟大的散文”之列,而这也相当于诗歌:“全部有价值的散文——我理解为表达某种从来没有被表达过的东西、被写出来的东西——实际上都是诗歌”[11](338)。进一步而言,梅洛-庞蒂之所以看重诗歌正是因为诗歌在最大程度上展示了语言的含混性。梅氏认为象征派诗人瓦莱里的创作已经使得诗歌保护了这种含混,因为创作依然展示出:“词语一无所有,只是误解与误释的总和,这使其从本义趋向比喻义。因此他相信人类的哲学追问停止于人类将相互对立的意义统一于一个词语,这也是人们曾经意识到的危险,这依然只是再次过分认可理性。”[3](15)
瓦莱里对于语言含混性的理解,产生出所谓的“怀疑论”,即瓦莱里在多年的写作中所感到的疑惑:对于语言多义、含混有着深入的体会,但却无力征服。换言之,在一种既有的语言中,我们确实感觉到它对意义的绝对拥有,但在诗人、作家那里,并不存在着语言与意义的一一对应,尤其明显的是诗歌不打算说某种东西,这不是因为它缺少意义,而是因为它始终都不只有一种意义。在梅氏看来,诗歌的这种表现揭示出了一切语言的根本特性,即各种语言表达形式都在不断变化生成中,它们同样是多义、含混的,因此与诗歌仅仅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这种对于语言含混特性的理解来源于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意义差别的强调:“当我们读或者写时,话语的每一因素的意义应该被看作是通过它与话语的其他因素的差异才产生,同样,这一因素只有通过与第三因素的差异才有意义。”[11](341-342)梅洛-庞蒂则颇具开创意味地指出:语言在其肉身化过程中才是“活的语言”,即在交流中展呈身体间性,所以,读或写的人是在语言活动中失去了自己的主导性、所谓的初衷等等,最终,手足无措于这种难言的含混之中。梅洛-庞蒂通过对文学的研究,就是要证明含混是语言的根本特性:“我提出的并不仅仅建立在诗歌例子的基础上,这是一种可以被普遍化,可以运用到语言中的观念。”[11](342)
出色的诗人,在这一意义上是与那些伟大的散文家一样,那些成功的诗歌因此是与那些展示语言、经验之含混的表达形式相通的。可以直白地说,“我们生活在言语所建立的一个世界之中”[6](184),每一位真正的文学家都是在新的语言起跑线上谋划着创造,语言于其中不断重生,含混与模糊随之获得增长和暗示。“语言作为存在的亲临”[12](148),促成了人世,我们因此不可能逃避含混与模糊:“任何谈论模糊的世界如同曾经的模糊之计划,但是我们力求澄明,在那一时刻,我们澄明之处正是遏制模糊之处,我们想要确定、客观化,可是她离开得更远。”[11](343)人类历史充满了含混或者时刻孕育着含混,也就不足为奇。文学,这一最为独特的语用现象,其伟大因此并不在于对于人类经验的成功摹写,而是通过这种摹写,让我们体会到了存在良久的沉默,及其含混孕育的诸多可能性。
三、审美过程中的意义增殖
依照语言是思想、意义的载体这一观念及萨特对于“介入文学”的有关论述,写作与阅读将是一个意义流通的单向过程。原因就在于,倘若语词仅仅是意义的符号,那么它们汇集而成的文本就可以全无偏差地反映出作者的思想。“言语本身没有任何效力、没有任何能力掩蔽在言语之中。它是一种代表纯粹含义的纯粹符号。说话者将自己的思想编成密码,他用一种发声的或可见的排列——这不外乎是空气中的声音或者写在纸上的墨迹——取代他的思想。”[3](6)文本的价值莫过于作为思想、意义的完美载体,这再一次确保了思想的自知自足与纯粹。阅读成为接受这种思想的另一端,阅读者也谙熟依循这些符号去寻觅思想的把戏,会主动把意义贴合到符号上去,所以,不会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在这一过程产生。也就是说,阅读于此变成了了无新意的自画自说。
首先,这种阅读效果显然与真实状况不符。因为,倘若言语仅仅是思想、意义的符号,毫无偏差地保持着与意义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么,作家所传达的意义将是单一的,读者所得的意义也将是一种惊人的一致。所以,对于同一文学文本的众多阐释就绝无可能,事实是,“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种现象已经存在了千百年,对于同一文学文本天差地别的解释多达难以计数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
其次,虽然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表示,写作既是揭示世界又是把世界当作任务提供给读者的豪迈之情。这在一定程度否定了被动的写实主义,而且还在强调作者主动性、自由、风格、创造性的同时也肯定了读者的主动性、创造性,甚至认为阅读使读者有“从头至尾创作这本书”的激动感受。不过,这些说法与萨特对于语言、文学的基本看法似乎没有直接逻辑关系,换句话说,缺乏理论基础。因为依循萨特,“介入文学”所依赖的语词与意义保持一一对应,显然使得意义趋向明晰、单一,这自然使得写作、阅读的主动性、创造性降至最低。
上述这种写作、阅读观念,被梅洛-庞蒂称为“纯粹语言的幻象”:这种机械的写作、阅读理论根源于对语言的机械理解。对于梅氏而言,走出这一困境就是从自己所发现的语言是含混、多义的这一创见出发,对在萨特思想中已经萌芽的这些写作、阅读理论进行拓展。其前提就是走出萨特对语言、文学的狭隘理解。
梅氏指出,“如果这本书只不过说了些我所知道的东西,它就不会使我这般感兴趣。借助于我带来的一切,它把我引向我已经知道的东西之外……它处在我的世界之中,然后,它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那些符号的通常含义,它们就像旋风一样把我卷入我可能通达的其它意义。”[3](9)这其实是对于“处境”理论的进一步发挥。读者阅读文本,其实是读者这一场域与文本这一场域实现的某种奇异融合,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场域。文体即这种表达的存在方式使得语词符号的含义发生变化,从而也使得阅读者被这种意义场域包围。
进一步而言,读者与文本之间形成的是一种身体所决定的“间性关系”,梅氏甚至用“恋人关系”来说明两者之间难言的亲昵:“读者的忠诚不过是存于想象之中的,因为它从这本书所是的可怕机器中、从这一创造各种含义的装置中获得力量。读者与书的关系类似于相爱的两个人。”[3](11)
在这种“间性关系”中,阅读使语言的意义发生增殖,听或者读都不是固守某些既成的意义,所谓的作家更是需要使语言生发出一些陌生。进一步而言,阅读其实是一个新的现象场的形成,读者与作品,甚至读者与作者,都有着交汇,而非单向度的意义传递,内在生发的意义将在不间断的涌现中突破自身。“阅读是我的言语自命不凡的、不可触知的躯体和有着同样躯体的作者言语的一种遭遇。如同我们所说过的,阅读的确超出于我们自己的思想把我们投射到了他人的意指意向中,就像知觉超出于我们,只是在事后才发觉的视角把我们投向事物本身一样。”[3](12)
梅洛-庞蒂于此试图论述证明,阅读作为读者言语与作者言语的遭遇,其实是两个场域之间的融合,因此内蕴着一种建基于身体、知觉之上的“间性关系”。值得注意是,梅氏在此使用的是“类比法”来说明阅读与知觉的相通相似,这自然可以理解为便于他人理解,但更为贴切的解释应该是,阅读、知觉及两者之间的相似,其实都是难以精确描述的,或者说根本就无法描述,例如我们如何用精细的语言来描述在阅读时两种言语融为一体时所产生的风起云涌般的剧变。进一步而言,阅读现象其实与知觉保持着一个极为亲近的距离,因为阅读使得两种言语、两个场域实现了交融,自我局限由此真正被逾越。身体-知觉根本上所有的“难以言传”神秘在于确保意义不断发生激变,进而获得增殖,这种可能维系于身体对于这一超越唯我论的层面的决定性支持。
四、文学作为存在的铭写
这样,梅洛-庞蒂就通过对文学的各个环节的探讨,证明语言绝非萨特所说的那般是单义、透明,或者说,文学是将语言的多义、含混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场域。梅氏并没有停步于此:语言的这种特性,对于他而言,正是那把打开人类文化与历史的隐秘之锁的钥匙。
语言的出现是以交流、沟通为前提的,所以容易被视为工具,但语言并不是征服自然的工具。之所以内蕴着自然与文化这看似难以调和的两级,就在于在其内部有着向自然不断回溯的动力源,因此一直在变异,并由此获得一种强健的自主性,从而使意义的生成改变了自然主义式的传递模式。换言之,符号其实并不会顺从地传达意义:“自起始,符号就是可区分的,符号构建自我,符号有其内在世界,终究需要一种意义。在符号旁边生发出的这种意义,整体在部分中的这种接近,处在文化的历史之中”。[13](52)这种自主性才真正促成文化和意义的不断增长,所以“文化从不给予我们绝对透明的意义,意义的发生从来都是未完成的。我们从来都只是在那些注明我们的知识之时间的符号背景中,思考我们有充分理由确定为我们的真理的东西”[13](53)。真理的“被认定性”,揭示出我们所有的符号背后的巨大阴影:语言的含混、多义正是文化的不透明性的写照,但文化的流动、含混与语言多义、朦胧的“天性”又相互背离:意义衍生于语词的相互嵌合及其缝隙,表明语词相互间嵌合,排斥,进而构成力场。
在此基础上,梅氏直白地承认了语言的不透明特性:“因此存在着语言的不透明性:它绝不会不停地让位于纯粹意义,它从来都只是受到语言自身的限制,意义只有嵌入在语词中,才会显现于语言中”。[13](53)语言其实是意义与不透明性、含混等相互角斗的场域,借由语词获得表达的意义其实只是暂时的,它无法长久、稳定地停留于此。
抛开附加在语言之外并认定语言需要倾尽所能去表达的意义范本,含混特性就逾越功利层面,而使语言获得相当的自主性。语言由此诀别了传输意义之简单工具的固有形象,“任何语言都是间接或者暗示性的,也可以算是沉默。”[13](54)言语不再可能如我们一贯认定的那样,服服帖帖且必须一一对应。
梅洛-庞蒂因此表示,真正具有表达力的言语,并不只是为一种已经确定的意义选择一个符号,就像人们使用日常工具那样便利顺手。[13](58)我们(包括作家)对于语言的使用其实都是某种强迫,即为了借由语言表达我们的思想而扼制语言本身的非透明性。作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通过写作与语言无限接近,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语言绝非可以轻易制服的,而他自己已经被深蕴在语言中的多义、含混所包围。正是于此,言语活动才能如胡塞尔所愿,对于固有的分离,诸如“可能与现实、本质与存在”[11](112)进行切实粘合。
文学这种独特的语用现象在梅氏看来具有其他表达方式所不及的优势,它可以探入“不可见者”——沉默之经验:“我们应该探究在被说出之前的言语,始终围绕着言语,如果没有它言语就无法说出任何东西的沉默背景。”[13](58)这正是“最困难之处,也即肉身与观念之间的联系”,如果继续使用形而上学的概念系统,就注定只能错失这种机会,我们应该给予文学乃至艺术等等充足的信任:“音乐的观念、文学的观念、爱情的辩证法,还有光线的节奏,声音和触摸的展示方式,它们都在对我们说话,它们都有自己的逻辑、一致、交汇、协同,而且在这里也一样,现象是未知的‘力’和‘法则的伪装’。只不过这些未知的力、法则所是的秘密以及文学表达从之抽取出自身秘密似乎就是它们的存在方式’。”[7](153)文学这种语言方式的独特价值就在于通过逼迫语言,超越了形而上学的方法及其局限,切近并展示了存在,用感性的方式使得那些难以言明但却真实存在的“不可见者”随着可见者一起显身。
梅氏甚至认为文学势必促成哲学的革新,因为哲学作为“对于存在的追问”,作为沉默经验对自身的表达,始终坚持着一种创造。“艺术和哲学整体并非‘精神世界’(文化世界)中的任意创造,而是作为创造与存在的接触。存在就是为使我们从创造那里获得经验而要求我们进行创造的那种东西”,所以可以“在如此意义层面上分析文学:这是存在的铭写”[14]。由于存在作为动态的、通过人类活动展示自身的绽现,即所谓的“源初的东西并不在我们的背后——源初的召唤来自许多方向:源初的东西突然绽现出来”,所以,“必须伴随这一绽现、不一致、差异化”[7](15),通过语言这一导向“主体间性”的真正领域,我们才可能体会到我们与存在之间这一源初的亲密关系。文学这种守护语言自身含混性的语用方式,在其感性场域中实现了这种可能。
[1]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商务印书馆,2005.
[2]Chiasme International:Publication Trilingue autour de la pense de Merleau - Ponty,Vrin;Mimesis;University of Memphis,1999.
[3]Merleau - Ponty.The Prose of The World[M].trans:John O’Neil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3.
[4]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2004.
[5]Merleau - Ponty.Eloge de la Philosophie[M].Paris,Gallimard,1953.
[6]Merleau - 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otion[M].trans.:Colin Smith,Routledgy and Kegan Paul,1962.
[7]Merleau - Ponty.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M].trans:Alphonoso Lingi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8.
[8]Claude Imbert.Maurice Merleau - Ponty[M].Paris,Janvier,2005.
[9]杨大春.感性的诗学:梅洛-庞蒂与法国哲学主潮[M].人民出版社,2005.
[10]萨特.萨特文学论文集[Z].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11]Merleau - Ponty.Parcours deux,1951 -1961[M].Paris,Verdier,2000.
[12]Merleau - Ponty.Les Notes des Cours,1959 -1961[M].Paris,Gallimard,1996.
[13]Merleau - Ponty.Signes[M].Paris,Gallimard,1960.
[14]Merleau - Ponty.Le Visible et l’nvisible[M].Paris,Gallimard,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