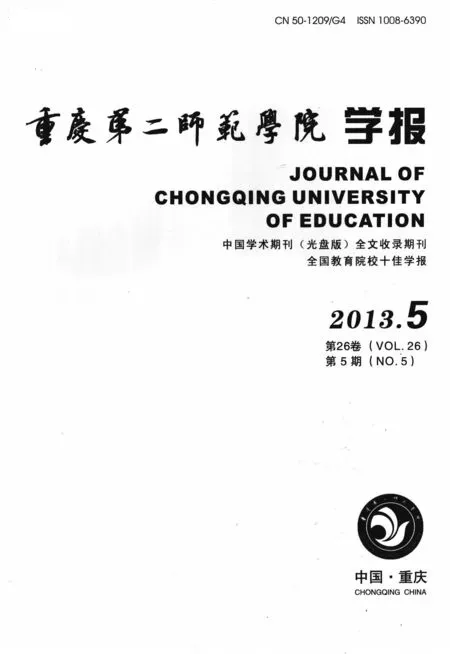西汉作家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2013-04-02汪耀明
汪耀明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对于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贾谊实际上以创作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表明自己观点。
作为汉初著名的文学家,贾谊创作了不少言之有物、言之有情、言之有序和言之有采的优秀作品。散文如《陈政事疏》、《论积贮疏》、《过秦论》等,它们展现历史和现实的生活画面,研究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提出作者的政治见解和治国措施,显得内容丰富、气势充沛、议论深刻、修辞出色。辞赋如《吊屈原赋》、《鵩鸟赋》等,它们表现出作者对社会正气的弘扬,对黑暗现象的抨击,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和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字里行间充满感情,富有文采。
这样的散文和辞赋自然显示出贾谊能意识到文学作品的内容对形式起决定的作用,形式是为表现内容服务的,适应内容需要的完美形式能够充分体现内容的价值,大大增加作品的艺术力量,内容与形式应融为一体。因此,他写作散文、辞赋,注重作品的思想感情和现实意义,讲究谋篇布局、表现手段和语言运用,力求作品丰富、深刻的内容与和谐、完美的形式结合。如果贾谊没有这样的认识和追求,恐怕他就写不出那些成为千古书疏典范的散文和感情浓郁、令人荡气回肠的辞赋。
在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上,自贾谊通过创作活动显示思想认识以后,西汉作家有的在创作上,有的在理论上,各自反映出或表现了与贾谊的认识相同的和接近的文学意见。这些文学意见是对贾谊文学认识的补充和发挥,进一步充实了西汉文学思想。
邹阳、枚乘都以文辞著称。前者曾为梁孝王客,遭谗下狱,就写了《狱中上梁王书》,申诉冤屈,表明心迹。文章引经据典,善于修辞,颇有纵横善辩之风。名为散文,实则赋体,气盛语壮,情真辞巧。后者的《七发》劝谏统治者不要沉迷音乐、饮食、车马,进而以田猎、观涛来启发,最后要太子听取圣人辩士的要言妙道。全篇表现出深刻的思想性和鲜明的讽喻性。同时,作者还指出辞赋创作应把众多事物的名称种类连缀、归纳起来并加以繁征博引。
司马相如《哀二世赋》指出秦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史记·司马相如列传》)[1](P3055)。作品所指责的正是贾谊《过秦论》所议论的和有关史书所描写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贾谊之言说二世“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1](P284),还记载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1](P271),信谗拒谏,死到临头还怪身旁宧者“何不蚤告我”,宧者回答“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诛,安得至今”[1](P274)。这篇赋以简洁朴素的语言充分说明史论与史实所包含的深刻道理,显得意味隽永。
司马迁《史记》里的许多人物传记,不仅包括丰富的思想内容,也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显示出内容与形式的审美性统一。
《留侯世家》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作。作品记载张良辅佐刘邦平定天下、完成帝业的全过程,通过破秦入关、计取项羽、分封雍齿、定都关中和保全太子等重要事件,充分显示了张良审时度势、谋略过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特点。
破秦入关,初露锋芒。张良开始协助刘邦进攻峣关之下的秦军时,就抓住对方守关将领易为财帛所买动的弱点,建议刘邦派郦食其以珍宝诱买秦将。在敌将得利而放松防备后,他又提出乘机打败对方。这说明他知己知彼,处事果断。刘邦直捣咸阳,进入秦宫,就流连忘返。对此,张良指出应胸怀远大,不要耽溺享乐。这显示他具有政治眼光。刘邦还军霸上,项羽兵驻鸿门,准备以绝对优势战胜对手。张良想方设法,成功地利用与项伯的特殊关系,针对项羽沽名钓誉的心理,劝说刘邦以卑词厚礼假意臣服对方,以解燃眉之急。鸿门宴上,他还帮助刘邦化险为夷。
计取项羽,智慧惊人。刘邦曾按照郦食其的建议,决定复立六国后代,使他们感激和追随自己,共同打击项羽。张良认为分封六国后代是极不高明的,如果照此办理,必将前功尽弃。传记一连用了八个排比句,详细记述了张良的正确意见。它们把历史经验与现实可能进行对比,又把客观存在和主观愿望作一比较,还把人们言行与心理联系起来。这就表明张良善于分析天下形势,深入了解人们心理,积极掌握楚汉战争的主动权。当韩信平定齐国而要求暂摄齐王之位时,刘邦起先不能容忍,听了张良的劝说后,才“使良授齐王信印”[1](P2042)。张良劝刘邦为灭楚大业而对韩信求封一事表示同意,这显示了他深谋远虑,随机应变。从过去反对复立六国后代到现在主张暂时分封韩信等人,这反映出张良是灵活多变的,他看到楚军将败的新形势,就及时提出明智的应变措施。
分封雍齿,防患未然。刘邦夺取天下后,由于分封不均,众人议论纷纷。张良指出刘邦所封之臣都是其所亲爱的人,所杀之臣也全是其所怨恨的人,自然,大多数就不满以亲疏关系分封,也担心天下有限的土地不足分封,还有些与刘邦矛盾已久的人更是害怕刘邦借机报复,这将不利于局势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他强调只有公正地分封功臣,尤其要首先分封像雍齿那样与刘邦意见不合而劳苦功高的人,才能消除嫌隙,赢得人心。这些生动地表明张良能够见微而知著,防患于未然。
定都关中,言之成理。张良力排众议,支持刘敬建都长安之策,说明不能定都洛阳的道理。传记突出了张良的正面主张,它先以“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这种骈散相间的语句排比铺陈,显示关中地区的地形便利;接着以“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与“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对举,显示交通运输的方便;再以“金城”与“天府”互称,突出关中之地坚固如钢,物产丰富;最后在充分说理的基础上,以简短之句点明“刘敬说是也”[1](P2044)。
保全太子,计出万全。张良对刘邦以个人偏爱而随意改立太子的做法不无意见,但还是出谋划策,保全太子,避免由废易太子而可能引起政局的不稳,从而为维护西汉初期的稳定局面作出一定的努力。考虑到当时很难用言辞使刘邦回心转意,张良就提出一个两全其美的计策。此计根据刘邦非常尊重商山四皓的特点,建议派人卑辞厚礼,请他们来辅佐太子,造成太子深得人心、拥有势力的局面,以此使刘邦翻然改图。果然,吕后等人按计行事,而且行之有效。
总之,《留侯世家》真实地记叙了张良帮助刘邦夺取了天下和巩固政权的重要言行,鲜明地突出了他聪明睿智、多谋善断的特点。通过刻画张良的形象,作品反映了秦末、楚汉之际和汉初历史的真实情况,也自然流露了作者对张良的赞赏之意,这表现出作品深刻的丰富的内容。同时,《留侯世家》为成功塑造人物形象而出色运用的多种表现手段又构成了作品的形式。这篇优秀作品基本实现了充实的内容与完美的形式具有审美价值的内在统一。
从邹阳、枚乘、司马相如、司马迁等人的创作实践和西汉许多辞赋、散文表现出情感与文辞并茂、事理与文采兼顾的情况来看,作家主观上应有一定的自觉性去积极争取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
不仅如此,《淮南子》与刘向、扬雄还对文学实践进行辩证的总结,论述文与质的问题,讲究两者的完美统一,表达了对文学艺术创作中内容与形式关系的正确看法。
《淮南子》肯定文质关系中质的主导作用,但又不一概反对文饰,而是强调文与质相结合,内容与形式相统一。
《本经训》说:“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则乐,乐斯动,动斯蹈,蹈斯荡,荡斯歌,歌斯舞,歌舞节则禽兽跳矣。人之性,心有忧丧则悲,悲则哀,哀斯愤,愤斯怒,怒斯动,动则手足不静。人之性,有侵犯则怒,怒则血充,血充则气激,气激则发怒,发怒则有所释憾矣。故钟鼓管箫,干鏚羽旄,所以饰喜也。衰绖苴杖,哭踊有节,所以饰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钺,所以饰怒也。必有其质,乃为之文。”[2](P265-266)它认为人们一旦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内心就会产生喜怒哀乐的感情,而且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质是决定文的内容,文是表现质的形式,有什么样的质就有什么样的文。
《缪称训》说:“锦绣登庙,贵文也;圭璋在前,尚质也。文不胜质之谓君子。”[2](P323)《说林训》说:“巧冶不能铸木,巧工不能斫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质有余也。”[2](P582-P583)它们指出不应使文饰的东西胜过内在的根本,具有质美的事物是自然美好的,也是不必过多文饰的。这种质或是物的本性,或是人的外貌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说山训》说:“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丑。……美之所在,虽污辱,世不能贱;恶之所在,虽高隆,世不能贵。”[2](P546-547)《说林训》说“石生而坚,兰生而芳,少自其质,长而愈明”[②](P577)。《修务训》说“曼颊皓齿,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泽而性可说者,西施、阳文也”[2](P639)。这些充分说明《淮南子》重视质美,强调内在的美比外表的美更为重要。不过,它并不反对外表的美,也不否定必要的文饰,而是认为美质一经文饰就愈增其美。
《修务训》说:“今夫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衔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带死蛇,则布衣韦带之人,过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尝试使之施芳泽,正娥眉,设笄珥,衣阿锡,曳齐纨,粉白黛黑,佩玉环揄步,杂芝若,笼蒙目视,冶由笑,目流眺”,这样“虽王公大人有严志颉颃之行者,无不惮悇痒心而悦其色矣。”[2](P658-659)它指出如果天下的美人毛嫱、西施佩戴丑恶之物,一般的人就会掩鼻而过,毫无兴趣;如果她们经过梳妆打扮而显得容姿更为漂亮,就连庄重严傲的王公大人也会油然而生爱慕之情。
因此,它强调只有把质美与文饰结合起来,才能使事物放射耀眼光辉,显得更加美好。《俶真训》说:“百围之木,斩而为牺尊,镂之以剞劂,杂之以青黄,华藻鎛鲜,龙蛇虎豹,曲成文章,然其断在沟中,壹比牺尊、沟中之断,则丑美有间矣。”[2](P59-60)
这种重质而不废文的观点比起先秦法家重质不重文的见解要全面、合理些。显然,《淮南子》不是重质轻文,而是注重质美兼取文饰,并使质美与文饰融为一体。
刘向论述了文质关系、诗歌写作和谈说之术。
就文质问题而言,他的论述并非议论文学,而是谈论人们的思想品德与文化修养、事物的功利与审美等的关系。不过,所言实际上表达了他对作品内容与形式之间关系的见解。《说苑·修文》说:“孔子曰:‘可也,简。’简者,易野也。易野者,无礼文也。孔子见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弟子曰:‘夫子何为见此人乎?’曰:‘其质美而无文,吾欲说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门人不说,曰‘何为见孔子乎!’曰:‘其质美而文繁,吾欲说而去其文。’故曰:文质修者谓之君子,有质而无文谓之易野。”[3](P498-499)它又指出“《诗》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质美也”,“德弥盛者文弥缛,中弥理者文弥章也”[3](P478-479)。《说苑·反质》谈到“圣人见人之文,必考其质”,“君子虽有外文,必不离内质矣”[3](P512-513),还引用墨子的话说“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3](P516)。所言肯定质美,批评有质无文,主张文质相称,辩证地论述了文与质的关系。
就诗歌写作和谈说之术而言,刘向发表了有关内容与形式问题的正确意见。他指出诗歌是人们感情内积、满而后发(《说苑·贵德》)的结果,这反映出他是强调作者抒情言志、注重作品思想内容的。同时,对于表现作品思想感情的外在形式,尤其是形式之一的语言,他也很重视,认为“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说苑·善说》说:“诗云:‘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夫辞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无辞,安所用之。’昔子产修其辞而赵武致其敬,王孙满明其言楚庄以惭,苏秦行其说而六国以安,蒯通陈说而身得以全。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而说不可不善。”[3](P267)这表明刘向认识到语言文辞在抒发作者感情、描写作品内容时的重要作用,人们应该研究语言文辞,擅长谈说之术。
刘向自己更是通过出色的言辞来议论时事政治、表达文章内容的。《汉书·楚元王传》记载他上疏言事,“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4](P1958)统治者闻言感动,这说明了刘向文章言之有物,理在其中,情溢文外,表现手段灵活多样,语言文辞丰富精美,令人不得不信服和赞叹,也充分显示出他注重内容,讲究形式,努力使两者巧妙结合。
扬雄就文与质的关系问题,发表了华实相副、事辞相称的文学意见。
扬雄首先肯定质即内容的主导地位,又谈到文即形式的重要性,强调质与文即内容与形式应该有机结合。《太玄·太玄莹》指出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5](P281)。《法言·吾子》说:“或曰:‘有人焉,自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门,升其堂,伏其几,袭其裳,则可谓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质非也。’‘敢问质?’曰:‘羊质而虎皮,见草而说,见豺而战,忘其皮之虎矣。圣人虎别,其文炳也。君子豹别,其文蔚也。辩人狸别,其文萃也。’”[6](P71-72)扬雄认为质与文、内容与形式比较,质是主要的,本质决定文采,内容对形式起决定的主导作用。文是并非质是,质是影响文是。貌合神离、羊质虎皮、文是质非、名不副实是不行的。因此,他赞美素朴有质的佳作,批评过度文饰的作品。《太玄·文》说:“大文弥朴,质有余也。”[5](P142)《法言·吾子》说:“或曰:‘女有色,书亦有色乎?’曰:‘有。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6](P57)作者极为讨厌白白浪费光阴的雕琢纤细之作和搅乱典则法度的淫滥辞采。
不过,他的《法言·寡见》在指责当时不少学者“非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绣其鞶帨”的不良倾向时,并不反对必要的文采和优美的形式,而是主张文饰,指出文章不能没有形式文采之美。它说:“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谓也?’曰:‘玉不雕,玙潘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6](P221)作者不赞成“良玉不雕,美言不文”的说法,认为玉不经雕刻,玙璠之类的美玉也不能成为器物;言没有文采,典谟之类的书籍也不能作为经典。
于是,扬雄进一步提出华实相副、事辞相称、文质一致的文学观。《法言·修身》说:“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6](P97)《法言·吾子》说:“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6](P60)作者认为内容充实而华采缺乏就显出粗野,华采多余而内容贫乏就好像商贾,事理胜于文辞就不免率直,文辞超过事理就如同作赋,只有内容与华采相副,事理与文辞相称,才符合礼义与经典,从而达到作品的最高水平。
此外,《法言·先知》也说圣人“文质者也。车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声音以扬之,《诗》、《书》以光之。笾豆不陈,玉帛不分,琴瑟不铿,钟鼓不抎,则吾无以见圣人矣”。[6](291)《太玄·文》谈到“阴敛其质,阳散其文,文质班班,万物粲然”。[5](P142)《太玄·太玄错》说过“睟文之道,或淳或班”。[5](P254)它们都包含了文质并重、丰富的内容与完美的形式相结合的意思。应该说,扬雄有关文与质即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见解是辩证而深刻的,也是符合文学艺术本身的特点和规律的。
这样的见解同样反映在作者的文学实践中,他在写作时力求作品既有内容又有文采。他的一些辞赋铺采摛文,体物叙事,显得内容丰富、形式美观、两者渗透。扬雄在辞赋写作方面的成就也表明他既重质又不轻文,主张文质兼备。
上述西汉作家或在创作中反映他们的认识,显出作品的内容是艺术化与形式化的内容,而形式又是适应内容、富有意味的形式;或在理论上发表各自的观点,强调质与文密切相联,质决定文,文表现质,质与文应该完美统一。
这些充分说明当时人们对内容与形式关系的问题,能从前人的思想认识和理论观点中受到启发,又通过自身的创作活动和理论探讨,有所发挥,更加注重和追求作品内容与形式在审美高度上的统一,从而显示了西汉文学创作的实绩和文学思想的成果。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向宗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郑万耕.太玄校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6]汪荣宝.法言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