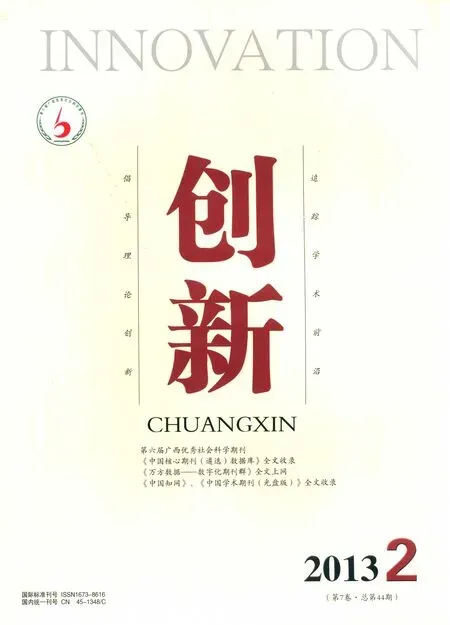生态文明重建的欲望之镜
2013-04-01王云鹏
王云鹏
欲望是人类一种最基本的、最原初的本能,它作为人类生活进步的动力极大地改变了人的物质世界,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然而,欲望的泛滥也造成了巨大的资源的浪费、人的精神的空乏,导致了现代的生态危机的发生。现代生态文明的重建,必须对欲望进行重新的定位和合理的规范。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而美丽中国建设,不仅仅是美丽中华河山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国人美丽心灵的建设,这其中也包含着对国人人文素质的全面提升,也在于构建一种新的生态文明观下的欲望的合理生成机制。
一、欲望“神话”的破灭
《易传·系辞下》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为中华文明首德,为中华民族延续之所系,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承之所在。但是这种不断生发的欲望,在中国几千年来并不完全被主流社会所推崇,尤其是宋明理学后的主流文化所推崇的是“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道德规范。而西方也经历了经院哲学“禁欲主义”时期。在这些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人的欲望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经过启蒙运动,进入到资本主义阶段以后,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人类的自由程度不断拓宽,人类的欲望也不断地被挖掘出来。
欲望的挖掘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对人的好奇心的全面开发。人的好奇心是科学家的发明创造的重要源动力,此外还诱使人们购买各种新鲜奇特的、未曾拥有的商品。二是工业社会中资本的不断扩张。这两个因素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使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人的依赖性,实现了在物的依赖的基础上人的相对的独立性。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交往范围得以不断扩大,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人想占有更多的对象,也有能力占有更多。同时,在双重动力的推动下,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77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这种创造了巨大财富的资本的文明作用,因为它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同时使人的丰富的感性需要成为现实,“随着艺术和科学的普遍进步,我们的视野扩大了;随着生产的增长,我们的需求也多样化了”。[2]人的感性世界的多样化必然会导致人的欲望多样化。
这样一来,如果人的各种复杂欲望不加限制,就势必会无限膨胀。这种欲望并不是人们希望得到更多的精神层面的对象,绝大多数都表现为物欲。而这种物欲如果任由其无限膨胀,则会对自然和人造成极大的危害。正如马克思1856年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所讲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775人类文明的一切进步,在工业文明阶段仅仅被对象化为物质,人类成为自然的奴隶,人类的生命的一切与外在的物质世界进行了颠倒,人类越来越成为外在的物质形态塑造的物欲的人,外在的物质被赋予了人的生命并反过来统治人,人丧失了真正的自己生命的本质。如同卢梭所描述的,“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的一切更是奴隶”。[3]一方面,人在这种物化的导向下,成为外在的物质的奴隶;另一方面,人类也逐渐的被这种外在的物质逐渐塑造,不仅包括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等,而且包括人的精神思维方式,人被全面地塑造成为充斥着物欲的人,自我欲望膨胀的人。而在这种膨胀的欲望中塑造了人类可以战胜一切的“神话”,这种“神话”促使人类不断对自然进行索取,最终带来的却是“自然的报复”——臭氧空洞、温室效应、人口爆炸、物种灭绝、资源枯竭、土地沙化等一系列的危机。
人类的欲望在塑造着物质的“神话”的同时,也塑造着精神的“神话”,即人类不断享受一切就可以带来幸福。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如同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所指出的,“这一推论与现在流行的这些相悖,流行的观点认为,既然密集度的小幅增加能丰富人类的生活,那么无限的增长就能无限地丰富人类的生活。生态学认为,不存在服务于无限扩展边界的密集关系。由增加密集度得来的额外利润都必然伴随着回报的缩减”。[4]337这就是说,欲望并不是无限制的,欲望的满足有着边界的效应,人们走入了物欲满足的怪圈,物欲走到了满足的极限,带来的并不是幸福,而是沉溺与痛苦。幸福和欲望之间并不是直接对等的关系,两者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相比的关系。“过”与“不及”所得到的是同样的效应和效果。欲望的“神话”从“不及”走向了“过”,也走向了它的破灭。
这种过度的欲望“神话”,带来的不仅仅是个体的心灵、人格、生活的紊乱,更为严重的是整个国家、社会的欲望过度,它以强大国家机器、市场机制、经济纽带,通过强大的生产、消费力量的带动,形成强大的物质壁垒,把人圈在其中,让人迷失其中。同时,通过国家工具向个人不断地进行外在的灌输,从而使个人在社会化中认同这种不合理的因素。这是个双向的运动,个人的欲望通过消费、交换等方式,不断的外化物化为外在,连成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一体的强大的壁垒,而反过来,这个强大的壁垒构筑的围城,约束人自身,使得人类迷失其中。人把自己圈存在自己构筑的物质壁垒中,外在物质成为强大的力量,人自身成为实现自我的、向外诉求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人自身成为被自己所轻视的,甚至是蔑视的事物。真正的事实是,外在壁垒的越坚固,越说明了人的内在的匮乏和缺失,人自身的真正的自我的缺失。人在过度欲望的驱使下,把自己带入物欲的“迷宫”中,信仰着欲望的“神话”。最终,生态危机打破了这个“神话”气泡,以人类生死存亡的选择的形式把真实的世界摆在人类面前。人类自我吹起的欲望“神话”的气泡破灭了。
二、欲望的回归和重建
欲望“神话”的破灭,并不是说整个人类都没有了希望,而是如狄更斯所说的时代是一个“物欲横流、欲望泛滥”的最坏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希望的春天”的最好的时代,也就是说,欲望“神话”的打破,使得人类有可能进行最彻底的反思、最深入的实践,带来人类发展的机遇。对欲望的反思和重建,并不是要对其进行堵塞,要如同大禹治水一般,对于欲望进行合理疏导以及规范,给予其适当的生发和合理的疏解途径。这不仅需要从国家机制的角度调整,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建设相契合,还要从个人的角度进行思想上引导、道德上规范、行为上约束。主要做到以下几大方面:
(一)做到生之有度
作为西方两大生态主义流派之一的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对人们的欲望进行规范,就要使人的欲望,从“感性的欲望”上升为“理性的欲望”,欲望并不能仅仅停留在感性的自发的阶段,而要以理性对欲望进行规范。如何对其进行规范,中间存在着度的问题。对此,英国生态社会主义者戴维·佩珀明确指出,“每一个人的物质需要都有自然的限度。因此,这些需要都能够在大自然所能包容的生产力发展的范围之内得到满足”。[5]在这里戴维·佩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界定了人类的需要的度的标准,它既不是空泛的精神标准,也不是空想的超时空标准,而是历史的现实标准,即是每个人需要的限度与自然所能承受的范围及其生产力发展直接的均衡协调而得出的一个度,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限度。这个度既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又是有着客观的规定的。同时,把生产力与自然的包容力结合起来,提出切实可行的标准。
这个标准的规定,并不是仅仅限制一个方面,而是对三个方面的限制,即是:人的需要的限度、自然的承受力和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三个解决生态危机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这三个方面也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类的需要是不断变化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是不断改变的,自然的承受力度也是不同的。它们各自的度的标准也不相同:人的需要的度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人之间的需要是不同的;自然的承受力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不同技术水平下、不同历史阶段规范的标准也应该不尽相同;生产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不同人群中分布也是不同的。但是同时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这三者又统一为现实的度。这样既从内在对人进行约束,也从外在对自然承受力提出客观的标准,还与历史的生产力发展相结合,把时间和空间、内在和外在、精神和物质、抽象和具体同时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对人类的行为的“度”的比较合理的、全面的规范。
(二)做到生之有术
当代,人类处理与自然的关系的行为是一种失范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它一旦形成就成为人们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一种惯性。因此,行为的改正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并不是出一个标准就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人类的不断重新学习、练习,从而内化为习惯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完全自发的,它是一个不断地教育的过程。
自然教育并不是今天才有,但是,到了今天工业社会中,一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思维方式都被打破;而有些传统的人与自然相处模式没有被正确的、有效地传承下来,新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又没有建立起来,造成了当代人的失范行为。因此,需要重新再教育、再学习。但是,这种教育和学习也并不是要回到老子在《道德经》中所描述的状态:“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而是在现代社会中寻求适合现代人生活和生产的欲望教育方式。
每个时代的文明程度不同,每个时代的环境现状不同,每个时代所需要的环境教育程度和方式也不同。但是,无论怎样的欲望教育、生态教育方式,都是对人的无限制的生理需要的制约。弗洛伊德指出,“我坚信人类文明是以牺牲原始的本能为代价而创造出来的”。人类文明的进步总是对人类的生理需要的一种有序的规导,这种有序的规导就是一种欲望的教育方式。在欲望教育中,就是要使得人真正的意识到,如何正确地、合理地生发人的欲望,生发人的何种欲望,以什么样的途径发挥。这并不是对人性的压抑,而是对人的欲望的一种符合社会、历史条件的疏导,而这也是人类正确的追求幸福的方式。叔本华就曾明确指出,“所谓幸福的人生历程,即是让欲望和满足彼此消长、交替出现的间隔,调整在不太长不太短的时间内,使二者各自产生的痛苦——贫乏和无聊——减小到最低限度”。[6]人的欲望是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欲望的教育目的就是既要给人以满足感,同时又激励人一定程度内的欲望,使两者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同时这种“度”的限制是在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条件下的。
(三)做到生之有途
戴维·佩珀提出的这个生态的限度是有着具体的历史的规定的,结合当代中国具体的历史阶段,就有着现实的规定。在现阶段,以合理的方式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应当是以一种“不招惹自然”的实践方式。它是一种基于中国当代生产力发展现状、自然环境客观现实以及人们的现实需要的基础上的,是人们可以接受的、可实施的行为途径。
首先,这种途径没有进一步破坏自然平衡和生态。美国生态主义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其代表著作《沙郡年记》中说到,“一个事情,只有有助于维持生物群落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美丽,才是正确的。如果它背道而驰,它就是错误的”。[4]345人类以一种不招惹自然的方式,就是在维护自然生物群落的平衡性的同时,在这种方式下给了自然以修复自身的空间和时间,同时满足人自身的生理需要,并没有完全否定人的欲望。所以,这种方式在现阶段下,是真正切实可行的方式。
其次,这种方式也没有完全否定经济的发展,而是要为生产力的发展寻求一条合理的途径,这种途径适用于现有的不破坏自然环境的情况。这也符合了企业盈利的需要,并没有要求企业以牺牲其绝大部分利润的方式去修复自然,而是要求尽可能的改进生产,实行生态生产,同时实现利润。因为,企业是盈利的组织,经济的发展是需要对环境作出开发。在这种方式下,经济发展找到合理的途径,为生态文明下经济建设探索了一条合理的途径。它是在现有的维护经济发展的框架内寻求一种合理的生态发展的方式。
再次,这种方式是对自然的一种现存方式下能做到的最好的保护方式。这种政策并不等同于修复,让自然回到原初的状态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进入人类视野的自然就已经不再是“自在的自然”,而是一种“人化的自然”,这种自然与人发生相互作用,经过人类的改造,是不可能完全磨灭人的痕迹回到原始状态的。人之所以为人,人与自然相分离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对自然的改造,人在劳动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自然的超越。人类不能完全脱离自然,也不能停止对自然的改造,因此,人类所能做的就是给自然以修复的空间和时间,让自然实现逐渐的平复,寻求新的平衡状态。
总之,对欲望的规范,并不仅仅是对它的诘问与批判,也不仅仅是一种伦理道德文化的呼吁,它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改变,是与此相对应的人类的现实的社会生活、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在外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制度的督促下,在强大的国家、社会、制度的力量的推动下,在人类自身不断的反省、教育的推进中,形成人的内在与外在的、精神与物质的、历史与空间的不断统一的过程,从而为建设美好家园、生态和谐提供一种现实的可能。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9.
[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
[4][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郡年记[M].张富华,刘琼歌,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5][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56.
[6][德]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M].金铃,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