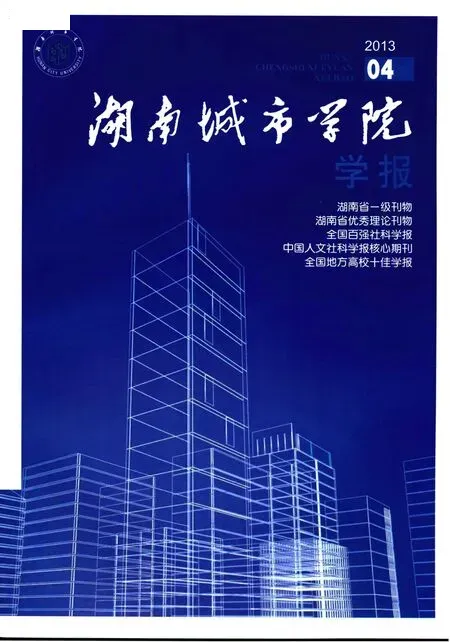论公序良俗原则的功能
2013-04-01杨德群
杨德群
(湖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长沙 410081)
民法基本原则在立法中的正式确立,是 20世纪之后的事情。民法中基本原则的确立,突破了传统民法的结构,这一创举并非出自立法者的任性,而是有其必然的原因。其原因的重要一面,在于民法基本原则所发挥的有利作用与效能弥补了传统民法之不足。[1]公序良俗在德国民法典中是以一般条款的形式出现的,公序良俗确立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使其既具有民法基本原则功能的共性,也具有基于自身属性的特性,具体而言,公序良俗原则具有立法准则与行为规范、克服成文法局限、追求实质正义及促进公私法价值融合等功能。
一、立法准则与行为规范
民法的基本原则系指效力贯穿于整个民事法律制度与规范之中的根本规则,是指导民事立法、民事司法及民事活动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行为规则。[2]黑尔认为法律原则至少须具有普遍性与规范性两项特征。[3]公序良俗原则属于得到普遍认同的民法的基本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的普遍性与规范性决定了其为民法的立法准则及当事人的行为规范。
公序良俗原则的普遍性系指内容的根本性与效力的贯彻始终性,是各项具体民事法律制度应当遵循的原则。民法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以市民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民法的基本原则直接体现市民社会的基本要求,是民法的灵魂与精神之所在。公序良俗原则因其迎合了商品经济对市场秩序与道德规范的需求,由最初仅限于对意思自治的限制逐渐发展为贯穿整个民法的基本原则。诸如物权法、债权法、侵权法、婚姻家庭法及继承法等具体民事法律制度均应遵循公序良俗原则,而不得与之相悖。公序良俗原则的这一特性也使其与民法的具体原则相区别开来。徐国栋先生认为传统的所有权绝对原则、契约自由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分别为为物权法、债权法与侵权法的基本原则,而非民法的基本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在大陆法国家则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当然内容,或者说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反面规范,因此,大陆法系民法仅有两项基本原则,即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1]37-160[[[
公序良俗原则的普遍性使其成为民事立法应当遵循的准则。法的创制过程中应遵循一定的立法原则,立法原则系指立法的总的精神,是立法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为立法的性质、根本任务与价值追求,是立法的总的精神在立法过程中的具体化与实践化。立法原则的遵循使立法在不偏离立法的总的精神前提下,兼顾法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对协调法律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维护法制的统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民事立法同样应当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则,民法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民法总的精神,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与其他民事生活对民法的基本要求,体现民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民事立法的出发点与指导思想。公序良俗原则是社会由权利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的必然产物,公序良俗所体现的秩序、道德以及由二者延伸的正义、自由、平等等价值理念不仅体现在一国现行法秩序之中,同时兼括整个法秩序的价值体系与规范原则,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序良俗不仅为民事立法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且是整个法律体系应当遵循的基本理念。
公序良俗原则的规范性系指其属于强行法的范畴,是行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法律规范与法律原则同属法的主要内容,法律规范对某一具体的事实状态赋予确定的法律后果,而法律原则则不预先对任何确定的事实设定确定的法律后果,是法律规范之上的规范。法律原则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并不防碍其属于强行法的特性,相反,“法律规范具有一种全有或全无的功能,因而未留下活动的空间,而法律原则占据着分量与重要性之维度”,[4]当具体法律规范缺乏明确规定时,法律原则具有极为宽阔的适用空间。法律原则的强行性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法律规范是由法律原则推导出来的,法律规范不得违背法律原则的价值理念,法律规范是法律原则价值的具体化,行为人对法律规范的遵守,正是对法律原则的遵守;另一方面,当法律规范缺乏明确规定时,行为人应当以法律规范本源的法律原则作为行为规范,否则,对法律原则的违背,将受到法律否定性的评价。此时,法院将直接适用法律原则对案件予以裁判,因此,法律原则不仅起着行为准则的功能,而且发挥着审判准则的功能。
民法基本原则均为强行性规定,不能由当事人自由选择,而应无条件遵循,其强行性源于其负载价值的根本性,对这些价值的不尊重或破坏将危害该社会赖以生存的根基。[1]31公序良俗原则在法国法与德国法中均以一般条款的形式存在,属于强行法的范畴。[5-7]大陆法各国民法均对公序良俗的违反规定了明确的法律效果。如德国法规定违反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无效及违反善良风俗的故意侵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国法规定禁止当事人以特别约定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及合同违反公序良俗原则无效;日本法规定以违反公序良俗原则为目的的法律行为无效等。当然,公序良俗原则的行为规范功能仅在缺乏具体公序良俗规范时方能得以明显体现,诚如曾世雄先生所言:“公序良俗规定的特质,在于补充强行法的强制或者禁止功能。当事人的作为或不作为违背公序良俗,而强行法既无强制性规范或禁止性规范时,公序良俗原则方可发挥其补充功能,公序良俗与强行法同为法的渊源。”[8]
二、克服成文法局限
成文法的局限也称为法律漏洞,是由法的自身特性决定的,主要表现为成文法的僵化性、滞后性、不周延性等方面。法的自身特性决定法绝非十全十美之物,法与其缺陷如影相随,相伴始终。博登海默认为尽管法已经成为国家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社会制度,但法与其他社会制度一样存在一些弊端。法律的缺陷部分源自于其自身的保守倾向,部分源自于其形式结构中的刚性因素,部分源自于其控制因素的限度。[9]其一,法的普遍性导致了法的僵化性。法的普遍性系指作为抽象性规范的法对其效力范围内的一切主体均具有约束力。其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法作为抽象性规范通常只注重其效力范围内对象的普遍性而忽视特殊性;二是调整对象的普遍性,法对其效力范围内的一切主体或事项均具有同等的约束力。法的普遍性保障了所有人均平等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与自由,符合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但对普遍性的强调使法趋向于规定一般适用条件、行为模式及法律后果,导致了成文法在形式结构上的僵化。[10]其二,法的保守性派生法的滞后性。法作为国家社会的重要调控方式,能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事先预测,进而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安全。正是基于法的安全价值的需要使法趋于保守性,法一经制定即不可轻易更改,法的朝令夕改,不仅会严重损害法的稳定性,而且会使人们因无法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而变得无所适从。社会的不断发展亟需法适时作出应对,这就使法的保守性与社会发展之间形成一对永恒的难以完全消除的矛盾。法一经制定便落后于时代,“法仅在社会初建时期,才能完全合法逻辑”,[11]此即法的滞后性。其三、法的确定性衍生法的不周延性。立法者通常尽可能的将应当纳入法调整范围的社会关系归入法的范畴,然后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确定法律主体的行为模式及法律后果。“绝大多数立法史表明,立法机关并不能预见法官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12]法对确定性的需求要求法律提供尽可能多的法律规范,但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立法者自身的缺陷、立法技术的局限以及法律语言的高度概括性等原因使法不能涵盖所有需其调整的社会关系,从而衍生出法的不周延。
授予法官适当的自由裁量权是得到两大法系普遍认同的克服成文法局限的重要途径。戴维斯认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系指法律对于公共官员予以适当限制的同时保留给公共官员在行动、不行动及如何行动的若干可能中自由选择的权力。[13]虽然关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定义极多,各定义之间的分歧也很大,但就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克服成文法的局限,实现法的正义、秩序等价值来说却是趋于一致的。法律原则的具体适用尤其需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贝勒斯认为法律规范与法律原则是可以区别的,前者系指以要么有效要么无效的方式适用,若其适用于某一情况,则限定了它的价值;后者并非必然限定一种估价,法律原则是需要去证成的东西,是由法官做出判决时使用的原则,或由发展立法以供法官使用的人们所适用的原则。[14]
就民法而言,民法基本原则的设立是克服成文法的僵化性、滞后性与不周延性等局限的重要途径之一。民法之所以要规定公序良俗原则,是因为立法者在立法时不可能预见所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与道德秩序的行为并作出详尽的禁止性规定,因此设立该原则弥补禁止性规定的不足。[15]王泽鉴先生将其视为公序良俗原则的正当化功能,即法院面对新问题,须依既存的社会价值观念,将其予以具体化,对法院的造法活动,予以正当化。[16]魏德士称其为一般条款漏洞,将善良风俗这种广泛而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与一般条款确立为法律漏洞是立法者的有意安排,其目的是使法官肩负立法任务。立法者希望希望法官能对特定案件类型灵活造法,以适应当时社会技术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发展。[17]无任是公序良俗的“正当化功能论”还是“一般条款漏洞说”,就其实质而言都是因公序良俗原则的内涵极为抽象,通常需要通过在具体案件中运用价值判断使其具体化,而主张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同时,公序良俗原则集灵活性与衡平性等特征于一体,使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处于能动地位,在司法活动中对法律进行局部的调整,以确保法律依其真正的目的得以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对成文法局限的克服还体现在法的解释的价值取向性之中,在实务中主要利用宪法上的基本价值决定(诸如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等)与分散于各部门法中的一般条款(诸如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等)以及不确定的概念,使其担负在法律解释或者适用上的角色。[18]
三、追求实质正义
法的实质正义应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法律是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但规范并非立法的目的,而仅为以和平手段获得人与人之间公平的手段,促成公平之和平的实现才是法律的终极目的。”[18]65-66但是法基于秩序、安全等价值的需要往往侧重于法的形式正义而忽视法的实质正义。形式正义也称为规则正义或制度正义,“强调对原则的坚持、对体系的服从”。[19]实质正义则强调法的内容其目的的正义性。富勒认为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在事实上趋于一致,因为那些不正义的制度是不可能被不偏不倚且一致执行,或至少这种情况极为罕见。[19]46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对立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形式正义强调对法律制度的严格遵守,但法的普遍性使其通常注重于一般对象,对特殊对象往往缺乏应有的关怀,而法对特殊对象的忽视可能使法违背自身的目的而导致非正义。再如形式正义强调对程序的绝对遵守,辛普森案即为典型,虽然辛普森案被誉为现代法治文明进步的标志,但对实质正义的忽视也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对立使法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法注重对一般对象的调整及对形式正义的苛求是法治社会的基本需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办事、法无明文规定不违法等为法治社会能得以有序发展的必备条件。另一方面法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从其产生之日起便承载着人类对正义、秩序等价值的理想与追求,也以此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
法对形式正义局限的克服,也即对实质正义的追求主要表现为立法中法律规则的弹性化以及法律适用的衡平化。[20]法治社会的根本特征为法律的至上性,社会公众从内心崇敬法律。也即法的普遍遵守应以社会公众自觉遵守为依归,而非以单纯的国家强制力的威慑为保障。而社会公众对法的自觉遵守建立在良法的基础上,唯有良法才能得到社会公众内心的认同。良法不仅要求法的形式正义,也即法对一切社会公众平等对待,而且要求法的实质正义,也即法能充分反映社会公众对正义、秩序、自由等价值的追求。正是源于对实质正义的追求,规范的局限性逐渐显露出来,《学说汇纂》中以规则当做法律的基本原则,一切规则均可以用逻辑的方式从中推导出来。但规则的僵化性、滞后性及不周延性等缺陷迫切需要弹性的规则予以取代,于是法律原则得到认同。德沃金认为用一套样板规则来说明法律不会有完美的效果,因为样板规则无法给一般法律原则提供充分的活动余地。[21]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官利用法律原则或一般条款,运用价值判断、法律解释、判例甚至法官造法以适应社会与价值观的变化,应对不断产生的新事物,进而体现法的实质正义,此即法律适用的衡平化。
公序良俗原则侧重于实现个案正义,以致有学者认为,公序良俗原则除非旨在实现个案正义,否则不得径行适用。[22]公序良俗原则确立的初衷为对意思自治的限制,因为意思自治建立于当事人能达成彼此意志共识的基础之上,侧重于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理念下对形式正义的追求,但意思自治忽视了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差别,对意思自治的过分注重势必损害弱者的利益,进而违背法的实质正义。在现代社会中,权利具有社会性及公益性,权利的存在不仅要保障个人权益,而且要维护社会公益、以推动社会整体和谐发展为目的。[23]因此,公序良俗对意思自治的限制,其实质是基于对法的实质正义的追求。同时,公序良俗原则的灵活性与衡平性使其符合法对实质正义追求的一般要求。公序良俗的内涵与外延极为广泛,兼具道德与秩序双重特性,集中体现了法对实质正义的追求。法对公序良俗的态度分为两种,一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将公序良俗的内涵纳入法律规范的范围,从而上升为具体公序良俗,对于这一类公序良俗,在法律适用时直接适用相应的法律规范予以裁判。此时,公序良俗在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上合为一体。二是法以法律原则或一般条款的形式将未被法律规范涵盖的公序良俗确立为原则性公序良俗。以法律原则的弹性广泛包容具体公序良俗之外的一切公序良俗,在法律适用时,由法官根据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行使自由裁量权对案件实行衡平裁判,克服法律规范的不周延性、滞后性、僵化性等缺陷,从而实现法对实质正义的追求。[24]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序良俗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其调整机能实现了由确保社会正义与伦理秩序到调节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确保市场交易公正性的转变。[25]其调整对象也早已突破仅限于对意思自治的限制,而发展到权利的行使及义务的履行等各个领域。诚如史尚宽先生所言:“有权利才有自由,权利与自由相对应而存在。私权的社会性乃至义务性表明私权并非仅因个人利益而存在,私权同样应符合公共利益与社会秩序。公序良俗原则中的公序强调私权的社会性,而良俗则强调私权的公共性。因此,权利的行使与义务的履行均应遵循公序良俗原则,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事项为内容的权利,应认定其不存在。”[26]
四、促进公私法价值融合
公私法的划分源自于古罗马法,乌尔比安认为公法事关罗马帝国的政体,而私法则事关个人利益。[27]虽然后世对公私法的划分存在不少争议,如拉德布鲁赫认为:“在一个社会的法律规则中,并存的公私法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而是互相渗透混杂。公法与私法的概念均为先验的法律概念,涉及所有单一法律原则的问题就可能十分有必要提出来,并极难得出单一法律原则是属于私法或公法的解答,公私法之间的价值关系与等级关系服务于历史的发展与价值世界观。”[28]各国对其划分也是在罗马法得以广泛传播之后,当然,虽然近代各国对公私法的划分存在不同标准,但对公私法的划分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公私法价值的融合不仅是法自身发展的必然,同样也是社会发展的需求。私法强调私权的自治,公权注重国家对社会的适当干预。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方面私权亟需国家公权的强有力的保护,另一方面国家基于对日趋复杂的社会关系调整需要,在确保私法自治的前提下加强对私法领域的干预,以之平衡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实现法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因此,法治国家中的立法几乎均反映了立法者对正义、良序等价值的追求。魏德士认为规范的目的是立法的动因,所有法律规范后面均隐藏着服从特定目的与目标的、立法者的、法政策学的形成意志。[17]310但法律规范基于确定性需要,严重压抑了立法的目的或价值观念的伸展空间。而法律原则是规范与价值观念的结合点,[29]法的基本原则蕴涵法的价值观念,法的价值观念派生法的基本原则,法的基本原则与价值观念互相包容、互相生发,共同反映法的宗旨。[30]公序良俗原则所蕴含道德、秩序的理念,充分体现了国家社会对其一般利益与公共道德保护的需求,这些价值观念也并非局限于民法中的某一个或几个条文,而是体现于一国现行法秩序之中,同时兼括整个法秩序的价值体系与规范原则,特别是宪法中的人权规定。从这个方面讲,公序良俗原则的价值观念不仅早已突破了原初的对意思自治的限制,而且突破了私法的范围,体现于公私法的各个领域之中。
公序良俗原则促进私法与宪法价值融合。宪法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产物,传统公私法的划分并未包括宪法。[31]宪法蕴含的基本权利规定、特别是人权的规定具有最高法秩序地位,是衡量立法、私法与公共行政的准绳,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法超越了简单公私法的分界,为其他个部门法提供法律基础。公序良俗原则发挥着宪法权利私法化的桥梁作用,[32]一方面,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既是个别、主观的权利,也是客观的价值体系,扩散到所有法律领域,特别是私法领域。由民法上的概括条款实现宪法基本价值体系,期能在法律体系上保障私法的自主性,是私法在其完整体系之内解决私法的问题,并维持法律整体秩序的一致性。[16]231-232另一方面,在私法自治原则下,当事人可得以其意愿塑造法律关系,但这种法律上的自由,须限定于法律及普遍认可的秩序原则及风俗规范的架构之内,才能发生效力。公共秩序系指实体法中的概括性原则,包括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是法律的基础性价值准据。将基本权利的基本价值以及权利内涵,纳入私法领域,公序良俗原则为不可或缺的媒介。[33]
公序良俗原则促进私法与经济法价值的融合。经济法在学术上的使用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战时德国在经济领域出现了新的立法活动与法律现象。战后德国颁布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复兴的法令,促使了“经济法”这一概括性概念的产生。[34]经济法概念随之在德国得以确立,并逐渐得到各国的认同。虽然各国在经济法的立法宗旨、调整对象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分歧,但对经济法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的认识却趋于一致。经济法的属性以公法为主兼具私法特性,其产生动摇了公私法划分的界限,体现了公私法价值的融合。有学者认为公序良俗与社会经济利益是民法与经济法的契合点。[35]经济法兼具公私法的特性使其对市场主体、市场交易、市场秩序的规范等民商关系领域的态度上,既对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自由意志给予充分尊重,也以国家力量对市场秩序进行干预。因此,经济法包含“平权性”与“非平权性”两种因素,[36]其目的在于构建一种立体秩序以维护经济安全,而经济安全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社会的一种至关重要的基本秩序和安全。[37]经济法为追求经济安全而体现的“立体秩序”抑或“基本秩序”价值理念,正是公序良俗为实现利益平衡而体现的“良序”价值理念的重要内容,从而实现了私法与经济法价值的融合。就整体而言,经济法以社会本位为归依,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公序良俗原则对私法自治的限制,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是权利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的体现,二者均体现了国家意志对私法领域的适当干预,体现了社会多元化时期对利益的平衡,也反映出现代国家社会对实质正义的不懈追求。
以上论述中,笔者侧重于关注公序良俗原则促进私法与宪法价值的融合以及促进私法与经济法价值的融合,但实际上,公序良俗原则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在宪法、经济法、诉讼法、国际法等领域均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公序良俗原则所具有的促进公私法价值融合的功能使民法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更彰显出民法作为万法之母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1] 徐国栋. 民法基本原则解释[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1.
[2] 马俊驹, 余延满. 民法原论[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 32.
[3] R.M.Hare.Essays in Ethical Theory [M]. Clarendon Press, 1989:49-65.
[4] [德] 阿图尔·考夫曼, 温弗里德·哈斯默尔. 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M]. 郑永流,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152.
[5] 尹田. 法国现代合同法[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9: 200.
[6] 德国法关于公序良俗属于一般条款的观点见[M]//陈卫佐, 译注。德国民法典.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 47.
[7] [德] 迪特尔·施瓦布. 民法导论[M]. 郑冲,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 474.
[8] 曾世雄. 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28.
[9] [美] E·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M]. 邓正来,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419-420.
[10] 高航. 成文法的局限性及其弥补[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6(1): 105-109.
[11] [法]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上)[M]. 董良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132.
[12] [美] 约翰·亨利·梅里曼. 大陆法系[M]. 顾培东, 禄正平,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48.
[13] K·C·Davis, Discretionary Justice [M]. Green-wood Press,1969: 4.
[14] 迈克尔·D·贝勒斯. 法律的原则[M]. 张文显, 朱卫国,黄文艺等, 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12-14.
[15] 崔文星. 民法总则专论[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2: 116.
[16] 王泽鉴. 民法总则[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231.
[17] 魏德士. 法理学[M]. 丁晓春, 吴越,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5: 353-354.
[18] 黄茂荣. 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9:318.
[19]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 译.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45.
[20] 孙笑侠. 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J].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9(5): 8-12.
[21] 彼得·斯坦, 约翰·香德. 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 王献平,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 145-146.
[22] 舒国滢. 法律原则适用中的难题何在[J]. 扬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6): 18-20.
[23] 施启扬. 民法总则[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362.
[24] B.S.Markesinis, W.Larenz, G.Dannemann.The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 [J].Viking Penguin Inc, 1997: 180.
[25] 李双元, 温世扬. 比较民法学[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70.
[26] 史尚宽. 民法总论[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38-40.
[27] [古罗马] 查士丁尼. 法学阶梯[M]. 张企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5-6.
[28] [德] G·拉德布鲁赫. 法哲学[M]. 王朴,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 127-129.
[29] N.MacCormick, O.Weinberger.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Law[M]. P.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73.
[30] 李锡鹤. 民法原理论稿[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9: 88.
[31] Peter Quint.Free Speech and Private Law in German Constitutional Theory [J]. Maryland Law Review, 2001(48):263.
[32] 余延满. 冉克平. 论公序良俗对宪法权利的保护[J]. 时代法学, 2006(2): 14-17.
[33] 黄立. 民法总则[M]. 台北: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5: 326.
[34] [日] 金泽良. 经济法概论[M]. 满达人, 译.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 1-2.
[35] 吴晓峰. 公序良俗的经济法分析——民法与经济法的的契合[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4(10): 117-122.
[36] 李金泽, 丁作提. 经济法定位理念的批判与超越[J]. 法商研究, 1996(5): 66-71.
[37] 单飞跃. 经济法范畴与理念的解析[M].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 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