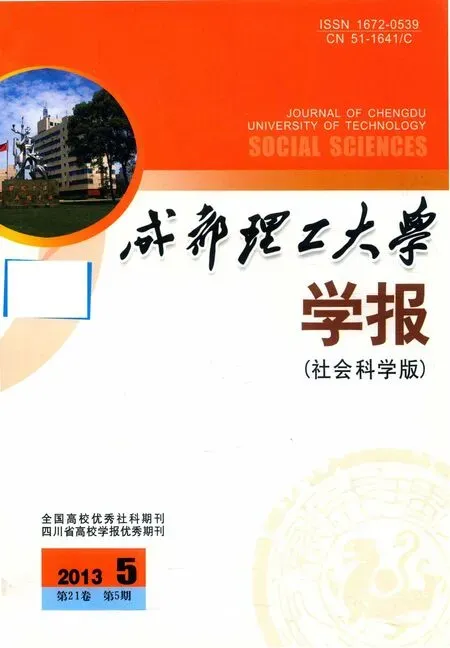论中国古代社会“礼治”与“法治”的合流及其利弊
2013-03-31赵玲
赵 玲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00)
在去年的“小悦悦”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国人心灵冷漠的一面,而这种冷漠被很多学者解读为“仁爱”之心的缺乏,因此当代许多学者都认为我国古代儒家所推行的“仁”“孝”等观念,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笔者认为,儒家的“仁爱”并不一定就是那一帖对症的药,当我们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时候,不能够仅仅局限于它所提倡的理论或纲领,更应该全面分析它的来龙去脉、它在推行自己的理念时所使用的手段以及对当时的社会起了怎样的影响,这些也是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的。
一、“礼治”与“法治”的由来
所谓周公“制礼作乐”,实际上是对上古时代就已存在的“礼、乐”加以损益,改变了“礼、乐”的性质和社会功能。周朝所提倡的“礼”和“乐”,其实就是以血缘和地位上的远近亲疏将人分为若干等级,同时又以共同的血缘为联系以声律为形式将不同等级的人结合成统一群体,这就是《乐记》所说的:“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
但由于分封制的推行使得王室所直接控制的土地和人民逐渐减少,周朝很快衰败了,反而需要对财势雄厚的诸侯曲意逢迎,周朝时所建立的“等级制度”形同虚设,此谓“礼崩”;同时,音乐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又使得春秋时的音乐节奏变得更加复杂而少平和庄严,失去了“合同”的作用。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时代。
春秋末期,孔子通过对当时社会情况的思考和对“礼乐”的反思,提出恢复周礼,认为只有改变现在“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1]32的现状,才能重建社会政治伦理秩序,战争才会停止。这就是“以礼治国”的“礼治”方针。
法家的源头可追溯至春秋前期的管仲变法、子产“铸刑书”和邓析(名家先驱)造“竹刑”,比孔子诞生还早一个多世纪,但按照章太炎先生“著书定律为法家”的说法,法家的真正开山鼻祖应为李悝,比孔子晚一百年左右。李悝最突出的事迹,就是在整理春秋以来各诸侯国新颁布的成文法的基础上,编撰了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成为秦汉以来封建立法的滥觞。商鞅借鉴了《法经》几乎所有条目,略添一二,改称《秦律》,律法的完备,帮助秦国迅速腾飞[2]37。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法家和儒家都是当时“四大显学”之一,但儒家学说因为与争霸的时代主题不符而未被广泛采纳,法家却因为其集权争霸的精神内涵受到推崇。商鞅曾三见秦孝公,以“帝道”“王道”言之则不用,第三次言之以“霸道”才终为所用,可见法家对时势的迎合[3]。值得注意的是,商鞅变法之前,曾与甘龙、杜挚有一段辩论,他说道:“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4]“三代不同礼而亡,五霸不同法而霸”“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这说明了他对“礼治”的看法——法家是名符其实的变革家,而周礼则是他们急需变革的对象。
二、“礼”与“法”的抗衡与合流
(一)礼与法的交锋
儒家思想以伦常为中心,“礼治”强调的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而法家“法治”则强调“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一以度量断之”[5]355。于是“礼治”与“法治”的交锋,便集中在“承认差别与否”这一点上。
在秦始皇时代,淳于越所提出的不合时宜的“废除中央集权制,恢复西周封建制”的建议让法家抓住了口实,使儒家遭受了“焚书坑儒”的劫难。而秦王朝夭折之后,汉初的统治者则将秦亡的教训归结于暴政,严苛的法制成为“罪魁祸首”。刘邦率起义军攻入关中后,首先宣布废除秦的苛法,“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1]50。汉初时虽然并未明确以何种学说治国,但在“礼”与“法”的抗衡中,法家的尊贵地位不再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礼治”与“法治”合流的起点
战国后期,儒家的代表思想家荀子最早开始吸收法家的思想,他认为统治者对民众要实行礼乐教化,不仅仅要依靠启发民众的道德自觉,还要以社会行为规范的“礼”来约束民众。他所谓的礼,具有法的成分,故他经常礼法连用,礼法不分。与孟子不同的是,他也不反对在治民中使用刑罚,“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1]37。也正因为如此,荀子的两位弟子李斯和韩非子后来都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也不足为怪了。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在教育和人才选拔上都重用儒家学者,儒者的高官厚禄吸引了大量士子加入,法家以及其他学派的地位日益下降,但法律却依然是统治者不可或缺的工具。儒者应试做官后,便不能不懂法律,于是法律的制定便加入了更多的“三纲五常”的“礼”的色彩,这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也是“法治”与“礼治”合流的起点。
(三)“春秋决狱”:礼法交融的典范
礼治与法治交融带来的影响中,最为明显的是西汉中期,儒家取得绝对统治地位之后,由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决狱”(又称“经义决狱”)办法,即以六经中的思想来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作为判案的依据,犯罪者的动机是否合“礼”,对审判结果造成直接的重大影响。
例如,藏匿犯罪者应受重刑,但儒家却不主张“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而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5]62,于是在“春秋决狱”思想的指导下,藏匿杀人犯儿子的父亲可以无罪。
“春秋决狱”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立法。以卑幼殴打长辈为例,为了严格执行“周礼”中的“亲疏有别”,卑幼与长辈的关系越是亲近,则罪刑越重;反之,长辈殴杀卑幼则是越亲近的关系则罪刑越轻。亲属间的盗窃也不同于常人,关系越亲则罪刑越轻,关系越疏则罪刑越重。为了严格遵循儒家所提倡的“孝道”,“不孝”是一项重罪,唐律规定凡是骂父母、祖父母即是绞罪[5]30,如果有父母告子女不孝,无需提出证据,子女就会得到杖击甚至处死的惩罚,清代法律还赋予了父母将子女呈送发遣的权利,只要子女不服教诲且有触犯情节便可依例请求,永远剥夺其自由,放逐在边远的云、贵、两广地区[5]12。
三、中国“礼治”与“法治”合流的利与弊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得知,中国历史上的“礼”“法”合流,是以“礼”绝对控制“法”而形成,儒家之“法”是为“礼法”与“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一以度量断之”的法家之“法”已相去甚远。汉廷尉陈宠疏中有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5]349
那么,中国沿袭上千年的礼法制度,究竟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怎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我们要承认“礼”“法”合一对古代中国社会普通百姓的教化起到了强大的推进作用,“三纲五常”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孔子曾说:“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5]315。而“礼”“法”结合,则是双管齐下,“刑不善而赏善”[4],儒家所推行的礼乐教化使人向善,而法律则制裁那些不善的恶人,相得益彰,有利于民风教化,而儒家所倡导的封建等级秩序也就愈发稳固。而对中国当代社会而言,儒家伦理中对孝悌仁德的提倡若得到贯彻,本身就能成为有效的社会黏合剂,减少犯罪率,同时也能使道德舆论成为法律鞭长莫及时的一种弥补措施。然而,这种“礼”“法”合流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儒家学说本身有重大的缺陷,通过法律深入贯彻到了民众的头脑中,包括贵贱有别、特权思想、家长制度等,如上文提及的父母对子女享有流放的权力,如果去县衙状告子女不孝,子女都会受到廷杖甚至斩首的惩罚,子女的人权则被排在孝道之后。又如,古代法律中严格规定了各个阶级祭祀、丧葬、婚礼用品的数量和内容,如后唐《丧葬令》云:“诸丧不得备礼者,贵得用贱,贱不得用贵”。而且,官吏犯法,可用官阶抵罪,他们的特权甚至可延伸至亲属,官阶越大,其辐射范围越大,而现代国际社会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在儒家的“礼法”中全无体现,使得当代中国国民心理的转型异常艰难。
第二,这种有差别的行为规范使得法律失去了最初的公平公正的意义,造成了社会道德与法律的混淆;而春秋决狱或恭请钦定的理念,扩大了断案者的主观判断效力,使得古代法律中“人治”的成分大于“法治”,其中的“主观性”和“模糊性”为后代文字狱的发生提供了依据,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法治进程。
第三,春秋决狱的理念踌就了后来的中国社会中凡事向儒家经典寻找支撑的文化心理,后代的所有修身治国的准则皆由圣人经典敷衍而来,凡事遵循“祖制”,这种极度封闭的文化心理定势使得中国社会缺乏改革的动力,发展至19世纪使得中国蒙受了巨大的耻辱。
第四,以“礼”入“法”使得道德规范僵化,空有“仪”而无“礼”。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充满了“礼数”需要遵循,这加深了长幼尊卑的外在身份差别意识,却没有相应的“乐”来起到“合同”的作用。“礼乐”文明实际上成为徒有其表的“礼法”文明。当今中国强调“和谐”社会,究竟应该以什么理念或手段来替代春秋时就被迫退出的“乐”应该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话题。
四、结语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知,儒家所提倡的“孝”与“爱”并不是一种平等、真诚的互爱,而是基于伦理与纲常中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所提倡的孝,是完全否定子女人权的孝,所提倡的爱,是由亲到疏的有差别的爱,当儒家所提倡的伦理与纲常上升到“法”的高度时就摧毁了法律的平等与理性。
当今中国,如果按照儒家的理想来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将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人情社会无疑。我们不愿再见秦时的“苛法”,但后来的“礼法”,亦非今人所欲。对儒家伦理的提倡需要慎而又慎地去粗取精,万不可盲目推崇。
[1]马振铎,徐远和,郑家栋.儒家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卫东海.中国法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
[3][汉]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G].北京:中华书局,1982.
[4][战国]商鞅.商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