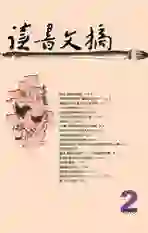鲁迅、吴宓、邵祖平
2013-03-27散木
大概从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文化受到质疑、东方文化以对方暴露出的窳劣衬托出其自身的生命力起,也就开始了迄今已经近一个世纪的周而复始的文化论战。这中间以哲人的姿态应对人类棘手的“二律背反”,很有影响力的“调和”说堪为根深蒂固。比如个中主人公之一的吴宓1915年在其《日记》中说:“窃谓时至今日,学说理解,非适合世界现势,不足促国民之进步;尽弃旧物,又失其国性之凭依。唯一两全调和之法,即于旧学说另下新理解,以期有裨实是。”但是后来这种“调和”立场虽以《学衡》的“衡”相标榜,不过毕竟“语境”过于峻急而难以守“衡”,“学衡派”大张挞伐于“五四派”也就顺理成章。如吴宓,出于对激进主义的恐惧,以为“但使礼教衰微,法令不行,则蜂起不可收拾。如法国大革命,则以‘平等、‘自由为号召;我国之乱徒,以‘护法等为号召;今之过激派,以‘民主主义为号召。其实皆不外汉高祖‘取而代之之一种宗旨”,于是,其视新思想新文化,则鄙为“今国中所谓‘文化运动,其所提倡之事,皆西方所视为病毒者”,若《新潮》等不免受其讥为“无知狂徒,妖言煽惑,耸动听闻,淆乱人心,贻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惊忧”以及“今之倡‘新文学者,岂其有眼无珠,不能确察切视,乃取西洋之疮痂狗粪,以进于中国之人”等。这样,所谓“抨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同样是在与新派的争夺霸权话语,这个“衡”难免进退失据,表现出它被鲁迅冷冷地一“估”,那很不堪的一些“铢两”。
眼见五四就要快百年了,明日黄花可曾雨打风吹去?譬如“学衡派”,今人又在“重估”了。不错,如吴宓当日所说的“中国受世界影响,科学化、工业化,必不可免。正唯其不可免,吾人乃益感保存宗教精神与道德意志之必要”,问题是如何来“保存”或者说“发扬”?这说来话长。就说当年壁垒森严如“五四派”与“学衡派”的主力鲁迅与吴宓,且依据《吴宓日记》,比照鲁迅对其的批评,看鲁迅如何“棒喝”吴宓,或者说也看看吴宓如何“棒喝”鲁迅;再就是又依吴宓晚年手撰的《自编年谱》,揣度他后来如何看待这场公案,是对鲁迅的批评真是今人首肯的“实甚公允”,抑或他“仍有保留意见”以及“失记”或干脆“不说”?吴宓先生是个君子,如其《年谱》被视为中国的卢梭《忏悔录》(见李赋宁先生序)一样,他的《日记》不妨亦可作如是看。虽然出版的《吴宓日记》止于1948年,不过也就可以看出个大概,揆以性情,吴宓先生的确是“这一个”。这又比如当年他在王国维灵前的誓言:“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淟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何其慷慨!此前,吴宓亦有“党军到京,宓身甚危,至少亦恐受辱”之虑,他甚至猜度自己“虽与政治无关,而文学思想之仇敌甚多,乘机报复,得而甘之,亦固其所耳”,处此也许并非臆测的政治和文化的语境。吴先生岸然介守,若投水的王国维,若他推崇再三的陈寅恪平生“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他们是“文化神州系一身”的抱负者,若说“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他们是不屑的,所以吴宓先生的日记就不仅一时一地的意义了。
先说鲁迅对吴宓的“棒喝”。舒芜先生以为不能称为“棒喝”,因为鲁迅批评学衡及吴宓只有两篇文章:《估〈学衡〉》和《“一是之学说”》,且“都只是一两千字的小评论,是应战而非挑战,所指责的都是对方文章中语法修辞逻辑上的‘硬伤,无可辩解,有嘲笑而无谩骂,态度非常和平”(《鲁迅‘棒喝过吴宓么?》)。为什么呢?这恐怕是不是不想去“棒喝”对方,而是对方不足论道,其人既然“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也就不屑与之周旋和论战了,鲁迅不是有“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的名言么。
鲁迅怎么看《学衡》?1922年该刊由中华书局出版发刊,吴宓主编,可惜当年《鲁迅日记》不存,今天人们只能从两篇文章里看鲁迅对它的小小一“衡”。一是“估”《学衡》首期胡先骕、梅光迪、邵祖平等诗文“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一是讥刺吴宓“平情衡理,执中驭物,造成一是之学问”之虚伪,分量都不及对付章士钊等,实在是鲁迅的不屑。这痕迹如果细察,就有鲁迅名篇《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说到“文学研究会”曾受三方之攻击:新才子派的创造社、鸳鸯蝴蝶派和留美绅士派。后者,“他们以为文艺是专给老爷太太们看的,所以主角除老爷太太之外,只配有文人,学士,艺术家,教授,小姐等等,要会说YES,NO,这才是绅士的庄严,那时吴宓先生就曾发表过文章,说是真不懂为什么有些人竟喜欢描写下流社会”。鲁迅1931年的演讲还提到吴宓,说明吴宓那篇文章对他的印象的深刻。大概五四新文学曾掀起“平民文学”旗帜,“劳工神圣”口号下鲁迅《一件小事》、胡适《人力车夫》等等诗文屡出,吴宓不满,有所指摘(这可以查找《学衡》)。与吴宓同一营垒捍守“吾国固有”的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即指陈鲁迅“揭‘平民文学四字以自张大”,到后来又为后生可畏的创造派所鄙,“只抒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云云。此前鲁迅始到上海,1927年10月25日在劳动大学讲演《关于知识阶级》,从爱罗先珂在华演讲时提出知识阶级的概念。鲁迅以为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其实是与中国的不同的,在俄国革命之前,社会还是欢迎知识阶级的,“因为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他为什么能把平民的苦痛说出来?因为他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鲁迅说到这里想起吴宓,“前有一位中国大学教授,他很奇怪,为什么有人要描写一个车夫的事情,这就因为大学教授一向住在高大的洋房里,不明白平民的生活”。《全集》注释“中国大学”为误记,应为东南大学,这当然又是吴宓了。鲁迅的话对不对?看业已出版的《吴宓日记》,鲁迅不诬。吴先生的日记如出版者所说,是他“学术生涯、个人际遇”等的记录,保存至今自是弥足珍贵,不过若有鲁迅“车夫误辗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等等句子,吴先生于“终极关怀”之外,形而下于“平民关怀”如“引车卖浆者流”,则鲜见矣,恐怕更多的是他令人发噱的感情心路。
再说吴宓对鲁迅批评的“公允”。经整理者整理出版的《吴宓自编年谱》于1922年目下说:《学衡》的对头有三:“文学研究会”茅盾等,“创造社”郭沫若等,第三是鲁迅。后者有《估〈学衡〉》一文,吴宓称“实甚公允”,其实其立论即在鲁迅该文批评《学衡》首期,而该期“文苑”一栏“所登录之古文、诗、词,皆邵祖平一人所作,实甚陋劣,不足为全中国文士、诗人以及学子之模范者也!”《吴宓日记》怨怼邵氏之处颇多,因即以名士作风即傲慢又猜忌,吴宓编刊,常为其苦。吴又怨恨胡先骕偏袒邵氏,以其皆江西人氏,胡主持的“学苑”遂充斥江西诗派如胡、邵以及汪辟疆等诗文,吴遭彼辈横逆,气无所出,只好在日记中宣泄,所以鲁迅批评《学衡》,正其所感同身受,乃称“公允”不置。而《吴宓日记》中记鲁迅处,则“公”或“不公”并见矣。
“公”,他读鲁迅著译《中国小说史略》(1927年)、《思想山水人物》(1929年2月22日),许为“颇佳”。如后者之“切中我辈书生之弊”——“其言学窗生活之危险有二:一、消极与冷嘲;二、虚骄与妄自尊大”等;而“不公”,则如与陈铨议论中国近今新派学者,“不特获盛名,且享巨金,如周树人《呐喊》一书,稿费得万元以上。……而一则刻酷之讥讽,一则以情欲之堕落,为其特点。其著作之害世,实非浅鲜”。鲁迅“刻酷之讥讽”不假(“情欲之堕落”是说张资平、郁达夫之辈),说鲁迅稿费奇高,是吴宓由其主持《学衡》惨淡经营和为《大公报》编《文学副刊》不如意所带出的愤懑。如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略谓“张若谷访郁达夫于创造社,叹其月入之薄,告知‘鲁迅年可坐得版税万金,以为盛事”几近之,若究其实,《呐喊》先由新潮社、北新书局出版,二者相加可曾有万金之数?后来鲁迅与李小峰以版税案对簿公堂,所补交也不过八千余元,那是“北新”所欠鲁迅各项款目(版税、编辑费等),岂《呐喊》一书哉!吴宓看视新派学者与自己,曾在西南联大课堂上比喻:如胡适,为16世纪法国作家团体之“七星诗社”;如鲁迅,为《巨人传》作者之法国拉伯雷;自己,为法国作家思想家之蒙田。这个比喻恰当否可以一议,则胡适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文学语言之改革大师、鲁迅则为从粗俗戏谑到深邃讽刺的喜剧作家、吴宓为怀疑论智者和坚守传统礼仪习俗并主张宽容的自由派?这倒颇合时下的观察和追慕的风气,不妨说,吴宓以与新派两位并峙的大师比肩是自信的。
可惜多元的文化场景不在中国的语境中,吴宓自称秉性不能宽容,也就难以企及蒙田“每个人都包含人类的整个形式”的有容乃大。吴宓是情感中人,读他的日记常常为之迭叹,可能是伤于自己的际遇,在他与人交谈中就自比鲁迅而伤感命奇。1937年6月他与清华女学生邵景渊杂谈,谓“景宋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伺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既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吴宓不免嗟叹:“宓之实际负责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他还与曾与鲁迅有过交往的孙福熙夫妇交谈过鲁迅的生活琐事(1941年2月),也徒增伤感而已。
吴宓在《年谱》中记邵祖平事,有邵记恨鲁迅批评《学衡》,至有1951年在重庆诋毁鲁迅之事,事见张紫葛《心香泪洒祭吴宓》一书。原来,重庆文联学习纪念毛泽东“延安讲话”,时为重庆大学中文系的邵祖平发言,歌颂鲁迅“孺子牛”精神,却举例不当,形容彼病体清瘦,“很像久吸鸦片的瘾客”。结果自是可知,以肆意诋毁遭批判,连带当年《学衡》反对新文化罪状,吴亦被要求交代和揭发。事后,吴谈及色变,谓“祸累几及于宓,亦可谓不智之甚者矣”,又为免被深文周纳之祸,将日记焚烧。邵与吴相识在吴在东南大学办《学衡》之初,邵是东大附中国文教员,“彼为中学教员,又未出洋,不通西学,故鄙视之”,不过相与同志,邵又能诗,有《历代诗选》及《培风楼诗存》、《续存》(曾获教育部文艺奖),吴多少对他容忍大度。《学衡》创刊后,吴为“集稿员”,各栏主编分由梅光迪(通论)、马宗霍(述学)、胡先骕(文苑)、邵祖平(杂俎)。吴与众人多有冲突,《学衡》最初各期吴宓未尝作文,仅译英国萨克雷小说《钮康氏家传》而已,故鲁迅批评《学衡》,如吴《年谱》中所称:“为评者所讥毁,宜也。”吴之“公允”似也仅此而已。若以新派对“学衡派”的批评,前如蒋梦麟、江绍原在美国时对它的批评,斥吴泥古,及鲁迅发难,实并未“棒喝”,所以估计吴宓也未引起回应,但这不能说是他的“公允”。
由邵祖平联想到笔者所在的浙江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末竺可桢校长任职期间,因竺的办学思想和他此前东南大学的关系,形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学衡派”的阵地后来迁移至浙大,除梅光迪、张荫麟、胡刚复、王焕镳等先后随竺而来,前“东大”学生的郭斌和(白壁德弟子)、张其昀、陈训慈等亦相继抵达,加上刘节、钱基博等新聘人员,所谓“学衡”雄风再起不为过矣。时吴宓几欲受聘浙大,终不能行。彼时之浙大,文学院由梅光迪主持(兼外文系),中文系为郭斌和,史地系则有张其昀、张荫麟、钱穆(客座)等。人事如此,则发扬“学衡精神”,有“大一”要上古文课,文、师学生要上文选课,郭主任还将所有白话作文一律不及格处理。以致当时中国“三大中学”之一的浙大附中毕业高考,因之大多转往它处。就是今日,纪念浙大百年,《求是先哲群英传》语及“学衡风范,万世师表”的梅光迪,作者尚云《学衡》并不违背新文化精神,倒是胡适为代表流行的“偏激新潮”群起而攻之,诬为保守落后,“极其污蔑之能事”。所以不提鲁迅而提胡适,原因至明,又说“历史公正”,“当年反对梅光迪者皆销声匿迹,历史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云云,则“重估派”以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一样也是不能宽容新派了。
(选自《灯火阑珊处》/散木 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