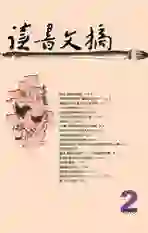震动文坛的《“歌德”与“缺德”》风波中的人与事
2013-03-27邢卓
邢卓
惊见奇文
1979年6月中旬的一个午后,我在保定市图书馆翻阅文学期刊。当时我在保定师范学校读书进修,受刚刚开闸的文学大潮的影响,兴冲冲跻身“文学青年”之列,几番耕耘,也有两三篇作品发表。由于中华大地从冰雪严封的十年浩劫中苏醒不久,压抑在人们心中的悲哀、愤懑、怨恨、憎恶之情借助文学的力量喷薄而出。我在1974年曾和两位知青好友以“王亚卓”名义给反“师道尊严”的造反小将黄帅写批评信,也因此遭到过沉重打击和残酷迫害,握笔在手就有汹涌澎湃的批判情绪翻卷胸中。以卢新华小说《伤痕》为代表的一大批“伤痕文学”作品一扫“高、大、全”的虚伪和腐臭,涤荡文坛,激动人心,而就在这时,在这间阳光透窗、宁静安谧的图书室中我读到了一篇散发着阴风冷气的文章,它刊登在《河北文艺》1979年第6期上,题目为《歌德与缺德》,作者李剑。这篇不到三千字的短文闪现着刀枪剑戟的寒光,弥漫着呛鼻的火药味。文章说:
据说,现在在我们的文学艺术队伍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一些人称之为“歌德派”并进行猛烈抨击,那么,“歌德派”有什么罪呢?据说是他们的文章和作品长于“歌德”——歌颂是其文字的主要特色。这就有罪吗?这就应当批判吗?我看未必。
……坚持四个原则,在创作上首先表现为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树碑立传,为“四化”英雄们撰写新篇。这既是坚持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的具体表现,又是人民感情向作家提出的创作要求。如果人民的作家不为人民大“歌”其“德”,那么,要这些人又有何用?在创作队伍中,有些人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对别人满腔热情歌颂“四化”的创作行为大吹冷风,开口闭口“你是‘歌德派”。这里,你不为人民“歌德”,要为谁“歌德”?须知,我们的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它的党性原则和阶级特色仍然存在。鼓吹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既然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和阶级性没有消失,那么,就存在为哪个阶级歌德的问题。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有着无产阶级感情的人当然要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有些人不愿这样做,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也不强求他非这样做不可,阶级感情不一样嘛!向阳的花木展开娉婷的容姿献给金色的太阳,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那种不“歌德”的人,倒是有点“缺德”。
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衣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而那种昧着良心,不看事实,把洋人的擦脚布当做钡带挂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们不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人,虽没有“歌德”之嫌,但却有“缺德”之行……
让我们的作品中亢溢着泥土和油浪的芳香,闪烁着青春的火花。让我们伟大祖国的春天在作品中展现出来,让人民从作品中看到绿于金色软于丝的万千细柳,闻到塞外原野的悠扬牧歌和战士打靶归来的阵阵欢笑……至于那些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意攻击的人,让其跟着其主子——林彪、“四人帮”一伙到阴沟里去寻找“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了。
李剑的这篇“奇文”令我颇感震惊。《河北文艺》是河北省文联主办的省内最高级别的文学刊物,发表此文意欲何在?十年浩劫,中国人民在民主缺失的制度下遭受了那么深重的苦难,今朝血污未褪、伤痕未愈,而造成苦难深渊的历史教训尚是一团模糊,有良心有道德的文学工作者有责任将那血雨腥风的景象和成因铸成文字,以唤今人,以戒后世,这篇《歌德与缺德》却大逞杀伐之势,让人嗅到了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的气息。
当天晚上,在一位青年作家家里的文学沙龙活动中,我向几个文友报告了这篇文章出笼的消息,小屋里一片激荡。因为我在图书馆只是读了《歌》文并未抄录,转述的是大意,大家议论一阵之后,有文友提议明天再找到那篇文章,看个仔细,录下文字,再作讨论。
次日晚上,大家又聚一堂,《歌》文已一字不落地摆在面前。有人读了一遍,随之是一片谴责之声。有人提议给作者李剑写信,也有人建言向《河北文艺》及其主管部门、省文联的领导提出质问。因为我曾有过写信给黄帅轰动全国的历史,大家就推我为执笔人。考虑到李剑代表的的确是一批人,是一种思潮,根子应在省里的文艺领导身上。当时的文联主席是著名诗人田间,他也是《河北文艺》的主编。“歌德”文章的出世必然跟他有关,而我与田间有过几面之交,对他的印象很好,于是就说不妨先给田间写封信问个究竟,先别忙着向他开炮。有人说:“田间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咱人微言轻,他能理睬?”我说:“本人了解田老师,他温和善良,没有架子,有沟通的可能。”
我与田间相识于1978年春季北京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我俩都是河北团的代表,因仰慕他的名声,会议期间我主动与他接触,谈了几次。当年暑期,我写了一篇小说,主人公为“四五”天安门事件青年勇士,当时这个事件还没有正式平反,稿子压在《河北文艺》,田间捎话给我,说时机一到就发表。半年后这篇题为《惊涛》的小说刊登在了1979年第1期的《河北文艺》上,引起一定反响,我也凭此加入了河北省作家协会,而就在此前不久刚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我与田间进一步接近,相谈甚欢,所以不愿对他炮轰。两天后信写好,大意是李剑的这篇不得人心的文章是否很符合省文联领导人的观点?此文是引导百家争鸣还是指引文学方向?信件在小沙龙上念了,略作修改后径寄省文联田间。
潮起潮落
《歌德与缺德》一文不仅触动了我们的神经,很快在全国也激起了波澜。文友们不断把各种报刊上的反应汇拢过来。7月1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阎钢的文章,批评《歌》文“以为中央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文艺界反右的信号,因而又操起棍子准备打人了”。7月20日,《光明日报》刊载王若望的文章《春天里的一股冷风》,指出:“只许歌德不许暴露的法则实际上是扼杀文艺创作……”接着,《河北日报》连续发文驳斥《歌》文;上海文联举行有50多位文艺界著名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巴金抱病出席;在北京,《文艺报》《文学评论》两刊联合召开座谈会,中青年作家以及文学理论工作者、首都报刊编辑80人出席;全国各地许多文艺刊物如《星火》《山花》《延河》《四川文学》《思想战线》《湘江文艺》《当代》《诗刊》《边疆文艺》《福建文艺》《安徽文学》《戏剧界》《雨花》《作品》《上海文学》《北方文学》《奔流》《鸭绿江》《长江文艺》等都载文参与对《歌》文的谴责和批判。同时,为李剑文章叫好的声音也不断出现,有人认为李剑的文章是正确的,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已经引起了“思想混乱”,走上了“否定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道路,搞得不好,“会出现五七年反右派前夕的那种状况”,甚至指责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大都是“欧洲18世纪文学的染缸里染过的”。《山东文艺》第8期刊载署名益言的文章,指责文学界一些人“字里行间明鞭封建帝王,暗笞革命导师,已经到了不作掩饰的地步”,是“阴谋文艺”。同月的《河北文艺》上以读者来信形式刊登题为《关于歌颂领袖的问题》为“歌德派”助声壮色,文中大声呼唤把“歌德”进行到底。8月末,河北省委宣传部召集各地、市文联主席、宣传部长共60余人开会,省委宣传部领导讲话,要求河北文艺界认真补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课,继续批“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消除阻力,繁荣文艺创作。
保定市文联副主席、荷花淀派重要作家韩映山从省里开完会回来,约我见面。他说,田间同志让他向我转达,说见到我的信了,让我多学马列,多出作品。关于《歌》文的事却一字未提。韩映山告诉我,省委宣传部领导在“歌德与缺德”问题上态度明朗,不容许“歌德”思潮蔓延,此事已惊动中宣部,引起了胡耀邦部长的重视。韩映山认为,田间对李剑文章的观点是认同的,他不点头文章是发不出来的。韩映山又说中宣部要为此开会,纠正《歌》文的错误倾向。听罢,我赶紧召集文友开会,传达这令人兴奋的消息。
果然,几天后的9月4日,中宣部就《歌德与缺德》引起的风波召集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此会由胡耀邦倡导,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主持。参加座谈会的除了“当事方”李剑与河北省委宣传部、省文联有关负责人以外,还有全国文联及作协的负责同志林默涵、陈荒煤、冯牧、李季和中宣部有关部门及文艺局的同志等共20余人。其时,李剑心情紧张,压力巨大,懊悔不已,惶惶不可终日,如此高规格的阵势他何曾见过。“四人帮”时期打击不同意见的血腥事例比比皆是,全国批《歌》文的火药味又是如此之烈,他担心会被降薪除职、挨批挨斗。会议从9月4日至6日开了3天。胡耀邦6日参加会议和与会同志座谈,并作了循循善诱的讲话。
胡耀邦说:
《歌德与缺德》一文的出现和围绕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论,是粉碎“四人帮”将近3年来文坛上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我们召开这个会,目的是用同志式的、平心静气的方法交谈讨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这种方法,根本区别于林彪、“四人帮”那套打棍子的方法,也区别于文化大革命前有时曾经采取过的简单、粗暴的方法。我们这样做,是总结了一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如果再遇到类似问题(当然不希望再发生),我们就推广这种方法,使文艺上的争论,纳入到一种健康的轨道上来。
《“歌德”与“缺德”》这篇文章,确有缺点毛病,毛病错误就是同毛主席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相违背。特别是党中央一再声明要在一切战线,包括文艺战线拨乱反正,把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东西端正过来,把搞乱了的加以澄清。要保护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文章的毛病就出在同中央的方针不合拍,李剑同志的调子不合时宜。青年人犯点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要采取教育的方法,诚诚恳恳帮助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传统。对《“歌德”与“缺德”》文章的批评是对的,但是王若望同志的批评文章说理不够,火气也大了些。对王若望这样文坛上的老同志,应提出严格要求。当然也不能各打五十大板,主要责任在李剑同志。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文章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环境。今年春天,恰恰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三中全会跨的步子较大,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键时期,一些人容易转向,对新的东西接受不了,所以我们要破除老框框,要解放思想,思想不要僵化……李剑同志的文章不是偶然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一定环境中产生的。离开历史条件、历史环境去解决问题,要犯错误。因此,我们不过分地追究个人的责任,也不要过分地追究河北省文联有关同志的责任。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开创河北省文学艺术工作的新局面,把河北省的文学艺术活跃起来,繁荣起来。你们回去以后,不要再争论、算账,这个账已经算清了。李剑同志回去检讨几句我们欢迎,但主要是商量几条措施;调兵遣将,调动千军万马,放开手脚,鼓励和组织大家大胆创作,使我们的文艺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满足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听了耀邦讲话,李剑如释重负。他作了自我批评,田间也代表河北省文联表了态,说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认真总结《歌》文引起的争论并吸取教训,希望大家帮助纠正错误观点,端正思想认识,把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上来,回去后将以《河北文艺》的名义,写一篇由《歌德与缺德》所引起的争论并从中吸取教训的文章。胡耀邦的讲话,使这场争论趋于平息,李剑也平安无事。
9月21日,河北省文联在石家庄召开各地、市文联主席、重点作者会议,传达了中宣部会议精神和胡耀邦的讲话内容,大家为之欢欣,都为中国思想战线有耀邦这样一位开明领导人感到高兴。数月后我见到田间,提及此事,他由衷感叹说:“耀邦同志处理问题的方式真叫人心服口服。”
后来的事
一年之后,李剑一反“歌德”姿态,在1980年第6期《湛江文艺》上发表一篇小说《醉卧花丛》,以尖锐、深刻、彻底的批判之笔再一次震动了文坛。小说描写在大串连途中的一位女红卫兵,掉队后遇到一个男性农民。农民想亲亲这个城里姑娘,姑娘起初犹豫,想到毛主席语录“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就是否认革命……”就顺从了。农民要求和她发生关系,她想到最高指示:“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她的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
李剑这篇涉及领袖及最高指示的创作又一次震动了文坛,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一些地方举行了大型的讨论会,上海《文汇报》发表批判文章,《人民日报》也撰文对李剑上纲上线,说他是攻击伟大领袖的“恶徒”。此时《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署名华铭的文章《评〈醉卧花丛〉》,对小说的创作手法和思想价值作了细致中肯的分析评判,否定了那些上纲上线的批评态度。胡耀邦读了这篇文章,予以肯定,并作批示内容如下:
默涵、敬之、光年、冯牧同志:
这篇小评论,也许你们都看过了,如果谁还没有看过,请他看看。我对文艺批评能够健康地发展是充满信心的。文艺报已经带了一个头,从这篇小评论也看出了一个好苗头。我不是说这篇东西写得很成熟,而是说他多少说了一点道理,并且根本没有打棍子。再进一步说,也只有报刊上,首先是各种文艺刊物经常有点文艺评论,才能真正带出一个好的文艺批评的风气来。坐而论道,什么恰如其分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文艺批评风气,永远学不会,永远带不出。能不能向文联和各个协会的负责同志提出一个指标:每人每年亲自写两篇?当然可以评论好创作,也可以批评坏作品。能不能把这个指标看作是加强对文艺工作领导的一条重要要求?请你们议一议。
胡耀邦
10.13
胡耀邦这条批示的后面还附有《评〈醉卧花丛〉》影印件。耀邦同志态度明确:思想战线不能再棍棒飞舞,不能再让疾风暴雨降临到百花盛开的园地。
8年后,即1988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有幸与耀邦同志会面,提及《歌德与缺德》和《醉卧花丛》事件。当时我以文联干部的身份在河北易县西陵乡五道河村下乡扶贫,伙食在西陵文管处食堂解决。这天听文管处的人讲胡耀邦到西陵来了,住在行宫招待所。其时,耀邦已经从总书记位子上退下,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来此边休养边考察,要住一段时间。我考虑耀邦无实职在身,工作应不会太过繁忙,他又是我非常崇敬的一个人,当时就起了见一见他的念头。耀邦此行本也是要接近群众的,但也不能个个都见,总得有个由头,想来想去,决定写封信,请行宫招待所的领导帮忙交给耀邦作一下沟通,当晚很费思量地写下一张字条,大意是:“尊敬的耀邦同志,得知您来此考察,我作为扶贫工作组的一员想当面向您汇报一下工作……1981年,北京那个反‘师道尊严的小学生黄帅考大学通过了分数线无校录取,您亲自作了指示,使其入学,我是当年与黄帅作过辩论的‘王亚卓的那个卓,不知您能否百忙中抽点时间,给我个与您见面的机会……”信交出后,我在忐忑中等来了消息,让我次日晚8时到耀邦的下榻之所。
次日晚,我骑自行车到达15里之外、青松掩映的行宫招待所。随行同志说耀邦一天下乡考察,人累了,嘱我谈话尽量简短,不要超过半个小时,随即把我带到耀邦房间。耀邦气色不是很好,人显得有些憔悴。他问我来此“扶贫”有什么收获,又问了我们当年和黄帅的那场论争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又乘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敬重之情:“您辞去总书记的消息一出来,我和其他几个搞写作的朋友就给您发了电报。”耀邦颇感兴趣地问:“什么内容?”我说:“就一句话‘您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您收到了吗?”耀邦神情凝重,没回答。随后问及我个人和保定地区的文学创作情况,我作了简短汇报后说:“文学事业的局面也是在您的领导下开创的。当年我省那篇《歌德与缺德》的文章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要不是您亲自引导,文学没准又得走到邪路上去。”耀邦说:“潮流所趋,倒退是不可能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我说:“有时候一个人就能撬动历史。”耀邦问:“李剑现在怎样?”我说:“听说调北京了。”耀邦说:“他还写小说吗?”我说:“好像不怎么写了,没见他再发表什么东西。”耀邦说:“这个人挺有才华的。”我说:“要不是您的保护他恐怕真得倒大霉呢。这人忽左忽右,后来的那篇《醉卧花丛》和《歌德与缺德》哪像是一个人写的。”耀邦说:“思想领域的立场、观点固然重要,但对待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方式方法同样重要……”我接上去说:“让人讲话,让人表达,不能因言给罪,才是真正的宽松自由,才能有真正的百花齐放。”
半个小时倏忽而过,秘书提醒,外面还有人等见耀邦。我告辞出来,在初夏暖暖的晚风中心旌摇荡地回返住地。
(选自《钟山风雨》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