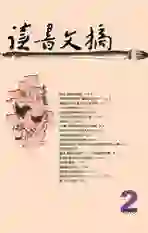小说《班主任》的发表
2013-03-27罗平汉
在文艺界对“文艺黑线专政”论和“文艺黑线”论展开批判之时,被誉为“新时期文学的发端”的“伤痕文学”,开始登上文学的殿堂,成为1978年文坛的一道独特风景。
邓小平1977年8月初的科教工作座谈会和9月19日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肯定了教育战线十七年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指出科研、教育工作者是劳动者,提出要恢复知识分子的名誉,这不但为科教战线拨乱反正提供了思想动力,也极大地推动了文艺战线思想的解放和拨乱反正的展开。得知邓小平的上述讲话内容后,《人民文学》杂志“闻风而动”,“很想通过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反映科学、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以便多少尽一点文学推动生活的责任”。
就在此时,杂志社收到了曾在中学担任过多年的老师和班主任,当时在北京人民出版社任职的刘心武寄来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对于作品的写作情况,刘心武后来回忆说:
“1977年夏天我开始在家里那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偷偷铺开稿纸写《班主任》,写得很顺利,但写完后,夜深人静时自己一读,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在发表欲的支配下,我终于鼓起勇气,有一天下了班,我到离编辑部最近的东单邮电局去投寄它,要把它投给《人民文学》杂志;柜台里的女工作人员检查了我大信封里的东西,严肃地跟我指出,稿子里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我心理上本来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冒险的事,她这样一‘公事公办,毫不通融,令我气闷,于是我就跟她说我不寄了。从东单邮局我骑车到了中山公园,在比较僻静的水榭,我坐在一角,想作出最后决定:这稿子还要不要投出去?还是干脆拉倒?后来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细读,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呢?过了若干天,我到另一家邮电所寄出了它。”
这篇小说立即在编辑部范围内引起了震动。在责任编辑、小说散文组负责人、编辑部负责人三级审稿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小说提出的问题是现实的,而且新颖、深刻、尖锐,但它暴露社会真实问题、社会阴暗面,过于尖锐,难以发表。另一种意见认为,小说提出的问题及时、新鲜、深刻,很合时宜,它符合当前文教战线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总的精神,可以发表,无须做大的修改。
由于小说在编辑部内部有不同意见,最后送到了《人民文学》的主编张光年手中。张光年看完稿件,肯定了《班主任》,认为不要怕小说尖锐,但是反映的内容要准确,如果说还需修改,也就是小说人物描写的分寸要掌握更准确,并对小说如何修改提出了具体意见。随后,编辑部同刘心武交换了看法。经过刘心武的推敲修改后,小说发表在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的头条上。
《班主任》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小说写的是1977年春天的一天,光明中学党支部书记老曹,让初三(三)班班主任张俊石,把前些日子从拘留所放出来的小流氓宋宝琦,收到自己班上。因为张老师有十几年的班主任工作经验,又是这个年级班主任里唯一的党员。
张俊石从公安局回到学校,已经是下午三点。在年级组办公室,他跟数学教师尹达磊就收不收宋玉琦这个问题,产生了不同看法。尹老师对张老师在狠抓教学质量的时候,弄个小流氓进来表示不理解,生怕“一粒耗子屎坏掉一锅粥”。张老师静静地考虑了一分钟,便答辩似地说:“现在,既没有道理把宋宝琦退回给公安局,也没有必要让他回原学校上学。我既然是个班主任老师,那么,他来了,我就开展工作吧。”
张老师还没开展工作,班上的团支书谢惠敏就找他来了。谢惠敏单纯真诚,品行端正,除了随着大伙看看电影、唱唱每个阶段的推荐歌曲,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她功课平平,作业有时完不成,主要是由于社会工作占去的精力和时间太多了。“四人帮”垮台前,谢惠敏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四人帮”在市里的黑干将已经控制了市团委,并向光明中学派驻了联络员,谢惠敏经常被找去谈话。打从这时候起,张老师同谢惠敏之间开始显露出某种似乎解释不清的矛盾。比如团支部过组织生活能不能搞爬山比赛,夏天好学生能不能穿短袖衬衫和裙子等。班上只有宣传委员石红穿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还有那种带褶子的短裙,这在谢惠敏看来,乃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的表现。
粉碎“四人帮”后,张老师和谢惠敏之间的矛盾还没有完全消除。听说小流氓宋宝琦要来班上后,谢惠敏找到张老师说,班上同学都知道宋宝琦要来,有些女生害怕了,说是明天宋宝琦真来,她们就不上学!张老师问谢惠敏怕不怕?谢惠敏晃晃小短辫说:“我怕什么?这是阶级斗争!他敢犯狂,我们就跟他斗!”
听了谢惠敏的汇报后,张老师决定召开一次班干部会,要求男女班干部分头做男同学和女同学的工作,然后同谢惠敏单独谈了一次话。谈话结束后,张老师在清点宋宝琦从派出所带回的物品时,发现里面有一本“文化大革命”前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牛虻》,张老师没想到宋宝琦还有这本书,顿时神情有点异常,谢惠敏见状忙把那本书要过来翻看。她以前没听说过、更没看见过这本书,她见里头有外国男女谈恋爱的插图,不禁惊叫起来:“唉呀!真黄!明天得狠批这本黄书!”张老师马上说:“这本《牛虻》可不能说成是黄书。”两人关于《牛虻》是否是“黄书”的谈话,引起了正在教室一旁写“号角诗”的石红的注意,石红早就想找到这本书,于是跑过来与谢惠敏争辩起来。张老师见此,将已被撕掉封面、插图中女主角的脸上被画上八字胡须的小说放进书包,说:“关于这本书的事儿,咱们改天再谈。”
在宋宝琦家里,张老师跟这个明天将要进班上课的学生进行了第一次谈话。谈话中,张老师感到宋宝琦缺乏起码的政治觉悟,知识水平大约只有初一程度。宋宝琦将“牛虻”念成“牛亡”,说书是偷来的,看不懂。张老师问宋宝琦为什么给插图上的女人全画上胡子,宋宝琦说:“我们比赛来着,一人拿一本,翻画儿,翻着女的就画,谁画的多,谁运气就好。”宝琦的话引起了张老师的深思:谢惠敏和宋宝琦之间那么大的差别,但在认定《牛虻》是“黄书”这一点上,却又不谋而合,其实他们都没有读过这本书。
从宋宝琦家出来,张老师碰到了前往学生家进行个别辅导的尹老师。尹老师虽然爱发牢骚,却是一个教学认真负责的人。路上尹老师告诉张老师:谢惠敏跟石红吵架了。张老师一听,又赶到石红家。石红从小受家庭认真读书的气氛熏陶,是个“小书迷”。此时,她正在灯下朗读苏联小说《表》,旁边还有张老师班上的几位女同学。她们争先恐后地问张老师:“谢惠敏说我们读毒草,这本书能叫毒草吗?”“宋宝琦跟这本书里的小流氓比,他好点儿还是坏点儿呢?”她们还向张老师表示,明天不罢课了。
从石红家出来,张老师又骑车前往谢惠敏家。到谢惠敏家门口时,张老师心中的计划已经明朗:不仅要从这件事入手,来帮助谢惠敏消除“四人帮”的流毒,而且,还要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开展有指导的阅读活动,来教育包括宋宝琦在内的全班同学。
《人民文学》在编发刘心武的《班主任》时,正在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那时谁也不知道有一篇恢复‘五四以来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短篇佳作行将问世,谁也不知道刘心武这位默默无闻的文学新人即将破土而出”。
《班主任》的发表,既是历史给予作者的机遇,又与刘心武长期的生活积累有关。刘心武曾在中学当过很长时间的老师和班主任。他在谈到《班主任》的创作经过时说:“我所熟悉的生活,是城市中学的生活,我所熟悉的人物是一些平凡的教师、学生,以及学生的家长们,加上学校附近的胡同,街道上的一些市民。《班主任》当然也是我对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的一种提炼和开掘,但引起我提炼和开掘的动力,不仅来自我自己,也来自整个社会。整个社会都在孕育着一种‘救救孩子的呼声,只不过我呼出得比较早。而且,我剖析得比较深入,不仅指出了小流氓宋宝琦是畸形儿,还指出了团部书记谢惠敏是畸形儿。”
这并不是刘心武第一次发表作品。刘心武后来说:“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谈第四十一》,发表在1958年《读书》杂志第16期上,当时我还是个高中生,十六岁。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发表过约七十篇小小说、散文、评论什么的,大都非常幼稚;1974年到1976年,为调离中学,我为当时恢复出版业务的机构提供合乎当时要求的文稿,发表出若干短篇小说,一部儿童文学中篇作品,一部电影文学作品,这虽然都是些现在提起令我脸红的东西,但它们也可能使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们多少对我有些个印象,因而能及时审阅我的稿子。我对《班主任》敝帚自珍,因为那毕竟是我第一篇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自己真实认知的作品,我并因此成名,为世所知。”
《班主任》的创作毫无疑问带着当年那个年代的印记。小说有这样一个情节:张老师到任不久便轮到这个班下乡学农,返校的那天,队伍离村二里多了,谢惠敏突然发现有个男生手里转动着个麦穗,她不禁又惊又气地跑过去批评说:“你怎么能带走贫下中农的麦子?给我!得送回去!”那个男生不服气地辩解说:“我要拿回家给家长看,让他们知道这儿的麦子长得有多么棒!”结果引起一场争论,多数同学并不站在谢惠敏一边,有的说她“死心眼”,有的说她“太过分”。最后自然轮到张老师表态。出乎许多同学的意料,张老师同意了谢惠敏送回麦穗的请求。
小说中的张老师通过同宋宝琦谈话后,感到“宋宝琦的确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令他困惑的是究竟是哪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又说不清楚,最后张老师得出的结论是,“资产阶级在上升阶段的那些个思想观点,他头脑里并不多甚至没有,他有的反倒是封建时代的‘哥儿们义气以及资产阶级在没落阶段的享乐主义一类的反动思想影响”。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作者创作这篇小说的时候,“四人帮”倒台还不到一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刚刚启动,思想解放的大潮还在酝酿之中。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是一个崇尚文学的年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文化沙漠之后,人们对文学有着特别的渴求。《班主任》发表以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这也许是作者和编者都没有预料到的。“编辑部收到的各界读者来信不下数千封,来自祖国东西南北二十几个省区。当然教育战线的来信最多了,也有不少中学生、青少年写信控诉‘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对他们心灵造成的伤害”。贵州偏远山区某劳改所一个少年罪犯,在给《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信中,讲述自己与宋宝琦类似的经历,沉痛控诉“四人帮”“杀人不见血”。读了《班主任》之后,他翻然悔悟,决心重新起步。
湖北沙市的一百多名中学教师读了《班主任》后,给作者写了一封长达几十页的信。他们在信中写道:“和我们同样职务的张老师,以他强烈的责任感和求实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们的心。我们不是一样吗?身边有宋宝琦需要去挽救,周围有谢惠敏,有待引导。就连我们自己的思想,不也和谢惠敏一样,打下了‘四人帮愚民政策的烙印!我们要和张老师一样,为了中华民族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强盛地延续、发展下去,做一个党和人民满意的班主任。”
《班主任》发表的时候,人们已经有许多年没有看到这样的作品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几部样板戏外,只有少量的像《西沙儿女》那样的名为“高大全”实为“假大空”的作品。《班主任》给文艺界带来的是一缕新风。《班主任》的发表也引起了文艺界的高度关注,认为它是一部有思想深度,有独特风格的优秀作品,当然也有人认为它是“问题小说”和“暴露小说”。
1978年8月15日,《文学评论》举行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冯牧、孔罗荪、李季、严文井、韩作黎、许觉民、朱寨、林斤澜、刘厚民、屠崖、江晓天、邓绍基等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以及北京、上海有关报社、杂志社的编辑、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二中、北京市铁路中学的研究人员和教师等。与会者一致认为,《班主任》是一部粉碎“四人帮”之后出现的优秀作品。
作家韩作黎说,《班主任》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帮”对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的破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提出了人们普遍关心的青少年教育问题。《班主任》的作者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可贵的求实精神,通过文艺形式第一次尖锐地揭露了“四人帮”对青少年的毒害,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声。这是动人心弦的呼声,是亿万人民的呼声。
针对社会上一些人对《班主任》的责难,例如有人认为《班主任》是“暴露文学”,是“批判现实主义”,“没有写英雄人物”等。儿童文学家严文井说,如果说《班主任》是“暴露文学”,那是暴露“四人帮”的文学;如果说是“批判现实主义”,那是批判“四人帮”的革命现实主义;如果说是“问题小说”,那么“四人帮”留下的问题成堆,《班主任》提出来了问题,这仅仅是开始,还应该有一大批这样的“问题小说”问世才好。
文艺评论家冯牧说,参加会议的目的是来对刘心武同志的作品投赞成票的,对于《班主任》这样的作品,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用常理思考问题的人,有一定阅读能力的人,大概是不大可能作出小说有错误的结论的。但这样的作品居然受到了挑剔和指责,这说明“四人帮”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市场。对发展文艺创作来说,这还是一个严重课题,需要开这样的会来澄清事实,给予肯定。冯牧还希望作家、艺术家们都像刘心武那样勇敢地对待生活,勇敢地挖掘生活,不断扩大生活的视野,坚持创作从生活出发,坚持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塑造出真实的、不是千人一面的艺术形象,对人民群众起教育作用。
文艺评论家何西来也发表文章说:有人说,《班主任》是“问题小说”。问题小说有什么不好?《班主任》之所以能够强烈地激动着读者的心,不仅因为它坚持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发扬了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给了人们一幅生动的社会生活的图景,更重要的是它以震撼心灵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提出了尖锐迫切的社会问题。既然问题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必然会有“问题小说”、“问题戏剧”等等。优秀的作家总是为它生活的时代写作的,他不能、也不应当回避现实生活中的迫切问题;优秀的作品,总是表现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才能够激起读者,产生社会影响。否则,这样的作家就会被忘记,这样的作品也就没有什么价值。因此,我们要提倡《班主任》这样的问题小说。
一篇短篇小说能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像的。小说为广大读者所重视,最根本的是它提出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为广大读者所关注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们。尽管这篇小说发表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被彻底加以否定,但小说通过对“四人帮”的谴责和鞭挞,实际上是对这场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的所谓“革命”的控诉,从而引起了广大读者强烈的共鸣。
(选自《春天——1978年的中国知识界》/罗平汉 著/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