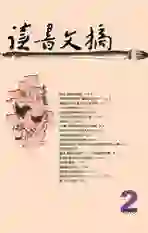何满子:特立独行的人与文
2013-03-27邵燕祥
满子本色是诗人。1998年春,他写了《开八秩自寿两律求和柬》:
坎壈一生,常忧非命;浑噩经年,竟开八秩。患难备尝,战乱亲更;能登中寿,亦堪自庆。才视袜线犹短,身较鸿毛益轻。劳体拂心,似天之将降大任;芜年荒月,胡帝之不佑斯文。昔尝自标独行无侣,不期归为小集团;今仍心许和而不同,甘作文学个体户。七十之年,曾叹臣之壮也窝囊极;今更耄矣,愈憾浪掷韶华不复回。聊占两律自寿,窃盼好事赐和。拙句抛砖,不吝还玉,不胜感祷。
垂暮光阴更骤催,浑浑噩噩八旬开。廉颇老矣犹乘马,陶潜归欤独举杯。秃笔何从排愤懑,长歌不足振虺尵。一生颠沛非由己,浪掷韶华不复回。
悬弧恰属绵羊岁,分合为时作宰牲。无得自然不患失,置之死地复逢生。播迁一世老方定,恩怨多端今乃明。仍有知心如许个,人间谁道乏真情。
我当时写了《奉和满子先生八十自寿诗》二首:
至今荷戟独行侠,昔日称名小集团。负轭盐车穷朔漠,校书海隅远文坛。辞章西汉夸双马,歌啸竹林只七贤。闻道汨罗江里水,流经笔管见微蓝。
集团有个又何妨,党锢千年忆范滂。或有高升或退隐,孰仍前进孰落荒。睥睨市井独慷慨,叹息光阴转杳茫。桑海孑遗康而寿,昂藏举酒不窝囊。
我与何满子先生过从不密,只是有事才通讯的朋友,见面机会不多,二三十年间,累计不超过十次。但我以为我和他的心是相通的。我读他写的书,文学评论研究可能没有读遍,但杂文集子差不多都读了。诗有唱和,文有呼应,也勉强可以攀为文章知己了吧。
坚守“我是我”
上世纪90年代初,林贤治拟办《散文与人》丛刊,嘱我约些稿子。满子写来的是《如果我是我》。此文层层剥笋,步步为营,先讲了在特殊年代里人们梦寐以求“如果我不是我”,即“宁不作我”的悲剧,指出“当人失去了自己,我不复为我时,所有的价值观可以听从摆布而随意颠倒,现成的理由是‘吾从众”,“在神州大地一步一步地走向神经病大地”。满子说:
我之所以为我,系于我有主体意识,我必须像忠实于人、忠实于世界那样忠实于我自己。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前,首先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己”。于是我才能心安理得,以我是我而欣慰,才有“宁作我”的自尊的执著。可叹的是,要做到“宁作我”,我行我素,宠辱不惊,虽千万人我往矣,实在不容易,很难很难。易卜生称颂孤独者是最强的人,正是痛感于独立特行之不易坚执。抗拒外力难,抱朴守素也难,何况生于斯世,还不仅仅是安贫乐道的问题,要守住“我是我”的防线,真须大勇者;能念兹在兹地提出“如果我是我”的自问,判定我该怎么说,怎么做,也已可算是称职的“人”了。完全失去了“我”,也就失去了“人”,当然仍不是称谓,而是实质。
是的,“如果我是我”,是一个严峻的命题。满子以他的为人和为文完成了“我是我”的坚守。他的所谓“独行无侣”,他的力求和而不同,他虽有“知心如许个”,却宁愿背向文坛,作“文学个体户”(以致他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后,所在地作协竟还说本地无一作家获奖,因为他不是作协会员,不计在“作家”之列),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行我素,言我所欲言。
满子有个他同代人多半没有的经历,就是少年时练习过八股文。“从旧的营垒中来”,他深知八股文的精神就是“代圣贤立言”,兜来兜去耍弄四书五经上那几句话,那诀窍就是孔夫子说的“述而不作”,是不必自己有什么见解的。满子反对这种八股文精神,他反其道而行之。无论做学问,写杂文,都有个“我”在,其独立思考、独立识见,同他独立的人格精神不可分。近有论者评述也是去年逝世的诗人彭燕郊,称颂这位同遭“反胡风”政治迫害的老诗人,具有“独立的精神立场”,两者庶几近之,虽说各自表现亦有不同。
提倡打笔仗
满子的笔管里流着汨罗江水,他坚执着屈原式的“发愤以抒情”或如他自己说的“排愤懑”,但他一般不止于情绪性的挥发,可怨可怒,而不忘“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文章学传统。他也有情不能已的时候,矫枉过正或显偏激,但仍然是言论生态的一环。所谓“深刻的片面”,某些情况下也许竟胜于平庸的全面,客观上足以激发争议,使真理愈辩愈明,至少聊备一说,打破官方主导超稳定的舆论一律或是民间舆论自发的一边倒,有助于考验乃至培育“异议正常”和“尊重(并保护)少数”的氛围。他写过《文学争执还是诉诸笔墨明智》,提倡“打笔仗”,以解决文人论世评文的“参商”,申说此理甚详。
满子不止一次指点过我杂文中某些观点的天真而近迂,那么他果然会相信这个呼吁能有多大的实效吗?无非是要求扩大言论空间,减少行政权力和长官意志的干预,也不过是“不说白不说”,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主动或被动打的笔仗,以致逼得鲁迅“横站”的,大体有文献保存下来了。还有一些与鲁迅无关的笔仗,近年也正由有心人拂去尘封。1940年代国统区的各样笔仗,作为报人和学人的何满子,都曾目击或亲经的。只是1950年代截止到1955年“反胡风”和1957年“反右派”致满子落难时,实际上已经没有双向的“笔仗”可言,有的是指挥刀下发出的大批判,甚至假借法律名义以至直接诉诸政治暴力对“思想犯”的“实际解决”。后来的二十多年固毋论矣。因此“文革”以后,满子似略无踌躇,就投入发言。以我当时的印象,他在1980年发表的《道德、时代思潮与爱情》对张洁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所作评论,分析透辟,逻辑严密,所见远远高于当时参与评骘的“正反”双方,显示了他厚积多年的功力,不因二十年的尘埋而稍弱。同年写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和非现实主义的评论——近年来〈红楼梦〉的研究现象一瞥》,次年为纪念吴敬梓诞生280周年写的《吴敬梓是对时代和对他自己的战胜者》,在当时都是发人所未曾发的谠论。后来他在文化批评中对相当大量市场化娱乐性读物(以言情和武侠小说为主)的严厉指斥,也早在1982年《论庸俗》等篇中就已定调,而其观点的形成则可在他一系列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专著中溯其源流。满子不是故步自封、抱残守缺者,但他也不是随时跟风逐势之辈。他自然赞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却不意谓他首肯市场经济对精神价值的侵犯,更不会对诸多这类现象默不作声。
评周扬与舒芜
满子自知他的处境。关于文化批评,他说,他写出来的,不免是些“背时的”话头,如现实主义和鲁迅传统之类,“很容易惹时下新才子的嫌”。其实,即使“现实主义和鲁迅传统之类”有其历史的局限,但在勘破“新才子”们的真面目时还是够用的。满子有《文人活得很累》一文,说:一种是为争当大众情人而累,一种是为儿童强装大人而累,一种是为不甘寂寞没话找话而累,此外,还有为无故寻愁觅恨而累,为窥风测向而累,为制造轰动效应而累,为赶新潮而累,为炒自己炒得不露痕迹而累……总之是鲁迅所说“借革命以营私”的变种,争做官场或商场的帮闲而已。满子活画出这路人的体态和眼神。鲁迅杂文“砭锢弊常取类型”,满子也正是这样。
对周扬和舒芜,满子的态度可以说“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矣,他就此为文既是作文化批评,也是作社会政治批评。固然,这里有围绕胡风一案的恩怨,但更要看到,在这里,被点名的个人是作为一种社会角色的符号甚至是“等而上之”者的代号而存在。他的《宜粗不宜细》一文,对所谓“宜粗不宜细”作了自己的诠释:“评论人物的是非功过,包括文人的是非功过,要从历史这本大账来评衡,不管其人从别的方面说来有这好那好,主要的和基本的就要看其人在应肯定的或应否定的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如何?这也是‘宜粗不宜细之道。”“如周扬,说好说坏的都有。但从历史作用论人物,十七年(邵按,即指从1949年建国至1966年“文革”)中的一条‘左的文艺路线最终导致文艺荒漠,作为文艺负责人的周扬的功与过,正面或反面就可一言而决。否则,叫什么历史唯物论,叫什么以历史观点评价人物?全是废话。”不是强调区分本质和主流么?不是要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么?这真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更可以说是“快刀斩乱麻”了。
当然,满子也无意叫周扬负他所不能负的责任。他只是点名点到周扬为止。他在《与邵燕祥议点名》和《以良知呼唤同代人的良知》两文中,一再说到曹禺名剧《日出》虚写了一个满台阴影无所不在、迄未出场却是全剧关键人物的恶霸金八,始终没有露面,然而呼之欲出,满子指出剧作家这一极具匠心的表现手法,较之“关键人物都应直写其名”的主张,可以说是另一路的“史笔”。
满子1998年写过一篇《同感于李辉和绿原》,因二人文中只写了受害者一方而未及一语于加害者,受到求全者的责备,满子为之辩护时回忆说,1983年某次他和已故的聂绀弩争辩胡风冤案中“交出私信”的责任时,绀弩说世人专门责怪犹大而不问总督是不对的。“他说这话当然另有一番感慨。我复述了赫鲁晓夫的故事(,说那时,以及还是‘格鲁吉亚化的当时,谁敢责怪总督呢?只有责怪犹大来泄忿”。所谓犹大,不过是总督的代号,正如“四人帮”在人们心目中早就成为封建法西斯主义及其体制的代号,并不限于“王张江姚”四个具体的人了。
捍卫鲁迅
满子对于贬损鲁迅的人,无论是操“文革”文风写官样文章的“帮忙”文人,还是从另一边鸣鞭示警的小文人,都不吝其疾恶如仇的健笔。前者如提倡所谓杂文只能以“歌颂”为基调而不宜进行“批判”的“新基调杂文”论一伙,其实是不值一驳的;后者则如有一人竟说鲁迅后期是“病中鲁迅”,是“鲁迅后期感染的‘新基调病态,带来一场历时半个世纪的杂文的悲哀”,这个加之于鲁迅的破坏杂文的罪名不小,而其根据就是鲁迅晚年对中共的同情和“对苏俄革命的全盘赞同,奋力歌颂”。此人欲抑先扬地说:“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学者,一个杂文家,特别是作为中华民族魂的代表,他是否可以根据中外历史规律而预测苏俄的发展,从而对这新生事物的呐喊有所保留,有所警钟(原文如此)呢?以他的胆识才智,完全应该是可以的。可惜他没有。”这就成了大张挞伐的理由。满子在申说鲁迅后期杂文成就的同时,也把这样胡说八道的苛责(时髦说法是酷评)保留下来,可算得“立此存照”吧。
满子于鲁迅后期杂文中,格外推许《病后杂谈》、《阿金》、《题未定草》诸篇,以为哪个杂文家能写出这样的一篇,就堪千古不朽。看得出满子也是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他的杂文以文化批评居多,其社会批评或融入文化批评之中,或有确实按捺不住的激情,如谈血亲交班,权力挪用,流氓当道,外行领导,也多用鲁迅笔法,“奴隶语言”,痛快淋漓后面有隐喻曲笔,嬉笑怒骂之中是兴观群怨。
勘破新才子的真面目
满子作文化批评,因有坚实的文史根柢,杂家的旁收博览,常能举重若轻,揭隐发微,触及要害。试举一例。针对一种指批评者与盗版者为合谋,说一个谋作家的财、一个毁作家的名,共同扼杀文化的妙论,满子转引了一个《黠妓斥盗》的佛经故事,起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寓言有趣,录如下:
昔有一娼,姿质平常。
性擅魅惑,艳帜高张。
雅善辞令,风流名扬。
颠倒众生,蝶浪蜂狂。
收敛夜度,缠头盈箱。
子弟沉迷,父兄怨怅。
邻舍侧目,视为祸殃。
群起咒责,惊动街坊。
此娼积怒,强自包荒。
爱侬恋侬,是彼儿郎。
尔辈詈骂,于侬何伤。
乃甚矜持,得意扬扬。
忽有一日,遭逢强梁。
细软被劫,痛彻肝肠。
怒火填膺,怨忿盈腔。
兼怀夙嫌,骂槐指桑。
痛诟盗贼,又诬善良。
谓鄙己者,与盗同行。
里应外合,谋害娇娘。
意在为己,构一屏障。
义形于色,冠冕堂皇。
从此天下,谁敢平章。
如此黠妓,天下无双。
这个黠妓把指责她卖笑的邻人和盗窃她卖笑所积财富的强盗一锅煮,来堵指责者之口,满子说他“盗一下版”,称发上述妙论的文人为“黠文人”,“不亦宜乎!”
其实早在几年之前,此“黠文人”还是个小文人的时候,满子和拾风就曾对他进行批评,缘于他在为学生讲课中,不知是一时失言还是处心积虑,指责巴金在“文革”中表现软弱云云(大意如此,原话还要难听),而他在运动中却正是大批判组的红人,大有得便宜卖乖之概;彼时居高临下,此时还是居高临下,彼时所居者是权势制高点,此时还仿佛要占领道德制高点,满子和拾风忍无可忍了,但他们的文章,也不过是教他怎样做人,可惜这不是他所需要的,便如对牛弹琴了。
笔法直追鲁迅
有报人的杂文,有学人的杂文,前者多为时评,后者近文史随笔。满子作为杂文家,他融报人杂文和学人杂文于一炉,指点时事,针砭时弊,不限于就事论事,常能揭示沿革,理清脉络,且如梁启超“笔端常带感情”;而于书评序跋,叙事怀人,则往往扩大视野,纵贯古今,感发深广,而又迫近现实,拷问时流,笔法直追鲁迅。
在他的《论〈儒林外史〉》、《中古文人风采》、《中国爱情与两性关系——中国小说研究》等学术著作中,同样毫无八股气与学究气,既见其学养沃厚,复见其思维活跃,视角独特,且是面向当前来发言。
何满子先生的学术专著和杂文随笔,文体多样,异彩纷呈,而贯穿其间的是一派浩然之气,憎爱分明,心口如一。这使我想起他对尼采的评论,摒弃了尼采的超人理念和权力意志说,以及非理性的狂悖之后,推崇尼采对奴隶道德的彻底否定,对陈腐秩序的抨击,对麻木的庸众的恼恨,满子说,“这种人格力量和叛逆精神都值得珍视,特别在封建陋习尚未蜕尽的今日中国更是如此”。早年的鲁迅从尼采那里取得了冲击旧势力改革国民痼疾的精神力量,师从鲁迅的满子也该是从这一渠道接受了尼采的一些影响——属于积极方面的影响吧。
纪念满子先生,文字俱在,其人不远。让我们清点他的精神遗产,化为我们的精神财富:这一定是无私的先生所乐意看到的。
(选自《先生之风》/丁东 主编/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