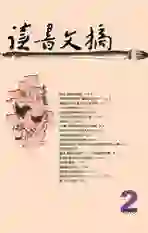“文革”暴风骤雨中的人艺群星
2013-03-27周冉
周冉
人艺群星璀璨,但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太过短暂。建院初期绽放光芒后,随着“反右”和“文革”的风暴来袭,人艺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运动的汹涌洪流。优秀的艺术家们,被裹挟着向前,身不由己。
老舍:少开会,让我下乡
解放后老舍回国,他对国内的重大政治题材并不熟悉,接到写作任务,觉得既然是党的要求,就应该边学边写。1952年初,“三反”、“五反”运动尚未结束,老舍为人艺写了反映该运动的《两面虎》,后改名为《春华秋实》。
当时他看了很多政策材料,家里还请了个老先生,专门抄文稿。初稿出来后,各方的修改意见纷至沓来,有来自基层的,也有来自“上面”的。《春华秋实》前后写了十二稿,每次都是从头写起,最后定稿时已经完全没了初稿的样子。采纳的意见太多,剧本像个大杂烩。
老演员蓝天野说,让谁写《春华秋实》都很难,戏都在资本家身上,工人、干部形象很难写。社会上出现什么大事,老舍很快就有作品出来反映。1955年写了《青年突击队》,1958年赶写《红大院》,都是配合一时一事,演完了,戏也就完了。
1956年,中国作协收集会员对作协的建议和要求,老舍就写了两句话:“少叫我参加会议与社会活动,允许我下乡数月。”他曾跟人艺老演员李翔发牢骚:“作家是写书的,不要参加这会那会,让我写不了书。”
焦菊隐:给《茶馆》加条红线
1958年《茶馆》上演,在文艺界引起不小反响。有人说戏宣扬了“一代不如一代”、“今不如昔”的调子,认为作者有怀旧思想,对没落贵族给予极大同情。更有甚者说,这是在影射“公私合营”。
7月10日,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在人艺党组扩大会上说:“你们现在偏重艺术方面去建立风格,政治灵魂不在意了……焦菊隐是资产阶级的教条主义。……生产上我们很先进,比如白薯一亩地产五十万斤,本身就是很大的浪漫主义。惟独艺术上,我们还像乌龟一样在爬。”
不久,《茶馆》停演。欧阳山尊后来回忆说:“1958年开始‘左倾,越来越厉害,一直到‘文革。”
一次周恩来到人艺看《红旗飘飘》,散戏后上台和演员合影,突然问身边的于是之:“《茶馆》这个戏,你们为什么不演了呢?”于是之怔住,半天没说话。周恩来说:“那个戏改改还可以演嘛!”周恩来说这话之后,人艺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研究《茶馆》的改动方案。
1963年,《茶馆》重排。“反右”时被保护过关的焦菊隐花了很大力气抓“红线”问题,他说:“加的红线都是主要的戏,是为了提髙戏的思想性。要搞好红线,才能压住那些表现旧的、要否定的生活的戏。”
最后《茶馆》加了一条学生反帝反封、反国民党统治的“红线”,全剧结尾改为学生上台贴标语,常四爷张罗送开水……当时扮演常四爷的郑榕说:“这些都是硬贴上去的,和老舍先生的格调极不协调。”
复排演出时,老舍兴致颇高地又看了一遍,但看完后不像以往那么爱说话了,对《茶馆》加红线问题也不言语。后来他只淡淡地说:“我对这个情况不熟悉,你们看着办吧。”
周恩来:人艺要放个“大卫星”
1958年,“大跃进”高潮来临,剧院对口支援北京大兴,提出创作鼓词、快板、诗歌、壁画、舞蹈、歌词二十万件,争取每乡有一个文化馆,每村有一个合唱团,每个生产小队有文艺小组。当时的口号是:“盖门头沟,压西城区,大干苦干创第一。”
8月26日,北京市文化界开展群众“文化工作跃进誓师大会”,几十个文艺团体竞相做“比武”发言。人艺党委秘书周瑞祥回忆,当时青艺盯着人艺,舒绣文在台上报数字,放出一年演出九百场这个“卫星”时,书记赵起扬说:“打住了,打住了,不能再上了。”为了凑这个数字,在火车上打快板就算一场演出,下火车在车站再打快板,又算一场。
一天中午,剧院接到上级指示,要求全院立即投入炼钢战斗,争取第二天出钢。院里马上找人联系炼钢炉及原料,成立“炼钢办公室”。院领导分析情况后,认定第二天出钢不可能。又缓了几天,终于在剧场后院花房西侧建立了炼钢炉,碾碎很多水管、通风管和铁锅,统统扔进炼钢炉。
据欧阳山尊回忆,突击炼钢那几天,恰逢日本戏剧家千田来剧院访问。欧阳山尊正跟千田说着话,外面有人喊:“欧阳院长,要出钢了。”千田很诧异,问明情况,连连说道:“新经验,我要看看。”到了剧院里的炼钢现场,千田连竖大拇指:“向你们学习。”
剧院快速写出了反映大炼钢铁运动的《烈火红心》,仅排了三四天就上演了。周恩来曾问人艺,新作《英雄万岁》几天能排出来,有人回答六天,还有的说十天。当时在场的演员李婉芬、马群、英若诚回忆,那天周恩来兴致颇高,表示:“你们人艺是老剧团了,明年应该放个‘大卫星吧。”周恩来还引用了当时人艺剧中的一句台词:“我把这个合同就订在你们这儿了。”
老舍:祥子能活到现在吗
1965年,人艺曾把舞台搬到天安门广场,剧院除了排练革命歌曲大联唱,演的话剧、快板等,内容都是声援刚果(布)反帝,还递交了声援书。
剧院党委决定在十几天内写出斗争戏《刚果风雷》提纲,还没操作完,市文化局又布置创作反对美帝侵略越南、支援越南人民斗争的剧本。剧院只好在两个排练厅分组突击排练,每天分三班进行,五天内排出大样。紧接着,中央又决定举行活动支援多米尼加人民反美斗争。剧院在当晚十点半召开全院动员会,决定第二天全天突击排练大型活报剧《反帝怒火》。郑榕说:那时候一个运动跟着一个运动,躲不过去。往往以运动为主,排戏为辅。
老舍越来越觉得自己跟不上外面轰轰烈烈的形势了,他已经很少去看人艺的反帝戏,人艺也没有再请他写戏。有一次,他突发奇想,对演员李翔说:“你说,咱们的祥子能活到现在吗?”老舍要创作《骆驼祥子》的续集,让祥子变成解放军干部,领导车夫闹革命、迎解放。后来算了算,祥子要是活到那个时候,年纪太大,早就干不动了,剧本太不可信。已经写好的两幕戏成了永远没完成的半成品,被老舍扔进废纸篓。
有一次看完意大利歌剧《女理发师》,周恩来留下一些艺术界人士,讨论该剧存在的问题。一个个问过去,别人都不敢说话,只有老舍说了一句:“我反正听不懂。”
文联组织人员下基层,偏偏不理老舍。他回家后带着微笑,但是说话非常凄凉:“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
赵起扬:“好书记”成了一大罪状
1966年开始,人艺不搞业务,转而务农搞运动。1月31日,北京市委决定撤销焦菊隐的副院长职务,勒令《茶馆》演员揭发焦菊隐在创作上的问题。4月16日“三家村”被批,北京市委宣传部指示,“批焦”的工作立即上马。
6月18日,人艺党委书记赵起扬遭受批判。群众组织宣布夺权,剧院领导一律列为黑帮,北京人艺改名“北京人民文工团”,剧院领导被抄家。“好书记”成了赵起扬的一大罪名,这是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对他的评价,当时周扬已被打倒。早在1955年肃反时,赵起扬就力保过一些历史上有问题的演员“继续演戏,在工作中教育改造”。曹禺评价赵“敢于作出重大决定”“是个‘顶得住的人”。但是这次,赵起扬也没能“顶得住”。
老舍在京剧院里和马连良等人一起跪着,看造反派烧戏服,在家中被暴徒打骂。8月24日清晨,他向小孙女告别,说了声“跟爷爷再见”便一去不返了。后来有人在太平湖畔发现了老舍的一只鞋,尸体始终没捞到。
老舍投湖前不久,跟郭沫若和人艺的领导、演员们一起坐船逛颐和园,几个人下水游泳,欧阳山尊在一旁劝老舍也下水。老舍说:“我扎猛子下去,半天都上不来,上来后又白又胖。”这句无心玩笑,竟一语成谶。“这么大的事,本来大家应该议论纷纷,但没有。”人艺当年冷漠麻木的氛围,让演员英若诚感慨万千。
曹禺:最大的毛病是听话
剧作家吴祖光曾说:“万家宝的最大毛病就是听话。”万家宝是曹禺本名,他向来礼数周全,哪怕是小字辈去看他,他也会恭敬地送出门。对周恩来,曹禺更要目送汽车远去,还要对着车尾鞠一躬。
造反派对曹禺还比较温和,只让他每天按时上下班,看大字报,写大字报,学习政策,准备交代问题。曹禺每天从铁狮子胡同三号的住宅,胆战心惊赶到首都剧场,见谁也不敢说话。有时造反派还要曹禺按照“两报一刊”的社论,写出自己的表态文章。
“文革”时期,剧院搞部队编制,“历史清白”的梁秉堃当了联排班班长,曹禺是班员,他管梁叫“老班长”。写交待材料时,曹禺总过不了关,梁秉堃就帮他写,从《红旗》杂志上抄口号,把自己骂得不是人。曹禺回家难受得直抽自己嘴巴。
一天夜里,红卫兵破门而入,把曹禺从床上拖下来,押到中央音乐学院小礼堂。屋里不许开灯,所有人靠墙席地而坐。直到天渐渐放亮,曹禺偷偷一看,发现和自己关在一起的有彭真、刘仁等领导,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周恩来听了有关方面报告,赶到关押曹禺的现场,对红卫兵头头说:“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嘛,你们为什么把他抓来?赶快把他放回去!”
欧阳山尊:不敢和邓颖超打招呼
样板戏盛行的年代,欧阳山尊就与话剧无缘了。他被冠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帝苏修的狗洋奴”、“大流氓坏分子”三个“头衔”,被罚站小板凳,关进牛棚。他的学生专门去人艺的牛棚看望他,师生静坐片刻,相顾无言。学生悄悄塞给老师两包好烟,含泪起身离去。
“文革”期间,周恩来再没有到首都剧场看过戏。一次偶然的机会,欧阳山尊遇到邓颖超,他后来回忆这次见面说:“由于我那时尚未‘解放,不敢和她打招呼,倒是她主动来招呼我,并意味深长地说:‘有一些文艺界的朋友给总理和我写信,我和总理约好了,在这期间,所有给我们的信都只好暂不作复。”
1971年,人艺恢复运转,改名北京话剧团。江青提倡“救活话剧”,于是重新开始排剧。剧院花了几年时间排《云泉战歌》,歌颂农村干部阶级斗争精神,导演是欧阳山尊和夏淳。主演郑榕说:“那时每出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云泉战歌》就得改台词,主角天天背新词。”
焦菊隐:七块钱的骨灰盒
1972年,焦菊隐被允许观看了《云泉战歌》联排。看完戏后有人征求意见,焦菊隐直言不讳:“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打二十分。”
很快,剧团临时党委决定,把焦菊隐作为“靶子”开展批判,成立专案组。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高潮中,焦菊隐被点名批判,并被定为死不悔改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以剧目为纲”和“重用牛鬼蛇神”是他的两大罪状。他悲愤地对友人说:“我已经彻底绝望了,今后我再也不能做导演了!”
焦菊隐被抄家后,独自住在剧院大楼背后一间常年不见天日的小屋里,靠近公厕,阴暗潮湿。一次他因胸部疼痛住进医院,经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他对女儿说,自己在“文革”中写了几百万字,可惜都是交代材料,现在只想把自己多年做导演的心得体会写下,留给后人。
1975年2月18日,身心备受折磨的焦菊隐,没来得及留下只字片语便郁郁而终。此时,老舍已去世九年。焦菊隐死时,军宣队长宣布:只能给他买最便宜的、七块钱的骨灰盒。
1976年“文革”结束后,坚冰开始融化。1978年,人艺恢复本名。这一年,于是之主演的《丹心谱》是最重要的大戏。6月6日,人艺第一台复排大戏《蔡文姬》开始售票,每人限购四张,购票的人潮势不可挡,一度挤塌了首都剧场的南墙。人们都在热情期待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选自《文史参考》201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