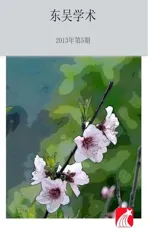地狱门前的思索
——《双典批判》①序
2013-03-26林岗
林岗
地狱门前的思索
——《双典批判》①序
林岗
刘再复一九八九年去国远游,正值学术研磨和积累的盛年。不少他的朋友为此惋惜,他自己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人生考验。然而,他的人生正是在颠沛流离的异国漂流中获得了凤凰涅槃般的再生,完成了心灵与精神生命的蜕变。二十年来,语言就是他的故土,语言就是他的祖国。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并不能截断由语言纽带连接起来的文化与精神的通道,顺着这条由圣哲先贤、先知前辈构筑的神秘小道的指引,他接通精神血脉,在遥远而陌生的土地抒写性灵,寻绎人性,反思现实,探索历史。一如八十年代时那样,他在文学创作和学问探索两个方向用功,笔耕不辍。一面以饱含深情和智慧的诗性文字,绵延着文学的血脉;另一面以无畏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承继着博学、审问、明辨、慎思的问学传统。这二十年的文学创作有《漂流手记》、《远游岁月》、《西寻故乡》、《独语天涯》、《漫步高原》、《共悟人间》、《阅读美国》、《沧桑百感》、《面壁沉思录》、《大观心得》等漂流系列散文,共十卷;而学术著作也在思想史、文学史和作家评论等数个方向上展开,先后出版有《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等被称为“红楼四书”的关于《红楼梦》的四种评论,还有《现代文学诸子论》、《放逐诸神》、《高行健论》、《罪与文学》等多种著作,还有产生广泛回响的与李泽厚的对谈集《告别革命》和海外访谈集《思想者十八题》。刘再复的学术眼光在去国之后益加深邃,学术视野益加宽阔,学术境界亦进入纯粹之境。近日读到他刚写完的新著《双典批判》,更是深有感触,他的思想锋芒一如往日。
一
“双典”是刘再复书中用语,指《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今次,他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几乎是最多国人阅读、最受读者和通俗媒体追捧的古典小说。水浒和三国不仅是被国人阅读了数百年,而且是被国人崇拜了数百年。如果以不计阅读质量而仅计算发行数量而言,笔者相信 “双典”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古典小说,在红楼、西游、金瓶之上。文学批评关注的虽然只是小说,要是算上说书、鼓词、评弹、影视、漫画、网络游戏等古老和现代的媒介形式,那水浒和三国的流传程度,更是惊人。“双典”浸润了一代又一代的“三国迷”、“水浒迷”,喂养了一代又一代“三国中人”、“水浒中人”;“双典”既是语言文字载体的小说艺术,又同读者的崇拜、批评的追捧、其他媒体的利用一起,构成一种文化现象。刘再复的《双典批判》,以一人之力与这种文化现象抗衡,大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他提出的基本论点是具有震撼性的,对“三国迷”和“水浒迷”无异于当头棒喝:
五百年来,危害中国世道人心最大最广泛的文学作品,就是这两部经典。可怕的是,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仍然在影响和破坏中国的人心,并化作中国人的潜意识。现在到处是“三国中人”和“水浒中人”,即到处是具有三国文化心理和水浒文化心理的人。可以说,这两部小说,正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
不过,刘再复也是讲道理的,他并不是要故作惊人之论,并不是要跟中国无数的“水浒迷”、“三国迷”过不去,而是把自己对作品真切的见解提出来,唤起读者的思索。哪怕是不认同刘再复的看法,也不要跳将起来,而是要心平静气,好好想一想,他提出的问题值不值得我们顺势检讨“双典”的基本价值观。文学作品是以潜移默化之力去影响读者和人心的,也就是梁启超说的“浸、熏、提、刺”的作用。艺术的水准越高,修辞越加精妙,如果它的基本价值观是与人类的善道有背离的,那它的“毒性”就越大。就像毒药之中加了糖丸,喝的人只赏其甜味,而不知觉毒素已随之进入体内。水浒和三国正是这样艺术水准很高而修辞精妙的文学作品。刘再复虽然批判“双典”,但并不否认“双典”的艺术价值。而正因为它们的艺术性,才要将被伪装包裹起来的有问题的文化价值发掘出来,郑重地指出来。用他的话说,这两部小说的最大问题是,“一部是暴力崇拜;一部是权术崇拜”。
刘再复是以文化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两部小说的,他把水浒和三国的文化现象放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观察,提出了“伪形文化”的问题。刘再复受斯宾格勒的启迪,从斯氏《西方的没落》中分析阿拉伯文化的“伪形”演变,而联想到中国文化在历史演变中的“伪形”问题。不过斯宾格勒以为宗教力量的渗入是引起阿拉伯文化“伪形化”的原因,而刘再复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新解,认为中国文化的“伪形化”不是由于外部文化力量的融入渗透,而是由于“民族内部的沧桑苦难,尤其是战争的苦难和政治的变动”原因。笔者以为,这确实是一个对历史有锐见的观察。
晚清时期进化论思想弥漫中国的知识界,以为努力进化,人生与社会也必将臻至一个尽善尽美的境地。章太炎先信后疑,提出“俱分进化论”,抗诘来自西方的这股“科学乐观主义”。他怀疑“进化终极,必能达于尽美醇善之区”的看法,而以为“善亦进化,恶亦进化”。章太炎这“恶亦进化”的思想,与刘再复《双典批判》讨论的文化“伪形化”,实在就是异词而同指,“伪形”其实就是人类恶根及其文化在历史演变中的积累和沉淀。返观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历史是朝着道德至善的方向进化。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人类的善根在发扬光大的同时,恶根也不甘示弱,所以人类的为祸也呈层级递进之势。这一点,中西皆然。“伪形文化”开了苗头,也如同杯中茶垢一样,日积月累,越来越厚,而人们的生活也因此而习非成是,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欧洲史上,迫害异端是其文化的“伪形”之一。从罗马帝国时期迫使不甘就范的基督徒徒手与猛兽搏戏于斗兽场,到中世纪教廷对付巫女、异教徒的火刑柱,再到二战纳粹以工厂流水线的现代技术屠杀犹太人。这种迫害异端的“恶的进化”使人触目惊心。
刘再复揭出“双典”崇拜权术、崇拜权力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其来有自。从先秦诸子开始讲“术”讲“势”,教导人主如何使用“诡道”,以四两拨千斤。同时,更重要的是大一统局面开创了巨大无比的官场舞台,供各式人主、人臣于其间长袖善舞。历经兵燹人祸,朝代更迭,权力舞台如走马灯来来去去,你方唱罢我登场。其间的残忍苛刻、阴谋诡计不计其数,这种反复进行的逆向淘汰,终于在元明之际结晶为它的 “伪形”表述——叙述一场场勾心斗角故事的文学文本,成就了一本中国人生的通俗教科书。任何一个有观察能力的人,都不能否认小说三国与这种历史和文化的联系,而这部小说之所以受到那么多国人的追捧,亦只有从这种历史和文化中才得到说明。北宋欧阳修作《新五代史》,就写过一位与罗贯中笔下三国诸君貌异心同的人物,这就是历事五姓九君而与孔子同寿七十三岁而亡的冯道。他的寡廉鲜耻真是堪当虚拟的文学形象与真实历史人物的恰当匹配。怪不得欧阳修在冯道传的序文中感叹:“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而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从先秦诸子的讲“术”讲“势”,至五代史冯道出神入化的运用,再到《三国演义》的荟萃提炼,或以为这就是权术文化的炉火纯青,达到了极致了吧?孰知不然,它的当代演变还有更精彩的“集大成”。刘再复在《双典批判》中提到他“文革”中痛切的经验,知晓所谓“政治斗争三原则”:
1.“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2.“结成死党”,3.“抹黑对手”。
这个总结,比之《三国演义》更画龙点睛,也更有“现代性”。但是这种“现代性”不是使一个国家的政治迈向文明和人道的现代性,而是迈向万劫不复深渊的“现代性”,也就是中国历史文化演变数千年而沉淀下来的“伪形”。这是绵延不断的“恶的进化”,这是讲究权谋术数的渣滓。
同样对造反性的暴力无条件的崇拜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演变而形成的“国粹”。暴力相向在人类历史上也许是与人类存在相始终的现象,但是对于造反的暴力在伦理和道义上给予如此积极而正面的价值,在各大文明传统中,恐怕是只此一家而别无分店。西方世界给予造反性的暴力在伦理上的首肯始于现代史上的法国大革命,而中国,笔者相信从神话至文明史的开端便是如此。如果这也是人类史本身一种伦理的“突破”,则中国文明无疑是先拔了头筹。可惜的是,这种“先知先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留下了沉重的伦理包袱。如何评价造反性的暴力在中国史上的意义,也许不是这篇短文能说清楚的。但是今天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它是一种灾难性的“伦理突破”,它连同它造成的历史灾难确实应当唤起现代中国人反省此种政治伦理。从古至今一贯不容置疑的暴力造反的正当性,应当被放在现代政治伦理的天平上拷问。
当年齐宣王与孟子论起汤放桀和武王伐纣的事,因汤和武王都曾向桀和纣称臣,至少是伪装地称臣,所以齐宣王略有挑衅地问孟子,“臣弑其君,可乎?”不料孟子起而强辩,“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未闻弑君也。”这段对话是中国政治伦理学史上的一个分界线。一夫是否可诛,这是一个可容辩论的问题。但从此以后,臣诛君、民诛官、下诛上,甚至彼诛此,都可以借助“诛一夫”的旗号进行而有了充分的道义正当性。孟子这种政治伦理观念,不仅仅是他个人“好辩”的产物,而是表现了悠久的民族集体意识。比“诛一夫”更流行的古代口号无疑就是“替天行道”了,“一夫”的抹黑毕竟比不上“天道”那样崇高而有美名。而比“替天行道”更通俗的现代口号是“造反有理”。现代的降临伴随着“天道”的隐替,“天道”无人相信了,当然就比不上“有理”更加鼓舞现代人心。至于有什么理,则不需说明,这“造反有理”的口号更带着一股横蛮无忌、勇往直前的“现代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领教过了的“最高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有千条,有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什么理,老人家还是没有讲出来,我们可以视作这代表了路人皆知而不必讲的常识,连老祖宗的精华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那它不是日常生活的常识是什么?
翻开历史,历代揭竿谋反的豪杰之士无不利用“天意”来佐证暴力的正当性。喊着“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口号的造反始祖陈胜、吴广,当年便自书“大楚兴,陈胜王”,将它塞入鱼腹,置于鱼肆,再阴使人取回剖开,示愚民百姓以为“天意”,又使心腹夜晚学狐狸叫说,大楚当兴陈胜当王。将这种伪造的天垂示当作自己 “替天行道”的证据。汉末张角行五斗米道,自编民谣,“苍天当死,皇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又使亲信传唱,以为民谣。元末红巾军谋反前,好事者先凿一独眼石人,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然后趁着月色将它埋在即将开凿的河道中,并预先散布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待开河民工掘出石人后,谋反者群起煽动,以为上合天意,下符民心,由此而展开轰轰烈烈的元末群雄大起义。水浒所写两个造反的头领,晁盖和宋江都善于运用此种由来已久的手法,证明啸聚山寨,暴力揭竿的正当性。晁盖等七人策划取“那一套富贵”生辰纲时,晁盖便向众人说了自己的一个梦兆,“我昨夜梦见北斗七星,直坠在我屋脊上,斗柄上另有一颗小星,化道白光去了。我想星照本家,安得不利?”一个实际上的抢劫行为,经梦兆的打扮就成为“替天行道”的光荣。诸路好汉“小聚义”于梁山,经过一番推让排定座次,宋江便津津乐道给他带来灾难的民谣:“‘耗国因家木’,耗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家头着个木字,不是个‘宋’字?‘刀兵点水工’,兴动刀兵之人,必是三点水着个工字,不是个‘江’字?这个正应在宋江身上。”他的应声虫李逵闻声跳将起来呼应:“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无论古代的“替天行道”,还是现代的“造反有理”,笔者相信,草根的复仇和被压迫者原始的仇恨本身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造反者的暴力在中国史上可以那么血腥、残酷,在此基础上必须加上政治伦理的力量,才能说明它的血腥性和残酷性。因为政治伦理就是意识形态,它给人的行动赋予正当性,当一个暴力行为被说明了是“替天行道”或“造反有理”的时候,当事人便只觉得其合理,而不觉得其残酷、血腥。当风云际会,人们集合在这种正当性的旗帜下之时,人性中的暴力倾向就被组织化了,组织的力量便把暴力的灾难推向更高的层级。人的良知和天性被这种意识形态层层遮蔽,往而不返。当我们观察历史上暴力现象的时候,深感可怕的甚至不是暴力本身,而是把暴力打扮得合理正当的这种“替天行道”和“造反有理”的意识形态。当我们从当代的暴力灾难远溯历史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绵延而累代加强的这种文化的“伪形化”。此种“恶的进化”造就了中国文化中对造反性暴力的崇拜。
二
权谋术数,有人群存在的地方就有它的市场,本无足怪。但是由于有了三国,它获得了生动而通俗的表达方式,耳濡目染,口沫手胝,于是造就了传人无数;同样揭竿谋反,有国家神器便有它的存在。但是由于有了水浒,一纸风行,深入人心,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它使勇者效法,“该出手时便出手”;它使心窃喜而怯者元神振作,“风风火火闯九州”。三国和水浒传递的拙劣的文化价值及其老少皆宜的魅力使得“双典”成了国人“厚黑之学”的最为通俗而引人入胜的教科书。在历史上,“厚黑之学”教导出来而最成功的门徒其实就是中国最末一个朝代——清朝——的统治者。清人得以定鼎中原,《三国演义》之功不可没。如果当年不是皇太极效法周瑜利用蒋干盗书的反间计使崇祯杀害了令满洲人闻之胆丧的明朝边疆大将袁崇焕,清人的入关乃是难以想象的。说不定一部国史没有什么“清朝”的字眼儿而只有“后金”。一本通俗小说开创了一个朝代,这样的说法多少有点儿夸张,但是只有那些食髓知味的实践者,才会对坊间的演义小说感激涕零,深知其价值。文学的作用从来就是难以估量的,我们无法将它数量化,也无法将它实证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的作用可有可无,看看“双典”的风行程度,便可知它们潜移默化的力量巨大。
对于三国和水浒中的负面遗产,其实本来是应该好好清理的,尤其是一个国家迈向现代文明和建设自己现代生活的时候,崇拜权术和崇拜暴力可以演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刘再复的《双典批判》提出一个很有价值的假设:“如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把孔夫子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而是把《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作为主要批判对象就好了。”或以为历史不能假设。当然过去的事情不能重来,但通过假设我们能够看清历史,能够分清善恶,能够辨明义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迈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关键一步,胡适就认同五四新思潮是“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运动。而被置于“重估”的那些价值中,恰恰是缺漏了水浒和三国,而儒家和孔夫子则被置于清算的火炉上烘烤。九十年过去了,事后想来确实觉得这是一个当年的“战略误判”。这个误判或许与先驱者造反心理存在某些联系,对一切来自民间、来自大众喜好的东西有一种不加鉴别的奉承倾向。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中,“平易”和“通俗”的文学就列入未来向往的目标。按照胡适白话文和陈独秀“三大主义”的标准,水浒和三国除了属于古代的之外,与五四文学革命并没有冲突。由于语言选择和民众喜爱,“双典”逃过了五四文化价值的 “重估”。不过,我们不能由此而苛求五四,中国社会的现代进程是漫长的,价值的“重估”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刘再复在新的社会现实条件下,提出“双典”批判的话题,正是对五四“重估一切价值”精神的传承,也是补足了五四未能完成的“国民性”检讨和批判的一课。
正如刘再复在《双典批判》中指出的那样,鲁迅其实是明确意识到水浒和三国与国民性的深刻联系。鲁迅的话可以作证:“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与水浒气的缘故。”没有国民拥戴的基础,任何小说都不能“盛行”。既然盛行,当然就有 “三国气”、“水浒气”,代有传人而子孙徒众。不过可惜的是鲁迅就此打住话头。究竟什么是“三国气”,什么是“水浒气”也没有明确道出来。把话挑明,“三国气”其实就是权术气、厚黑气;“水浒气”其实就是流氓气、痞子气。它们代表了国民性中阴暗而伪劣的部分,代表了人性中万劫不复的深渊。《双典批判》将水浒和三国这方面的问题摊在至善和人道主义的阳光下来讨论,从小说的故事及其叙述中发现问题,将鲁迅当年的问题意识,推进到更加深入的地步。笔者觉得,刘再复提出“双典”存在的暴力、权术和对女性态度这三大问题,实在值得好好检讨。
三国和水浒的成书并非像通行本署名的那样,是由罗贯中、施耐庵写出来的,这已经是学术圈的共识。这两部作品是由很多至今都不知名的说书者创始了众多不同的流行话本或故事底本,再行由文人汇集、增删、整理、润色、编定而成的。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两部古典小说集合了来自不同甚至矛盾的文化价值观,但是他们最基本的层面、最大量的叙事,确实是传达出文化“伪形”的信息。刘再复将它概括为对暴力的崇拜、对权谋术数的崇拜和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这并未冤枉“双典”。水浒讲述的是各式不同的江湖好汉揭竿造反的故事,而三国叙述的则是汉末群雄争霸的故事。我们都会认同,故事的题材并不能决定故事讲述所隐含的价值观的选择,所以“双典”的文化“伪形”,崇拜暴力和权术,并不是因为故事的讲述选择了这样的题材,完全是因为作者的叙事伦理,即由于作者在故事的讲述中所体现出来的伦理观念,它们认同或加强了故事角色那种违背至善之道的卑劣行为;或者至少是叙述者是带着亵玩的态度品赏故事角色的残忍而伪善的行为。文学所以潜移默化影响读者,它往往不是像宣传那样由外面灌输,而是通过看似与故事本身天衣无缝结合在一起的叙述者传达的叙事伦理,令读者不期然地影照于眼前,默识于心。古人所谓词曲小说,移人心性,说的就是这回事。所以,“双典”的崇拜暴力和权术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作者所持的叙事伦理,违背了文明的原则,违背了人道精神。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麦克白》,所讲述的是逆臣篡权弑君的故事。麦克白杀害无辜老王的行为不亚于梁山的好汉,而麦克白的阴险、权谋亦不让于三国群雄。如果单以题材而论,《麦克白》的故事更加牵涉血腥、阴险和卑鄙,但是莎士比亚面对宫廷阴谋的题材,却写出谴责暴力和卑鄙权谋的不朽悲剧。如果以这一点与水浒和三国比较,两者的根本差异就在于作者所持的叙述伦理的不同,不惟不同,简直有霄壤之别;两者的思想境界、人生境界、美学趣味,其差别有如天上人间。文学,如《麦克白》可以称作伟大和不朽,而如水浒和三国则只能叫作流行和平庸。为了说明问题,不妨略加引用。第二幕麦克白刺杀了睡梦中的国王后,听到了敲门声,莎士比亚让这位权欲熏心的逆臣来了一段道白:
那打门的声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点点的声音都会吓得我心惊肉跳?这是什么手!嘿!它们要挖出我的眼睛。大洋里所有的水,能够洗净我手上的血迹吗?不,恐怕我这一手的血,倒要把一碧无垠的海水染成一片殷红呢。
欲望、贪婪通向了可怕的罪行,而可怕的罪行通向了无休止的恐惧和心理紊乱,这恐惧本身就成了对罪行铁板钉钉的确认。这段麦克白的独白,既是角色的心理活动的表白,也是叙述者无言的谴责和批判。莎士比亚的类似笔法再见于第五幕麦克白夫人自杀的消息传来,麦克白预感来日无多而作的一段诗一样美的念白:
明天,明天,又一个明天,
一天一天地蹑步前行,
直到最后的一秒钟。
我们所有的昨天,
不过替傻子照亮了通向死亡的路。
要熄灭了,要熄灭了,短促的烛光!
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
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戏子,
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悄然退下。
它是一个蠢人讲的故事,
充满了喧哗和骚动,却全无意义。
这既是麦克白由贪婪而引发的弑君篡位的邪恶行径即将落幕收场时的悲鸣,又是对贪欲的哲学的反思,更是对罪行的审判。莎士比亚就是这样,讲述出来的事件本身和叙述者对它的态度是有清楚区别的,读者能够感受到莎氏对罪行的谴责和批判,道义的审判始终凌驾了题材本身。作为事件的故事虽然是阴暗的,但却有一道人性和哲思的光芒照亮了这阴暗的地狱。叙述不是对弑君篡权的血腥阴谋的默认、玩赏和无评价的呈现,而是伴随着最严厉的谴责、最富智慧的嘲弄和最富有道义感的审判,而这谴责、嘲弄、审判恰恰就是融化在对人物及其行为的叙述之中的。
以此返观“双典”的故事讲述,则境界的高下立见。让我们举水浒所写武松的例子。武松杀嫂获罪流放到孟州,以义气相感,效劳于营管儿子施恩,为报蒋门神侵夺家财而最后演出血溅鸳鸯楼的故事。这个报仇雪恨的事儿看起来颇有大义凛然的味道,但看过恩仇的来龙去脉之后,却觉得施恩也是一个巧取豪夺之徒,他与蒋门神以及背后的张团练、张都监其实都是一丘之貉。施恩一家的发迹勾画出一幅活生生的图景,讲出中国社会中靠着政治权力的庇护和暴力的威吓从事垄断经营而大发其财的秘密。武松效力于这样的社会恶势力,而醉打蒋门神,人虽勇而天良泯灭。作者却将此事当成善恶之争,期望写出武松义薄云天的英雄气概,何其善恶不分,良知泯灭而至于此!可以说武松的这种“义气”全无价值,简直就是流氓气,若剔除了叙述者美化之词,武松此举充其量便是一个街头流氓的所为,一个地头恶霸的打手。事件的叙述虽然生动,但笔者深为作者的才华惋惜,因为作者欠缺至善的人生价值和慈悲怜悯之心,使得绝世的语言表现能力只能写出一场街头闹剧。及至血溅鸳鸯楼,武松的行为更是令人发指。一刀一个杀死的共十五个人之中,只有蒋门神等三人与事件有关,其余都是无辜。对于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杀戮,叙述者让武松杀戮之余,留下自以为精彩神勇的一笔:“便去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蘸着血,去白粉壁上,大写下八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这里写的固然是角色的行为,表现了角色的无所畏惧,但作者的落笔也不可能是单纯的角色行为,这角色行为本身便传达出叙述者对此种行为的肯定和赞美。因为叙述者在这里要表现的主要不是杀人行为的本身,除了手起刀落,也无太多细节。作者主要表现的是杀人杀得大义凛然,杀人杀得理直气壮,杀人杀得神勇无惧。这角色的大义凛然、理直气壮和神勇无惧本身,便包含了作者的残忍、嗜血和善恶不分。刘再复在《双典批判》中说:
中国的评论者和读者,只求满足自己的心理快意,忘了用“生命”的尺度即人性的尺度去衡量英雄的行为。当然,与其说忘了,不如说是根本没有意识到,因为一种“嗜杀”的变态文化心理已经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鲁迅一再批评中国人喜欢看同胞们杀头,骨子里是血腥式的自私与冷漠,可惜没有觉悟到。武松至今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他那些杀小丫环、小女儿和底层社会的马夫等血淋淋的举动,是可以忽略不记的。
三国故事叙述所表现的伦理观念,表面上看与水浒大有区别,好像水浒犯在善恶颠倒或善恶的界线不分,而一部三国忠奸邪正则自始至终念念不忘。但是掀开这层表象的区别,实质还是很接近的,“双典”都病在叙述者价值观的庸俗与浅薄。与水浒的善恶颠倒不同,三国的叙事伦理出在它的教科书心态,犹如自恃自家的宝贝,生怕世人不知,一件一件拿出来炫耀摆谱,玩赏小智权诈。作者犹如一位教匠,启蒙教众。当然我们也要承认,作者是出众的教匠。教什么呢?自然是权谋厚黑一类。《双典批判》说中了它的要害:“《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的大全,机谋、权谋、阴谋的集大成者,是指它展示了中国权术的各种形态。全书所呈现的政治、军事、外交、人际等领域,全都突显一个‘诡’字,所有的术术全是诡术。”它的忠奸邪正,以刘蜀为忠正,以曹魏为奸邪,这道统观是外加上去的。无论忠奸,都奉权诈为宗,无论邪正,都是奸狡的豪雄。其中所写的种种得意权谋,多数不见于正史,如桃园结义、貂婵美人计、诸葛亮三气周瑜、孔明借箭、蒋干盗书、周瑜打黄盖、刘备掷子、司马懿诈病赚曹爽等,史书上并无一言道及。有的是根据正史一言半语或野史杂陈无根之谈添油加醋而成,如三顾草庐、曹刘煮酒论英雄和刘备种菜园子等。当然笔者指出这些,并不是认为史书所无,演义就不许虚构和添加,而是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借着中国官场或人生的一般经验从中提炼而加诸三国人物的身上。而作者所注重添加的成分,恰恰是权诈阴谋一类。作者要把现实人生中种种权谋机变之道作一个集中的展示,以为后学效法之用。三国作者的这个用心,我们不能说它险恶,但至少是平庸,缺乏崇高的人生境界,缺乏人文的关怀;就历史观念而言,也是浅薄的,远不如《三国志》或《晋史》。
刘再复的 《双典批判》还向我们提出一个“双典”阅读史的问题。三国和水浒以接近于现今的版本流传,也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而在这漫长的阅读流传史上,暴力崇拜和权术崇拜的阅读,始终是占据了主流的位置。这固然是“双典”的文化“伪形”和它自身的文化价值观的问题,但是明清之际的评点家的推波助澜也是要负上很大的责任,这同样是一笔阅读史上的宿债。正是他们当年漫无节制和不负责任的褒扬,形成了此后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前理解”。而缺乏批判眼光的读者,自觉不自觉便先入为主,接受他们的观点。看一看至今都流传不息的对武松和李逵的褒扬,看一看坊间层出不穷的 “水煮三国”、“三国的商战理念”、“三国官场之道”之类的书,就可以知道明清之际的评点家大有传人。在水浒评点中,容与堂本署名李卓吾评本和贯华堂金圣叹评本影响最大,而流毒也最广。刘再复的指出十分中肯:
李卓吾的水浒评点,其致命的错误是对暴力的化身李逵的崇拜。他之后,金圣叹延续这种崇拜,但他的第一崇拜对象是武松,并献给他一个“天人”的最高桂冠。而李卓吾的第一崇拜对象是李逵,他献给李逵的最高桂冠是“活佛”。
“天人”和“活佛”两顶帽子戴在武松和李逵身上,可谓荒唐之极。这两人是水浒着墨最多而最为暴力的两人,作者对暴力的偏好很大程度上是借着他们的故事传递出来的。明清评点着力鼓吹两人无道放纵的杀戮,可谓失教丧心,任性张狂,一如晚明揽妓纵酒的狂禅,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病态。值得指出的是,其实金圣叹是看出水浒故事的杀戮性的,例如贯华堂本他写的《序二》,说到水浒一百单八人:“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不过,水浒一干人,除宋江之外,他采取的是抽象否定,具体肯定的评点策略。他的上述认识并没有体现在具体的文本评点之中。或许是那个时代他也有隐衷,对情之所钟也不得不用虚以委蛇的手法遮掩一下,也未可知。但是他所遮掩的恰恰是丝毫不用遮掩的,而他肯定的恰恰是最不值得肯定的。他具体肯定最多的两个人,恰恰就是水浒的两架杀戮机器——武松和李逵。金圣叹此评为后世评家,开了恶例。这笔评点家不负责任的遗产,也是要好好清理的。
八十年代在北京的时候,笔者知晓刘再复有一个学术研究的兴趣点,他要写一部自晚明西学东渐以来的中国人自我反省和自我认识的精神史。毫无疑问,他的这一学术兴趣与五四新思潮的“重估一切价值”和批判国民性有内在的关联。五四新思潮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也自有它深刻的地方,然而不能说已经尽善尽美,尤其是思考自己民族文化传统中那些带有负面价值的东西,批判而扬弃之,更是一个长期的课题。五四新思潮是过去了,但是它开创的民族自我反省的思想课题却是未竟之业。刘再复的《双典批判》是他对五四新思潮反思国民性的未竟之业多年系怀于心的交代,也是他去国之后于颠沛流离之中矢志不渝追求自己学术理想的创获。他新著完成,嘱我写序文。我读后有所感,于是便借题发挥,序不敢言,仅附于骥尾,与读者分享阅读《双典批判》的所得。
林岗,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刘再复:《双典批判》,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