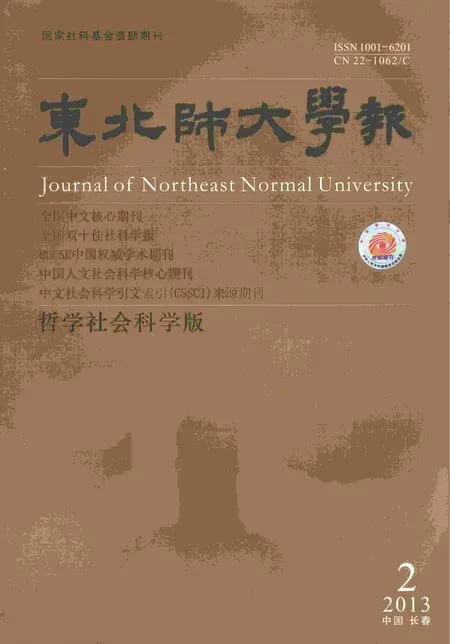论历史叙事对文学叙事的影响机理
2013-03-22高萍
高 萍
(西安文理学院 文学院,陕西 西安710065)
叙事是人类所独有的根植于自身本性的一种要求和能力,它“首先不是一种主要包括长篇和短篇小说的文类概念,而是一种人类在时间中认识世界、社会和个人的基本方式”[1]325。叙事最初作为一种能力,不仅发生于文学之中,而且存在于历史等多种学科之中。与西方叙事文学由“epic(史诗)-romance(罗曼司)-novel(小说)”发展轨迹不同,中国叙事以历史文本为源,文学叙事从一开始就在历史的荫庇下生长,历史文本为文学叙事提供了文类特征和叙事模式,成为后起叙事性作品唯一可资仿效的榜样。中国叙事传统可以勾勒出与西方相对应的一条道路:神话—史传—小说。历史叙事何以影响文学叙事?笔者认为主要由于中国神话的特质、历史叙事范型的形成、历史叙事中虚构语境的营造以及“史贵于文”的观念的影响。
一、中国神话的特性及其发展流向
神话是一切意识形态的始祖,中西方叙事传统都可追溯到神话传说。但是中国神话只在《山海经》、《楚辞》、《淮南子》、《尚书》、《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古籍中零散、非系统地记录下来,它们保留的仅仅是神话内容,神话的文体原貌、文体形式无法考知。浦安迪先生曾用原型批评理论比较中西神话,认为西方神话注重保留具体细节,而中国神话更注重保留传说的骨架和神韵,西方神话是“叙述性+时间化”,中国神话则是“非叙述性+空间化”[2]40-48。与希腊神话相比较,中国神话具有“头、身、尾”连贯结构原型的完整的故事寥寥无几,缺少对任何神话人物事迹的完整叙述。著名的神话如黄帝与蚩尤之战,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羿射十日、精卫填海、鲧禹治水等等,大多只有形象的简单描画和事迹的简略说明,叙事性相当薄弱。神话虽与叙事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由于中国神话非叙述性特质及其保存的非系统性,使得它对叙事文类的影响在于题材和精神上,而不在叙事文体上。
中国神话的发展流向与西方也大相径庭。欧洲进入奴隶社会后,其文化即以宗教为中心,神权统治一直维持到中世纪末,这为神话的成系统性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使得希腊神话直接演化为史诗,演化为希腊古典时期的悲剧和喜剧。在公元前六世纪则演变出相当成熟的叙事文学,而中国在春秋末战国初,宗教气氛开始淡化,理性精神得到充分的阐发和弘扬。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占据了中国文化的中心位置,“子不语怪力乱神”,一方面高扬了人文主义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又把神话引向了历史化的道路。神话历史化,是以公元前四世纪希腊无神论哲学家尤赫墨洛斯命名的一种神话学说,希腊人曾明确地提出过这个观点,但学术观点归学术观点,研究对象归研究对象,神话的庞大体系和尤赫墨洛斯的神话学说相安无事地并存着。而在中国,虽未明确提出这种学说,但是实际上对神话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神变成了人,变成了帝王,神话中种种不可思议的幻想性内容,都获得了符合逻辑和常识,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新的阐释。“子贡问于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太平御览》卷七十九)神话中的黄帝有四张面孔,被孔子解释为黄帝派遣四个人去治理四方。不合理的事被合理化了,神话也就变成了历史。
中国神话在理性张扬下被解释为合乎逻辑的事实,并向历史学方向演变。神话历史化进程的直接后果是神话被历史意识所掩埋,无数远古神话短小故事没有象欧洲那样汇聚成完整的神话体系,而是变成了史传巨大建筑中的砖石瓦片。神话历史化一方面使叙事能力向历史领域转移,另一方面形成了“史贵于文”的价值观念。前者使历史文本成为中国叙事文类的泱泱大国,为历史叙事成为中国叙事范式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而后者使历史文本在叙事文类中占据绝对权威性,并为其向小说、戏剧等叙事文类施加影响提供了现实性。
二、历史叙事范型的形成
在神话历史化的作用下,中国古代叙事向历史领域发展,在历史文本的编纂中叙事能力不断提高,叙事文的文类特征、形式技巧及叙事谋略开始在史传中形成。宋代真德秀云:“叙事起于史官”,章学诚认为“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无论从史官的职能上还是史的语义上看,历史和叙事都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史官最原始的职能是“巫”,其职业特点便是“接神见鬼”,充当勾通人鬼的角色。殷商之后,巫史分流,到周代史官的职责划分更为细致。徐复观先生对春秋时“史”的任务做了全面的考察,认为主要有:祭神时向神祷告、主管筮的事务、主管天文星历、灾异解说、锡命或策命、掌管氏族谱系等六种职能[3]137-139。无论史官职能何等宽泛,都与叙事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语义看,《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并把“史”和“事”字放在一起,“事,职也,从史”。王贵民先生通过对勘殷墟卜辞也认为“甲骨文中的史字大部分是‘事’字的意义”[4]339,在篆体字以前的文字结构上,这两个字是存在着渊源关系的。在古汉语中,“叙”与“序”相通。《说文·攴部》云“叙,次弟也”。《周礼·天官·小宰》有“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郑玄注曰:“叙,秩次也,谓先尊后卑也。”“叙”为次序,次第,“叙”与“序”相通,指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安排。叙,又通“诸”,《尔雅·释诂上》云:“叙,绪也”。《说文》云:“诸,丝耑也,盖有耑绪可以次序,故叙又训绪也”。叙作陈述之意出现较晚,《国语·晋语三》有“纪言以叙之,述意以导之”,韦昭注曰:“叙,述也。”从语义学角度看,叙与序、绪相通,即用语言来表达事件的始末,包含时间、空间、事件等要素。
中国史籍产生极早,早在殷代卜辞与周代彝铭中就把握住叙事的要则,根据刘节先生《中国史学史稿》论证“历史的事件,不外于三个要素:就是时、地、人,三者的关系。殷墟卜辞所记简单确实,把三个要素包含在里面。”[5]16。发展到《春秋》则为中国叙事开创了编年记事的规范,“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使叙事走向有序化。同时《春秋》在叙事方法上“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在书法体例上渗透着主观性与目的性的春秋笔法成为弥漫在叙事领域内的集体无意识。发展到《左传》,第一次将叙事作品所应具备的基本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用书面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中国叙事文类特征渐已具备。《左传》突破了前代历史叙事的言事分离,达到了言事兼宜,文史交融,在编年的叙述框架中夹杂倒叙、补叙、插叙,丰富了叙事时间,同时以事实为骨架踵事增华,使叙事更具波澜,开始了由“历史”到“文学”的变化。《史记》则标志着中国历史叙事的高峰,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分立而又纵横交错,为漫长而杂乱的古史建立了一套严密而有效的叙事体系,尤其是“以人系事”的纪传体开创了新的叙事模式,使创作主体具备了以人物形象为中心的叙事意识。
中国人的叙事思维和叙事能力在修史中逐渐成熟,从最初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单纯载录发展到融铸史事、构筑史述体系,并形成了以编年体、纪传体为主的结构模式;以顺叙为主并杂有插叙、补叙的时间模式;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为主杂有限知视角的视角模式。这种叙事范型的形成为文学叙事提供了博大而深厚的温床。
三、历史叙事中虚构语境的营造
历史和文学本属于不同学科范畴,二者之间存在真与假、实与虚的差异,但二者都使用讲故事的叙事体,阐明事件的开始如何导致不同的结局,分享着共同的叙事法则。历史叙事不仅在文类特征上为文学叙事提供范型,而且在叙事谋略、技巧上亦与文学相通。虚构是文学叙事区别于历史叙事的最本质特征,然而历史叙事从来都是史家“以心观物”的结果,史家在实录的基础上追求叙事的价值判断与叙事技巧,渗透着主观因素。扬雄《法言·君子篇》云:“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史家在对“义”和“奇”的追求中,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构语境的营造使中国史书具有了浓郁的文学色彩,也为其影响文学叙事提供了可能性。
中国史学家往往在历史叙事中蕴含着价值倾向,表现出对“义”的追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出于伦理和政教本位的自觉,古代史家将“义”作为叙事之首,价值判断成为贯穿“事”与“文”的核心。西方学者浦安迪也指出“中国叙事传统的历史分支和虚构分支都是真实的——或是实事意义上的真实,或是人情意义上的真实。”[2]32中国历史叙事普遍带有主观色彩。孔子修《春秋》蕴含着“使乱臣贼子惧”、“拨乱反正”、“寓褒贬,别善恶”的价值追求。班固称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实录,但司马迁修《史记》“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其中蕴含着“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教化意图。历史叙事的政教功能与资治功用被后来的文学叙事所肯定,文学叙事“羽翼信史而不违”,正是分享着历史叙事的价值倾向和教化功用。
史家之爱奇则从叙事空间、叙事方法上沟通了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界限。海登·怀特充分肯定了文史因缘,认为“历史——随着时间而进展的真正世界是按照诗人或小说家所描写的那样使人理解”[6]178,历史叙事通过虚构语境的营造弥补了缺失的链条,把看起来似乎是独立没有关联的事件变成了具有因果关系的、可以理解和令人熟悉的模式。
历史叙事中的虚构有两个层面。第一层呈露于外,即记写鬼神灾异。在早期历史文本中多记载卜筮、灾祥、鬼怪、报应、梦兆等。《左传》记述卜筮达十九起,日常卜问不计其数,记写梦兆达二十六条,以致后人评价“左丘明即千秋谎祖也”(《绿野仙踪》序)。《史记》叙事亦是爱奇反经,后人讥评“专搜奥僻,诩为神奇”(《少室山房笔丛》)。这种虚构语境的营造源自史官之职能,史出于巫,直到春秋时代,史官依然身兼天神、灾祥、卜筮之职事。从记神事之巫向记人事之史的转化中间必然出现一个巫史不分、神人混杂的过渡阶段,从而形成了历史叙事“闻异则书”的传统。于史而言,未能客观真实;于文而言,为史传增添了浓郁的文学色彩。
在先秦理性精神的影响下,神话历史化也为历史叙事的虚构提供了方法和空间。史官将神话中的不合理成分予以理性化,将其以半历史化或准历史化的形式载录在史籍中。司马迁在写《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时,由于史料的缺少,大量采用神话传说,但去除“其文不雅驯”者,把诡秘荒诞的神话传说改造为构筑远古历史的基石。董乃斌指出神话历史化使艺术想象力向历史写作活动中渗透,形成了中国历史叙事“文史不分”的现象,历史叙事是文学叙事的真正渊薮。[7]90。
历史叙事中虚构的第二层面则隐含其中,即以再造想象弥补历史资料的缺略与断层。历史概念具有两重性:一是指人类过往存在的史实,一是指史家根据资料所记载下来的历史,两者之间试图无限接近但永远难以重合。史家在记写时往往存在资料的空白与缺略。适当的想象成为历史重构的重要手段。克罗齐认为“没有这种想象性重建或综合是无法写历史或读历史的”[8]24,合理性想象弥补了历史的空隙,赋予历史叙事以连续性,同时也使历史叙事具有了文学性。钱钟书概括了中国历史叙事中想象的营造方法,“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9]166史家再造的方式是以理揆真,踵事增华,虽不一定就是历史原貌,但达到了再现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再现历史事件的生动气氛。史书中的心理描写、语言描写、细节描写皆是史家虚构想象的结果。虚构语境的营造沟通了与文学叙事的隔阂,使二者不尽同而可相通。史家的悬想事势、臆造人物、拟言代言为文学虚构提供了方法借鉴,闻异则书、接踵神话则在虚构空间上给文学叙事以启迪。
四、“史贵于文”价值观念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历史和以记事为职业的史官。这种极端重史的集体潜意识,推动了神话历史化运动的进程。神话历史化的成功,可以说是“史贵于文”价值观的胜利,以文字载录的史册开始具有了上帝式的伟大法典的权威性。
“史贵于文”价值观的确立,增强了后世一切叙事性文体自觉向史传看齐的向心力量。在后代小说中,处处可以看到史传的影响。东晋干宝在《搜神记》序中自称撰写《搜神记》系“考先志于载籍”,“访行事于故老”,“足以明神道之不诬”,并得到“鬼之董狐”的称号。唐传奇大多以“记”、“传”题名,直接仿效《史记》开创的纪传体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说:“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唐人李肇说:“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之才也。”明清小说家亦是如此。明清小说内容大多写历史题材,历史人物,形式上不仅以编年体、纪传体方式结构全篇,而且大多采用历史叙事的全知视角、客观叙述,甚至在情节的写法上都摹拟历史叙事。如《三国演义》的作者非常喜欢通过对剑拔弩张、惊心动魄的酒宴的描写来突出人物性格、推动情节的发展,与司马迁笔下的“鸿门宴”非常相似。从六朝志怪、志人小说到唐传奇,再到明清小说,几乎所有的小说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历史叙事的艺术滋养。历史叙事这种绝对的权威性使其成为整个中国叙事文类的范式,文学叙事以此模式创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特点[10]。
“史贵于文”价值观的确立导致了中国小说批评家“拟史批评”的产生,推动小说家进一步向史靠拢。批评家在评点小说时,总以历史叙事作为参照,动辄便以“班马史法”相称。金圣叹处处以《史记》作为标的和对照,“《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毛宗岗在评论《三国志演义》:“《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戚蓼生评《红楼梦》“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由于拟史批评,使得古代小说叙事对史家实录规范和历史叙事更加肯定,“羽翼信史而不违”,成为正史之补,以提高小说的地位。
综之,中国神话的非系统性及神话历史化现象使得叙事能力向史学领域渗透。历史文本成为中国叙事文类唯一可资仿效的范本,历史叙事的形式技巧及叙事谋略成为文学叙事的骨干。正如学者所言:“史著散文为小说的发生、发展发射了信息,输送了基本因子。具有某种惯性力的恒稳意识和传达手段一旦晶化就必然在小说中富有韧力地表现出来”[11]。
[1]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3[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王贵民.说邗史[A]胡厚宣.甲骨探史录[C].北京:三联书店,1982.
[5]刘节.中国史学史稿[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6]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7]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8]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9]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邹志远.韩少功与鲁迅小说叙事功能之比较[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42.
[11]吴功正.传记散文和古典小说的审美关系[J].学习与探索,1986(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