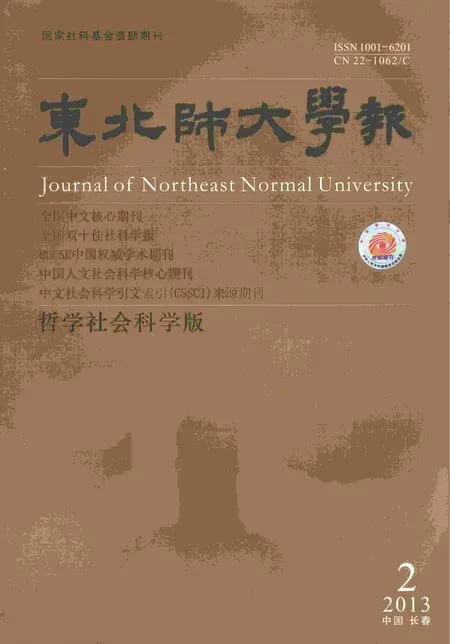论《钢琴课》中的性别政治
2013-03-22朱海峰申富英
朱海峰,申富英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随着20世纪90年代现代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兴起,一些西方评论家认为黑人剧作家威尔逊(August Wilson)在《钢琴课》中表现了“女权主义对父权文化的解构”[1]146。然而,另外一些批评家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威尔逊在该剧中暗示了黑人女权主义运动使非裔文化沦为残缺的“劣等文化”[2]。实际上,威尔逊不仅批判了黑人的父权文化,也批判了黑人的女权主义思想,更进一步揭示出黑人群体要想走出种族的困境,就须抛弃这种非此即彼(either/or)的父权/女权的二元思维,接受黑人男女存在差异和平等的观念,走后女权主义倡导的男女两性多元共生、和谐平衡(both/and)的道路。
一、对黑人父权文化的批判
西方的传统文化价值是以维护父权文化为目的的,它认为男性代表着理智、文明、权威、主动等,而女性则代表着直觉、自然、沉默、被动等,因此,得出“男性是优于女性的第一性,女性是劣于男性的第二性”的结论[3]。作为一名非裔男性剧作家,威尔逊也不可避免地被多数批评家贴以“父权文化宣传者”的标签,对他的研究也大多集中在对《钢琴课》中的父权文化的构建或女性“他者化”的视角上。实际上,威尔逊在《钢琴课》中暴露了黑人男性嗜偷成癖、实施暴力复仇、玩弄黑人女性等人格缺陷,批判了他们的人格缺陷对种族发展的危害。
在《钢琴课》中,威尔逊批判了美国黑人男性嗜偷成癖的恶习。威尔逊不赞同黑人采用偷窃的方式报复白人,并使他们遭到了应有的惩罚:白人放火烧了偷盗者乘坐的火车,把他们活活烧死在车上,使他们成了“黄狗列车”上的鬼魂。而这些黑人男性后代不但没有从父辈的悲惨遭遇中吸取教训,反而继承了这种偷窃劣行,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黑人男性嗜偷成癖的恶习给黑人种族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破坏了黑人男女两性的团结并遭到白人主流社会的排斥。以伯尼斯为代表的黑人女性谴责黑人男性,认为他们嗜偷成癖的劣行造成了母女两人“独守寒夜和空床”的凄惨命运,从而造成了黑人男性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孤立处境。同时,黑人男性的偷窃劣行不仅引发了与白人的冲突,而且遭到了法律制裁而锒铛入狱,从而导致了白人主流文化对黑人群体的排斥。如果说黑人要在这两代人的悲剧中指责什么人的话,那么黑人男性首先应该毫不留情地指责自己。
《钢琴课》中的黑人男性具有暴力倾向,他们不停地寻找释放这些暴力冲动的途径,从而发泄对白人奴隶主的仇恨。威利在杀死一只猫后领悟到了死亡的权利:杀死白人的权利。他认为这种死亡权利是黑人被剥脱了其他一切权利后所剩下的唯一权利,它不但能使黑人成为白人畏惧的对手,也能使“一个不怕死的黑人吓坏白人”[4]104,甚至“黑人心脏跳动”的声音都足以令白人毛骨悚然。威利还为黑人的暴力复仇找到了权威解释,认为《圣经》支持受害者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的方式报复仇人[4]105。这种暴力复仇手段不仅被活着的黑人男性采用,而且也被黑人的鬼魂用作攻击白人的惯用武器。黑人男性对白人的复仇行为不但没有得到女性同胞的支持,反而遭到了黑人女性同胞的反对。伯尼斯认识到以暴抗暴的手段使双方落得“被烧死”、“被枪杀”、“被淹死”的结果,最终使整个社会处在一个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中。同样,美国白人对黑人男性的复仇行动进行了惩罚和报复:烧死了查尔斯、枪杀了克罗雷、判处威利和莱曼入狱。同时,白人还对黑人男性的形象进行了“他者化”,认为黑人男性天性懒散、喜好暴力、教育匮乏。黑人男性所从事的工种不仅注定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而且注定他们要遭受经济贫困、政治歧视、文化排斥之苦,从而使他们形成了“社会负我,你奈我何”的逻辑,并采用暴力手段发泄对美国社会的不满,最终将他们的种族事业抛入了失望的深渊。
如果说黑人男性采用暴力手段抵抗白人“入侵者”的目的在于保护自己和黑人女性的话,那么长期以来他们对黑人女性的勾引和玩弄却不可原谅。在《钢琴课》中,黑人男性津津乐道地议论着勾引女性的话题。威尼、莱曼、威利、多克都以此为能事,暴露了黑人男性人性恶的一面。威尼最初从女性身上获得了肉体快乐,但后来逐渐意识到肉体快乐欺骗了他的心灵,认定女性是他精神沉沦的替罪羊,并疯狂地喊出了“杀死女人”的口号。莱曼终日沉浸于玩弄女人的幻想中,把种族的危难抛在脑后,只顾肉体享乐,当了种族解放战斗中的“逃兵”。威利因祖母的悲惨经历和贫困而感到在白人面前失去了正常的人格和尊严,沦为被白人阉割了的、软弱无能的施暴者。因此,他试图通过玩弄女性来“弥补在白人世界里缺失的权威,并妄图以此重塑男性强者身份。”[1]126如果说白人的种族歧视的确是造成黑人被压迫的直接原因,但黑人却没有认识到他们的人格缺陷也罪责难逃。他们只顾把自身的不幸归咎于白人的种族歧视,却没有对自己的人格缺陷进行反省,这种以叶障目、自欺欺人的做法无益于他们的种族解放事业,只能最终使种族的解放事业沦为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
二、对黑人女权主义的批判
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是黑人民权运动和黑人妇女争取权利斗争的产物,它反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异性暴力和阶级压迫,倡议颠覆传统的二元性别观,构建一种新的性别价值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不是“男性在上层,女性在底层,而是女性在上层,男性在底层”[5]。黑人女权主义者既反对黑人的父权文化,也反对白人的主流文化,试图通过建立一个由女性为首的姊妹王国带领黑人探索种族解放的出路,这对当时的黑人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作为同时代的剧作家,威尔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黑人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甚至被女权批评家贝尔·胡克(bell hooks)拉入了女权主义阵营。对此,在一次访谈中,威尔逊明确表明自己的创作受到了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但坚决“反对被冠以女权主义者之名”[6],认为黑人女性还不足以担当实现救赎种族的重任。威尔逊之所以认识到黑人女权主义者宣传的种族救赎的虚幻本质,主要是因为他洞悉到黑人女性深受传统文化对其划分的“圣母玛利亚和耶洗别二分法(Madonna/Jezebel Dichotomy)的束缚”[1]133。根据这种二分法,黑人女性要么被划为“圣母玛利亚”一类,担当哺育子女的任务,要么被划为“耶洗别”一类,沦为出卖肉体的妓女。“圣母玛利亚”型的黑人妇女被白人文化和黑人的父权文化禁锢在家庭和生殖领域,以持家和教子为己任,而把种族解放事业的重任交给男性同胞,甘做种族解放事业的“麻木的局外人”;“耶洗别”型的黑人女性则偷吃了白人文化和黑人父权文化的“禁果”,以肉体享乐为目标并给黑人男性下了毒药,沦为种族解放事业的“快乐的背叛者”,两者都成了黑人种族解放事业发展的障碍。
在《钢琴课》中,伯尼斯与其母及祖母缺乏独立的个性和反抗精神,遵从白人和黑人男性定义的习俗,主动戴上枷锁,甘愿沦为“圣母玛利亚”。顺从、被动、懦弱的性格使她们不能走上解放自我的道路,更不能承担救赎种族及复兴种族的重任。伯尼斯缺乏面对痛苦经历的勇气,一直不碰钢琴,无奈地选择逃避过去。伯尼斯的母亲薇拉是一位丧夫的“哀悼者”,用余生守护这架要了她丈夫性命的钢琴,她不能走出丧夫的阴影,整日生活在极端痛苦之中。伯尼斯的曾祖母以善良、能干、忠诚的品格赢得了白人奴隶主的喜欢,但由于她长期被白人灌以忠诚主人、逆来顺受的思想,未能摆脱被奴隶主物化的命运,最终沦为交换钢琴的商品。剧中的三代黑人女性都生活在丧夫的阴影下,失去了理性的判断力,不但没有认识到她们悲剧的根源在于白人的种族歧视政策,反而指责黑人男性是其悲剧的始作俑者,并拒绝加入以男性为主导的种族解放运动。
剧中的黑人女性除了担当男性霸权下的“圣母玛利亚”角色外,她们还沦为“耶洗别”,充当遭白人文化阉割的黑人男性重塑霸权身份的发泄工具。作为威利和莱曼都渴望勾引的对象,格蕾丝被塑造为与多人发生性关系的“荡妇”。作为一名“耶洗别”,格蕾丝只关注肉体享乐,不关注黑人种族解放事业。在驱鬼仪式中,她看不到萨特的鬼魂,这象征着她看不到种族面临的危险;她勾走了莱曼,这显示出她毒害了男性同胞的反抗意识。除了格蕾丝外,还有多名黑人女性也沦为“耶洗别”,她们或者为争男人打得头破血流,或者“穿上衣服,在火车站排成一行”[4]24,渴望成为过往男人的消费对象,这无疑助长了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在《钢琴课》中,威尔逊洞悉到当时黑人女性沦为“耶洗别”绝不是个别现象,并通过塑造这一类形象揭示她们对黑人种族发展的危害。
三、威尔逊的后女权主义倾向
后女权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它解构了父权制的宏大叙述,反对男性的菲逻各中心主义,同时也动摇了女权主义的固有起点,谴责她们过分夸大妇女受父权的统治和压迫的普遍论观点,并举出“打倒女权主义”的标语。后女权主义者否认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本质论思想,强调“一致性和同质性让位于差异性和异质性”[7],认为这些差异不仅是个体存在的意义,而且是实现男女多元共生、和谐平衡的基础。
威尔逊在《钢琴课》中对黑人性别政治的见解与后女权主义有诸多暗合之处。威尔逊不满足于仅仅批判黑人的父权文化和女权主义思想,还揭示出单独的任何一性(男性/女性)都不能实现黑人的种族解放事业,只有男女两性消解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本质论思想,在承认差异和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多元共生、和谐平衡的两性关系,才能跨越种族内部的性别冲突,从而彻底实现种族解放的理想。
后女权主义认为,只有存在差异的男女两性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完整的人,而任一性的缺场都会打破这个整体,最终将导致男女两性陷入极端痛苦的深渊[8]。在《钢琴课》中,威尔逊认同“男人离不离开女人,女人也离不开男人”的观念,并一开场说出了“家里虽有女人的痕迹,(但因缺失男人),显得没有温暖和活力。”[4]1黑人男女两性的结合能带来和谐,而婚姻的破裂则能带来精神上的痛苦。威尼得知妻子去世的消息,遭到巨大打击,无法承受现实的痛苦,开始在精神世界里与“黄狗列车”上的鬼魂交谈,并呼喊妻子的鬼魂现身。威尼的哥哥多克遭妻子柯琳抛弃后,深感男性的尊严遭到了阉割,丧失了抵抗白人文化的男性特征,进而在传统女性承担的洗衣、做饭、打扫房间等家务中寻求安慰。威尼和多克都是两性关系失衡的受害者,他们不但无法走出创伤的阴影,还整日生活在极端痛苦之中,这注定他们无力投身于种族的解放事业。
后女权主义认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建构的;男女两性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并提倡男女两性用“对话、互补和共识取代矛盾、冲突和对抗”[9],从而构建一种新型的男女平等、尊重、幸福和团结的两性关系。在《钢琴课》中,威尔逊表达了同后女权主义相暗合的思想,认为黑人女性想要实现种族解放,首先应该获得性别解放,使男性摆脱暴力、自私、规训等特征;而男性要想实现种族的解放,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女性的性别解放和她们争取种族解放的主动性和坚定性。作为父权文化的代言人,剧中的威利拥有传统男性的暴力、残忍、主动、刚强等气质,主张用残忍的暴力手段抵抗白人主流文化。而伯尼斯则具有女性仁慈、包容、被动、懦弱等气质,害怕碰钢琴,更不向女儿讲述钢琴的历史,成为白人权威下缄默的“臣属”,丧失了反抗种族压迫的意识。伯尼斯姐弟因气质差异而产生矛盾斗争:伯尼斯认为威利是个只顾复仇的“暴君”,而威利认为伯尼斯是个忘记复仇的“白痴”。在剧尾,威利未能用暴力手段驱走白人奴隶主萨特的鬼魂。此时,伯尼斯汲取了男性的刚强、主动、勇敢等气质,担起家庭女祭司的圣职,弹起多年一直因惧怕惊动祖先的鬼魂而不敢弹的钢琴。黑人家族的父、母系祖先的鬼魂被琴声唤来,赶走了萨特的鬼魂,这揭示出黑人男女两性只有融为一个整体,才能驱走笼罩在他们上空的白色幽灵,才能彻底实现黑人种族解放的理想。此外,“鬼魂”作为一种异己实体,也是威尔逊消解二元对立思维、颠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一种有效策略。二元对立思维认为,两个对立项——人类与异类、男人与女人、白人与黑人、自我与他者并非和平共处,而是处于一个等级森严的秩序中。在这个等级秩序中,前一项往往优于后者,是第一位上的存在。为了消解、颠覆这一二元对立思维,威尔逊便借助“鬼魂”的在场与缺场、生与死、灵与肉、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来消解男人与女人、白人与黑人的二元对立思维,从而颠覆了男性优越的性别歧视和白人中心主义的种族歧视。
总之,威尔逊在《钢琴课》中批判了黑人的父权文化和女权主义思想,并探究到两性冲突是钳制黑人种族发展的症结所在,并找到了与后女权主义相暗合的威尔逊式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创建多元共生、和谐平衡的两性关系:即黑人男性要认识到自身的性格缺陷,颠覆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压迫,消解黑人男性的霸权气质;同时女性要打破“圣母玛利亚和耶洗别”的二元思维,建构独立、刚强的女性形象。因此不难看出,黑人两性群体只有消弭内部性别冲突,才能团结一致抵制白人文化的侵蚀和冲击,从而最终实现“黑白平等、黑白共存”的理想。
[1]Marra,Kim.Ma Rainey and the Boyz:Gender Ideology in August Wilson's Broadway Canon [A].Marilyn Elkins.August Wilson:a casebook [C].New York:Carland Publishing,Inc,2000.
[2]Collins,Hill.Black Feminist Thought:Knowledge,Consciousness,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1:75.
[3]申富英.男性、女性、第三性——论《夜林》中超前的女性意识[J].山东大学学报,2006(3):73.
[4]Wilson,August.The Piano Lesson [M].London:Penguin Books,Ltd,1990.
[5]Wandor,Michelene.Carry On,Understudies:Theatre &Sexual Politics[M].London:Routledge &Kegal Paul,1986:132-133.
[6]Lewis,Marshall.Interview with August Wilson[N].The Believer Magazine,Nov,2004:126-138.
[7]刘岩.后现代视野中的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J].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1(4):10.
[8]孟繁红.《一个人的遭遇》艺术创作视角的转换与生成[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62.
[9]张广利,杨明光.后现代女权理论与女性发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