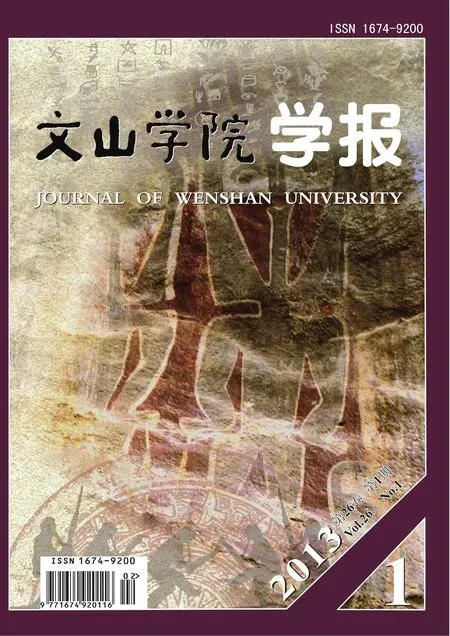13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的云南社会经济与饮食习俗
2013-03-19方铁
方 铁
(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
一、社会经济状况
13世纪中叶,为打破与南宋战争的胶着状态,蒙古国大汗蒙哥命其弟忽必烈率兵远征大理国,以汲取当地的人力与物力,形成对南宋的夹击之势。1253年平定云南后,蒙古统治者在云南先设19处万户府,但未能稳定局势。时已继位的世祖忽必烈,命老臣赛典赤·赡思丁于1274年建立云南行省。
云南行省建立后,统辖37路、54州与府县数十处。其统治范围,包括今云南省、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以及今缅甸、老挝和泰国的北部地区。赛典赤把省治设在中庆(在今昆明),改变了南诏、大理国约500年以洱海地区为统治腹心的格局。以后中庆地区获得迅速发展,不久便超过大理成为全省政治、经济中心。十余年后马可波罗途经中庆,此处已是一个“大而名贵、工商甚众”的重要城市。
云南行省重视发展交通。由中庆经大理至金齿的道路,是通往邻邦最重要的通道,沿此道入今缅甸北部,往西可至今印度的阿萨姆邦,往南沿伊洛瓦底江南下可达缅甸南部。元代自云南达印度的道路不仅畅通,而且两地的联系还相当密切。马可波罗说:今云南大理、开远一带盛产良马,“多售之印度人,而为一种极盛之贸易”。云南行省流行以海贝为货币,马可波罗认为这些海贝来自印度。云南行省的官吏述律杰,也指出云南行省流行佛教是因受印度的影响,他说:“(云南人)手捻普提珠,口诵阿弥陀者,比比皆然,由其地连西竺,与佛国通,理势然也。”[1]
除在前代开通的诸道普遍设置驿站外,元朝还拓建了以下道路:其一,中庆经普安达湖广道。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开通这条道路并设驿站。普安道的走向,是自中庆经曲靖、普安、贵州(今贵阳)、黄平达镇远(今贵州镇远),遂接通辰州(今湖南沅陵)以东的“常行站道”。此道开通后交通繁忙,赴京进贡的各族首领与赴内地的官员多至镇远再乘船北上,“实为便当”。[2][3]元朝遂裁减云南联系四川道路的驿马和站丁,云南联系内地从此主要走普安道。其二,由中庆达邕州(今广西南宁)的道路,1259年元军经邕州攻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即沿经此道。其三,大理或中庆至车里(今西双版纳景洪)道。这条道路的走向,是经今建水、元江、普洱、小橄榄坝至车里。沿以上两条道路,元朝也设了驿站。
在新开通的诸路中,以普安道最为重要,影响也甚为深远。元朝以云南为独立的行政区,同时把省治设于昆明,又开通由昆明经贵州达湖南的通道,结束了千余年来云南受四川管辖的历史。以后云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联系大为加强,两湖、江西等地的移民大量进入云南,云南外地移民以四川人为主的局面随之改观。位于道路附近的贵阳、曲靖、昆明、楚雄、昭通、玉溪等地,也成为云南行省经济发展较快、接受两湖、江西等地文化较多的地区。
在蒙元统治云南及附近地区的100余年间,不少蒙古人、色目人(主体是属于穆斯林的回回人)和汉人移居云南,他们带来新的文化与习尚。元朝灭亡后,为避免王朝更替造成的迫害,蒙古族的不少人改称他族,但蒙古族的一些饮食习俗,在云南仍保留并延续下来。元明之际,从中亚迁入中国的穆斯林融合汉族和其他民族形成回族。明代又有不少回族人口以军人、商人的身份迁入云贵高原,逐渐形成昆明、巍山、楚雄、保山、曲靖、寻甸等回族重要的聚居点。回族的经济生活和饮食文化颇具特点,为云南的饮食文化增添了堪称光彩的部分。
元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官制度。土官制度有以下特点:首先,为防范主要的对手汉人,蒙古统治者较为信任南方少数民族,并广泛任用其首领为各级土官。其次,把对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的任用纳入国家官吏系统管理,任命的土官有正式品秩,在待遇、权力与义务等方面,与内地官吏大体一致。其三,注重在土官地区征收赋税,虽可酌情减免,但已属于正式征收,与汉唐的情形不同。在少数民族地区征收赋税,虽加重居民的负担,但在促进资源开发、发展商品经济以及边疆各民族接受内地文化等方面,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云南行省广开屯田。据《元史·兵三》:蒙古军南下,遇坚城大敌必屯田困守,统一全国后各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云南、八番、海南等地,因是蛮夷腹心,尤“设兵屯旅以控扼之”。赛典赤查阅中庆地区百姓户籍,得隐户万余,以四千户即其地屯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乃全面设立云南屯田,“以供军需”。
据《元史·兵三》与《元史·地理四》,云南行省屯田的重点,包括威楚路(治今云南楚雄)军屯,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治今云南保山)军民屯,鹤庆路军民屯,武定路总管府军屯,中庆路军民屯,曲靖等处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军民屯,乌撒宣慰司(治今贵州威宁)军民屯,临安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治今云南建水)军民屯,梁千翼军屯(先在乌蒙地区,后迁新兴州),罗罗斯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治今四川西昌)军民屯,乌蒙等处屯田总管府(治今云南昭通)军屯。屯田总户数有19149户及6000人,屯田483335亩,数量颇为可观。但上述记载亦有缺漏,如普定路(治今贵州安顺)、八番顺元(治今贵州贵阳)等处亦有屯田,但这些记载未统计在内。以上诸处屯田,以乌蒙、中庆、大理、威楚、曲靖、临安等处规模较大,乌蒙等处屯田总管府的军屯达125000亩,相当于全省屯田数的四分之一强,意味着东晋以来遭受战乱残破的滇东北地区,农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屯田规模次于乌蒙者为中庆地区,《元史·兵三》的记载尚不齐备,因治理滇池后得到的近万顷土地未包括在内。元朝在中庆、大理、鹤庆、威楚、临安、曲靖等传统农业地区广开屯田,表明屯田主要是复垦过去的耕地,而与明朝大量开垦荒地相区别。
进行屯田后,不仅农业生产获得发展,内地先进的经济文化因素亦随之传入。元人说:云南东部蛮夷屡叛,“议者请据其腹心而制之”,乃于乌蒙立宣抚司并开屯田,初时吏士或亡或叛莫能定。此后行省官员兼领其事,命专人负责屯田,数年后风气大变,“几不异于中州”,屯田地区出现了“府中储积多如山,陂池种鱼无暵干,几闻春硙响林际,仍为窳蔬流圃间”的兴旺景象。[4][5]
中庆城紧邻宽广500余里的滇池。大理国后期,滇池因年久失修经常泛滥,乃至“夏潦暴至,必冒城郭”。[6]赛典赤至云南后,用在上段六河疏蓄、下段海口扩导的方法治理。他以滇池上游的盘龙江为重点,沿河疏浚并修筑松华坝,“以时启闭,缺则放水,治则索蓄之”。又派张立道等疏通滇池下游的泄水口海口河,使滇池水位大幅度下降。云南人民对赛典赤浚六河、张立道等扩海口十分感激,喻之为李冰凿离堆传颂至今。在其他地区,行省也兴建不少水利工程。《大理行纪》说今祥云有“青湖”,颇有灌溉之利。又说今凤仪县有神庄江,可溉田千顷,“以故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灾”。作者郭松年于元初宦滇,所述水利工程应为大理国所建,但当有元朝修缮方能维持功用。另据《元一统志·通安州》载,丽江通安州引山泉下注成溪,灌溉民田万顷。姚安府建有13处陂堰,为镇守云南的蒙古梁王等主持修建。[7]
蒙古是草原游牧民族,历来重视马匹的饲养。元朝在全国设14处大型养马场,云南、贵州等地均牧养国马。各地诸族也大量喂养马匹,不少地方以马匹为进贡的主要贡品。因云南盛产马匹,各级官府所需的马匹多在本地购买。云南各地出产的良马,还是补充驿马的主要来源。
食盐也是大宗生产的产品,尤以大理路和中庆路的产量较大。《马可波罗行纪》说:押赤城(中庆城)有盐井,“其地之人皆恃此盐为活,国王赖此收入甚巨”。其他地区的盐井也得到进一步开采,《元一统志》说:威楚“地利盐井”;建昌路“牛羊、盐、马、毡布通商货殖”。除充分利用前代开采的100余处盐井外,云南行省还新开一些盐井,如开南州的哀卜白盐井即未见前代记载。云南行省生产食盐,还注意到便利百姓,马可波罗说建都一带的小货币用盐制成,其法是取盐煮之,再用模型范铸为块,“每块重约半磅”。这种以食盐范铸制成“小货币”的做法肇自南诏,其产品既充货币流通,在缺盐地区亦可溶解食用,元朝沿袭前代旧制未改。
1368年建立的明朝,其统治长达277年,是包括云南在内西南地区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明代云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内地的距离明显缩小,同时较多地接受了内地的文化与习尚。
云南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被平定后,明军虽一度撤回内地,但以后又多次增兵这一地区。据《明实录》,洪武中后期明廷调兵入滇十次,人数达25万,连同原驻的8万余人,常年驻守的应有20~30万人。以每位军户有3口人计,驻守云南的军人及家眷应不少于60~70万人,为数甚巨。由于派驻的军队数量甚多,给养便成为令人头疼的问题。为解决军粮的供应,明朝在军队驻守之地开展大规模屯田,并规定驻军三分守城、七分屯种。据《明史·沐英传》,云南总兵官沐英镇守时垦田至100万余亩;沐英卒后子沐春袭职,施政七年间“大修屯政”,辟田30余万亩。估计云南军屯的面积应在100余万亩以上。除军屯以外,明朝还在云南举办“商屯”,即由商人经营屯田,收粮交给当地官府,换取盐引领盐贩卖。明朝还组织“移民就宽乡”,召募或征徙百姓至边疆屯田。据研究,明代云南的人口超过元代甚多,应在 350 万以上。[8](P744,747,751)明代进入云南的外来人口,在当地人口中占较大比例,占到四分之一强。明朝在云南的大量驻军与屯田,形成大规模的经济开发运动,使明代成为云南进步较快的一个时期。
伴随大规模的屯田,农田水利事业获得空前发展。滇池地区最大的水利系统工程是滇池流域的治理。洪武初至正德年间,云南官府三次修治滇池,疏通修浚后溉田千顷,“滇人颂之”。[9](卷126)[10]1549年滇池地区连降大雨,水位猛涨淹没不少房屋田地。云南巡抚顾应祥等组织第四次修治,动用民工15000余人,使水患得以控制。以后明朝对滇池又进行多次治理,重要者如1618年,将滇池上游盘龙江之松华土坝改造为石坝,“地有安流而不能灾。”[11][12]重要水利工程还有宜良县汤池渠,1396年,沐春派士兵15000人,拓建长36里的河渠引汤池水,“灌宜良涸田数万亩。”嘉靖年间,官府又组织将汤池渠延至50余里,灌溉田地达10万亩。[13][14]明朝在云南修建的重要水利工程,还有洱海疏浚工程、邓川州的弥苴佉江堤、石屏县的异龙湖引水工程、永昌引易罗池水灌溉的九龙渠、澄江府的漱玉泉堤、沾益州的交水坝与杨柳坝、楚雄府的梁王坝与城南堰等。明代云南修建较重要的水利工程,见于天启《滇志·地理志》记载者近200处,一些水利工程浇灌的田地,在1000亩至10000亩以上。
明代云南农业有很大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1388年,官吏奏报云南都司储粮336007石。1431年总兵官沐晟奏报,云南都司上年军屯获粮492100石,可满足驻军11个月的供应,较前增加46%以上。据成书于正德五年的《云南志》卷一,云南都司屯田粮折米806218石,较宣德时增加63%以上。[15](卷194)[16]谢肇淛《滇略》卷四说:云南丰年米价甚贱,即遇凶荒,斗米亦不及百钱,云南斗斛甚大,倍于其他地方。秋收时各处丰收,无复粮食转贩,足谷之家时时以此为苦,“至于市无乞丐,物无腾踊,安土乐业,数世不知迁徙”。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得到开发。如云南景东府所居百夷,“田旧种秫,今皆为禾稻”;临安府百姓以前采猎为业,明代中后期则农耕于野、商行于路。广西府则是“士知向学,民勤耕织,风化渐行,殊异夙昔”。[17](卷3)
畜牧业较前代有更大发展,马牛等大牲畜明显增加,饲养羊猪犬等极为普遍。各地养牛的数量大为增加。云南都司拥有的屯牛,洪武时为15284头;另据弘治时呈报,云南都司所属25卫,有耕牛15650头。[18]民间饲养的耕牛还未统计在内。马匹的饲养量也很大。1372年明朝在川陕设五个茶马司,向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买马。四川茶马司所购马多来自川西南、滇东北和黔西南。1384年云南东川府与黔西南地区售马之数,“乌撒岁易马六千五百匹,乌蒙、东川、芒部皆四千匹”。[9](卷311)1386 年,明朝派百户甘美率军士1000人携大量白金,往云南东川等府买马2380余匹;不久又命将士携带白金13万两再往云南购马。[15](卷176,卷178)依前次价格计算,后一次购马当在万匹以上。西南边疆的马匹还通过朝贡途径输入内地,输入量仍以云南居首位。据统计,永乐在位22年,其中云南贡马74次,产马地点除滇池、滇东北与滇西外,还有景东、镇沅、顺宁、镇康、大侯、麓川、湾甸、潞江、孟定、孟连、车里、临安、溪处、广西与维摩等地,几乎遍及全省。[19]
云南地区大量养羊。彝族等山居民族不仅大量食用羊肉、羊乳,还普遍以羊皮制作服饰,以羊毛制毡。北方多养绵羊少养山羊,原因之一是山羊虽耐粗饲,产肉率亦高,但喜刨食草根,在生态脆弱地区易破坏植被。而云南地区温暖多雨,茂盛草地随处可见,山羊虽刨食草根但植被恢复较易,因此各地饲养山羊甚多,明清时云南已培育出一些优良的山羊品种。
云南的景东、元江、麓川、车里与八百等地产象。象可供耕作或为贡物,亦可驱使参战。云南土司常向朝廷贡象,朝廷亦派人至云南买象。如1578年与1608年,云南布政司两次购驯象60头,并派驯象人送至京城。史籍中有使用战象的记载。1388年,麓川土官思伦发进攻定边,以战象100余头充前锋,被沐英所率明军打败,战象死亡过半,生擒37头。[17](卷3,卷6)[9](卷314)
明代云南制盐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据《明史·职官四》:明朝在全国设七处盐课提举司,其中四处在云南,即黑盐井(楚雄)、白盐井(姚安)、安宁(安宁)、五井(大理)。洪武时,云南盐课提举司岁办大引盐17800余引,岁入太仓盐课银35000余两,可窥知采盐规模不小。据《明实录》:“滇南唯矿盐二课,为力滋大。”既将制盐业与矿冶业相提并论,可见滇南等地的制盐业较发达。由记载观之,云南出产之盐基本上可满足本省的需要。
云南的手工业趋向繁荣。尤其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用具,品种繁多,制作精美。万历《云南通志》记载有“窑课”,即瓷瓦窑须向官府纳税,证明云南生产瓷器已达到较大的规模。近年在云南玉溪发现明代的瓷窑遗址,亦为其佐证。另据《滇海虞衡志·志器》:凡铜器、玉器,以滇制者为美。明代抽调江宁(今南京)工匠入滇,云南百姓交口赞誉的白铜面盆,“皆江宁工匠造之”。除面盆以外,以白铜制作的器皿还甚多。云南还出产铜锣锅,其制式如小盆而卷口,旁有缀环之耳,上部有盖,大小能供二三人炊食,“客旅便之”。出门者亦背之而行,人称“背锣锅”。
经济繁荣,促使交易与消费活跃。昆明为人口众多、交易繁忙之地,元代即有“千艘蚁聚于云津,万舶蜂屯于城垠;致川陆之百物,富昆明之众民”的赞誉。明代昆明的集市,以十二生肖为率,寅日属虎街,午日为马街,以此类推,不明究里者听说云南有“鼠街”、“狗街”或“龙街”,多深感困惑。另外还依时令、物产的繁盛,定期举办大型集市,如十月为酒市之期。昆明城东关、南关为商阜之地,“列肆纵横”,商旅则在三市街一带交易。大理是滇西的重要城市。除每日进行交易外,还举办大型商贸集市“三月街”。“三月街”的地点在点苍山下演武场,会期五天,届时全国的商贾皆来贸易,“若长安灯市然”。[20](卷4)1639 年徐霞客至大理恰逢“三月街”,亲睹其盛况:演武场俱结棚为市,环错纷杂;北面为易马场,千骑交集;“男女杂沓,交臂不辨”,场中交易之物,多药、毡布及铜器木具,亦有永昌商人携宝石、琥珀及翠生石出售,“十三省物无不至,滇中诸彝物亦无不至”。[21]永昌(今保山)为通往缅甸的重镇,集市时人头攒动,声音嘈杂难辩。来自各地的商品辐辏转贩,不胫而远走四方。时谚谓永昌一日费酿米200石,“亭午以后,途皆醉人”。
明代是云南风气骤变的时期。成化时云南布政使周正巡视澄江,题对联以赞其民风,对联言:“文风不让中原盛,民俗还如太古醇。”万历末年谢肇淛《滇略》,形容云南常见的风尚:“衣冠礼法,言词习尚,大率类建业。……熏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嘉靖《寻甸府志》说:澄江的白罗罗,“渐习王化,同于编氓,新兴(今玉溪)者力田为生”。《明史·土司传》亦赞:“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以上情形,反映出云南不少地区已深受内地文化与习俗的浸染。
二、饮食习俗
农业经济的长足发展,为云南饮食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并由此形成一些新的饮食习俗。
元代,赴云南镇守的蒙古人与色目人,也把自己的饮食习俗传播到居住的地区。云南多牛羊,在很早的时候,当地民族便普遍饮用牛羊奶,并擅长制作各种乳制品。元代云南的各民族,融合、吸收南北方做乳制品的方法,制作出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乳饼与乳扇。云南的白蛮、乌蛮都擅长制作乳饼。其制作的方法与风味,则有别于北方草原民族的奶豆腐。如产于云南路南县的乳饼,以羊奶经酸浆点制而成,成品呈乳白色豆腐块状,形状白嫩细腻,嗅之有新鲜乳香味,食法灵活多样,既可生食,亦可煎、贴、烩或蒸;尤以生煎乳饼、乳饼夹蒸火腿、乳饼串炒嫩蚕豆颇具特色,为云南各民族所喜爱。
乳扇是大理地区的特产,自食或馈赠均甚相宜。近年还推出真空包装的产品,远销云南省内外,食者赞不绝口。《滇海虞衡志·乳扇》言其制法:以黄牛乳煎酿而成,以其状如扇而得名,主要产自大理地区的邓川、浪穹一带。若母牛产犊,主人乳之月余遂断其乳,换豆浆以饲,置牛犊于别栏。乃取母牛之乳,以小铛盛酸浆半碗,煎之将沸,倾入乳汁半碗,酿之顷刻,其精华渐结成乳质,其余悉化为水。人揉其乳质成团,以二短箸轮卷而引长之,布置于竹架成张页,遍布而晒干之。成品微黄,滋润洁净,似稍卷带乳香的厚纸,干燥后可对折如扇,故称“乳扇”。其精品价格甚昂,人多贩及远方。邓川有德源岗,草佳适宜牧牛,于此得牛乳数量倍于他处,故远近人家,皆畜二三牛或四五牛。山岗宽五里许,而万牛放牧其间,草根几被食尽。凡产乳扇之地,若生公牛,主人出售以耕田,生母牛则畜之以取乳,因此牡贱牝贵,“以取乳之利厚然也”。
乳扇的食法有多种。通常生食或煎食,亦是大理白族待客的“三道茶”必用原料。唯煎时灶火及烹油不可过旺,下锅乳扇变软如煮熟面条,须敏捷以二箸翻裹、折叠数次,嗅香见黄即可起锅,延时则焦糊不可食。乳扇成品香脆,若裹之以豆沙,其味尤佳。以乳扇佐餐或下酒,可谓无不相宜。
云南所产岩盐,制法大都是汲取盐水以柴火煎干,铸以为块盐或筒盐。块盐坚硬味香,食时须捣碎或敲碎。亦有山区百姓将块盐吊于铁锅上方,煮汤时垂入汤中,晃荡数次以取咸味者。云南诸族很早便知,以筒盐腌制火腿或腊肉,色鲜而有老腊肉香味,年代愈久其香愈烈;若烹煮多年老火腿,弥屋香味尤使人馋涎欲滴。清代云南著名的宣威火腿,即规定必须以指定盐井所产的筒盐腌制。元代云南诸族,还以筒盐为马匹保健或治病的良药。据《元史·文宗四》:至顺二年(1331年),云南行省奏:亦奚不薜(指今贵州地区)之地所牧国马,每月于上寅日按时喂盐,“马健无病”。今因官军叛乱而“云南盐不可到”,以致所牧国马多有病死。可见云南所产筒盐,用于马匹的保健与治病确有奇效。宋代大理国已有喂盐助马复膘的做法,元代亦奚不薜的养马场给马喂盐以防疾病,可能是沿用云南诸族的传统方法。
云南本地民族大量饲养牛羊猪,视牛羊猪之肉为日常饮食及待客的佳品,如乌蛮即喜食“砣砣肉”。烹饪方法是取年齿稍嫩的猪或羊,切成巴掌大小的方块,放入汤锅烹煮。块肉以肥瘦相间者为佳,煮前须一次把水加够,烹煮时不再加水,如此方肉香味足。煮熟后以漆盘盛之上桌,食客勿论成人儿童每人分以一块,以献上肥壮之肉为敬。食砣砣肉可以蘸盐,亦可蘸以盐、辣椒、酱油、麻油与腐乳配制而成的“蘸水”。肉类、蔬菜烹煮时不放盐,食时蘸“蘸水”以提味,是云贵各民族地区常见的食俗。采用如此食法,菜肴盐味的浓淡、配料的辛辣与否可各自掌握,入口别有一番滋味。偏远地区的居民,以“蘸水”蘸食蔬菜或肉类,还有节省食盐的用意。在乌蛮等山地民族中,砣砣肉是待客最佳的食品,也是待客最高的礼数。乌蛮等山地民族“打冤家”(械斗),出发前必宰杀猪或牛羊款待出征者,不愿参加“打冤家”者不得入席。若食主人的杯酒块肉,参加“打冤家”须拼死向前,丧命亦不足惜。既食酒肉而临阵退却,对这些民族来说是莫大的耻辱,当事人将永远抬不起头。
一些本地民族待客甚为大方,如居今丽江的磨些蛮(今纳西族),富有者每年冬天宰杀牛羊,竞相邀客请延无虚日,“一客不至,则为深耻”。乌蛮祭祀之时,亲友毕至,宰杀牛羊亦动以千数,少者也不下数百。少数民族视为祭祀而宰杀牛羊为吉利之事,如云南大姚的彝族毕摩(巫师),在祭牧羊神的祭词中说:“今天祭了牧羊神,我的牧畜要兴旺。”
云南一些本地民族嗜食生肉或半熟之肉,视之为难得的至味。马可波罗述其在金齿州(今云南德宏)的见闻说:当地居民食一切肉,“不问生熟,习以熟肉共米而食”。称哈剌章州(今大理一带)居民有食生肉的习俗,勿论羊、黄牛、水牛或鸡之肉,均细切其生肝,置热水掺香料的酌料而食。另据元代《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白蛮“食贵生,如猪牛鸡鱼皆生醢之,和以蒜泥而食”;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德《云南志》亦有类似的记载。
云南诸民族喜好饮酒。其酒以粮食或水果、野果等酿造。马可波罗说:建都州(今四川西昌一带)无葡萄酒,但有一种小麦、稻米搀和香料酿制之酒,“其味甚佳”。他还说建都州丁香繁茂,亦有一种小树,其叶类似月桂树叶,但花白而小,如同丁香。其他地方亦产生姜、肉桂等甚丰饶,这些都是当地人酿酒常用的香料。[22]《马可波罗行纪》又说:押赤城(今昆明城)颇有米麦,但百姓认为此地小麦不卫生,多不以为食,仅食稻米,“并以之掺和香料酿成一种饮料,味良而色明”。说秃落蛮州(今云南镇雄)居民以肉乳米为粮,“用米及最好香料酿酒饮之”。
明代外来人口大量移居云南,传播了内地的文化与习尚。见于记载的明代云南各地节庆与饮食活动,明显有受内地影响的痕迹,同时也表现出云南本地的特点。据明代谢肇淛《滇略》卷四:云南的节令与礼仪,大致与中原相同,如元旦贴桃符贺岁,上元节观灯,清明节插柳,四月八日浴佛,端午节悬艾及饮菖蒲酒,七夕乞巧与中元祭祀,中秋赏月和重阳登高,腊月二十四祀灶及除夕守岁,以及饮酒顺序是先少后老,“惟夷地风俗稍异耳”。
谢肇淛又称云南的饮食,公宴、礼会与中原相同,但具有特色的饮食风俗,则是糅杂各地的习俗而成,如缕切饼饵乱如蓬麻,称“蓬饵”;水磨蒟蒻而兑之,谓“鬼药”;以熟糯米粉和芋泥且淋以油,缀以采糁称“饧枝”;浓煎乳酪而揭之,为“乳线”;揉合糯米与山药,圆而煠之如荔枝,谓“粉荔”。至于鱼肉、畜肉、鱼蚌之属,则生斫若丝,和以诸椒、桂等香料而食,称为“斫生”,实为古人斫脍之法,明代闽、广等地间或有之,而云南诸族则习以为常。又说:元旦、清明、端午、七夕、长至诸节,云南百姓多做赤豆羹以食且互赠。《初学记》称:“共工氏有不才子七人,死而为厉,性畏赤豆,故作羹以祛之。”逢元旦等节日云南人喜食赤豆羹,颇有中原远古的遗风。谢肇淛又说:云南举办宴饮,进烹鱼然后撤席,人称湖南以西皆有此俗。他认为江浙一带亦然。江浙宴会烹鱼多至三四种,其末乃上一大鲤,戏称为“春牛”,谓迎春之时,牛必居其后之意。广西亦有此俗。可见进烹鱼后撤席的习俗,主要是受江浙一带的影响。
天启《滇志》卷三,称云南与饮食有关的节庆习俗如下:逢春日,备春盘赏春,以饼酒相馈。若上元之夕,多设宴赏灯张乐。至二月三日,全城居民出谒龙泉观,还归憩于石嘴庄,为临江之饮。四月八日,浴佛并献乌饭。五月五日,悬艾虎、饮菖蒲酒,以角黍(类似于粽子)互馈。遇中元节,多祭先祖于祠堂。中秋节设宴赏月,以瓜饼祭月。重阳节,老少登高并赏菊,饮茱萸酒,以面簇诸果为花糕,亲识相互馈赠。过长至节,亲识之人相贺,喜食赤豆羹。逢腊八日,多作五味粥。念四日祀灶,送五祀之神。除夕夜燃爆竹,饮分岁酒,顺序先少后老,四更时喜迎灶神。
据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三:昆明地区有以饵块互赠的习俗。称该地百姓遇时令节庆,必煮白粳米为软饭,杵之为饼,折而捻之,置之半月,盛以磁盘致馈亲友,为礼节之至重。此为云南制作饵块较早的记载。食饵块之法,除折而捻之为薄饼,烧烤见黄、涂以芝麻酱即食外,还可制为砖型,覆以湿巾,可保存月余不坏。砖型饵食可切片或缕丝,既可与鲜肉、豌豆苗及腌菜共炒,也可稍蒸其丝后浇以肉汁,充当早食或作正餐,无不相宜,滇人视饵块为家居所须臾不可缺。另外,昆明城外的吴井地方,井泉清冽,官民取以泡茶,茶味甚佳。时人以为若取之以酿酒,必与广西有名的瑞露酒争先。
元代开通由昆明经贵州入湖广的道路以后,大批湖广、江西的移民沿此道进入云南,也带来故乡的饮食文化。湖北有一道家家皆喜的菜称“排骨煨汤”,于所用砂锅、排骨、藕均极讲究。客人来访,主人不奉茶而端上一碗藕煨排骨,主客皆大欢喜。老昆明人亦喜以土锅煨排骨及藕,食法与湖北人并无二致。昆明人视土锅为至宝,新购土锅须先熬粥,称以粥汤填塞砂眼,土锅乃不漏水。市场上排骨因此价昂,几近于精肉。
除省城以外,各地的节庆与饮食习俗又有不同。如大理一带流行佛教,老人多手捻念珠,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一岁之中,斋戒居半。朔望时节,人多裹饭袖香入寺,礼佛饭僧。时有饮酒食肉、托言来自印度的僧人,民家崇奉若神,或出妻女侍之,惟恐留其不住。五六月间,取苍山之雪售卖者满市,家家以蜜和雪品尝,称为“蜜雪”,谓可去心腹热疾。七月二十三日,洱海之滨有赛龙神会,届时大小游艇咸集,众人祷于洱海神祠,既毕泛舟于洱海碧波之间。大理郡人勿论贵贱贫富,皆倾城出游,载酒肴鼓笙歌,扬帆以竞渡。不登舟者则列坐水边,藉草酣歌自得。售酒脯、瓜果的商肆,沿湖堤布列十余里。大理一带有风俗,九月登苍山之麓崇圣寺唐塔,阖城士女与缙绅,尽携食物果品前往,错杂列坐松阴之下,入夜方返家。[20](卷4)
明代临安(今建水)繁华富庶,谚云:“金临安,银大理。”言其地之繁华富饶。其地多高山大川,蔬果、鱼鲜等类甚多而不可尽述,又说临安有铜锡诸矿,乃致人丁繁杂,商贾辐辏。其民习尚奢靡,“好宴会,酒肴筐篚,殆无虚日”。永昌(今保山)、腾越(今腾冲)之地,沃野千里,为滇西一大都会。其地饶竹木、鹿豕、鱼虾之利,盛产金银、铜铁、象牙、宝石、丝料之属,又邻通缅甸,各地商品辐辏转贩,故其人习尚奢华,讲究饮食与宴乐,谚谓“永昌一日费二百石酿米”,亭午以后,集市沿途皆见醉人。
永昌的西南面,主要为百夷(今傣族先民)所居。百夷举办筵宴,贵人上坐,其次以贵至贱,顺序列坐其下。先奉以茶并萎叶、槟榔啖之,以次进饭,之后上酒馔。每客必有一仆持水瓶侧跪其旁,侍客嗽口、净手而后食,食毕复进如前。烹饪食物有蒸、煮或炙诸法,多精洁可食。酒则烧酒,茶则谷茶,饭则糯米。饮酒以杯或以竹筒,酒与食物必祭而后食。酒初行,必一人大噪,众人和之,如是者三轮,乃奏乐。食不用匙箸,以手搏而啮之,所啖不多。亦喜食榨取果实与嫩树叶汁酿造的“树酒”,善以竹笋制醋,味颇香美。[20](卷9)[23][24]其言百夷食不用匙箸,实为南方一些少数民族中常见习俗。一法是就食者以手抓取米饭,在芭蕉叶或竹篾上团成块食用。另一方法如元人马端临所形容:“性好洁,数人供饭一盘,中植一匕,置杯中其旁,少长共匕而食。探匕于水,抄饭哺许,搏之盘,令圆净,始加之匕上,跃以入口,盖不欲污匕妨及他人。”[25]明代田汝成《炎徼纪闻》卷四称罗罗聚会,列坐无几席,食饭用前述之后一法,食毕必涤舌刷齿以为洁。
由于种植业有较大发展,粮食种类颇有增加,出现了不少优良的品种。种植的优质稻谷,以八宝米、遮放米、香糯米、紫米为人们所称道。八宝米产于广南县八宝乡,有味香粒大、蒸煮耗时少、饭粒带粘性等特点,分雪白、青玉两个品种。明代以来选为贡米,声名远播省内外。遮放米产于芒市以西的遮放(在今德宏州潞西县),民间有“芒市谷子遮放米”之说。其米洁白透亮,粒长清香,煮熟后甜糯香软,亦为明代以来知名贡米。香米产滇南、滇西一带,景谷县香糯米尤佳。特点是香气袭人,煮饭松软可口,人称“无菜也要食三碗”,有糯性香米与非糯性香米两种。紫米因色紫而得名,产于蒙自、建水、石屏、墨江等县,其米具较高的营养与药物价值,当地百姓以其酿造紫米酒,多供不应求。较之北方稻谷,云南山田、平田所产稻米,米粒略细,略近于川、广等地所产的籼米。[26]
广大山区的粮食作物则以杂粮为主,有小米、红稗、豆类、大麦、小麦、燕麦等种类,一概称为“麦莜”。荞麦、青稞为云贵地区的传统粮食品种。吴大勋《滇南闻见录》记云贵地区的旱地、荒山遍植荞麦,勿论时节随处可见,植株现红梗、绿叶与白花,皆清新可观。民间食荞,多磨面烤制为饼,蘸蜂蜜食之尤佳。远行力役之人,多携此为干粮,食时于山沟内取凉水伴饮。荞有甘、苦两种,苦者可食,甘者则味不佳。荞性寒与稗相同。山区多酿荞稗烧酒,味清香可饮,但饮多成手颤之病。荞产量虽低,但耐粗放种植,播种后可任其自长,无须移种;稗则须播种和分苗,方法与水稻相同。天寒地瘠之地,尤宜栽种荞麦。青稞形似小麦而色青,宜在高寒地区种之。藏民多磨青稞做稀饭,杂牛羊肉煮食之。
燕麦亦是山民常食之物。包汝辑《南中纪行》说:贵州禾米佳于中原,彼处之人以燕麦为正粮,间或食稻米。燕麦状如小麦,外皆糠模,内有芥粒,色黄可食。群苗磨燕麦为面,每人携一羊皮袋,内装燕麦粉数升,途中遇饥辄就山涧取水调食,称为“香面”。《滇略》卷三认为云贵地区百姓食用燕麦,始于唐昭宗时。其时南诏大旱,荞麦不收,饥民食“乌昧”充饥,不足乃取草根、木叶充饥。所说“乌昧”即野燕麦,滇中如沾益等处皆有,当地人喜采食,谓之“鬼麦”。滇东北一带还以大麦、苦荞或黄稗酿酒。
明末清初,包谷、洋芋与番薯自外地传入云南地区,因其耐旱高产,适于山地种植而很快推广,逐渐成为山区居民的主粮。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山区,玉米、番薯还取代稻米成为酿酒的主要原料。清代外地流民大量进入云南,因盆地与河流冲积地带已人烟密集,流民遂多上山或赴边远之地垦荒种地。由于得益于种包谷、洋芋与番薯,外地流民可以果腹,并在山区或边远之地落籍。
云南居民的饮食,也逐渐向精细化方向发展,对山野间的菌类等物产颇讲究滋味。云南地区的知名野生菌,有鸡棕、干巴菌、松茸、牛肝菌、青头菌、羊肚菌、猴头菌、蜜环菌、鸡油菌、灵芝和竹荪等。云南人视鸡棕为菌类中的极品①,称其优点是既肥且嫩,味特清甜。鸡棕颜色棕黄,中部凸起若斗笠,菌盖光滑如鸡敛羽,因而得名。鸡棕盛产于云南,尤以永昌永平所产甜美且多,当地官吏索要之,动辄数百斤。此物于六月大雷雨后出于山坡沙土,或在松树之下,或在丛林之间,不一而定。出土一日即须采,此时朵小而嫩,若过五六日即烂。民间有“鸡棕必三窝”之说,谓发现鸡棕以后,后二三日前往寻觅,仍可采集附近的两处鸡棕,过三乃止。采后须洗所附泥土,以盐煮烘干,若见炊烟即串味不堪食。采后未洗而过夜,则香味俱尽,因此采集甚难。鸡棕的食法有多种,可炒食、煮汤,若与菜油同熬为汁以代酱豉,尤为美妙。[20](卷3)[27]抗战时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他称鸡棕为“植物鸡”,说昆明甬道街有一家本地饭馆,因擅长做鸡棕而“极有名”。
对上桌鸡棕之香甜美味,古人赞不绝口。清代陈鼎《滇游记》甚至说:蒙化府所产鸡棕,炼以椒油,色碧如泉,其香如兰,食之沁人肺腑,“溲溺皆馥”。但似乎太过夸张。清代的鸡棕,以滇中的富民、滇西的顺宁、滇南的蒙自出产最为有名。富民年产鸡棕至万斤以上,出产最盛之地为赤鹫乡。[28]滇人喜爱鸡棕,遂传言明太祖朱元璋极嗜此物,每年必令贡之,小心收藏而暗自独享;马皇后口馋索要,太祖不得已分与数棵。古代宫廷生活奢华的程度,固然非小民所可想象,但由此传说,却可窥见云南百姓性情的可爱朴实。
近年云南山野之间出产的块菌,输出欧洲而价格甚昂,称为“松露”。据说每公斤价值欧元上千元。其菌因猪嗅知其味拱土而食,当地百姓遂淡看之而不喜食,称之为“猪拱菌”。块菌颜色稍黑,形状似丛林间的土块,味清香而产量甚少。可见云贵山野间菌类之佳者,有不少当时的人们尚未知晓其价值。
云南百姓钟情朝廷,还可由“大救驾”的得名窥知。据说南明政权避难滇西,逃避清军追击而奔走狼狈。当地百姓献上炒饵丝,永历帝朱由榔几口食尽,抹嘴叹曰:“真是救了朕的驾。”所献炒饵丝遂被称为“大救驾”。迄今云南人至腾冲,若不品尝“大救驾”,无不引以为憾。“大救驾”的做法并不复杂,以饵块切丝,倾热油炒以鲜肉、鸡蛋、番茄、香菌与辣酱,上桌但见色彩斑斓,香味扑鼻,令人食指大动。
由明入清,云南各地的淡水鱼类,因肉嫩味美而知名者为数颇多。例如:洱海所产工鱼,细鳞纤长,无鳞少骨,腹腴而味美,《滇海虞衡志》卷十二说就河水煮鱼,作鱼粥食之,“虽松江鲈脍,味殆不及也”。云南旧志记载,称云南土人不识“江”字,因语为“工”,不知古韵“江”仍有“工”音,大理自古晓熟文义,故用古韵称之。大理地区的佳鱼不少。又如上关石穴,八九月产油鱼,较工鱼更小,而肥美过之,灸则膏溢。赵州所产丁鱼,细小如钉;螺则大如拳,有黄、卵及膏,待秋夏之交盈肆出售,颇受众人欢迎。金沙江有细鳞鱼,大者三尺许,肥甘异常。滇中澄江抚仙湖所产大头鱼,与江川星云湖的康郎鱼,皆肉多味美,制鱼酢尤佳。传说抚仙湖与星云湖相通,但二鱼不相往来,若见则相啮。附近通海的杞麓湖出水鸟章鸡,颜色类似乌鸦,身子长似白鹭,烹之香脆柔美。但非土产,每年开春由外地飞来,重阳飞去,来时必为夜间,群飞声响如雷。为宦澄江者遂作诗云:“康郎不入湖,大头不入海,十年万里滇云梦,惟有章鸡没处买。”
滇池佳鱼亦多。如发鱼,带细发形如妇人,肥白无鳞。金线鱼,出晋宁牛恋乡岩洞下,仲秋之际,鱼群自滇池溯泉至洞口,渔人就洞口置笱捕之。长仅三四寸,细鳞修体,鱼脊有一线如金色,因此得名。煎以泉水,有膏浮于汤面,味极鲜美。渔人苦于官吏诛求,不敢入城兜售,唯民间私购且先与银,方乃得之。因捕捞过度,前二十年金线鱼渐趋灭绝,近年有关部门向滇池放养了一些金线鱼苗,据说生长情况不错。金线鱼亦厕身于云南六大名鱼之列。滇池多有藻类,出细虾,渔人捕之晒干市售,价甚低廉,百钱可购一筐。渔人说亦有长数寸的大虾,但恐官吏诛求,多匿而私售。[20](卷3)[29]《滇海虞衡志》卷八还说:滇南半是水国,产鱼处甚多,其中以鲤最美,满腹鱼子,为江南所不见者。云南可为席间珍品的水产,还有白鱼、鲇鱼、乌鱼、吹沙鱼、黄师鱼、泥鳝、草鱼、蚬、田鸡(类似牛蛙)、大螺、海参、蟹、驼背鱼与鲈鱼等。
注释:
①古籍记载“鸡棕”之后一字,为“土”旁加“从”字,字典多不收,初见其字者亦难识其音。故改记为“鸡棕”,亦近其古意。
[1](元)述律杰.重修大胜寺碑铭[A].新纂云南通志卷94金石考[Z].
[2]永乐大典卷19423·22勘.站·站赤八[Z].
[3](元)熊梦祥.析津志·天下站名[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辑佚本.
[4]福建总管刘侯墓碑[A].(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3[Z].
[5]题蒙泉吏隐图[A].(元)陈旅.安雅堂集卷3[Z].
[6]元史卷61地理四[M].
[7](景泰)云南图经·姚安军民府·山川[Z].
[8]路遇,等.中国人口通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9]明史[M].
[10](正德)云南志卷2[Z].
[11](明)杨慎.海口修浚碑[A].(天启)滇志卷24[Z].
[12](明)江和.新建松华坝石闸碑记铭[A].(天启)滇志卷19[Z].
[13](明)平显.汤池渠记[A].(天启)滇志卷19[Z].
[14](道光)云南通志稿卷52.建置志[Z].
[15](明)太祖洪武实录[Z].
[16](明)宣宗宣德实录卷84[Z].
[17](天启)滇志[Z].
[18]明会典卷201[M].
[19]汪宁生.古代云南的养马业[J].思想战线,1980(3):38-44.
[20](明)谢肇淛.滇略[Z].
[21](明)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八[Z].
[22][意]马可波罗行纪·建都州[Z].
[23](明)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Z].
[24](明)钱古训.百夷传[Z].
[25](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9四裔考五[Z].
[26](清)吴大勋.滇南闻见录[Z].
[27](明)张志淳.南园漫录[Z].
[28](民国)罗养儒.云南掌故卷9[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
[29](清)倪蜕.滇海虞衡志卷12杂志[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