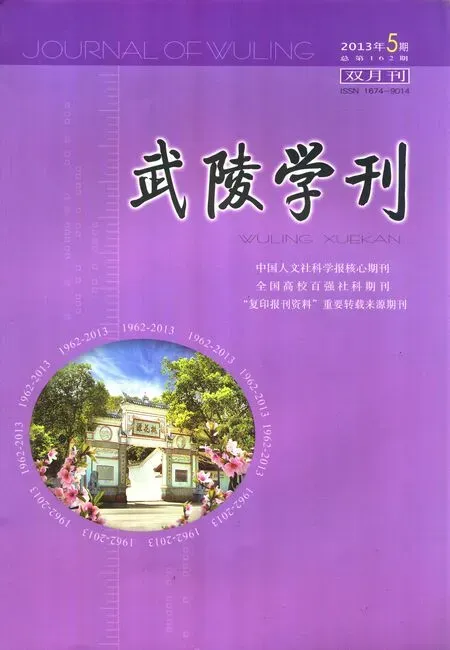曾巩《归老桥记》中“青陵”及其相关问题辨正
2013-03-19梁颂成
梁颂成
(湖南文理学院 文史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常德旧城西北,今柳叶湖以西,有一座自古闻名的白马湖。唐刘禹锡的《采菱行》有“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彩鸳翔”的精彩描绘。北宋,这里又出了著名的“武陵五柳”。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百十一专列“武陵柳氏”一条:“柳拱辰,本青州人。祖南徙居武陵。举进士,通判鄂、岳州,有惠爱。弟应辰,子平、猷等,皆相继擢第,时号武陵五柳。”[1]名列唐宋古文八大家的曾巩为柳拱辰写了《归老桥记》,苏辙为柳平写了《寄题武陵柳氏所居二首》。凭借文豪的诗文,白马湖和“武陵五柳”名扬天下。这里,主要讨论一下曾巩《归老桥记》中提到的地名“青陵”及其相关问题。
一 《归老桥记》中的“青陵”本来应该是“清陵”
常德旧城西北太阳山下的白马湖畔,自古就有古迹“清陵馆”,文献记载传承不绝。由此衍生,这一带又有“青陵”地名、“青溪”水名,和“清陵村”村落名。在各种方志和其他文献中,只有水名“青溪”的用字比较固定。其余古迹“清陵馆”、地名“青陵”和村落名“清陵村”,其首字则“清”、“青”两者并存。如出身于这附近的名人中,就有两位以此作为字号:一是明代杨嗣昌,天启年间著《武陵竞渡略》,刊刻时即署名为“清陵亭长”,现存《古今图书集成》中;一是清代著名诗人王敬禧的儿子王慎甸,亦笃学工文,则以“青陵”为字(见清嘉庆《常德府志》卷四十一)。这都是出于对故乡的纪念。
那么,究竟应该是“清陵”还是“青陵”呢?
对此,清人郭嵩焘(1818~1891年)在《湖南金石志》(即《湖南通志》卷二百六十)中提出过意见:“汉青陵馆碑,《舆地碑目》在武陵县城西西明寺,有台。云汉李陵为临沅令,游息于此,有古碑,漫灭不可读。又云青波馆。《方舆》为青陵馆,以后人思陵,以‘陵’为是。嘉庆《通志》案:《明统志》载,李陵为临沅令,后没匈奴,邑人思之,为立清陵馆。考《元丰类稿》《归老桥记》云:柳侯图其青陵之居,属予为序。又云:吾之先人青陵之田。又考《方舆胜览》云:柳拱辰,其先青州人,五季避地荆楚,为武陵之青陵人。年六十,即有挂冠之志,创亭于青陵馆,名桥曰归老。‘清陵’之‘清’皆作‘青’。《明统志》作‘清’,非是。”[2]
笔者认为,《湖南金石志》的这一判断,只是例举了一些文献的用法,没有深入到这一称号的内涵,因此缺乏说服力。如果我们探究一下“清陵馆”的来历及其本身的含义,孰先孰后,该用哪个也就十分明白了。
据宋王象之(1163~1230年)《舆地碑记目》卷三载:“清陵馆碑,在郡西西明寺。寺后有台,云是李陵为临沅令游息于此,有古碑,漫灭不可读。”[3]说明当时古碑还在。《明一统志》卷六十四载:“李陵,临沅令。后没匈奴,邑人思之,为立清陵馆。”后来,明嘉靖《常德府志》卷之十二、清嘉庆《常德府志》卷六、清同治《武陵县志》卷之六等各种方志的记载也都是一致的,即写作“清陵馆”。并且,这“清陵馆”是为纪念汉武帝时期曾在此地担任过临沅县令的李陵而立。
那么,为何要为李陵立“清陵馆”呢?文献中一致的说法是“邑人思之”。“思”他什么?光绪《桃源县志》卷之七回答了这个问题:“思其清德,为立清陵馆。”[4]“清德”,就是清正廉洁的品德。《后汉书·列女传·皇甫规妻》:“妾之先人,清德奕世。”《新唐书·李石传》:“毛玠以清德为魏尚书。”用的就是这层意思。因此,“清德”是一种高尚的品德,值得思念,值得纪念!由此可见,“清陵”最初的含义,是纪念李陵的清正廉洁之德,“清陵馆”是标准的,正确的,由此衍生的其他名称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 柳拱辰给曾巩的信中,将“清陵”写作“青陵”之原因
曾巩的《归老桥记》中,三次提到这一地名,皆作“青陵”:“武陵柳侯图其青陵之居,属予而叙。以书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属于梁山者,白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属于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筑庐于是,而将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于两崖之间而东注于湖者,曰采陵之涧。吾为桥于其上,而为屋以覆之。武陵之往来有事于吾庐者,与吾异日得老而归,皆出于此也,故题之曰归老之桥。”[5]看来,曾巩是根据柳拱辰写给他的信来说的。那么,柳拱辰将“清陵”写作“青陵”,是纯粹笔误,还是有意而为?
笔者认为,柳拱辰将“清陵”写作“青陵”,是有意而为,这其中包含了他本人乃至家族的一种故乡情结。武陵白马湖清陵村的柳氏家族,是五代时因避乱由山东青州(今山东省青州市)迁徙而来。到武陵以后,柳拱辰的祖父购置了白马湖清陵村的田产,也就是他给曾巩的信中所称的“先人青陵之田”。到他手里才第三代,他本人乃至家人们对故乡山东“青州”应该还念念难忘。恰好又定居在清陵村,有意无意家人们都会将新家和老家联系起来。因此,他将武陵白马湖清陵村的“清陵”写作“青陵”,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总之,“青陵”的写法从柳拱辰开始,其中蕴涵了他对故乡青州的记念,也蕴涵了对武陵白马湖清陵村新家的认可,是可以理解的。
三 李陵和苏武在古代武陵的活动记载
另一个同“清陵馆”相关的问题,是清同治《武陵县志》曾经提出过的,即“《汉书》本传,(李陵)未尝为临沅令,此说恐属附会”[6]。这一判断是否正确,笔者不好结论。但我们知道,早期的正史,限于素材的搜集和选择,遗漏和舛误之处比较多,前人对史书进行研究纠错的著述都不少,这也是明摆的。光凭“《汉书》本传”没有记载,便否定李陵曾任临沅县令,显然也缺乏说服力。
无独有偶,常德市桃源县还有“苏溪”的记载,文献都说是得名于李陵的好友苏武。光绪《桃源县志》卷之七载:“汉武帝朝,县令李陵来任。李陵少为侍中,建章监,迁临沅令。后邑人思其清德,为立清陵馆。今桃邑有清陵庵。又邑北九十里有苏武祠。相传李陵为令时,武尝游此也。”[4]今桃源县地方,西汉为临沅县,属武陵郡。至隋开皇九年(589年)灭陈后,改武陵郡为朗州,合并临沅、沅南、汉寿三县而建立武陵县。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采纳转运使张咏建议,分出武陵县乌头、延口等数村,建立桃源县。因此,宋以前,桃源县的历史也就是武陵县或者临沅县的历史。
此外,还有一个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苏武于天汉元年(前100年)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被扣。匈奴多次威逼利诱,迫其投降,甚至将他流放北海(今贝加尔湖)边牧羊,声称“羝乳乃得归(公羊生了崽才让回国)”[7]。苏武历尽艰辛,坚持19年不屈,直到始元六年(前81年)才获释回汉,成为我国历史上突出的爱国典型。而李陵,本是西汉名将李广之孙。他率五千人马对阵匈奴主力,单于先是“骑可三万围陵军”,继又“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7]。李陵殊死抵抗,十多万大军坚持了十几天,最后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了匈奴。后果是汉朝夷其三族,致使他彻底断绝了同汉的关系。因此李陵的一生,可说是充满了国仇家恨的矛盾,历来对他的评价争议很大。
总之,作为历史人物,无论其结局如何,我们对于其平生的了解应该是越多越好,越有助于综合比较,进行研究。苏武和李陵,《汉书》都只记载了他们在朝廷的任职情况,没有反映他们在地方的活动经历。湖南常德的地方志乃至其他一些文献,则历代相传地记载了李陵和苏武在汉代“临沅县”的任职及活动情况。要说完全是空穴来风,恐怕也说不过去。希望史学界的行家对此类问题能予以关注。
[1](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之二百十一[M].明万历三十一年曹时聘等刻本.
[2](清)郭嵩焘.(光绪)湖南通志·卷二百六十[M].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影印本.
[3](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三[M].乾隆庚寅五月李君文藻抄本.
[4](清)刘凤苞.(光绪)桃源县志·卷之七[M].清光绪十八年刻本.
[5](宋)曾巩.南丰先生元丰类稿·卷十八[M].明刊本.
[6](清)陈启迈.(同治)武陵县志·卷之六[M].清鼎雅堂藏本.
[7](汉)班固.前汉书·卷五十四[M].武英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