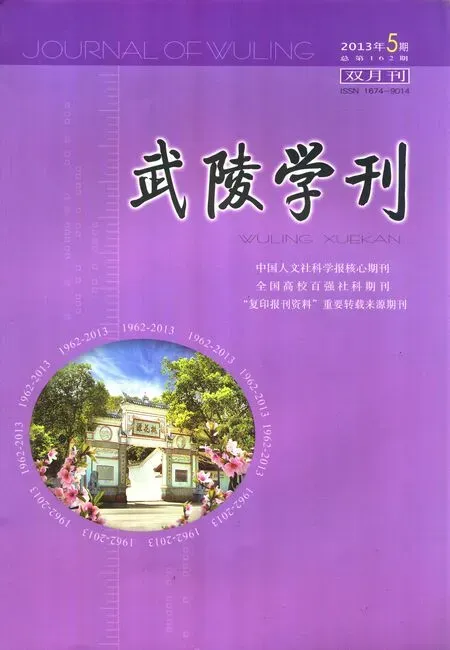文人话语的诗性特征
2013-03-19叶建明
叶建明
(福建警察学院基础部,福建 福州 350007)
文人话语的诗性特征
叶建明
(福建警察学院基础部,福建 福州 350007)
中国传统文人话语以文人的诗意栖居为表达对象,以意象为审美策略,形成兴观群怨的话语轨迹,其汉字游戏的趣味张扬了汉语的诗意美。文人话语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是始终与官场话语、民间话语保持互文性。
文人话语;汉字;意象;兴观群怨
《说文》解“文”为“错画也,象交文”,意思是交错的纹理。《文心雕龙》强调“文”的重要性:“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虎豹之所以成为“虎豹”而不是“犬羊”,不是因为“虎豹”内在的质,而是因为外在形式的“文”(纹)的存在。“文”是事物之所以成其为本身的理由,在刘勰看来,“文”甚至有超越“质”的地位。所谓文人(litterateur)就是对“文”感兴趣的人,是德里达笔下的文化“踪迹痕”(trace)的发现者、传承者、创造者。所谓“话语”(discourse)是语言现象或语言的运用,是与权力运作交织在一起的语言事件[1]。所以,“文人话语”往往暗示出表达形式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从屈原的离骚汉代文赋到魏晋文人的自觉、从唐人王维的禅诗到明代董其昌文人画论、从宋代苏轼柳永到明清笔记、从浮生六记陶庵梦忆到民国小品文直至现代沈从文汪曾祺等等,呈现的是一条清晰的中国文人话语脉络。勾勒文人话语对象、文人话语的汉字情结、文人话语之发端、文人话语的审美策略,会发现文人群体的鲜明话语趣味,从而寻找其在历史语境下的深层文化意义。
一 诗意栖居:文人的话语对象
文人话语的典型文本是文人笔记文人信札文人诗文人书画,都是人生“踪迹痕”的记录,浸透文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有意味的形式符号。对日常生活的品味早在孔子那里就初显端倪,子曰:“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也。”(《礼记·中庸》)“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文人的“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唐诗纪事》卷六十五),文人的诗意栖居是“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文心雕龙·物色》)。正如林语堂所言:“凡方寸中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皆可听其由笔端流露出来。”(《论小品文笔调》)一草一木一花一惊喜一声叹息一次短暂的欢乐一个碰撞一个小小的得意一次艳遇一番领悟,都是对日常生活碎片式的记录。这种闲谈往往看似无聊无用无礼,实则最本真最自然,绝不为文造情。周作人在《再谈俳文》中说:明代文人张岱“写正经文章但是结果很有点俳谐;你当他作俳谐文去看,然而内容还是正经的,而且又夹着悲哀”。不是有意识的,而是无意识的有意味的,不是为人生的,而是为生活的。文人的诗意栖居“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林语堂《小品文之遗绪》)。发自内心的闲笔趣笔充分体现老庄的恬淡生活哲学,不过多渲染,不刻意为之,随手记下,所谓笔墨趣味讲求天然随意,绝不虚无,是对人生须臾欢乐的把握,这也正是汉语文人的生活态度:即时行乐,确信美在日常生活之中。
当然,经过文人话语观照的日常生活又呈现别样的风景:肉鱼羹汤、牛溲马渤,世俗而非庸俗,是经过文人话语过滤了的日常生活,是“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沧浪诗话》)。庄子的鼓盆而歌、屈原的香草美人、竹林七贤的引吭长啸、陶渊明的荷锄戴月、苏东坡的夜醉复醒、张岱的湖心亭看雪、八大山人画鸟的有眼无珠,甚至是对日常生活的有意误读。这种对日常生活的有意误读是文人对世俗的有意隔离,从而实现对世俗生活的文人化话语化个性化。误读恰恰体现了“语言的内在价值”[2]123,并给文本接受者提出了一定要求:阅读必须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和,摆在文人的角色定位上,否则很难理解文人话语。正是因为这一点,后来者总能从前人的文人话语展开心灵的对话。
文人话语热衷于日常生活乐此不疲的记述,以此集中了全部的生活愿望和对日常生活的乐趣,对于自由境界的向往和所获得的小小自由的欣喜。因为生活(存在的现实)与意义本就是矛盾的[2]131,只有通过日常生活不厌其烦地叙述,才能证明“我还活着”、“我在表达”、“我在”。文人话语也充分体现了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充满日常生活趣味的汉字哲学。儒家思想就是日常生活的哲学,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这一点正是区别于西方由“上帝之手”所掌控的逻格斯的永恒存在驱动万物的形而上学。所以,长期以来,历代文人的生活情调能够引领所有儒家哲学背景下中国人的生活情调,即使是魏晋时期那些富得流油的显贵也未尝不以文人生活格调为时尚指南。比如,文人画始终是中国书画的主流,中国书画史几乎就是文人书画史。
二 取象尽意:文人的话语策略
文人话语的表达对象看似日常生活,但实质是观物取象尽意,以达到主客观的融合。“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易·系辞上》),“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尽象,象以言著”(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意象藉以传达本不可言说的意义,成为文人话语的策略。用语言构成的象具有语言本身所不具有的意义,特点是“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易·系辞下》),即以小喻大,以少总多,由此及彼。意是思想观念,象为表意而存在,意是象的主宰,象显意匿,象一意多。从言与象关系看,得意忘形,得言忘意,得象忘言,言成为制造者的符号。意象有别于具象,《唐诗纪事》载:“僧齐己《早梅》诗:‘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曰:‘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齐己拜伏,人以郑为一字师。”郑谷把唐僧齐己的《早梅》诗句“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的“数”字改为“一”字。生活中的具体事实很可能的确是数枝开,但意象中的一枝则更好地显示了“早”意。所以文人笔下的意象无法去比附实际生活中的具象。文人话语虽然是表现现实的,但并非写实的日常生活,而是胸中“成竹”、胸中山水人物。
意象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具有丰富的言外之意。历代文人积累了大量有意味的意象。自风骚始,月亮、美人、黄昏、风雨、落叶、飞雁、春日、秋水、杨柳、桃花、浮云、岸路、菊荷、车马、鸟鱼等等,这些农业文明时代的日常生活景象逐渐成为文人笔下被固化的意象,形成了丰富的文化“踪迹痕”库。文人话语实质是从符号到符号,诚如文人书画是从线条到线条,文人诗是从意象到意象。这种意象的承袭极易与艺术创新的陌生化原则背道而驰,而陈旧的话语系统非常顽固,所以文人的贡献就是不断地从这些传统的文化“踪迹痕”中寻求突破,通过意象的组合,创造更新奇的符号形式。象同意新,语境的不同形成新意,从而形成各自的话语风格,并寓意不同时代的文化意味。如杜甫善用“受”、王维喜用“空”、李贺喜用“鬼”“死”、李白喜用“月”,鲁迅从灯光中看见的永远是“黑影”,海德格尔最爱“田野里的小径”。如马的意象,多指雄性的力量、男人的理想情怀,但李白的“郎骑竹马来”的“竹马”代表“宁为百夫长不为一书生”的唐人志向,李贺“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则是文人的怨愤郁结,柳永的“长安古道马迟迟”暗示名利争逐,东汉青铜“马踏飞燕”体现的是汉人的骄傲与浪漫。
三 兴观群怨:文人的话语轨迹
文人话语皆以兴发而起。“兴,起也。”(《说文解字》)“兴”是感兴,即景生情,因物起兴,文人话语记叙的闲言碎语看似无聊实则是有所兴寄。如果说文字活动有言志、抒情两面的话,那么文人话语活动更关乎抒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大序》)。孔子说“发乎情,止乎礼”,而“文以载道”观往往重点在于“止乎礼”,淡化了“发乎情”,于是文字里剩下的只有无关乎“情”的“礼”,在强调“言以足志”的同时,文字的真情没有了。而文人话语更注重的是“发乎情”,体现真性情的自然流露。魏晋文人之所以受到推崇就在于他们冲破“言以足志”的儒家桎梏而宗老庄,率性话语,表达真性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晋书·王衍传》),“起情故兴体以立”(《文心雕龙》),“诗工创心,以情为地,以兴为径”(皎然《诗式》)。苏轼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自评文》)这正是随物兴发的体现。兴是基础,由此兴发联想,通过兴才能达到观、群、怨。
“观”是品藻观照。观人观物观文观自然。钱钟书说:“盖吾人观物,有二结习:一,以无生者作有生看;二,以非人作人看,鉴画衡文,道一以贯。图画得具筋骨气韵,诗文何独不可。”(《管锥编》)人物品藻与品文品书品味日常生活所用词汇与形式是共通的。如钟嵘《诗品》:“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如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世说新语》评“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俄若玉山之将崩”,“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严仲弼九天之鸣鹤,空谷之白驹”,“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人物品评是“转喻性”的——所谓转喻就是用最接近的另一事物来代替事物,品评的是人物的衣着行为房间,“从人的生命的存在发展中去寻找美、表现美、欣赏美”[2]285,乃是文人的赏心乐事。
“群”是文人话语圈。文人之趣味相投,最重视的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知音传统。知音的感觉一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所描写的“忽逢幽人,如见道心。清涧之曲,碧松之阴。一客荷樵,一客听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泠然希音”,李挚的“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焚书·杂说》),林语堂之于公安竟陵派“近来识得袁中郎,喜从中来乱狂呼”(《四十自叙诗》)。文人话语圈是文人间自给自恰的小众化符号系统,其间的交流是无逻辑的无序流动的甚至没有语法规则的,而这其实正体现了语言的本质、语言的趣味、语言的奥妙。在这个系统内文人是彼此的作者和读者,这种“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是长期浸淫其中形成的境界。文人话语圈也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结构,在历时性的文本生成与接受中逐渐形成了大量无限生长经久不衰的母题:孔子的浮云、老子的自然、庄子的秋水、历代文人的赏菊饮酒登山临水看云赏月等等。事实上,对这种意味的考察很有可能比探究文本涵义更加必要:这些母题提供了话语的幻觉[2]127。幻觉提供了一个可供读者误读的多义性文本。人们愿意沉醉于这种幻觉的快乐。
至于“怨”,则是人的天性,“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旷夫怨女、迁客流人,舆人之诵、里巷讴歌。司马迁就把屈原的创作动机归为一个“怨”字,屈平“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贾生列传》)。“离骚”楚语意为牢骚,骚即是怨,离开了文化中心、失去了话语权,被边缘化的文人只好说说“无关痛痒”的花草美人。屈原的“怨”后来衍生为司马迁“发愤著书”、李白的“哀怨起骚人”、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应该说“怨”及其围绕“怨”的“忧”“伤”“悲”“哭”等是中国文人的审美基调,也是中国文化的情感基调。“《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刘鹗《老残游记·自叙》)。无大喜,无大悲,只是伤、怨,尤其是人生的悲怆。“怨”是快乐的忧伤、忧伤的快乐。“伤”在于人生之短暂、个体之渺小、人生之变化无常,与人之为人求长、求大、求静的矛盾。
四 汉字游戏:文人的话语狂欢
语言从来就是文化的第一标志[2]121。汉语文人的趣味更体现在对于汉语言的痴迷和敏感,对于自由运用文字的追求。从这个意义而言,文人话语的消长即是文学的消长也即文化的消长。
“敬惜字纸”的传统是对汉文字的虔诚尊敬,但汉字的游戏是中国传统文人或者雅附文人生活之人的重要内容,它构成了《红楼梦》大观园生活,也是中国传统生活中最具魅力的一个部分[3]。汉字的把玩、练字与度句,在文人话语里发挥到了一个极致。周作人概括汉字的游戏性、装饰性与音乐性[3],引出“许多雅俗不同的玩意儿,例如对联,诗钟,灯谜,是雅的一面”,“急急令,笑话,以至拆字,要归到俗一面去了”(周作人《药堂杂文·汉文学的传统》)。汉语是象形的表意的,是视觉的,是男人的、文人的,是意象的汉字、引人遐想的汉字、诗意的汉字,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如二人为“仁”,以手取月为“有”。几个汉字的堆砌就可以形成美丽的意境,如“杨柳岸晓风残月”,就是一幅文人画。对汉字的玩味,对于线条、对于笔墨趣味的把玩,和谐地统一成自由游戏。
一面沉湎于汉语言的狂欢游戏,一面苦恼于语言的无奈甚至对语言的不信任,又恰是古往今来文人们的普遍心态,许多文人一生“不离文字”,所发出的却是“不立文字”的感叹,如果非立不可,那就尽量追求简单纯粹干净的文字,所以其趣味立求清淡,“浅深聚散,万取一收”(司空图《诗品》),“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皎然《诗式》),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而其极端当属禅语禅诗禅画。周作人认为禅宗的“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差不多可以说是最高理想的艺术”[3]。钟惺说:“我辈文字到极无烟火处,便是(禅家)机锋。”(《答同年尹孔昭书》)儒家、老庄、禅宗逐渐在文人身上趋于统一。“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正如老子的道、佛祖的拈花微笑、恋人间的絮语,不用说话就十分美好。繁复的语言只能证明我们面对语言的无能为力。当彼此都想让对方懂的时候,真正的语言就淹没在声音嘈杂之中,那就没有话语只有声音了。禅宗的介入、文人画的出现,使文人话语有了更广阔的生长点。一方面进一步放大了汉语言的无逻辑性,体现的是对语言工具观(人是主人,语言是仆人。语言是外在的、为了表达主人的意旨而存在的身外工具[4])的强烈反抗;一方面使文人表达走向了脱离语言本身、走向文人书画的大言大美。
结语
所有的文本必须与文本外其他符号相观照,才具有自身的意义。作为底层文本的文人话语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是始终与其他文本如官场话语、民间话语具有互文性(intertexuality)。文言文是传统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通用语,一个人要进入文官系统,就必须接受文言文的教育。文言文或近现代的半文半白语言也是文人的通用语,但是文人话语并不完全等同于官场话语。文以载道的使命感,使中国文人做官写文章是一套正统的话语,而性情流露的是另一套话语即文人话语。前者中规中矩,后者轻灵活泼。文人话语就是载道文学之外的一块净土一块私留地一块个人空间。文人话语往往游走于政治与民间的边缘。文人话语常常会遭到强权话语的戕害,其最为极端的后果是文人异化或失语。文人话语也在文学语言系统与日常生活话语系统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正如文言文最早其实是先秦口语一样,中国文人话语其实与民间话语有着本源关系:对文人话语影响深远的《诗三百》本身大部分就是民歌,“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诗集传序》)。历史上凡是呼唤新鲜活泼的话语时代,就会出现向民间学习的声音。因为民间话语虽然是最粗糙的但又是最生动活泼的:“原初的语言就是诗”,“使存在变得澄明的语言是原初语言或诗意语言、未受形而上学污染的日常语言”[5]。当然,文人话语追求的永远是一种个性化小众化的趣味,文人话语更多的时候是有意脱离民间隔离大众即脱俗的。大众话语也始终有意无意地受文人话语影响,如《水浒传》中的粗人武松也能说“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文人话语对于美化大众话语具有积极的作用。文人话语是文学语言作用于社会语言系统的生动体现。
汉字充满感性的信息,接近生活、接近自然,体现了农业文明的时代特征。但在后现代主义语境、工业化社会的今天,“商品化的逻辑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维”,“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2]161。中国文人所惯于表现的农业社会“日常生活”日渐消失,一切“美”的艺术形式也都商品化了,伪文人话语大行其道。伪文人话语的特点是附庸风雅、句式欧化,“句子愈来愈长,信号愈来愈弱,信息消失在长长的扭曲的句子窄巷中已成了常见的文风”[4]。汉语言的工具性与语言美感割裂,对汉语言尤其是汉语言诗性美足够的尊重和敬畏之心已然在缺失。所以,在汉语言被大众文化网络文化任意践踏的当下,揭露伪文人话语,重拾本真的文人话语精神,显得尤为必要。
[1] 保罗·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M].陶元华,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135-206.
[2]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杰姆逊讲演[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 钱理群.周作人与五四文学语言的变革[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4):152-155.
[4] 郑敏.语言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与诗意价值[J].文学评论,1996(4):72-79.
[5]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J].文艺美学,1985(1):327-330.
(责任编辑:田皓)
I0
A
1674-9014(2013)05-0108-04
2013-04-12
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文人话语研究”(JA11294S)。
叶建明,男,湖北鄂州人,福建警察学院基础部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