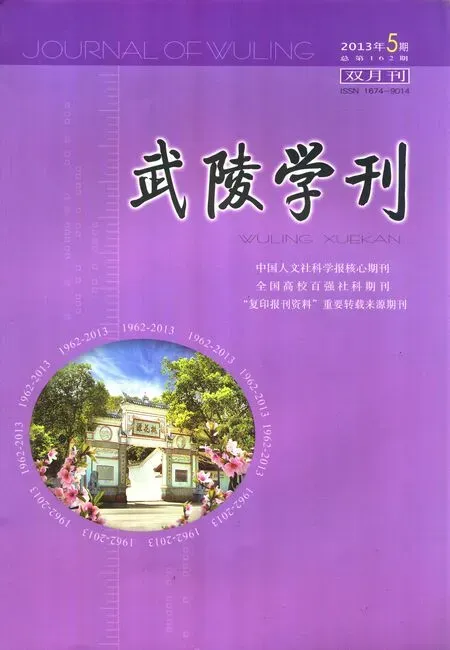构建民族文学话语系统的理论支点
2013-03-19龙长吟
龙长吟
(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 长沙,410007)
构建民族文学话语系统的理论支点
龙长吟
(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 长沙,410007)
民族文学学科由民族学与文艺学构成,主要研究文学与民族之关系,重心是探寻文学的民族性,任务是总结文学民族特质表达之规律。民族文学理论话语系统存在三个理论支点:文艺学支点、民族学支点和文化学支点。这三个理论支点在“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习惯的复合体”的民族文化特质上重叠起来,成为该学科三点合一的唯一理论支点。
民族文学;学科;理论支点
一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话语系统,可简称“少数民族文学学”。其中“民族文学”概念见诸文字,是歌德1827年1月31日的谈话。他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1]歌德使用民族文学概念时语气较为轻视,可见这个概念当时已流行很久了。一百多年后,新中国在世界的东方崛起,基于多民族国情和繁荣文学的需要,茅盾在1949年9月《人民文学》创刊的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了“少数民族的文学”概念[2]。1958年7月17日中宣部召开民族文艺座谈会,将“少数民族的文学”缩减为“少数民族文学”专有名词,“少数民族文学”这个中国独有的概念正式定型并普遍使用①。40年后,马学良先生在“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基础上延伸出一个新概念“少数民族文学学”。他在回顾提出这一概念的最初动因时说:“我和中央民族大学的部分同仁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时,曾提出过建立‘少数民族文学学'的设想……从而构建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3]在前辈的导引下,1997年7月,拙著《民族文学学论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近年间的民族文学理论高层论坛,多民族文学高峰论坛,以及民族文学学会每年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极大地推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话语系统的建设与发展。
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一个宏大的思想体系,一个完备的、科学的话语系统。每个系统一般都有如下节点:特定的研究对象,提挈全局的理论核心,独特的研究视角,坚实的学科基点,清晰的理论范畴,一定数量的配套新概念,具体的研究任务,适合的研究方法,支撑整个系统的理论支点。民族文学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是研究一切民族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及其与民族的内在联系的科学,同时也是从民族的角度所构建的一种文学理论新框架。那么,它的理论支点是什么呢?这看似一个常识性问题,但要作出力透纸背、一语中的的断言,还真有很高的难度。理论支点不明确,与之配套的新概念就难以生成。在此,我们就民族文学学的理论支点做初步的论述。
二
在展开论述之前,先撇清一种不同的观点:“文艺理论无支点论”。有学者认为,文艺现象无始无终,无边无际,是一种宇宙现象,因而根本不存在什么理论支点[4]。其实,这是混淆了文艺现象与文艺理论两个不同的事物和两类不同的概念。任何理论都是对现象和事物的概括,都有严格的边界和特定的对象,都有其哲学基础和理论体系,有其逻辑起点和研究重心,直接支撑起这一研究重心,进而支撑起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观点,就是理论支点。没有理论支点的理论体系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找到了还是没有找到。找到了科学的理论支撑点的理论体系会更有针对性,也更缜密,更有思想高度。那么,民族文学学话语体系的理论支点到底是什么呢?
任何话语系统的理论支点,都是由话语系统的内容构成、哲学基础、论述重心、理论所要解决实践问题的目标任务四个方面决定的。民族文学学的基本构成是民族学与文艺学,主要研究文学与民族之关系,它的重心是探寻文学的民族性,任务是总结文学民族特质表达之规律。因此,民族文学理论话语系统存在着三个理论支点:文艺学支点、民族学支点和文化学支点。
支点一——文学是民族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是民族学理论与文艺学理论相融合的产物,它是民族的,也是文学的,但归根结底是文学的。其理论支点应该先从文学方面来探寻。什么是文学?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以此推论,民族文学则是“社会生活在民族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作家的民族意识,自觉不自觉地反射到作品中,文学就具有了民族性。民族性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民族文学当然是民族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显然,民族文学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它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新的分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般原理,也是民族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民族文学理论的前提,是承认迄今为止世界上一切文学都是民族的文学。它与其他文学理论的区别仅仅在于,它是从民族的视角来观察、分析、研究文学,发掘文学的民族特质。在文学民族性的统驭下,过往的一切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思潮观念,都被放到“民族”这个高倍显微镜下面,重新予以论定、评判,从而构建起关于民族文学理论的系统学说。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所说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不是单一的被动的反映,而是方式多样的创造性的反映:有客观的,有主观的,有主观压倒客观的,有批判式的,有专门注重形式的……这种种不同的“反映”方式,实际上是作家对客观世界方式不同的“主体释放”。反映和释放的方式不同,就出现了不同的创作方法,形成了古典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和后现代主义、形式主义等等不同的文学流派,进而出现了各种流派的文学理论。由于理论家所强调的重点不同,同一文学理论体系中,理论支点也不同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有的把工具论、人本主义视作理论支点。而在民族文学理论话语中,虽然承认文学的实用功能,但重点不强调文学的功能性,工具论不可能成为民族文学理论的重心,当然也就不成其为理论支点。同样,我们承认文学是人学,但研究重心是文学与民族的关系,而不是文学与个体人的关系,人本主义也不是其理论支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着重研究文学中民族文化的作用,发掘文学的民族特色、提倡民族形式——文学是民族的,才是支撑起民族文学理论体系文学方面的理论支点。
承认文学是民族的,它的前提是承认人分民族,如欧美大地。可是,亚洲许多国家因为影响甚至决定社会秩序、国家体制的主导性社会团体的性质不是由部落、氏族形成的民族,而是教派、宗族或社区什么的,他们根本就不承认人有民族的差异,不承认民族是一种人类的群体形态,不承认民族的存在。在亚洲数十个国家中,只有中国、越南、缅甸、菲律宾四个国家承认人以文化差异分成不同的民族,菲律宾称民族为“民族文化少数集团”,印度、日本、土耳其、孟加拉等国根本不承认民族的存在[5]。在此,我们不想复述两百多年来,西方人类学家、中国孙中山和共产党人,发现民族世界,创立民族科学,划分民族成分,制定民族政策的一系列理由来重复论证民族的存在,那样会把简单的问题推向混沌的原始状态和复杂的历史漩涡中。我们只从浩如烟海的实例中举几个简单的不容辩驳的文学史实,就足可证明文学民族性差别的存在。例如,汉民族文学的思想重心是“明道、宗经、征圣”,少数民族文学则“艺事相因”,重心在于“纪事”,故从古至今,汉族文学很少叙事诗,而少数民族的叙事诗非常发达;汉民族文学的基本风格是《诗经》所开启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温柔敦厚”之风,少数民族文学则质直、痛快淋漓得多,有时甚至“多有枭音”。汉族韵律严格的格律诗,难于在非洲的丛林中流传,《唐伯虎戏秋香》一类胭脂文学难以在广袤的西北大地生根,《格萨尔王传》等严肃宏阔的英雄史诗在文人荟萃的苏杭民众中难以世代传播,都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元人论诗,都带有一些性灵的倾向”(郭绍虞语)?为什么沈从文虽然生在汉文化相当发达的凤凰县城,而他笔下的翠翠,却没有汉儒文化的丁点影响,没有丝毫“五四”以来流行的个性解放观念,没有受过任何官方教育,只是“光人一个”?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元代、在后来的沈从文身上,汉文化的道德律令相当薄弱,天然的生命意识却很旺盛。所以,元代开始性灵派昌行;沈从文天才地写出了翠翠从三五岁的小女孩到十四五岁大姑娘,自然人性自然生长的生物性过程。当然,任何民族的民族性最终受生活与政治的制约,但政治制约是一时的,生活的制约才是永久的。中国“金”“元”“清”三代,对汉文化压制厉害,但停留在他们夺取政权的初期;而吃斋的佛教传到西藏,藏民多食肉,就成了永远的“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留”的藏传佛教;西藏的宗教文学与印度、与中国内地的宗教文学所歌咏的风俗也就有了很大的不同。
支点二——民族是文化的。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文化,定义繁多,各有道理。斯大林从文化的角度定义民族,最为缜密、完备、便于操作。他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6]由于民族是人类社会中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类文化共同体,民族文化便是一民族区别于另一民族的主要标志。共同的文化和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生成了民族文学的民族共同性,并由此区别于他民族的文学。民族的文化特异性便成了民族文学的生命之源,成了民族文学理论的根基,成为民族文学理论体系最重要的支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人是文化动物”,由人组成的社会各个盖面、各领域都有各自的文化属性。文学是文化的资源,同时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文学的书写对象,又是文学的深层次内涵。文学表现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参与构建文学形态,能使文学作品内容厚重,质量提升。所以,后现代以来,文学向文化偏移成了世界性的大趋势。在中国,1985年,韩少功等一批青年作家在杭州开会,正式提出了“文学寻根”的主张。韩少功《文学的“根”》、郑万隆《我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都把文化作为各自创作的资源,并创作了《爸爸爸》《棋王》等一大批说明自己理论的寻根小说。泰勒在《原始文化》第一章“关于文化的科学”开篇就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7]由此,在研究文学文本时,学者们有意突出人文意识,注重从历史、政治、精神、信仰、道德、风俗、法律和美学各个层面进行广泛深入的人文阐释。这种从文化角度研究民族文学的文化阐释,较好地发掘了作家的民族意识、民族经验与政治无意识,阐明了它们对作家选材与表达的深刻影响,不仅回答了作家写什么、怎样写,还回答了作家为什么写、为什么会这样写等深层次问题。这样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较之孤立地研究文学作品,自然深刻得多。
支点三——文化潜藏在民族经典文献文化和世俗民间文化两种文明形态中。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意识,不是耳提面命,而是作家民族文化意识的有意投射或自然流露,它潜藏于字里行间,需要读者和专家的体会、发现。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两种民族文化。这里不是指列宁所说的任何民族都有先进与落后两种民族文化成分,而是说,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两种存在形态:一是潜藏于平民生活中的民族民间文化,二是传统的、文献形式的民族经典文化。美国人类学家雷德斐(Robert Redfield)在调查、分析墨西哥社区文化时说:“在一个文明中,存在着一个具有思考性的少数人的大传统和一般而言不属思考性的多数人的小传统。大传统存在于学校或教堂的有教养的人中,而小传统是处于其外的,存在于不用书写文字的乡村社区生活中。哲学家、神学家、文学家的传统是一个在意识上的培养的传统,并输送下去。而最大部分人民所属的小传统被认为是被赋予的,不用仔细推敲的或被认为要提炼和润色的文化。”[8]大传统文化主要指上层士绅文化,即今日所说的精英文化或经典文献文化;小传统文化,指民间世俗文化,亦即通俗文化。韩少功等青年作家1985年提出的“文化寻根”,就是从民族的经典文献文化或世俗的民间文化中寻找文化资源,赋予文学作品深邃的文化意蕴。韩少功主张从民间生活中寻找原始文化遗存;阿城主张从传统经典文化中寻找文化资源。无论是作家在作品中注入民族文化特质,抑或是理论家发掘、总结作家作品中民族文化特质的表达,都不外乎从雷德斐所说的这两方面入手:将作品与经典文献中的大传统文化相比照,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民间小传统文化相比照。雷德斐的文化二分法理论与韩少功、阿城等人的文学寻根主张精神相通,与实际状况最接近,最适合指导民族文学创作、评论和理论研究。雷德斐的理论1956年面世,20世纪90年代末由台湾学者引入大陆学术界。精通英语的韩少功事先是否涉猎了雷德斐的理论还是与雷德斐精神完全相通,我们不得而知,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韩少功等人向民间和经典文献寻找文学之根的主张,与雷德斐“二分法”的文化理论推进了文学及其理论的发展。运用他们的理论,能最准确、最清楚地揭示出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文化特质,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与研究。所以,我们把雷德斐的文化理论作为民族文学理论体系中文化学方面的理论支点。
在雷德斐“大文化传统和小文化传统”的理论支撑下,民族文学理论家常常通过丰富有趣的生活事实与文学细节的具体展示,洞见作家如何运用民间世俗文化铸就生动的、不朽的文学篇章,发掘作家作品所受民间世俗文化的影响,进而影响到该民族普遍的生活态度与价值取向。20世纪80年代,美国汉学家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实地考察了湘西历史、民俗,在大量占有民间文化材料的基础上,解读沈从文和沈从文的作品,别有见地,使他的沈从文研究独树一帜。韩少功《爸爸爸》《女女女》等寻根小说不尽如人意,非“主张”之过,乃是对湘西民间民俗文化把握不准。这方面,沈从文昔日的《边城》,王跃文今日的《漫水》,对湘西乡土社会民间文化的把握要准确得多。民族作家和民族地区的作家在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占有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在大传统文化方面,问题非常突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设中,仅仅对汉族经典文论资源,尤其是对历代“诗话”,二十六史的“艺文志”,利用得比较充分,相反,对各少数民族自身的经典文论,这些本是建设民族文学理论体系最重要、最宝贵的资源,可以作为直接构件进入民族文学理论体系的宝贵财富,反而掌握、运用得很少很少,急需进一步发掘、发现、整合。重视和发掘中华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经典文论,是民族文学理论建设重中之重。这里必须处理好单一民族文学历史研究、单一作家作品研究与民族文学系统理论整合的总体研究之关系: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提高。没有前者的积累,理论体系凌空蹈虚,不切实际;囿于前者,胸无全局,视野不宽,理论境界不高。单一研究与整体综合研究,像各民族的大传统文化与小传统文化一样,他们都不是完全割裂的,更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常常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相互生发。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单一研究与整体综合研究,民族的大传统文化与小传统文化,相互交流融会的趋势愈来愈强烈:单一研究推进综合研究、综合研究提升单一研究;精英文化向通俗文化靠拢,通俗文化向精英文化渗透。
三
文化学和民族学兴起的历史都比较晚近,他们的理论常常相互通用,互为支撑。文化学告诉我们,文学作品中潜藏着丰厚的民族文化特质;文艺学告诉我们,这种文化特质,是作家在文学作品中自觉不自觉地注入民族意识赋予的;民族学告诉我们,民族文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探寻、揭示蕴含在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文化特质,总结和发现文学表现民族文化特质的规律。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民族文化特质”,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包含了许多具体丰富的内容。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质,在任何时候、任何方面都会有具体的展现,大而言之是泰勒所说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习惯的复合体”。这样一来,文学是民族的,民族是文化的,文化潜藏两种文明形态中——民族文学理论话语系统三个理论支点,最终便在“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习惯的复合体”上重叠起来。民族文化特质的文学表达,是民族文学创作的重心;总结民族文化特质文学表达之规律,则是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重心;承认文学作品中潜藏着民族文化特质,则是民族文学学科体系得以成立的基础。总之,“民族文化特质论”是民族文学学科理论三点合一的理论支点。用“民族文化特质论”支撑起来的民族文学理论体系,纲举目张,全面、深入地揭示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发现新的创作机遇,造成新的创作态势,洞见民族文学与客观世界的种种关联,确定民族文学理论各个节点的具体内容,确立民族文学话语系统的基本范畴。埃里克·纽特(挪威)的“未来学”告诉我们,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不光是研究已有的成品和成就,还要面向未来,研究各类文学叙事新的方式、新的空间。因此,各民族文学的交流与融合,也是本学科重要的理论范畴。只要抓住民族文学与地域的关系,民族文学与人种的关系,民族文学与民族历史的关系,民族文学与民族经济生活方式、政治生活方式的关系,民族文学与民族宗教的关系,民族文学与民族心理性格的关系,民族文学与民族审美情趣的关系,民族文学与民族风俗习惯的关系,民族文学和民族语言的关系,民族民间文学与民族作家文学的关系,文学交流与文学融合的关系等十二对关系,紧密结合各民族文学的实际状况,在单一研究与整体综合研究两大路径上展开,作深入而清晰的论定,民族文学理论体系建设便初步奠定了。
多年来,中国文艺理论界不时在讨论、努力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这其实是个有待论证是否成立的命题。思想理论体系是否成立,客观条件是研究对象的极大丰富性,资源的永不衰竭性,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完全创新的必要性,完全超越以往的可能性。四个条件缺一不可。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社会基础和政治体制,不同社会基础与政治体制下的意识形态有所不同,作为受政治制约的意识形态的文学,其价值取向、思想倾向、美学追求有较大的区别,但这些都只能局部影响文艺学理论的内容与观念,不可能导致文艺理论整体构架的重造与整体性超越。文学和文学理论虽有流派之分,文艺理论观念也有政治之别,但作为文学科学之工具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国别之分,没有政治体制之分,不可能每个国家、每种政治体制都来搞一套超越以往的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民族文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分支,承认民族,承认民族文学,从民族的角度进入文学,表现和研究文学的民族独特性,从而建设一套民族文艺理论体系,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不过这样的理论体系一旦建成,也便是世界性的文艺理论话语系统,而不只是某单一国家的话语系统了。
注释:
①参见1986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马学良编撰的“少数民族文学”词条。
[1] 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11.
[2] 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7.
[3] 龙长吟.民族文学学论纲[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2.
[4] 单影.文艺理论支点批判[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9(5).
[5] 丁金光,主编.世界民族与宗教[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47-49.
[6] 斯大林.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1-2.
[7] 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1.
[8] 转引自庄孔韶.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研究进程[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1):02-16.
(责任编辑:田皓)
古典诗歌标题对鉴赏的暗示性
常言道,文有“文眼”,诗有“诗眼”。诗歌的标题就是诗歌的眼睛之一。古典诗歌的标题有极强的暗示性,往往为阅读者提供了很多重要信息,在解读诗歌主体之前,从标题入手,可以帮助阅读者了解诗歌的内涵,从而对诗歌有一个大致把握。
诗歌标题提示诗歌类别。古典诗歌就题材内容看,有写景、叙事、咏物、抒情、悟理等;再具体一些,则可分为田园、山水、边塞、羁旅、行役、饯别、悼亡、闺怨、怀古、咏物、感悟等。古典诗歌的标题一般都有标示诗歌类别的关键词。田园诗多以田园风景入题,如王维的《山居秋瞑》。边塞诗的标题常含“塞、征、军、塞上、塞下、征人、从军”等字眼,如柳中庸的《征人怨》、王昌龄的《从军行》。送别诗的标题常含“别”或“送”字,如高适的《别董大》、韦应物的《赋得春雨送李胄》。明月高悬的夜晚最能勾起游子的思乡之情,所以思乡诗的标题常含“夜”或“月”字,如杜甫的《月夜忆舍弟》;“每逢佳节倍思亲”,思乡诗的标题还常有中秋、寒食、重阳、冬至等古代节日名,如白居易的《邯郸冬至夜思家》。咏物诗的标题或是“咏(题)+物”的格式,如贺知章的《咏柳》;或直接以所咏之物为题,如虞世南的《蝉》。咏史诗的标题常含“怀古”一词,如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或直接以历史人物、历史地点入题,如李商隐的《贾生》、杜牧的《赤壁》。写景抒情诗多以所绘之景入题,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刘攽的《雨后池上》、王维的《山居秋暝》。
诗歌标题提示主体内容。标题是文章的“眼睛”,它往往提示作品的主要内容。如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单从标题就很容易捕捉到诗歌的内容:或写演奏者的技艺高超,或写听笛之感想,或兼而有之。又如王湾的《次北固山下》,“次”是“停留”或“驻扎”之意,一个“次”字很容易让人想到这可能是羁旅之作。而羁旅之作,诗歌的内容就应该或为旅途所见,或为思乡之情。另外,有的诗歌标题直接反映诗歌的主要内容,如寇准的《春日登楼怀旧》,标题就明确地告诉了读者写的是作者在春天这个撩拨思绪的季节里登楼望远、身在异乡思念家乡的情感。
诗歌标题提示思想情感脉络。“诗言志”。“一切景语皆情语”。诗歌是诗人缘情而发的产物,情感是诗歌的灵魂。诗歌标题中有的隐藏着饱含诗人情感的字眼,阅读时如果能够捕捉到标题中的这些字眼,便找到了鉴赏诗歌的钥匙。如李白《独坐敬亭山》,从标题看,“独”表明作者独自一人,“坐敬亭山”表明要描写的是敬亭山的景色,根据“独”字,可以猜测诗人的情感流向——寂寞孤独。如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左迁”本为“贬谪”之意,诗人闻听朋友遭贬而写此诗,其情感或为表达安慰,或为表示愤慨,据此可以推测。再如杜甫的《春夜喜雨》、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柳中庸的《征人怨》,诗歌中的“喜、怀、怨”这些字眼,就很容易让人捕捉到诗歌表达的情感走向,有利于对诗歌的整体把握。
诗歌标题提示写作背景材料。古典诗歌标题中,往往蕴含着一些背景信息,诗歌鉴赏要善于从标题中挖掘出诗人写作的时间、场景以及时代背景,为准确解读诗歌打下基础。如白居易的《邯郸冬至夜思家》,从标题可以得到如下背景信息:写作时间是重要的节日冬至的晚上,地点是客居的邯郸,要传达的情感是思家。综合这些信息,可以明确这是一首思家诗。又如高启的《暮春西园》,从诗歌标题即知:时间是暮春,地点是西园,可以推测这是一首田园诗,写的是晚春时景。
(常德芷兰实验学校 谭建清)
I0;I106.9
A
1674-9014(2013)05-0103-05
2013-04-17
龙长吟,男,湖南邵东人,湖南省作家协会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民族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