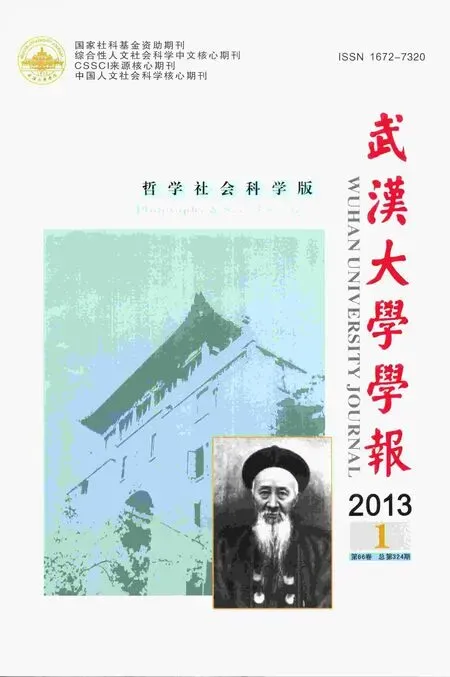城市公共参与和社会问责——以广州市恩宁路改造为例
2013-03-19黄冬娅
黄冬娅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的政治问责的形式都是一种“向上问责”的制度安排,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意对于政府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近年来社会公众对于政府问责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日益强化,都使得政府不能再仅仅追求经济发展绩效,如何有效地回应民意,如何恰当地处理社会诉求,推动政府社会问责,已经成为了关乎民众对于政府信任度和满意度的重要标尺。
现有研究表明,以公共参与推动社会问责是加强政治问责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在我国城市公共生活中,公共参与日益活跃,这为社会问责的有效施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社会问责过程中,社会各种行动者相互呼应,推动局部性事件公共化,形成公共意见,以一种有序参与的形式参与到公共政策过程中。这种公共参与寻求影响公共政策,要求政府对其所做出的决策承担责任,从而指向城市政府的社会问责。本文将以广州市恩宁路改造中的公共参与和社会问责为例,从一个侧面揭示当前中国公共参与和社会问责的图景,并进而分析当前以公共参与推动社会问责的实现方式及其局限性。
一、公共参与和社会问责:概念和关系
在政治问责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在许多新兴民主国家,选举制度的广泛推行并没有有效地制约权力掌有者,公民的利益和诉求仍然被侵扰和蔑视,选举制度并未成为公共权力问责的基石。在对这些经验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研究者日益认识到西方政治制度中以选举为核心的问责制度之局限,特别是西方责任政府之经验难以照搬到第三世界国家。因此,与过去强调选举和权力制衡的问责机制不同,研究者越来越重视“社会问责”对于构建责任政府的重要性①O’Donnell,Guillermo.Polyarchies and the (Un)rule of Law in Latin America,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Latin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Chicago,1998;Adam Przeworski,etal.(eds.)Democracy,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Enrique Peruzzotti,Catalina Smulovitz.“Held to Account:Experiences of Social Accountability in Latin America”,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2002,3(2).。
研究者将政治问责分为横向问责和纵向问责两种。横向问责主要指的是来自国家内部的立法、司法和独立行政监督机构这三种主体进行的问责形式;而纵向问责是指来自国家外部的问责,它包括选举问责和社会问责(Social Accountability)两种形式。不同于选举问责,“社会问责”是通过普通公民或者公民社会组织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来实施问责的问责方式②Andreas Schedler,Diamond Larry & Marc Plattner(eds.).The Self-restraining State:Power and Accountability in New Democracies.New York:Boulder,1999;马骏:《政治问责研究:新的进展》,载《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4期。。
世界银行将“社会问责”界定为:一种依靠公共参与(civic engagement)来实现问责的问责途径,它通过普通的市民或公民社会组织的公共参与来寻求政府对于社会负责③World Bank.“State-Society Synergy for Accountability:Lessons for the World Bank”,Working Paper,No.30,2004b;Charles D.Kenney.“Reflection on 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Democratic Legitimacy,Majority Parties and Democratic Stability in Latin A-merica”,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Institution,Accountability,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Latin America,Kellog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 of Notre Dame,May,2000.。可以看到,公共参与是社会问责的根本实现途径。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公共参与可以从三个方面促进问责。第一,公民社会直接监督政府、直接向他们施加压力,以实现一种不同于选举的纵向问责。第二,通过持续有效的公共参与促进横向问责。当公民社会对某一行政部门进行指责时,同时也在向监督它的平行部门施压,如果问责效果没有达到,说明该监督部门也是无作为的。因此,公共参与会促进平行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第三,促进斜向问责(diagonal accountability)④World Bank.“Social Accountability: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ncept and Emerging Practice”,Social Development Paper,No.76,2004a。这种参与方式突破了将问责区分为“横向问责”和“纵向问责”两种类型,而是结合了这两种问责类型,即“斜向问责”⑤G Anne Marie oetz,Rob Jenkins.“Hybrid Forms of Accountability:Citizen Engagement in Institutions of Public-Sector Oversight in India”,Public Management Review2001,3(3),pp.363~383.,主要是指公共社会不拘泥于自下而上的问责方式,而是可以参与到横向问责的监督机构中去。
当然,与其他政治问责形式相比,依靠公民参与实施社会问责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他的问责形式往往是事后的责任追究和惩罚,而社会问责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过程,它包括了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事前或者事中的参与、对话和评估,官员需要告知和论证他们的决策方案、行为和结果。同时,社会问责虽然不能够直接对公共权力掌有者进行惩罚,但是,它可以对有悖民意的政府施以公众压力和合法性质疑等正式和非正式的象征性惩罚,还可以通过公共参与来推动国家内部问责的启动。由此,社会问责的最终结果是让政府和官员更加对民众负责,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加反映民众的意愿和利益⑥World Bank.“Social Accountability in the Public Sector:A Conceptual Discussion”;Adam Przeworski,etal.(eds.)Democracy,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Mainwaring Scott(eds.).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in Latin Americ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在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以选举为核心的纵向问责以及依靠立法、司法和审计机构等施加的平行问责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现有关于官员问责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行政条例规定基本上都是在政府内部自上而下地进行责任追究和惩罚。在外部问责机制存在局限性的情况下,这种内部纵向问责就相应地会存在一定的可操作性和随意性,究竟什么情况下官员会受到问责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依靠公共参与、推动社会问责是在现有制度架构下强化政府和官员问责、积极回应民意的切实可行途径⑦马骏:《实现政治问责的第三条道路》,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在社会问责过程中,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游行、静坐和群体性上访等非制度化的方式来表达抗议、寻求政府的问责,公民也可以通过更加制度化的公共参与机制来寻求政府的社会问责。相对于非制度化的方式而言,制度化的公共参与机制能够建立更加协作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以公共参与推动社会问责已成为了一种切实的民主实践。信息公开立法、公共听证、社会审计(social audit)、公民陪审团(citizen jury)和参与式预算等制度化的公共参与机制广泛地建立⑧Enrique Peruzzotti,Catalina Smulovitz.“Held to Account:Experiences of Social Accountability in Latin America”.。比较而言,我国的公共参与机制仍然不够健全。2010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其中,公众参与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它模糊规定了“做出重大决策前,要广泛听取、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意见采纳情况及其理由要以适当形式反馈或者公布”;其二,它明确规定了要完善重大决策听证制度,扩大听证范围,规范听证程序,听证参加人要有广泛的代表性,听证意见要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①《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号,载人民网。。我们可以看到,在实践中,作为目前主要的制度化公众参与机制,听证会仍然难以发挥切实的作用②Jamie P.Horsley.“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Developing a More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Model in China”,China Law Center.New Haven:Yale Law School,2009.;而参与式预算和参与式立法等地方公共参与创新仍然缺乏更广泛的实践③Jun Ma.“The Dilemma of Developing Finanical Accountability without Election”,Australi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9,68,pp.62~72;Ting Gong.“Audit for Accountability in China:An Incomplete Mission”,Australi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9,68,pp.5~16.。可以说,这种制度化公共参与机制的不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造成当前许多非制度化参与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我们需要探讨,在当前制度化的公共参与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以公共参与推动社会问责的实现途径是什么?鉴于此,本文选择广州市恩宁路改造作为案例。案例的选择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恩宁路改造是较为典型的城市拆迁改造问题。在当前的城市公共生活中,涉及到土地规划和房屋拆迁的公共参与比例非常大,在拆迁改造中,如何推动政府向民众负责成为了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其二,恩宁路改造是以公共参与推动社会问责较为成功的案例。在城市拆迁改造中,不乏引发了对抗性群体性事件的情况,而在恩宁路改造案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一个相对封闭决策体制中公共参与面对的困境,也可以看到广泛的公共参与对政府决策确实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是以较为有序的公共参与有效地达致社会问责较为成功的案例。这两者都将有助于我们考察以下问题,即在当代中国城市生活中,如何能够以公共参与有效地达致社会问责?本文将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二手资料分析的方法,勾勒转型期中国以公共参与推动社会问责的图景,力图把握其动力机制和局限性。
二、广州恩宁路改造中的公共参与和社会问责
恩宁路改造从2007年启动,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政策波动。广泛的公共参与推动了恩宁路改造局部事件的公共化,向政府施加了强大的社会压力,促使政府逐步开始回应民意。在政策上,拆迁改造方案从最初的“全部拆迁”到最后“只要有争议的都保留”,从“商业开发”到“不追求收支平衡”,从“政府主导”到“居民自主更新”;在公共参与机制上,政府逐步通过“向社会征求意见”、“专家咨询”和“媒体通报会”等畅通民意表达的渠道。在社会和政府的良性互动下,公共参与较为有效地推动了社会问责。
(一)恩宁路改造概况
恩宁路位于广州市荔湾区多宝街道,与龙津西路 、第十甫路、上下九步行街骑楼相连,是广州最完整和最长的骑楼街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广州在“南拓、北优、东进、西联”的八字方针中增加了“中调”的概念,强调拓展广州未来发展空间的同时,必须重视老城区作用。2007年,广州市启动“恩宁路危破房连片综合改造项目”。
(二)作为局部事件的恩宁路改造
信息公开是公共参与的基础。在城市拆迁改造中,国家已经对城市规划、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领域的信息公开作了明确的规定。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的时间不得少于30日。关于房屋拆迁及其补偿和补助,200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特别强调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是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之一;2011年新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做出房屋征收决定后应当及时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偿方案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等事项。”《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2004)更明确规定,拆迁范围变更要书面通知被拆迁人。
虽然这些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地对城市拆迁改造中的信息公开进行了规定,然而,在恩宁路改造过程中,“改造规划”迟迟未有确定,更难以谈得上公开和参与。在规划方案仍未确定、拆迁范围尚未明确的情况下,政府就启动了动迁和拆迁。居民最初只能通过信访来探听改造的信息,反映他们的诉求。
2007年12月,穗房拆字[2007]22号文拆迁公告贴到了恩宁路永庆大街老房子的砖墙上,许多居民住所被列入拆迁范围,可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相关部门与居民沟通,居民不知道这个拆迁方案从何而来,也不知道自己的房子如果被拆应该拿到多少补偿、应该搬往何处①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城市房屋拆迁公告》,穗房拆字〔2007〕22号,2007年9月24日,载http://www.laho.gov.cn/ywpd/fwgl/zwxx/fwcqgg/200710/t20071008_158842.htm。。同时,由于在拆迁规划尚未确定和公布之前,许多民居已经被纳入拆迁范围并被强制拆迁;其中有的已经签订拆迁协议的,却不在公告的拆迁范围之内。比如,2008年,被划入拆迁范围的宝华路宝庆新南约10号、12号楼业主发现,在所有公布的法律文件中,新南约10号楼竟然不在拆迁范围之内,但当时已有一些居民与改造办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②《恩宁路改造项目追踪:拆迁公告中找不到10号楼》,载《新快报》2008年7月31日,见http://www.ycwb.com/news/2008-07/31/content_1943315.htm。。同时,当年6月刚刚在恩宁路购置房产、拿到房产证的几户居民更加不满,他们才刚刚拿到房产证,居然又被通知房子要拆除③《广州业主6月买房子9月要拆迁,集体上书全国人大》,载《新快报》2008年5月12日,见http://news.sohu.com/20080512/n256789018.shtml.。此外,在拆迁安置和拆迁补偿方面,不管是开始的商业开发方案,还是后来的“社会开发”方案,政府都确定不能回迁,其间拆迁补偿又经历了楼市的快速上涨期,因而造成了拆迁安置和拆迁补偿引发的巨大矛盾。
针对这些问题,恩宁路居民多次到荔湾区规划局、荔湾区城市更新改造办公室上访,要求先有规划确定拆迁范围再进行动迁和拆迁,要求政府要公开改造项目相关信息,特别是规划制定进展,并要求居民参与到规划制定过程中。2008年5月11日,广州市荔湾区宝华街宝庆新南约10号、12号楼80多户居民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指荔湾区“恩宁路连片危破房改造拆迁项目”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对新南约10号和12号楼的拆迁有悖《物权法》原则。
(三)广泛的公共参与:恩宁路改造事件的公共化
广泛的公共参与是恩宁改造事件出现转机的重要根源。随着“恩宁路历史文化建筑保护”以及“亚运城市市容建设”这两大议题的提出,促使恩宁路改造从一个局部事件转向一个公共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公共参与,在新闻媒体的穿针引线之下,不同的社会行动者加入到恩宁路改造事件中,塑造了公共舆论,向政府施加了社会压力,从而推动了政府向社会的问责,影响了政府决策的制定和转变。
1.恩宁路居民:提出公共议题
在恩宁路改造事件中,居民不仅提出了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拆迁安置和补偿等问题,还进一步将恩宁路改造从局部话题演化为一个公共话题,提出了包括根据《物权法》保障公民相关权益、传统文化保护以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等更加公共性的诉求。事实证明,发掘恩宁路改造的公共话题,是推动恩宁路改造从局部事件转为公共事件、吸引更广泛的公共参与的重要因素。
在恩宁路改造过程中,历史文化建筑保护和亚运城市市容建设是两个核心的公共议题。在恩宁路改造事件中,居民一直在强调保护恩宁路的西关文化,保护“广州符号”,包括骑楼、粤剧名伶故居、金声电影院和西关大屋等历史文化建筑的意义被反复强调。比如,人大代表陈安薇也正是抓住亚运这个时机向人大和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恩宁路拆迁中存在的公共卫生问题,吸引了广州市万庆良市长走访恩宁路,并进一步把历史文化建筑保护问题提出来,推动了恩宁路改造规划的重新修改。
2.新闻媒体:塑造公共舆论
与此同时,媒体的报道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新闻媒体为政府报道有关恩宁路改造方案的情况,另一方面它们又代表居民向政府、社会公众表达利益诉求,反映恩宁路改造项目中出现的问题。他们既扮演着事件的观察者,也充当着事件的推动者,扩大了居民的声音,对公共舆论起到了建构作用。如《新快报》从2007年恩宁路拆迁启动、引发骑楼去留之争就开始关注、报道,历时5年之久,一直追踪报道每一年每一阶段的新进展新问题。2010年1月6日、7日,2月4日,《新快报》就以“最后的恩宁路”为主题,用大量图片对恩宁路现状进行了三次系列报道,分别为“触摸恩宁路的灵魂”①《触摸恩宁路的灵魂》,载《新快报》2011年1月7日,见http://www.ycwb.com/ePaper/xkb/html/2010-01/06/content_705714.htm。、“一个岭南建筑专家眼里的恩宁路应犹在?”②《一个岭南建筑专家眼里的恩宁路应犹在》,载《新快报》2011年1月7日,见http://www.ycwb.com/ePaper/xkb/html/2010-01/07/content_706670.htm。、“日暮西关何处是——最后的原住民”③《日暮西关何处是——最后的原住民》,载《新快报》2010年2月4日,见http://www.ycwb.com/ePaper/xkb/html/2010-02/04/content_737627.htm。。此外,媒体从业者独有的敏锐的观察力和新闻嗅觉,使之与恩宁路的居民积极合作,让恩宁路居民扮演了“爆料者”的身份。新闻媒体的扩散效应以及公共舆论的建构,增加了居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能力。
3.青年学生:传递社会支援
也正在此时,一些关注恩宁路事件的大学生和志愿者自发组织了起来。几个关注恩宁路拆迁的学生在豆瓣上成立了一个小组,而后,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小组。起初,组织的形式非常松散,由于每个人加入进来的动机不尽相同,并没什么明确的目标,也没有什么一致的行动。真正将小组凝结起来的是一次以研究为目的的调研。2010年3月,一群来自广州高校的学生和一些志愿者组成了“恩宁路学术关注组”(以下简称“关注组”)。组员们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涉及城市规划、建筑、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新闻学、艺术类等,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从不同侧面推进恩宁路保护。就这样,以做调查问卷为契机,目标不明晰的小组成员逐步凝聚到了一起,在进行问卷、访谈过程中,他们与恩宁路居民相互熟悉,更多地了解到居民的利益诉求,并获取了一些有关恩宁路历史文化的信息。从2010年3月开始,经历5个多月的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形成了两份研究成果——《针对〈恩宁路地块更新改造规划〉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恩宁路更新改造项目社会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其中《意见书》对恩宁路的规划时序、公众参与、公共利益界定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听取了居民及一些专家学者意见基础上提出了几点意见。而《评估报告》则是反映改造项目对居民造成的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剩余未搬迁居民的利益诉求④恩宁路学术关注组:《恩宁路更新改造项目社会评估报告》,载豆瓣网,“恩宁路学术关注小组”,2010年10月18日。。
4.专家学者:提出专业批评
在恩宁路改造规划出台过程中,专家学者加入并不断呼吁进一步信息公开和扩大公共参与。知名的广州美院李公明教授透过媒体发出了“恩宁路改造规划不能偷偷摸摸进行”的强烈呼声,此后,有关部门才匆忙向社会公布“保护开发规划方案”。此外,许多专家学者透过新闻媒体对恩宁路改造提出了批评建议,引导了公共舆论,从外部向政府施加压力。这些批评建议既关注恩宁路改造的规划方案以及历史文化建筑保护范围,又关注恩宁路改造的程序合法性和扩大公共参与问题。早在2008年6月,市人大常委会举办的“旧城保护和改造大家谈”论坛上,广州大学建筑系教授汤国华就指出:规划未获批怎能拆迁?哪来的有法可依?他认为,这也正是恩宁路拆迁推进过程中困难重重的关键。广州市律师协会民法委主任詹礼愿律师也提出,确定一个项目是否涉及公共利益,要看其详尽的规划而不是叫什么名称,旧城和危房改造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属于公共利益。中山大学教授李以庄则致信当时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呼吁连片保护开发,打造广州靓名片。
5.人大代表:启动横向问责
在恩宁路改造事件中,广泛的公共参与不仅直接给政府施加了压力,推动了政府向社会的问责,而且,它还进一步启动了人大对于政府的横向问责。在恩宁路改造事件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2010年8月,新快报社记者联系到广州市人大代表陈安薇,希望她能够去了解一下恩宁路的情况。此后她将恩宁路改造问题纳入到亚运城市市容建设这一公共话题之中,直接推动了恩宁路改造项目的政策转变⑤陈安薇,广州医学院教授、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的主任医师,曾担任过广医三院的副院长,民革广州市委委员。1993年起成为第八、第九届广东省人大代表。之后,她又成为了广州市人大代表。。2011年亚运前夕,万庆良市长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谈广州迎接亚运会问题。在座谈会上,陈安薇将恩宁路改造引起的公众不满的问题提了出来,并希望万庆良市长能够到恩宁路现场去看一看。至此,恩宁路规划改造问题才暴露在广州市政府这一决策层,也正是这一事件推动了恩宁路规划方案的更改。
(四)政府的逐步回应:社会问责的初步实现
在恩宁路改造的案例中,我们看到,公共参与的空间在逐步扩大。政府最初只提供了信访这个极为有限的参与渠道,将公民的诉求表达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诸如信息公开、听证和征求意见等关于公共参与的相关制度安排在实际中被刻意地规避。然而,随着公共关注的增加,公共舆论压力的扩大,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卷入到事件中,政府不仅开始进行政策的修改,而且还不得不扩大公共参与的空间,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采用“向社会征求意见”、“居民咨询小组”、“媒体通报会”、“专家顾问团”以及“规划研讨会”等方式来扩大信息的公开,部分地吸纳居民、专家、社会活跃分子以及人大代表的意见。
1.政策的修改
直至2011年底,恩宁路更新改造项目规划方案的制定有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恩宁路改造项目文物及历史建筑保护方案》的编制为标志。2007年恩宁路改造项目启动后,恩宁路历史建筑保护问题开始被提出,广州文化部门编制了相关的保护方案。但是,由于文化部门的方案只属于“建议”性质,恩宁路历史文化建筑仍然被纳入拆迁范围。第二阶段,以《恩宁路危破房改造地段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规划》的编制为标志,这是规划部门首次厘清历史文化建筑的保留范围。第三阶段,以《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开发规划方案》的公布为标志,这是恩宁路改造规划首次明确地向社会公布,并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第四阶段,以《荔湾区恩宁路旧城更新规划》制定为标志,明确将文化保护放在规划设计思路第一位,并进而将越剧名伶故居等纳入到保护范围。最后一个阶段,以广州市规划委通过恩宁路改造新规划为标志。虽然未有正式公布,但是,根据媒体的报道,2011年6月,以《广州市历史文化保护名城规划》《广州市骑楼街保护与开发规划研究》《广州旧城更新改造规划纲要》等上层次规划为依据,广州市规划委制定并通过了新的恩宁路改造规划,对改造后的地块提出了新的功能布局。其一,扩大保护保留范围。“所有公众意见反映应该保留的我们都决定保留,虽然也有人存在不同看法,认为有些房子并没有太大的文物价值,但不管怎样,只要有争议的,全部从历史文化保护角度出发予以保留。”根据审议通过的新方案,地块内将保留历史特色建筑面积11.84万平方米,占现状总建筑面积的55%,比上轮规划方案增加了2.3万平方米。其二,居民自主更新。新规划为了保护片区的历史文化风貌,留下来的房子虽不全由政府收回,但需接受相应的规划管理,由居民进行自主修缮更新,对于不具备条件的,则结合商业运作的模式加以修缮更新。其三,改变追求经济收益的改造思路,并进一步提高补偿标准。
2.公共参与机制的初步建立
从上文可以看到,在恩宁路改造启动之初,政府在规划方案仍未制定的情况下就迅速启动了动迁和拆迁,在这个时期,居民只有两个渠道来传递自己的声音。其一,信访。居民通过不断地到相关部门信访来了解改造的相关信息、进展以及反映意见和诉求。其二,媒体。居民通过媒体反映自己的意见和诉求,并配合媒体的报道,采取“上书”等方式来吸引公众关注,传递声音。然而,随着恩宁路改造吸引越来越多的公共关注和公共参与,政府感受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这时,政府开始逐步建立一些之前被刻意规避的公共参与机制来缓解压力,部分地吸纳居民和公众的意见,包括“向社会征求意见”、“居民顾问小组”、“媒体通报会”和“专家顾问团”等等。
2009年12月,《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开发规划方案》颁布时,政府就采用现场、电话、网络等方式向群众、专家和关心岭南文化保护开发的各界人士征询意见。不过,这次征求意见仍然有很大的局限,征求意见结束半个月后,恩宁路居民张先生等人找到了荔湾区规划局的工作人员,询问《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开发规划方案》征求意见的情况,新快报记者也按照公布的电话询问本次征求意见的情况,然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却回复说,意见还在整理中,要公布请问宣传部去,而宣传部什么时候公布他们也还不清楚。
到2012年1月,《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向社会征求公众意见,不过,这次政府雇请了“广州参客”这个专业的公众参与专业服务机构来收集和整理公众意见。在此次征求公众意见过程中,“恩宁路民间关注组”也到现场表达意见和建议,并得到了实施征询意见部门的关注。2012年2月19日,实施本次征询意见的“公众参与专业服务机构”主动联系“关注组”,听他们谈了对历史文化保护、恩宁路改造等问题的建议。并且,在征求意见结束后,政府主动召开了“媒体通报会”,将征求意见的情况和反馈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
同时,面对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政府也逐步真正开始重视居民和专家学者的意见。最初,2009年7月,荔湾城市更新改造办聘请首批4个城市规划建设、岭南文化建筑专家学者组成的旧城改造专家顾问团,不过,广州大学汤国华教授却透露,专家顾问团完全是象征性的。直至2010年,荔湾区召开新闻发布会承认恩宁路改造走了弯路,接着万庆良市长视察恩宁路后,荔湾区的三旧改造办又另外成立了“恩宁路改造项目顾问小组”,由14人组成,9名建筑和历史方面的专家,1名人大代表,1名政协委员,还有3位居民代表。到这时,恩宁路改造主管部门已经开始意识到必须听取顾问小组的意见。2011年6月,广州市规划委全票通过的恩宁路改造新规划所提出的“居民自主更新”改造思路,就是吸收了顾问小组成员汤国华教授的建议。
应该说,历时五年的恩宁路改造仍未结束。“恩宁路旧城改造更新地块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在市规划局全票通过,仍有部分居民的房子被告知延期拆除;提出的“自主更新”方案也没有详细的准则依据;一些被列入文化保护的建筑物没有得到正规的“身份证”,致使许多建筑物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公共参与的机制虽有初步建立,但是政府仍然有相当的操控权力,改造规划制定过程仍然不透明。恩宁路改造进一步的发展仍然需要我们继续观察。
三、结 论
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问责实践中,社会问责机制的建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推动力量,除了透明国际、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之外,社会问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国家与社会这两种力量的积极协作。这种协作关系是否达成不仅影响到公众参与机制能否建立,还直接决定了公共参与机制的有效性①Peter Evans.“Introduction:Development Strategies Across the Public-Private Divide”,World Development 1996,24(6),pp.1033~1037;Peter Evans.“Government Action,Social Capital and Development:Reviewing the Evidence on Synergy”,World Development 1996,24(6),pp.1119~1132.。无论是政府单方操控公共参与或是公众单方向政府施加压力,都不是最有效的公共参与形式,也很难达到社会问责的最佳效果。互动的参与方式不仅体现在政府与公众具有共同的观点和目的,也体现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争论、质疑,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才能达到最佳的社会问责效果。
在恩宁路改造的案例中,虽然公共参与的机制仍未实现制度化和常规化,但是政府还是逐步对民意诉求采取了积极回应的立场。以公共参与推动社会问责的初步实现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国家与社会达成了这种相对的良性互动。从案例研究中可以看到,在我国公共参与机制仍然相当不完善的情况下,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以公共参与推动社会问责有赖于以下几个要素。
第一,公共议题的提出。在社会问责过程中,能否吸引广泛的公共参与在于社会各种行动者是否有共同行动的基础,这种共同行动的基础就在于能够吸引广泛关注的公共议题的提出。在城市更新中,城市政府往往致力于寻找相应的价值资源,拓展合理性空间,以应对来自社会的压力。在很多情况下,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为城市更新提供了理由。在许多城市更新的案例中,最后能够成功达成自己利益诉求的居民只占少数,因为居民的愿望和要求并没有被真正转化成足以抗衡城市开发合理性的压力,社会成员没能为自身的权益愿望和抗争行为赋予足够的价值正当性②陈映芳:《城市开发的正当性危机与合理性空间》,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这使得政府常常声称他们以私人利益对抗公共利益。与此不同,恩宁路改造并没有仅仅囿于一个拆迁安置补偿的局部事件,它所蕴含的公共性被充分挖掘,居民将自身的私人利益诉求转化为具有价值正当性的公共利益诉求,他们一直在强调保护恩宁路的西关文化,保护“广州符号”,这便增加了居民与政府博弈的筹码,赋予他们的利益诉求价值正当性。这种“公共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博弈使居民获得了更大的参与公共政策空间,因为他们代表西关文化,他们被认为有权代表广州市民保护这片文化。他们通过采取策略行动与政府进行博弈,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积累社会资源以增加自身的博弈筹码,最终推动了广泛的公共参与。
第二,社会支持网络的形成。公共议题的提出为广泛的公共参与奠定了基础。进而,能否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是能否吸引广泛的公共参与的重要条件,是否拥有广泛的社会支持是能否以公共参与推动社会问责的关键因素。社会支持网络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盟友①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宏庆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5年。。体制内的盟友包括人大、政协和政府官员等,而体制外的盟友包括普通民众、新闻媒体、社会团体等。在较为封闭的政治体制下,体制内的盟友相对稀缺,体制外的盟友对于社会问责更为重要。普通民众可以通过网络发出支援的声音,也可以在现实中采取切实的行动去影响政府的决策;新闻媒体可以传播公众的诉求和行动,对政府构成强大的舆论压力;社会团体可以通过资金支持、信息提供和组织支援等方式将居民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建立起联系。这些都构成了对于国家的强有力压力,挑战了国家的合法性,迫使国家在公共参与的压力下向社会负责。在恩宁路改造案例中,文化保护和亚运话题使得它逐步扩散为一个公共事件,吸引了包括青年学生、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等群体在内的广泛公共参与,他们之间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支持网络,使得公众能够有效地动员体制内和体制外资源,影响政府决策,实现社会问责。
第三,政府的逐步回应。社会问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国家与社会这两种力量的积极协作。这种协作关系是否达成不仅影响到公众参与机制能否建立,还直接决定了公共参与机制的有效性。对于国家而言,面对公民社会的参与和问责诉求,它不应采取压制和冷漠的态度,国家需要承认公民社会的积极公民身份诉求,并为这种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行使提供途径。国家可以积极回应公民社会组织的倡议或者压力,接受公民社会对公共事务的监督,改善公共服务;国家还可以针对社会问责诉求启动内部的问责机制,从而增加社会问责的惩罚力量。在恩宁路改造案例中,虽然最初政府在房屋拆迁过程中存在许多违规操作之处,对于居民诉求的回应也显得迟缓而无力。但是,公共参与压力的增强,斜向问责的启动,都构成了政府回应的外部力量。而政府换届和新市长的上任构成了一个政治机遇,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较为有效地实现了社会问责。
总之,在当前的城市公共生活中,以公共参与推动社会问责日益成为可能。在制度化的公共参与机制仍然相当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相对有序的公共参与的实现有赖于一个吸引大众关注的公共议题的提出、较为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形成以及政府的逐步回应。正是这些因素促成了国家与社会相对良性的互动,从而使得社会问责得以达成。这种社会问责的实现彰显了公民社会的力量,制约了国家的权力,是当代中国城市公共生活的新图景,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